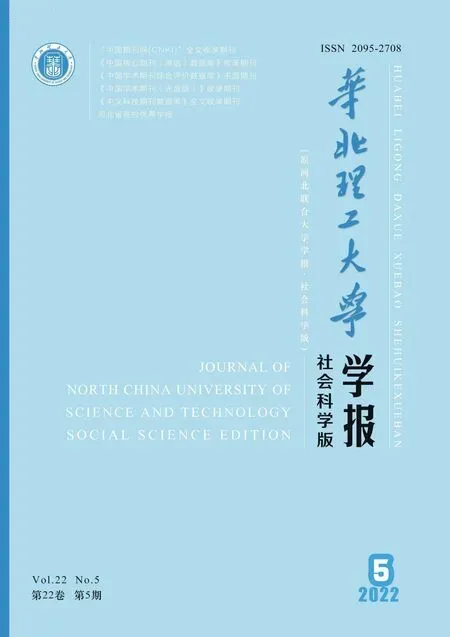《本草纲目》在欧美的译介与传播
张焱,尹娜
(西安理工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710054)
在我国中医药典籍体系中,本草古籍是一大重要分支,其中尤以《本草纲目》最具代表性,关注度最高。《本草纲目》为明代杰出医药学家李时珍呕心沥血之作,全书约190万余字,共分52卷,收录药物1892种,附 方11096首,是我国现存最为系统全面、详实完备的古代医药学典籍。在其成书之后,很快在亚洲和欧美各国传播开来,1607年传入日本,之后相继传入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17世纪末传入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18世纪后传入美国各地。《本草纲目》在欧美的传播肇始于17世纪,延续至今,时间久,范围广,形式多样,影响深远,通过厘清其西渐历程,旨在为今后中医药文化的海外译介与传播提供参考与借鉴,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推动东西方医药学的交流与合作。
一、《本草纲目》的版本及其在欧美的传播
早在17世纪,《本草纲目》便通过在华传教士开始传入欧洲,后又在18世纪逐渐传入美国,因此《本草纲目》在欧美国家的传播可谓历时已久。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由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初刻本在我国南京问世,由金陵书商胡承龙刊行,亦被称为“金陵本”,这也是迄今为止《本草纲目》最早的版本。此后,各类翻刻版本陆续问世,明末时期,基于“金陵本”,“江西本”和“杭州本”被翻刻出来;明末清初的各类刻本则是以“江西本”为底本;清朝中期的大部分版本是以“杭州本”为基础翻刻发行;清朝末期1885年,张绍棠主持刊行了味古斋本,亦称作“合肥本”,此后各家的翻刻又多基于“合肥本”[1]。如此便形成了《本草纲目》“一祖三系”的系统。基于这一系统,更多版本相继出现并传播至海外。

图1 金陵本 内页

图2 江西本 内页

图3 合肥本 内页
据考证,现欧美诸多高校图书馆和大型藏书机构都可见《本草纲目》不同版本的踪迹,且多为明清刻本,其中不乏十分罕见且极具历史价值的“金陵本”和“江西本”,其余版本包括但不限于武林本(1640)、太和堂本(1655)、张朝璘本(1657)、张温如重刻本(1658)、金阊绿荫堂本(1684)、本立堂本(1684)、三立斋本(1735)、清芥子园本(1767)、金阊书业堂本(1784)、金阊书业堂重刻本(1805)、英德堂本(1826)、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本(1893)、上海经香阁书庄石印本(1904)[2-4],由此可见《本草纲目》的不同版本,在欧美各国典藏之丰富。

图4 太和堂本 封面和内页

图6 清芥子园本 内页
《本草纲目》在欧美传播之初,是由来华传教士介绍并传至其本国,后被译为多种语言,引起了各界学者对这一著作的浓厚兴趣。汉学家,植物学家,药学家乃至生物学家相继对《本草纲目》本身及书中药物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大量有关《本草纲目》及中医药本草学的文章和著作涌现。这有效推动了《本草纲目》在欧美等国的进一步传播,深化了海外学者对于中医药物学和本草学的认知,同时也对其他学科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二、《本草纲目》在欧美的译介与传播
(一)法国为先,以译辅传
《本草纲目》的西渐之旅可追溯至17世纪,最早源于在华传教士的关注与传播。根据学者陈恒新的考证,1697年,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将四十九册汉籍呈送给国王路易十四,其中便有一套以金黄色丝绸包裹的《本草纲目》,后被收入法国国家图书馆[5]。18世纪前半叶,得益于西方传教士的介绍,欧洲学者开始注意到《本草纲目》。英国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有记载[6],1732年,法国医生范德蒙德(Jacques Francois Vandermonde)在澳门行医时偶得一部《本草纲目》,他按照书中所载药物采集了80多种矿物标本,之后借由华人的协助,根据《本草纲目》原文描述对标本逐一予以说明,并贴上相应的标签,最终还写了一部法文资料,名为《<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7],这份材料被视为《本草纲目》的法文摘译稿,后保存于巴黎自然史博物馆[4]。遗憾的是,范德蒙德采集的标本及其摘译稿在当时并未受到关注,直至1839年,法国汉学家毕瓯(Edouard Constant Biot)与友人合作对那些矿物标本进行化验并将结果公之于众。1896年,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德·梅里(F. de Mely)和库日尔(M. H. Courel)将那份摘译稿全文发表,使其重见天日[2]。
几乎就在这份摘译稿无人问津的同一时期,另一关于《本草纲目》的译本则名声大噪。1735年,《中华帝国全志》(法文原名: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 Empire de la Chine)在法国巴黎出版。本书由27位在华传教士共同撰稿,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主编,共四卷四册,是一部介绍中国的综合性著作,涉及古代中国政治、宗教、礼仪、风俗、地理、医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就包括对《本草纲目》卷首部分的摘译。《中华帝国全志》卷三第437页起有标题:《节录本草纲目,即中国本草学或中国医药用博物学》,该卷介绍了《本草纲目》为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编纂并对其刊行的细节加以说明,除此之外还对书中部分药性理论以及16种药物进行了节译[8]。作为《本草纲目》第一个用欧洲文公开出版的节译本,《中华帝国全志》的出版让欧洲读者对《本草纲目》有了较为全面、系统地了解,促进了欧洲学者对中医药理论体系的认知,是《本草纲目》在欧美传播的一大标志性事件。

图7 《中华帝国全志》内页
(二)多语翻译,研译相佐
十八世纪,“中国热”的风潮在欧洲兴起,法文版《中华帝国图志》一经出版,十分轰动,吸引了各层各界的注意,并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1735年法文版售罄;1736年,其英文本《中国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在伦敦出版,被称为“瓦次版”版(Ed. John Watts),1737~1741, 又出现“凯夫版”(Ed. E. Cave)[9];1747至1749年,全译德文本于罗斯托克出版[9];1789年由德文版译出的《中国帝华图志》俄文简明译本在莫斯科出版[10]。随着《中华帝国图志》的翻译与传播,《本草纲目》也相继拥有了法文、英文、德文及俄文节译本。
截止到18世纪,《本草纲目》的翻译主体多为传教士,传教士肩负着传递文化的使命与责任,作为译者,他们整体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本草纲目》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表达采用直译的方式,充分尊重了中医药文化。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读者对于《本草纲目》的不了解,加之中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译者在译本中先行介绍了《本草纲目》与李时珍,文内也加入了许多注解乃至译者的个人理解,从而帮助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本草纲目》,这种解释性翻译的手段有效弥补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使得译本更易被西方读者接受,进而有效促进了《本草纲目》这一传统东方典籍在西方的传播。
《本草纲目》多语译本的出现使得欧洲各界学者对其兴趣渐浓,因此与之相关的传播活动也不再局限于介绍和翻译的层面,更多目光聚焦于研究书中内容。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拉格斯特朗(M. von Laerstron)于中国南部收集到了大量植物标本,数量多达上千种,此行还收获了一本《本草纲目》原著。回国之后,他将自己采集到的标本赠予友人——瑞典生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e)并将《本草纲目》介绍给他,这对于正从事植物分类研究的林奈来说颇有裨益。为表谢意,林奈专门以拉格斯特朗的姓氏Lagerstroemia来命名紫薇属植物[7]。
(三)研究风潮,席卷欧洲
19世纪初期,法国汉学家勒牡萨(Jean Pierre Abei Remusat)在修道院目睹了院中藏品《本草纲目》,被深深吸引,但由于不懂汉语无法阅读书中文字。为此他潜心学习汉语,终在五年后化解了语言障碍,得偿所愿。1813年,时年25岁的勒牡萨向巴黎大学医学系提交了一份研究《本草纲目》及中医药的论文,论文对《本草纲目》中的理论及有关资料予以深刻分析和科学论述,受到了高度评价,勒牡萨也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授一职,以培养汉学人才和介绍中国文化己任。
勒牡萨的论文具有高度科学性和权威性,发表之后引发了欧洲对《本草纲目》和中医药的研究热潮,诸多与此相关的论文及专著诞生。1813年,法国学者勒佩奇(Frangois Albin Lepage)对在华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和吴多录的稿件进行整理并写成了《中国医史研究》,后于巴黎出版[4]。他在此书第二章“中国人的医疗与药学”中介绍了《本草纲目》并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对28种药物进行论述。勒佩奇充分肯定了《本草纲目》的博物学价值,也承认了欧洲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随后英国人雷弗(John Reeves)于1826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所用某些本草药物之说明》的文章。次年,德国人格尔森(Gerson)和尤利乌斯(Julius)共同撰写了《中国医史》。1847年,法国植物学家于安(Melchior-Honoré Yvan)将写给父亲的《关于中国药学的信》以小册子的形式公开出版。这本册子记载了于安此前在华旅行期间考察澳门、广州、宁波、上海等地药铺的所见所闻,并指出《本草纲目》是药师们的主要理论指导,进而对《本草纲目》的内容、目录及分类等予以介绍[3]。除此之外,于安还认为,尽管《本草纲目》所涵盖的内容广泛丰富,但一些药物缺乏科学验证,疗效存疑,还需要进一步花时间研究。19世纪上半期,俄国医学博士塔塔·林诺夫,长期从事中医药以及中国医史研究,同时还经常将在中国采集到的的植物标本寄至俄国。1853年,塔塔·林诺夫以《中国医学》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对李时珍以及《本草纲目》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英国著名药理学家、植物学家丹尼尔·韩伯里(Daniel Hanbury)长期热衷于研究各种天然药物,得益于弟弟汉璧礼(Thomas Hanbury)和多位友人的帮助,他收获了一些中国的植物样本以及中医书籍,其中就包括《本草纲目》一书,这为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与信息。1860年至1862年,韩伯里发表了《中国本草备注》一文,在该文中,他翻译了《本草纲目》的药图目录,对一些矿物和植物标本进行化验分析并附上拉丁文或英文标注[11],但对于正文部分的其他内容则鲜少涉及。这篇论文后被德国人马奇乌斯(W. C. Martius)翻译为德文并在1863年于斯派尔城出版。1876年韩伯里又出版了《药物学与植物学论丛》[12],整部专著长达543页,前半部分介绍了中医药有关内容,后半部分则着重分享《本草纲目》的内容梗概。1865年,法国植物学家、软体动物学家德彪(Jean Odon Debeaux)在巴黎发表了《论中国药物学及本草学》专著,文中提及了《本草纲目》并参考《本草纲目》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论述了300多种药物的产地、成分、性状、功效等[3]。1871年,英国伦敦布教会医生史密斯(Frederick Porter Smith)出版了《中国草药及博物学的贡献》一书,书中梳理了雷弗,韩伯里,汉斯等人对中国植物的研究并介绍了《本草纲目》的成书背景、记载药物、分类法。另外他也对上百种中药进行了论述,并实现了药物中外名称的对应[13]。1873年,在法国教授苏贝朗(J. Léon Soubeiran)和法国驻华领事铁桑(Dabry de Thiersant)长达两年对《本草纲目》的研究下,他们合力发表了《中国本草》,这一著作结合了两位早期有关中国本草学的学术报告,还引用了前人学者的中药研究,对《本草纲目》中的动植物、矿物进行了总结与分析[4],之后苏贝朗又于1886年发表了《中国本草研究》一文。同一时期,古伯勒(A. Gubler)在巴黎医学科学院也做了有关本草的学术报告,题为《中国本草学研究》。1876年,俄国学者柯尔尼耶夫斯基撰写了《中国医学史料》一书,书中收录了多位中国知名医药学家的生平事迹和著书论作,其中不乏李时珍与《本草纲目》。荷兰的日本学家吉尔茨(A. J. C. Geerts)也是欧洲《本草纲目》研究大军中的一员,1878年,他在日本横滨发表了法语著作《日本、中国天然产物之名称、历史及其在艺术、工业、经济与医学等方面之应用》,并赋其汉文名字——《新撰本草纲目》,基尔茨基于前人的有关文献,在该书中对《本草纲目》的金石部加以考释,具有非凡的学术意义[4]。19世纪后半期最为著名的《本草纲目》学者莫过于贝勒(Emll Bretschnelder)。贝勒长期致力于研究植物学史和中外交通史,创作了多部与中国植物本草相关的著作,成果颇丰。1870年,贝勒在福州发表了《对中国植物学著作之研究及述评》,1881年,贝勒在上海发表了《早期欧洲学者对中国本草学的研究》,对欧洲学者的本草研究史予以回顾,随后基于此书,他又扩写了《欧洲人在华植物学发现史》,1892年在伦敦出版[14]。除此之外,贝勒还著有《中国植物志·中西典籍所见中国植物学随笔》,该书包括《导言及书目提要》《中国典籍中的植物》《中国古代本草学之植物学研究》三部分,整个创作过程历时十余年,自1881始直至1894年才完成全部的撰写与发表工作[14]。在该书第三部分,贝勒专门对《本草纲目》所记载植物的种名给予考订,十分用心,他本人也多次给予《本草纲目》盛赞,将其视作中国本草学的代表性著作。贝勒的著作,让欧洲人对于《本草纲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知,也吸引了更多学者的研究兴趣。1887年,英国人福特(Charles Ford)和柯劳(W. Crow)合作发表了长文《中国本草学备注》,详细介绍了《本草纲目》。
值得一提的是,《本草纲目》对19世纪西方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医药学界还拓展至其他领域。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他的几部专著中都曾多次提及《本草纲目》,将其称作“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比如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的第七章《家鸡》中就有两处,根据学者潘吉星和吴德铎的研究与考证[4][15],达尔文曾邀请大英博物馆东方文献部主任倍契先生(Samuel Birch)翻译《本草纲目》第四十八卷中有关鸡的资料,继而在自己的文章中予以参考和引证。另外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关于金鱼的部分,达尔文参考了英国外交官麦耶斯(William F. Mayers)所著文章《关于中国的笔记和质疑》中的部分发现。经考证,麦耶斯的发现也正是查阅了《本草纲目》第四十四卷鳞部以及书中其他一些古籍引文得到的。因而《本草纲目》实为达尔文所谓的“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也是他科学研究的重要灵感来源。
综上所述,19世纪欧洲学者对于《本草纲目》的关注与研究此起彼伏,蔚然成风,而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则以介绍《本草纲目》本书和分析论述《本草纲目》所载药物两大方面为主,一方面对《本草纲目》的成书背景,内容梗概和分类法等进行介绍,另一方面着重分析与论述书中药物的产地、性状、功效等。此外,《本草纲目》的影响范围逐渐扩散,对其他领域如生物学界也有一定的启发。
(四)欧美并行,深入研究
进入20世纪后,美国对于《本草纲目》的关注与研究也逐渐增多。1911年,基于前文所提及的史密斯《中国草药及博物学的贡献》一作,美国人司徒柯德(G. A. Stuart)对其进行了修编,最终出版了《中国药物草木部》,该书摘译了《本草纲目》中第12至37卷的药物,而对于暂未加以校订的366种药物,司徒柯德在文末添加了附录和植物中外名称索引,这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6]。司徒柯德原计划要完成植物、动物、矿物三册内容,但可惜在完成植物册后他就去世了。与此同时,身为医校教授的美国人米尔斯(R. Mills)在朝鲜汉城工作,他一直都想要完成司徒柯德未竟之事,于是便与朝鲜同事合作,完成了对《本草纲目》及《本草拾遗》的翻译共40余册,1920年在返美之前他将译本和标本移交给英国人伊博恩供其收存采用。
基于米尔斯的研究成果,伊博恩与刘汝强、李玉田、朴秉柱等中朝学者齐心协力,数十年呕心沥血努力钻研,终于1928年至1941年分阶段完成了对《本草纲目》卷8至37和卷39至52颇为详细的英文介绍、研究与翻译,在其著作中,他采用药理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中药的有效成分[17],参考中外论著加以注释,每一种药物兼具原中文名称和学名,书中还配有相关插图和药物名称的索引,这极大的方便了西方读者对原文的阅读和理解。这份材料所涉《本草纲目》的部分包括草部、谷部、果部和木部、兽部和人部、禽部、鳞部、介部、虫部和金石部[16],完成后的稿件分期见刊于《北平博物志》[3]。得益于国内外学术机构互换学会杂志之举,伊博恩的翻译与研究很快流传至西方,其译著也被国外一些机构、研究所珍藏,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草纲目》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
同处20世纪初,结合《本草纲目》中的有关内容,美国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对栽培植物史,和中—伊文化交流史进行研究,完成了《中国伊朗编》一作,于1919年发表。他对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给予了客观中肯的评价,既点出错误与不足之处,也认可其包罗万象、内容充实等优点。1942年,法国人卢瓦(Jacques Roi)在《著名本草书<本草纲目>中的中草药》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本草纲目》中的植物药。1955年,德国学者莫西克(A.Mosig)与施拉姆(G.Schramm)共同完成了《中国药用植物及药材以及中国本草学标准著作<本草纲目>之意义》。进入七十年代,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和库帕(William C. Cooper)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人身中之药物》的文章,其中列出了八种产生于人体且可用作药物的物质。在这篇文章中,《本草纲目》被称为“传统医生的一部标准参考书”[18],同时作者还指出文中讨论的八种物质的制品和应用是也以《本草纲目》为根据的。同年,席文为《科学家传记辞典》编写了李时珍的长篇传记,其中详细介绍了李时珍的生平,概括总结了《本草纲目》中外研究现状与成果,内容颇为完整全面。可以看出,19世纪至20世纪,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乃至整个中医药文化在欧美都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与关注度。相较前一时期,《本草纲目》的译本也有了显著变化,一方面翻译主体从先前的传教士变成诸多欧美学者,另一方面翻译内容以《本草纲目》中的药物为重点,而出于译者们的学者身份,译本中又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译者对于原著各类药物成分、形状、药理的分析,因此这一阶段的译本兼具了翻译和研究双重身份,更具科学价值。
(五)多元深化,全译终现
时至当代,有关《本草纲目》的翻译与研究活动仍未停止,并呈现出更为全面系统、丰富多元的趋势。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罗希文撰写的《本草纲目·全文英译本》公开出版发行,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整部译著共6卷,总计约600余万字,前后花费将近30年完成。
相较之前的译本,罗希文教授的译本独具特色,创新与务实并重,他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忠实于原著的体例,最大程度呈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特质,另外借助“汉语拼音-拉丁文-英文”三语对照、注解、索引等手段,使得中医药名称翻译更加科学严谨,为中外读者阅读、理解乃至研究文本内容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整体而言,该译本完备详实,自问世以来在欧美广泛流传,备受盛赞,是西方学者研究《本草纲目》以及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文献参考资料,有力地推动了《本草纲目》走向世界,传播海外。
2008年,编写英文版《本草纲目》词典的项目正式启动[19],该项目融合了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郑金生、张志生、文树德(Paul U.Unschuld)等诸多人的智慧与心血。这一重大项目以研究《本草纲目》中的实词为重点,将实词划分为病名、地名、人名书名、药名四类,基本遵循首先落实词目,其次考察中文释义,最终翻译至英文的步骤[3]。截至目前,这一项目已有三部著作通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别是《本草纲目词典·中国历史疾病术语》出版于2014年,《本草纲目词典·舆地通释》出版于2016年,《本草纲目词典·人物及著作》出版于2018年。这一翻译项目既为现当代临床医学实践提供了启示也促进了海外各界对中国传统医学、传统文明与文化的认知。
本世纪对于《本草纲目》的研究在创新性上也有所突破,更多立足于现代视角,实现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良好结合。2002年,Brian May发表了文章Seahorses in the Ben cao gang mu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cine[20],探讨《本草纲目》中的“海马”在现代药理学中的应用。2011年,《世界记忆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项目”都将《本草纲目》列入其中[19]。2018年,时值李时珍诞辰500周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于湖北蕲春主办了李时珍中医药与大健康国际高峰论坛,海内外众多著名学者专家与会并分享了最新研究[19],比如Eric Stoeger讨论了《本草纲目》到现代药典思维方式的递变,Michael Heinrich教授从全球化的角度,比较研究了《本草纲目》及同时期的欧洲药物的著作。
三、结语
《本草纲目》问世至今已逾4个世纪,漫长岁月里,这一伟大著作没有被淹没,相反,在时光的打磨下更加熠熠生辉。它是中医药文化中的经典瑰宝之作,也是中医药文化走出国门、传播海外的先驱之作,17世纪末期以来陆续传入欧美各国,相关译本与研究随之涌现。《本草纲目》的译介与传播,一方面展现了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强大生命力,为现代医学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促进了东西方医学文化相互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极大地展现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亦为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与传播提供了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