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政治的双重困境
——论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译后记”的几次删改
□蒋浩伟
【导 读】朱光潜曾于1951年、1959年和1962年为《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写了三篇不同的介绍文章。在后两篇文章里,朱光潜对1951年的“引论”做了大幅度的删改,其中就柏拉图的“两种诗和诗人”和两种灵感的概念进行了详尽的补充。不过,朱光潜误读了柏拉图所说的“第一等人”和“第六等人”,认为两者之间是有无灵感的对立关系。在这两者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个既有灵感注入又必须模仿的“第三者”,朱光潜曾在1951年的“引论”里注意到了这一点,却在之后的文章里删而不提。以德里达对柏拉图的解构为例,这个模棱两可的“第三者”既从内部颠覆了柏拉图关于哲人和诗人的对立划分,也威胁着当时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批评话语,造成了朱光潜在美学和政治上的双重困境,这也决定了它最终被驱逐和删改的命运。
朱光潜曾于1951年、1959年和1962年为《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写了三篇不同的文章来介绍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分别见于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版本(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中的 “引论”、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中的“前言”和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译后记”。这几个版本在许多有关朱光潜的论述中经常被混淆,而且其间的许多差异至今还未见有人详细讨论。简单来说,1951年的“引论”主要介绍了柏拉图的生平和生活背景,并简要总结了柏拉图的文艺观点;1959年的“前言”删去大部分生平介绍,而大大扩充了对柏拉图文艺观点的分析;至于1962年的“译后记”则与1959年的 “前言”差别不大,只是做了少量的补充,而几乎没有删动。其中关于柏拉图“两种诗和诗人”和 “迷狂”的说法,朱光潜在1959年的 “前言”里对之前的说法从表现到原因都做了细致的补充,但仍有一些引人误解和值得反思的地方需要分辨。这不仅关乎柏拉图思想的矛盾之处,还折射出朱光潜在美学和政治上的某些困境。
一、“两种诗和诗人”
在1959年版《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的“前言”里,朱光潜认为柏拉图的文艺观存在着前后矛盾的地方。首先,在 《斐德若篇》里,诗和诗人有两类,绝对不可以混淆。一种是第一等类的爱智者、爱美者,或者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另一种是很低的第六等类的诗人和艺术家这类模仿者。前者是柏拉图推崇的能够在灵魂中回忆起真理,观摹神明,从而礼拜真善美的那类人。这类人只需要观看和回忆真理,并不一定要进行艺术创作,而后一类就是通常所说的作为拙劣模仿者的诗人。在朱光潜看来,柏拉图是有意拿这受到神灵凭附、得到灵感的“第一等人”和普通的“诗人和其他模仿的艺术家”对立,来降低这些“第六等人”的身份;而之所以有着两类诗人和诗的区分,朱光潜认为有一定的阶级根源,来源于作为贵族的柏拉图对下层手艺人的轻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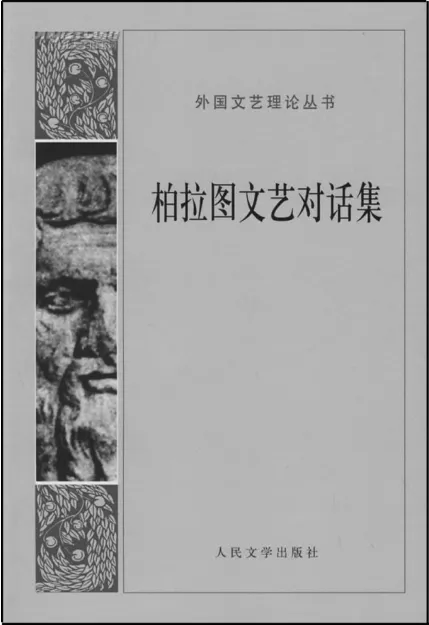
对于文艺创作的灵感,也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神灵凭附到诗人或艺术家身上,使他处在迷狂状态,把灵感输送给他,暗中操纵着他去创作。”[1]18这种解释来源于《伊安篇》。第二种解释则主要出现在《斐德若篇》,灵感被认为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上述所说的“第一等人”“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都是从这同一个根源来的。朱光潜在后面又解释说,前者神灵凭附的说法来源是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后者的灵魂轮回说则应该来自东方的埃及。
在这个地方,朱光潜对 《斐德若篇》中有两类诗人的分析并不是很仔细,容易使人认为《斐德若篇》里的“第六等人”只是普通的模仿诗人而与灵感无关,而只有“第一等人”才具有诗人的灵感,这样两者才能够被区分和对立起来,也能够被以不同的阶级立场来解释。但实际上“第一等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而“第六等人”也并非只会模仿的诗人和艺术家,后者与《伊安篇》里所描述的被神灵凭附的诗人一脉相承,也是能够进入“迷狂”状态的。
首先,柏拉图在 《斐德若篇》里并没有把爱智者和爱美者称作“诗人”,也没说他们能够创作诗歌,只是说他们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因而这类人严格来说并不是朱光潜所谓的“两种诗人”中的一种。其次,因为对 “诗人”的误读,导致了朱光潜对诗人的灵感来源做出了误判。柏拉图在这篇对话里清楚地分出两大类迷狂,一是疾病导致的迷狂,二是神灵凭附的迷狂,而后者又可再分为四种迷狂,即预言的、教仪的、诗神的、爱情 (或美)的。[2]118在这四种之中,爱和美的被认为是最高的迷狂。朱光潜所指九等人中的第一等人,所谓的爱美者和爱智者,其实就是这第四种美的迷狂的最高体现,它们之间有真正的美或“理式”作为连接的纽带:

以上所讲的都是关于第四种迷狂。有这种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因而恢复羽翼,而且新生羽翼,急于高飞远举,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像一个鸟儿一样,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为迷狂。现在我们可以得到这种迷狂的结论了,就是各种神灵凭附之中,这是最好的一种。[2]125
而其他八类人因为灵魂不同程度的受损难以观看真正的美的境界,也就无法进入这种迷狂的境界。但不能进入这种迷狂的境界,不等于说不能够进入其他三种迷狂的境界。在柏拉图所列的九等人中,第五等是预言家或掌宗教典礼的,第六等是诗人或其他模仿的艺术家。[2]123这正好是可以陷入以上所说的另外三类迷狂的人。因为,对于诗神的迷狂,柏拉图在《伊安篇》里说得很清楚,指的就是被神依附的诗人能够不知不觉地写出美妙诗歌的那种迷狂。但他们即使被灵感注入,也依然被认为是拙劣的技艺者,因为灵感的来源不在他们自身,而在附身于他们的神灵,这也是柏拉图贬低他们的原因。而在 《斐德若篇》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演说前,依然是祈求神灵的灵感注入来助他一臂之力,却绝不说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去演说。但这诗神的迷狂绝不等同于第一等人的爱与美的迷狂,苏格拉底在演说之后懊悔不已,因为这诗歌里对神有所污蔑,因而是一篇谩神的文章。所以,为了赎罪,苏格拉底又写了一篇“认错诗”,此时他并没再去祈求诗神。[2]113因此,并不能单纯从字面上来认为普通诗人和模仿者就与灵感绝对无缘,而不能陷入诗神的迷狂。不过,这类迷狂相对于爱美者和爱智者而言,它的等级是低的。陷入这类迷狂的人的灵魂是不如爱美者和爱智者那样纯粹和完美,因而附有罪孽。而如果要说这第一流的爱美者和爱智者的迷狂是诗神的迷狂,它们都是诗人的灵感,恐怕就不是那么贴切。他们之间有着等级的差别。[3]
如果爱美者和爱智者不能够创作诗歌,即使他们也陷入对诗神和爱神的顶礼,那也只不过是对神圣理念的观照,是对前世灵魂记忆的回忆而已。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美”或“真”的顶礼,而万万不可能自降等级。反之,那第六等的诗人即使陷入迷狂也万万不可能与这一类人混同。但朱光潜既然先行认定了那“第一等人”的迷狂与文艺创作的灵感没有什么不同,也就认为他们都是诗人,从而把本属于这“第六等人”的迷狂也一并归入了“第一等人”,认为柏拉图欣赏“第一等人”的灵感,而否定“第六等人”模仿的技艺。这样简单的区分并不符合柏拉图论述的逻辑。
朱光潜以为这两类人是柏拉图对“诗人”看法的矛盾,多半是他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待了柏拉图的思想,以为迷狂的诗人能够制作和演说美,因而与那类爱智者和爱美者可以算作同一类人,而与只是真正美的“影子的影子”的普通诗人和模仿者有本质区别。因而他们之间那些差别都成了柏拉图作为贵族阶级鄙视劳动者的结果。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只是这种说法不能完全再现柏拉图自身的逻辑,因为柏拉图没有称第一等人为“诗人”。把第一等人认作诗人只是朱光潜自己引申的意思,以为只要他们表现了“美”,或者“迷狂”,就可以借此相通,而不必关心两者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媒介的差异。这种误读应当是朱光潜所论述的焦点全在“美学”范畴里的“美”所导致的,他只以现在的目光看到了共性,而忽略了它们具体表现的逻辑和语境。因而,爱情、诗和艺术,以及其他美的有关事物都被朱光潜当作同一范围的对象来论述了:
在柏拉图的许多对话里,特别是在《斐德若篇》和《会饮篇》里,常拿诗和艺术与爱情相提并论,也就因为无论是文艺还是爱情,都要达到灵魂见到真美的影子时所发生的迷狂状态。[1]19
但《伊安篇》里的诗人的 “迷狂”并不如朱光潜所说的都是这同一类“迷狂”,因为柏拉图从未给诗人完全看见“美”的权利,虽然它们之间极为接近。这点接近自然也有柏拉图哲学自身矛盾的原因,后文还会提到,但就此处而言,它们之间的不同是很明显的。另外,朱光潜解释说,《伊安篇》中诗人迷狂的理论来源是古希腊的自有的神话和传说,而爱美者和爱智者的灵魂轮回说则应该来自东方的埃及。所谓这两类“诗人”的说法从来源就不相同,在柏拉图那里也从未被描述“诗人”这同一样事物。因为朱光潜只是觉得这两类迷狂比较相近,就认定它们都是诗人的迷狂,而与第六等模仿的诗人有天壤之别,从而推证柏拉图思想上存在着矛盾,这种说法也并不符合柏拉图文本所展现的逻辑。
二、既迷狂又模仿的诗人
其实,以上所说的这两类 “诗人”和两类“灵感”自始至终都是沿着各自逻辑发展的。这一点从柏拉图文本中“诗人”概念的出现时间顺序和逻辑发展中可以清晰辨认。柏拉图最先创作的是《伊安篇》,然后是《理想国》,晚一些是《斐德若篇》,最后是《法律篇》。在《伊安篇》里存在着技艺的诗人和迷狂的诗人间的区分,后者虽然有神灵依附,但依然被视为拙劣的诗人。在《理想国》里,诗人进一步被定义为拙劣技艺的模仿者,至于灵感说则被有意忽略了,因为如果要谈论诗人的灵感,就会牵扯神的意图而无法完全对诗人和诗做出负面评判。因而本在《伊安篇》里被视为神灵依附的荷马在《理想国》中则完全被视作模仿者。而《斐德若篇》里诗人可以看成对《伊安篇》和《理想国》的修正和总结,诗人既与神的迷狂相连,又被说成第六等的模仿者,而这诗人的迷狂因为必须模仿与哲人的迷狂是两码事。而在《法律篇》里,柏拉图则对以上说法又做了补充和总结。他说:
当诗人坐在诗神的祭坛上的时候,他不是神志清醒的;他就像一个喷泉一样,让任何流入的东西自由地喷射出来,而他的艺术则是模仿的,他往往被迫去表现具有相反气质的人,但不知道哪一方包含着真理。[4]
这里的诗人显然是《斐德若篇》里逻辑的延续,是 《伊安篇》和《理想国》里诗人的合体,他自身是迷狂的,他的诗则是模仿的。柏拉图看起来为自己这两种说法找到了一种有趣的调和方法。先不论这种说法合理与否,至少在柏拉图的表述里,他对诗人的定义有着清晰的逻辑发展线索。而至于“灵魂轮回”的说法,以及爱美者和爱智者的说法从来没有跟柏拉图关于诗人的说法混在一起论述,它总是作为柏拉图哲学的最高目的而出现。柏拉图这种区分的根据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但这两者在柏拉图确实是截然不同,无法混淆的。但朱光潜认为以上两类人都是柏拉图对诗人的描述,这两类迷狂都是文艺创作的灵感源泉,因而他自然得出柏拉图倾向灵感的创作,鄙视模仿的技艺者。“他有意要拿这‘第一等人’和普通的‘诗人和其他模仿的艺术家’对立”的结论。[1]9但如上所述,这 “第一等人”从未跟“第六等人”一同被当作“诗人”论述,而这 “第六等”的诗人本身就可以包含迷狂和模仿两个特征,虽然并不是必然能够迷狂。朱光潜因为混同了两者,又没有仔细审查柏拉图对这 “第六等”诗人的前后描述,就自然忽略了这“第六等”诗人其实与诗神的迷狂有着亲缘关系,反而认为创作的灵感都属于“第一等人”, “也就是贵族阶级中的文化修养最高的代表”,而“第六等人”都是模仿的技艺者,从而得出这是柏拉图的阶级局限性的结论。这是不确切的。
为了对以上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这里再引申一下柏拉图“第六等”诗人的观念。柏拉图关于“诗人”的观念大体上还是古希腊流行的观念,一是把诗人看作技艺的制作者,二是把诗人看作神灵注入灵感的迷狂者。因为同是技艺的制作者,他与其他日常生产的劳作者就没有什么不同,因而在柏拉图的理式之下,他比匠人和画者还要低,但仍是一类人,都是模仿者而已。因为是被神灵注入灵感的人,他又是无知和被动的。[5]而《斐德若篇》里的第一等人,爱智者和爱美者却能够通过今生的模仿而回忆前世的观看,从而生发出灵感。那么说到底,这两类人从根本上就处于不同的世界。诗人的迷狂因为神灵的附身而暴露了他们的无知, 《斐德若篇》里的爱智者和爱美者的迷狂则使他们能够回忆和模仿神明,因而观看真知。这种区分现在看起来毛病很多,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因为灵感倘若没有诗歌的创作实践,就很难称其为灵感。文艺创作的灵感在逻辑上看起来是在实际创作之先,但只有当它展现在具体的实践中时,它才能够被认定为灵感,也因此实则在创作成果之后。因而创作的灵感实际上必然跟创作的技艺联系在一起,从这点看,既能够迷狂又能够模仿的“第六等”的诗人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这“第一等人”审美的形式与克罗齐的“直觉说”形式上很相近,都否认外在的媒介来传达内在的美感,朱光潜对此一直有所批评,[6]179而在此却混为一谈,不得不说是另有原因。
三、美学与政治的双重困境
对于以上的种种矛盾之处,朱光潜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在1951年的 “引论”里,朱光潜在讲完“两种诗人”后总结道:“换句话说,一种是灵感的诗人,一种是模仿的诗人。因此,诗 (连艺术在内)也就要分成两种。但是模仿的诗人虽没有灵感,而灵感的诗人却仍须假道于模仿。因此,像荷马那样的大诗人,尽管是‘由诗神凭附的’,尽管柏拉图承认他从小就对他养成深挚的爱好,还是要谴责和驱逐。”[7]这里,朱光潜实际上已经察觉到迷狂的诗人与迷狂的哲人间有所不同(诗人必须模仿),而与模仿的诗人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局面,这也正是《伊安篇》和《法律篇》里所体现的内容。但很奇怪的是,在1959年的 “前言”和1962年的“译后记”里,这句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想国》里只模仿而不迷狂的诗人的论述,也就是朱光潜所认为的“第六等人”。与此相对的就只是不能模仿但依然能够受灵感注入的“第一等人”。按理来说,依据1959年和1962年所做的补充,朱光潜对柏拉图的认识应该更加丰富和充实,不应该会把自己的观点简单化来处理。但如上所述,事实上情况并不全然是这样。而作为一整段的总结句,简单归结为疏忽和遗漏,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删改的原因,有必要对它的写作过程和背景做一个全面的梳理。朱光潜在1959年的“前言”中对1951年的 “引论”做了很大更改,主要是删去了大量介绍柏拉图生平和当时社会背景的文字,而更多内容用来分析柏拉图的文艺观点,这一部分原本在1951年的“引论”中非常简略。如上所述,朱光潜在细致分析这些观点的逻辑之后,往往会把原因追溯到其背后的阶级根源,这其实是有直接的社会原因的。这篇 “前言”写于50年代后期的美学论争的高潮期间,朱光潜当时为了应对不同批评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评,已经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在不断调整自己所谓的“唯心主义”观点。而1962年再版的“译后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与同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史(上)》中柏拉图的章节内容基本重复,只是《西方美学史》的内容受篇幅所限,要简略很多。从《西方美学史》的绪论可以知道 《西方美学史》是1962年由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门下发给朱光潜的教材编写任务,虽然很难断定它与“译后记”里的写作谁先谁后,但可以猜测朱光潜借编写《西方美学史》机会又对柏拉图有了更多认识,才会去更改两年前刚刚更改过的“前言”。对于《西方美学史》的编写原则,朱光潜是这么说的:
1957年到1962年,在党的领导下,我积极参加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美学批判和讨论。这是我国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的重要性我认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就我自己来说,也是通过这次批判和讨论,初步认识到自己的美学思想的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开始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 《西方美学史》就是在这次讨论后开始编写的,这是我回国后头二十年中唯一的一部下过功夫的美学著作。我译了莱辛的《拉奥孔》、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8]
也就是说,从1959年的 “前言”到1962年的“译后记”的补充都是与这一条学习和实践马列主义观点的过程相伴的,所以比之1951年的“引论”多一些阶级分析批评是自然的事情。这当然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特征,但朱光潜的论述不是对复杂现象做片面化的总结,而是立足在对文本逻辑细致分析的前提上的。可以看到,1959年之后的更改大多仍是对柏拉图观点和逻辑的介绍和梳理,而非模板化的批评。而在1962年“译后记”的少量补充里,朱光潜更多的是在为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做辩解,让人们不要因为柏拉图的阶级身份而忽略了他学说的价值。这除了朱光潜自身对于学术学理性的坚持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与当时编写《西方美学史》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西方美学史》等一批教材的编写是在1959年到1961年“大跃进” “反右倾”,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等一系列经济困难之后,当时全国上下在各个领域都开始对这种过“左”的思想进行纠正。“重新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是党中央在文教战线一项重大决策,是克服‘左’的思想在高等专科院校的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9]因而,这也给了朱光潜在编写《西方美学史》和改写 “引论”留下了一定自由的空间。所以,1959年的“前言”和1962年的 “译后记”在再版之初可能就面临着双重的处境,既是自我观念的改正,又是组织编写的教材任务。因而这篇“译后记”的重写就不能简单断定为一件出自朱光潜自我意图或国家意志的更改,而可能包含着双重的意图和面向。这两篇更改的 “前言”和“译后记”里对柏拉图文艺观点的梳理远比1951年的“引论”内容更为充实和丰富,但也远多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观点和术语。所以,并不能与当时的其他一般的外在式阶级分析批评混为一谈,但又不得不有着紧密联系。而在面对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克罗齐观点时,朱光潜不断调整对其的理解和翻译,也深刻地反映了这种跟随当时理论运动的心态和思想变化。[6]144
从这则删去的内容来看,朱光潜即使不因自己的“美学”视角对柏拉图笔下这 “诗人”和 “迷狂”的矛盾关系有所疑惑,也至少因当时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风向所干扰。因为依照他1951年“引论”里所暗含的分类,实际上不是有两类诗人,而是有三类诗人,一类是《斐德若篇》里最高迷狂的爱智者、爱美者以及诗人和爱神的顶礼者,一类是《伊安篇》里受到诗神迷狂但仍须假道于模仿的诗人,还有一类是没有灵感只会模仿的诗人。恰恰是中间这种既受到灵感注入又模仿的诗人成了难以归类的或者说难以解释的事物。他好像既不属于上层贵族,也不属于下层平民;既不属于第一等人,也不属于第六等人;既能够被诗神凭附,却又因模仿而缺乏真理。而如果硬要以上层贵族和下层平民的阶级对立话语来评析柏拉图的这一等人,无疑将适得其反,难以解释。因此它已经超出了阶级分析话语的模式,成了一种无言的威胁。这处于中间的诗人不仅对朱光潜刚刚转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构成质疑,也在极端阶级化的社会环境里是非常不合时宜的。那么如何在 “前言”和 “译后记”里,甚至在面向全国的教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批评方法里处理它,将无疑是个难题。最好的方法就是略而不述,而就对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批评说明的部分来做分析。但这种忽略就可能导致以上所说的朱光潜从“美”的角度对柏拉图“两种诗和诗人”的误认在一改再改中不仅没有改正,反而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给进一步强化了。因此,与其说柏拉图有意让“第一等人”和“第六等人”形成对立,不如说是朱光潜的意图在发挥作用。
总之,因为美学论争后的形势,朱光潜在1959年的“前言”和1962年的“译后记”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柏拉图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改写,而由于后来编写《西方美学史》时文化政策的放宽又做了很多为柏拉图思想的辩护,但这种模棱两可的“诗人”还是消失了。另外,在1959年的“前言”里,朱光潜也说柏拉图的第一等人正是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家”,却没有进一步延伸,这或许也有他已经存了1951年“引论”的“两种诗人”区分的观念的原因,所以即使他进行了更多的补充,也依然没有对这种说法再详细审察。因而,这处于社会不同阶级和真理不同等级之间的第三类诗人的消失是当时阶级对立的影响,还是当时社会整体文化结构趋向极端对立的一个表征,抑或仅仅只是文艺层面上的逻辑问题,是朱光潜的由于“美”而对哲学的疏忽呢,恐怕难以定确凿之论。更为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双重的原因,既是美学的误认促使了政治的偏向,又是政治的偏向强化了美学的误认。
四、解构与诗哲之争
朱光潜的说法虽然并不符合柏拉图所想展现的意图,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其实暴露出了柏拉图观点的一个重要矛盾。从“美”的体验而言,柏拉图所谓的第一等的哲人和第六等的诗人的迷狂之间确实有很大的相通之处,而非绝对差异性。[2]113同样,从语言描述层面上试图分清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简单的,但实际上诗神的顶礼和诗神迷狂的注入之间很难被完全分离。如果说爱智者与诗人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距离,而就爱美者和诗神的顶礼者与灵感注入的诗人间却很容易被混淆一起,即使灵感诗人仍需要假道于模仿的说法与前者并不完全等同。[2]125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的文本里,这第一等人和第六等人之间本身虽有差异,但也有一些容易交集和混淆的地方。那么,柏拉图为什么在文本里费尽心机地要在爱智者、爱美者和诗神顶礼的迷狂中剥离出诗神的迷狂呢?又为什么把在涉及诗神的迷狂时一定要提示它的模仿罪,一定要把诗神的迷狂与第六等模仿的诗人分开论述而没有放在一起讨论呢?
从解构的视角来看,在柏拉图的文本很明显体现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一系列诸如言语/文字、在场/缺席、良药/毒药、真理/模仿的二元结构之间运作,并以前者为本原来贬斥后者。但通过德里达对柏拉图文本里的“药”的意义链分析以及对言语和文字之间关系的拆解后,它们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互不相关,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重关系。在此,德里达的解构的重心并不是强调以被贬斥的一方颠覆原统治的一方,而是以延异、播撒和补充等一系列活动来使人们重新看待原有僵化的结构关系。[10]
从这个角度而言,柏拉图也是在试图竭尽心思地去让第一等人与第六等人划清界限,这种既迷狂又模仿的“中间人”的存在很可能造成两者的混淆,因而必须把他排除在“哲学”之外。换而言之,如果诗人仅迷狂而不模仿,那就与哲人这种纯粹的迷狂没有差别,也就无须遭到排斥;而如果诗人只模仿而不迷狂,那么就难以对哲人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因而就可以随意处理。所以,真正意义的哲学与诗的争论在于诗的迷狂可以通达哲学的迷狂,而却不得不借用模仿来玷污其纯粹性,这才是柏拉图害怕和担心的地方。就像《理想国》中,柏拉图表面上指责诗的绘画般的拙劣模仿将会危害人的心灵,但仍为着诗的音乐性的魔力来欢迎诗重新回到理想的城邦之中。这音乐性的魔力见于荷马,也就是诗人的迷狂,而那拙劣的模仿却必须被驱逐于城邦之外。
在此,可以看到柏拉图言辞凿凿地试图从诗人的模仿里把诗人的迷狂剥离出来,又试图从诗人的迷狂里把哲人的迷狂剥离出来,不过是为了维护那个哲学意义上的本原的纯洁性。但哲人的迷狂根本无法自足存在,而又必须借用对诗人的迷狂来补充说明,而对诗人的迷狂也同样不是自足的,也必须借用诗人更加具体的模仿技艺来补充。在这条不断延异和补充的链条里,原有的哲人的迷狂就根本不可能排斥诗人的迷狂和模仿而孤立成为真理的在场。因而,柏拉图对第一等人和第六等人煞费苦心的区分就从内部不攻自破。从这个角度进而观之,柏拉图对于哲人和诗人之间的严格区分,以前者作为真理的代表来贬低和驱逐后者,也同样面临着内在的危机。在这里,所谓的哲学真理的核心总是以隐喻和差异的修辞来呈现,“柏拉图的语言和文本由这种差异之差异来构成,那种矛盾性也表现在它的主张和他阐述的顺序之间。文本的构成总是自然而绝对地由异质性构成,并被自身的异质力量所消解”[11]。而所谓的哲人和哲人的迷狂又必须与诗人的迷狂和模仿相连,总是作为“中间物”的第三者,这也正是一般而言的德里达以文学来解哲学的良药/毒药。反过来说,这种处在第一等人和第六等人、迷狂和模仿、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诗和诗人的修辞是否也是解朱光潜美学和政治困境上的一剂良药呢?
注释
[1]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本文对柏拉图著作观点的引用,主要依据朱光潜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部分涉及英文译本。除了此版本通用、方便的考虑,一方面,与朱光潜“前言”“引言”“译后记”的不断变迁相比,其译文本身的内容在文中提及的各个版本里几乎没有改动,显示出了前后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这种译文之外的不断变迁的外置观点与朱光潜的译文本身所显示出的柏拉图的思想往往并不一致,甚至矛盾。
[3]刁克利.柏拉图诗人论的矛盾及其启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1).
[4]Plato.Complete works/Plato.Trans,John M.Cooper.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p.1405.
[5]陈中梅.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批评——柏拉图诗学思想再认识[J].外国文学评论,1994(1).
[6]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7]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19.
[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2:358.
[9]郝怀明.周扬与大学文科教材建设[A].王蒙,袁鹰.忆周扬[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348-349.
[10]王榕.文字与药——通过《柏拉图的药》看解构的本质[J].国外文学,2019(3).
[11]陈晓明.“药”的文字游戏与解构的修辞学——论德里达的《柏拉图的药》[J].文艺理论研究,2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