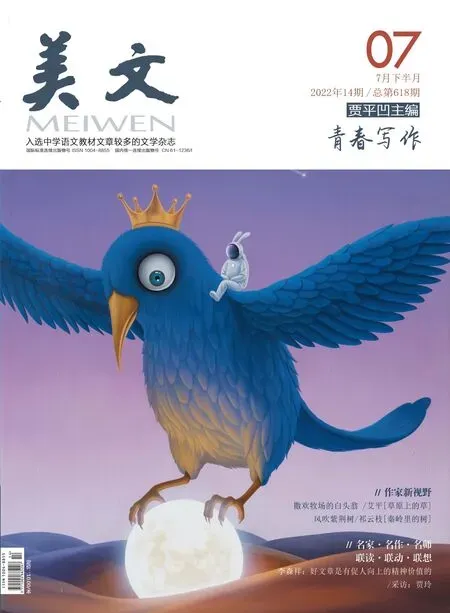我走进了敦煌的精神世界
北京鼎石学校高二年级 李沐白
那是一场以热爱开始、以奇迹结束的舞台盛宴,一场四五个人发起的校园戏剧,六个多月后竟然走到了那样高远的地方。
持续的疫情打断了学校中文戏剧的传统,有经验的学长大都毕业,一切都变成了全新的。在选题上几乎耗费了一个月时间,直到敦煌的历史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似乎是一个被常常提起却又无法穷尽的主题,即使书写了一千个故事,也没有一个能真正诠释出我们心中的敦煌。
汗牛充栋的采访、传记和回忆录里,常书鸿的眉目逐渐显现。就像资料中描绘的那样,他有着广受赞颂的真挚执着、饱受熏陶的温文尔雅、力挽狂澜的强大魄力……当然他也有不善言辞的内敛、舍我其谁的傲气、以及在家庭生活中暴露的柔软和笨拙。
剥去批判和谩骂的浓雾,陈芝秀也显露出原本的面孔。顺从、隐忍、孤独的她在压抑的时代里拿起刻刀学习雕塑。家庭、事业、儿女都被她妥善照顾,如果她的命运没有被裹挟着奔向大漠深处,也许她会作为一个封建社会里难得的自由女性度过一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最后为自己做了一次选择,便消失在光照不到的地方,成为了历史中的一抹暗影。
在我们的故事里,这两个角色既属于历史,也拥有超越历史的灵魂。他们张口倾诉理想与生活,作为两个与你我无异的存在被聆听、被理解。
除了他们二人,我们还将目光投向了其他人:第一个打开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将佛祖作为精神寄托的农村妇人阿龙,他们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将经文送到了外国人的手中;奉献一生的“敦煌女儿”樊锦诗,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守护着热爱敦煌的本心。那么多与敦煌有关的人中,对佛教徒、艺术家而言,敦煌是他们心灵与梦想的载体;对研究者、记录者来说,敦煌学是他们寄托信念的精神家园……这些人来了又去,即使大多籍籍无名的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却汇成了延续敦煌艺术的重要力量。
我们顺着这些人的目光去看他们眼中的彼此,看那个艰苦的、真挚的年代,看他们如何为了世上最瑰丽的人类文明奇迹之一,将自身的命运投入到不见底的深井中去,看他们像捧着雨夜里的星火一样把敦煌精神代代传承。
13名教师和106名学生,数以百计的现场观众,2天内超过4000人次的在线观看——这是令人欢呼的结果。我们前前后后写了五版剧本,改了13版英文字幕,编辑了三个版本的介绍,加入了六段舞蹈。像那些守护者们将生命献给敦煌一样,我们将自己几个月的生命投入到戏剧的排练与制作中。每一次幕帘拉起都吸引着希冀的目光、每一次音乐响起都激起热泪盈眶、每一个演员递出的眼神都鲜活的,好像历史就在我们眼前发生——《问道》,属于我们的敦煌,活了。
敦煌——一个不朽的人文奇迹,震撼人心的文化存在。我们用在语文课里培养的对伟大文本的热爱、在历史课里激发的对不朽遗产的好奇、在知识理论课里思考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去引导对敦煌遗存的发现,去揭示前人藏在资料和文献里活生生的“秘密”。
微笑的佛像在阴影里投下目光,半褪的色彩在穹顶转出宝花。为了深入敦煌的灵魂,我来到了这里,亲眼见证了敦煌的壮丽与雄伟。多少的资料文字都比不上那一眼来的深刻、一瞬间,我就像在异国他乡第一次看到敦煌画册的常书鸿一样,纯粹的美深深地烙印在了我记忆的深处,不必请人解释什么便能理解——那是属于这个民族,属于这个国家的伟大、绚丽的瑰宝。
清朝、民国以及建国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是我们设置的台上时空。《问道》的三幕时空跳跃,从第一次打开藏经洞到数字敦煌脱颖而出,从抱憾终生的放手到骄傲的捧于人前,数代人的爱与奉献终成就了如今的敦煌盛世。为了 “世界上最瑰丽、最伟大的事业” ,常书鸿用一生去扛起这份责任,他的女儿常沙娜也把自己的一生悉数奉献;当樊锦诗白发苍苍时,终于骄傲地向世界宣告 “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
时至今日,当我闭上眼睛,字幕器幽暗的蓝光仍挥之不去,充满激情的台词依旧萦绕耳旁。大幕落下、人潮散去,一种新的力量逐渐在心中浮现——那份被我们书写、演绎的爱与自豪沉淀成了心中的磐石。我们仰望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追寻先辈的足迹,我们也把心投入到这里,去爱,去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