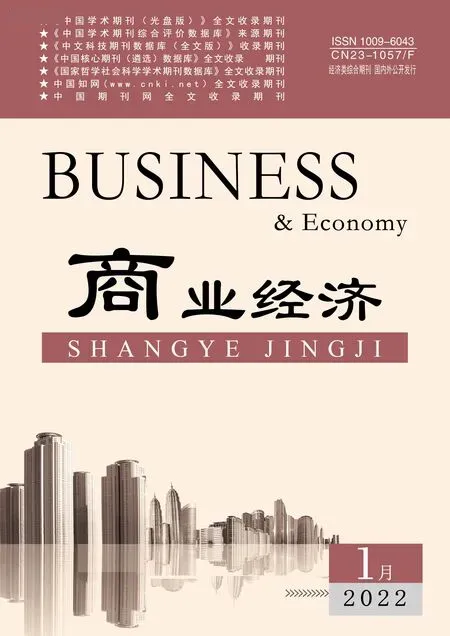普通法系视域下仲裁条款与法院管辖权条款的冲突与消解
——基于新加坡高等法院“BXHvBXI 案”
苟大凯
(1.北部湾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2.北部湾海洋发展研究中心, 广西 钦州 535011)
一、案情简介
新加坡高等法院“BXH v BXI 案”的原告和被告均为香港的公司。原告BXH 公司的业务是在俄罗斯分销被告BXI 公司生产的消费品。被告BXI 公司则是新加坡母公司设立在香港的以设计、开发、制造和销售消费品为业务的全资子公司。被告BXI 公司于2015 年10 月就其欠款3640 万美元及相关争端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提交了仲裁通知。原告BXH 公司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仲裁庭的管辖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于2016年4 月就该中心是否对具有管辖权的问题,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原告BXH 缺席出庭。该仲裁庭于2017 年5 月举行了一场证据听证会并于2017 年7 月发布了最终裁决。裁决驳回了原告BXH 公司对仲裁庭管辖权的异议并就有关实体争议也支持了被告BXI 公司的辩解。
二、案件争议焦点
原告BXH 公司和被告BXI 公司在其主合同《分销协议》中就其合同争端解决同时规定了两个条款,一个条款是仲裁条款(arbitration clause),另一条款是法院管辖权条款(jurisdiction clause)。该两个条款分别规定如下:
(1)法院管辖权条款(jurisdiction clause)双方在《销售协议》的第25.8 段约定:该《销售协议》应该受新加坡法律调整并根据新加坡法律予以解释,双方之间因本销售协议或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引起的法律诉讼的管辖权,或与本协议或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关的任何法律诉讼引起的法律诉讼的管辖权,应当由设立在新加坡的法院行使。
(2)仲裁条款(arbitration clause)双方在《销售协议》的第25.9 段约定:当事方之间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规则(SIACRules)在新加坡最终通过仲裁解决。仲裁裁决书应当载明事实认定和法律结论,当事方应当受其最终约束且不得上诉。
如何处理这两个同时存在于一份合同中的两个争端解决条款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本案的焦点之一。原告声称《销售协议》第25.9 段的所载的仲裁协议是无效的,其原因在于它与《销售协议》的第25.8 段的内容相冲突。被告则坚持认为仲裁条款有效。
三、新加坡高等法院的认定
首先,法院明确表示对原告的观点持否定立场。法院指出,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如果当事人双方业已表明了将其争端提交仲裁的明确意图(a clear intention),那么,法院就应当尽可能地寻去赋予该意图以效力。因此,即便是涉及仲裁条款自身存在瑕疵或空白的情形,只要当事人双方的仲裁意图是不容置疑的,法院就应尽量赋予其效力,作出使之有效的解释而不是否定其效力。对此,法院指出了当事人双方的仲裁意图可能表达不清楚的一种情形,即在主合同中同时存在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即便是这种情形,法院指出,普通法系的法庭所作的一系列的一审法院原判决也已表明法院试图将这种情形解释为同时兼顾两种条款的效力,而非完全否认其中之一的效力。随后,法院援引了三件案例以证明其观点。
案例一:“Paul Smith Ltd v H&S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案。该案是发生在英国的判例,但是,鉴于新加坡与英国同为普通法系国家,新加坡高等法院首先援引了该案。在该案中,当事人双方在主合同中规定:(1)合同争议根据国际商会(ICC)调解与仲裁规则通过仲裁解决;(2)合同解释以英国法律为准据法,英国的法院应当对当事人双方提交其裁判的争端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原告诉称,仲裁协议因存在与其自相矛盾的法院管辖权条款而应属于无效协议。时任主审大法官Steyn 则指出,把国际商事合同中当事人约定的争端解决方法认定为完全无效是极端不可取的审理结果。相反,Steyn 大法官进一步指出,准据法和法院管辖权条款并非指涉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方面争议的解决,而是指涉仲裁本身,也就是表明英国的法院对仲裁享有监督性管辖权(supervisory jurisdiction)。即便是承认作出这样的解释会导致法院管辖权条款在语言上的某种不适当,但是,Steyn 大法官认为这样做也比将仲裁条款视而不见地处理为无效约定更为恰当。
案例二:“Axa Re v Ace Global Markets Ltd 案”。该案也是发生在英国的判例,原被告双方也是在其主合同中同时约定了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对此,该案主审大法官Gloster 指出,主合同中同时约定英国法院管辖权条款和仲裁条款,表明当事人确定了对仲裁实施监督的法院,也就是说确定了适用于仲裁的准据法(crucial law)和适合仲裁后续程序的管辖法院。值得注意的是,该案例在 “Paul Smith Ltd v H&S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案”所确立的法院对仲裁享有监督性管辖权(supervisory jurisdiction)原则的基础上,似乎又将其解释向前推进了一步,即,确定了适用于仲裁的准据法(crucial law)。
案例三:“PT Tri-MG Intra Asia Airlines v Norse Air Charter Limited 案。”该案是在新加坡本土法院审理的判例。当事人在主合同中约定了由国际商会(ICC)通过仲裁解决合同争端的仲裁条款;与此同时,在同一合同中有载明由主合同所引起的任何争端均由新加坡的法院行使管辖权。在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该领域的相关判例后,该案助理主簿沿用了 “Paul Smith Ltd v H&S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案”中Steyn 大法官的审理方式,同时赋予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效力,判决当事方在约定合同争端由国际商会(ICC)仲裁的同时,也约定了新加坡的法院对仲裁的监督性管辖权(supervisory jurisdiction)。判决指出:“在对相关判例法的适当性和可援引性进行了仔细地研判之后,本人倾向于适用‘Paul Smith Ltd v H&S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案’的解释技术,通过将第22.2 段解释为提交新加坡的法院对仲裁行使监督性管辖权(supervisory jurisdiction)就可以做到将第15 段的仲裁协议与第22.2 段的法院管辖权协议协调一致。”
新加坡高等法院在援引上述案例之后,还引用了英国仲裁法权威Robert Merkin QC 在其最新的著作《仲裁法》(Arbitration Law)中就相关问题所作论述作为法理支持:“如有可能,法院将尽力赋予两个条款效力而非以一个条款效力否定另一个条款效力。就当下语境而言,法院所采纳的方法就是赋予仲裁条款效力的同时并不剥夺法院管辖权条款存在的全部意义,原因在于法院管辖条款仍然适用于任何仲裁裁决的执行,但是如果赋予法院管辖条款效力,则将会否定仲裁条款的效力。因此,结果就是法院通常会优先考虑当事人对仲裁条款的约定。”
新加坡高等院赞同上述推理和审理技术的运用。主合同双方已经在其合同中载入了第25.9 段的仲裁协议和第25.8 段的法院管辖权协议,并且并未以任何形式表明其中任何一个条款在某种程度上失效,这就表明合同双方认为两个条款都具有某种合同效力的意图。新加坡高等院指出,对案件的审理必须以此为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新加坡高等院也承认“Paul Smith Ltd v H&S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案”所确立的对同一合同中同时存在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条款争端的解释技术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在本案中,主合同双方在合同第25.8 段明确规定了“该《销售协议》应该受新加坡法律调整并根据新加坡法律予以解释。双方之间因本《销售协议》或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引起的法律诉讼的管辖权,或与本《销售协议》或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关的任何法律诉讼引起的法律诉讼的管辖权” 应当由设立在新加坡的法院行使。对此,新加坡高等院,主合同第28.5 段显然预设了围绕《销售协议》所引发的实体争端将提交新加坡的法院审理,而非仅仅预设了主合同第25.9 段规定的仲裁所涉及的准据法应接受新加坡的法院管辖问题。尽管如此,新加坡高等院仍然指出,经由《分销协议》所产生的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方面的争端或者与《分销协议》有关联的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方面的争端明显不能够同时即付诸诉讼又付诸仲裁。尽管不完全令人满意,化解此矛盾的唯一务实的办法就是采纳 “Paul Smith Ltd v H&S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案” 所确立的解释技术,将《销售协议》第25.9 段解释为当事人约定将合同实体争端提交仲裁解决,而将《销售协议》第25.8 段理解为经由任何此类仲裁所引发的争端应提交新加坡的法院并由其行使根据《销售协议》第25.8 条约定的法院监督性管辖权(supervisory jurisdiction)予以解决。鉴于这一解释技术与新加坡仲裁法理的潜在趋势具有一致性,所以,当事人通过缔结国际商事合同体现出来的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合同争端的明确的意思表示应予得到尽可能的支持。
总而言之,新加坡高等法院“BXH v BXI 案”及一系列相关案例表明,在普通法系的语境下,若当事人在同一主合同中同时存在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的约定,法院普遍采用“Paul Smith Ltd v H&S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案”的解释技术,优先承认仲裁条款对当事人合同实体权利义务的效力,然后承认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在于对仲裁具有监督性管辖权(supervisory jurisdiction),即,确定适用于仲裁的准据法(crucial law)和适合仲裁后续程序的管辖法院。总之,法院同时赋予了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以效力。
四、余论
当人事在同一合同中同时约定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解决其合同争端,此种约定在我国的效力如何?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6 年在《关于深圳联昌印染有限公司诉香港益锋行纺织有限公司承包合同纠纷案拟立案受理的报告的复函》中明确指出,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中解决争议的条款既约定涉外仲裁机构仲裁又约定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该仲裁约定无效。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由此看出,我国最高院对同一合同中同时约定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的问题的态度是,否定仲裁条款的效力。然而,我国最高法院对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却语焉不详。对此,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将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一并处理为无效,而由法定管辖原则来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例如,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审查协议的公正性原则,判定协议内容效力的尺度应当是统一的,在当事人既选择仲裁又选择诉讼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实际上是达成了两个合意,一个是关于仲裁的合意,一个是关于诉讼的合意。当两个合意发生冲突时,既然关于仲裁的合意由于约定不明而无效,那么双方关于诉讼管辖合意的效力也应同样无效。因此该条款整体无效,应根据法定管辖原则来确定管辖法院。
另一种处理方式是在认定仲裁条款无效的同时,另行审查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只要该法院管辖权条款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即认定其有效。例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认为,仲裁约定条款无效,但只要符合法律规定,诉讼管辖约条款的约定就应当有效;鉴于案件的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在上海签订,又约定争议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这是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的,所以,法院诉讼管辖权条款有效。
针对处理同一主合同中同时约定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问题,从法理上讲,据笔者考察,我国学者普遍支持采取先受理先管辖的原则。其理由是,当事人在管辖协议中选择了仲裁和诉讼,意味着彼此之间已经对于将要选择的争议方式达成了合意,因此,无论在争议发生后,一方当事人先选择哪一个解决方式,都在当事人的合理预期之内,并没有超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在化解仲裁条款和法院管辖权条款的冲突问题上,我国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借鉴普通法系法理和实践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