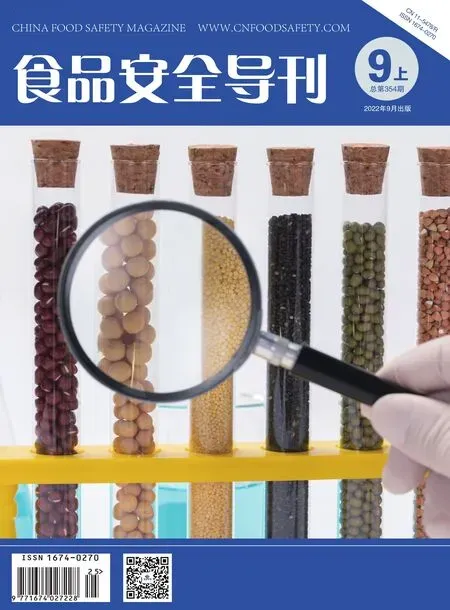植物基食品的规范标准适用问题和消费认知挑战
□ 张旭晟 上海骥路律师事务所
随着社会对食物来源的重视与饮食观念的变化,植物基食品的市场潜力和研究热度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加,这也对我国食品投资和消费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我国传统饮食中的豆类、坚果等植物早已形成丰富的加工及食用历史,由海外市场引领的植物基食品热潮,在中国消费市场或面临更为复杂的规范标准适用问题和消费认知挑战。
1 植物基食品热潮的创新要素
近年来,由海外消费市场率先引领的植物基食品热潮,其主要创新要素在于植物蛋白的多样性来源和相应的加工技术应用。植物蛋白原料的来源选择广泛,常见的包括豆类蛋白(大豆、豌豆、鹰嘴豆等)、谷物蛋白(小麦、燕麦、藜麦等)和坚果及籽类(花生、杏仁等)蛋白等;植物基食品的加工技术则包括应用于植物基肉制品的挤压拉丝、剪切、3D打印等,以及应用于植物基蛋白饮料的酶解技术等。因此,植物基食品是一个跨越多个食品类别的大概念,常见的产品类别分为植物基肉制品和植物基蛋白饮料。
相较于我国消费市场上长期存在的植物来源食品,前述植物基食品的差异性和附加值更多地体现在加工技术带来的味觉体验提升。然而,植物基食品需如何适应我国食品监管框架,使其在与传统植物来源食品的市场竞争中形成鲜明的消费认知,是目前该细分行业亟待突破的关键。
2 规范标准适用问题
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一大特点在于依靠大量的技术规范文本:通过不同层级的食品安全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要求特定食品类别满足相应标准中的食品质量安全规定。植物基食品,尤其是以豆类为原料的食品,目前能够被我国现有的食品生产经营规制体系较为完整地涵盖。例如,豆基肉制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品类属于我国《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项下的其他豆制品;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范围和限量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新型豆制品的相关规定;最终产品可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制品》(GB 2712-2014)、《大豆蛋白制品》(SB/T 10649-2012)或《植物基肉制品》(T/CIFST 001-2020)执行质量安全规定。由此可见,若植物基食品能遵循我国现行的各项食品管理规制,其在我国基本不会面临过多的监管壁垒。
尽管如此,植物基食品在我国仍无明确的官方定义,与我国传统植物来源食品的区别也无法从所适用的食品标准中得以直接体现,从而导致终产品的标准适用存在一定的自由选择度。同时,现行食品分类和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植物基食品品类的创新拓展。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行业组织率先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希望助力解决产品差异界定和产品标准缺失问题。在植物基肉制品领域,《植物基肉制品》(T/CIFST 001-2020)作为行业组织推出的团体标准,意在为产品差异界定提供规范支撑:适用该标准的植物基肉制品,需突出其加工技术的使用和风味调控特点。只有具备“类似动物肉制品质构、风味、形态特征”构成要件的,方能适用《植物基肉制品》(T/CIFST 001-2020),如此便与不意在模仿动物肉制品特征的植物蛋白食品形成明显差别。植物基蛋白饮料的标准化领域,《植物蛋白饮料 燕麦奶》(T/SSFS 0003-2021)、《植物蛋白饮料 亚麻籽乳》(T/ZJYLGYXH 002-2021)、《藜麦植物蛋白饮品》(T/SXFIA 004-2022)等的陆续出台,填补了相应植物蛋白来源饮品缺失产品标准的问题。这些团体标准与《植物蛋白饮料 核桃露(乳)》(GB/T 31325-2014)、《植物蛋白饮料豆奶和豆奶饮料》(GB/T 30885-2014)、《植物蛋白饮料 杏仁露》(GB/T 31324-2014)等国家推荐性标准,共同为细化植物基蛋白饮料分类管理提供了自愿性规范文本。
为了更好地解决规范标准的适用问题,笔者认为仍需进一步明确一些关键要件。例如,植物基食品是否可以含有部分动物源成分;植物基食品是否须以模拟动物源食品的特征为目的;植物基食品是否须匹配对应动物源食品的营养组成。将上述3个关键要件进行排列组合后,植物基食品可进一步细分为至多8种食品小类。若今后在宏观政策层面建立并完善相应规范,无疑将有助于植物基食品领域各细分市场的持续发展。
3 消费者认知挑战
鉴于我国居民具有长期食用植物蛋白的历史,公众对植物来源食品的熟悉程度和可接受度颇高。例如,豆基食品在我国已形成丰富的产品类型,并在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消费者对不同传统豆基素食的认知早已根深蒂固。这意味着植物基食品作为食品领域的“后来者”,如何让消费者形成清晰的产品认知并形成与传统植物来源食品有效的区分,是短期内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
在食品标签标识方面,《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第五项拟要求:“以植物源性食品原料生产制作模仿动物源性食品的,应当在名称前冠以‘仿’‘人造’或者‘素’等字样,并标注该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中第4.1.2.1条“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清晰地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规则要求相符。但是,此类规定形成的二阶化区分无法适用于植物来源食品大类内部的不同产品。换言之,在植物基肉制品和传统素肉并行的市场竞争中,各厂商产品的模仿接近程度不同,但均冠以‘仿’‘人造’或者‘素’等字样,难以形成植物基肉制品和传统素肉之间的有效区分,这也给受众的消费决策和认知判断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就品类对比而言,虽然植物基食品理应具备近似动物性食品的味觉体验,但现阶段而言仍主要受制于研发和加工技术的发展。以植物基肉制品为例,作为一类微观组织重构食品,其所呈现的质构、风味和形态等是消费者形成清晰认知的关键所在。若直观体验无法带来预期的模仿接近程度,则较难突破传统植物来源食品的显著优势地位。加之植物基肉制品在定价上的策略,缺失清晰的产品认知将导致消费者主动重复选择植物基肉制品存在可预见的困难。
4 总结与展望
我国对植物来源食品的加工和食用历史造就了一个较为特殊的消费市场,也给旨在通过创新加工技术带来味觉体验提升的植物基食品的经营战略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是与传统植物来源食品直接竞争,还是挖掘开拓新的细分市场?目前来看,植物基食品的差异性和附加值感知程度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期待各相关利益方进一步完善植物基食品的标准建设,为不同层级的植物基食品提供相适应的规范保障的同时,在植物基食品细分市场内形成更为清晰的差异化产品竞争布局,减少消费者对植物基食品的认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