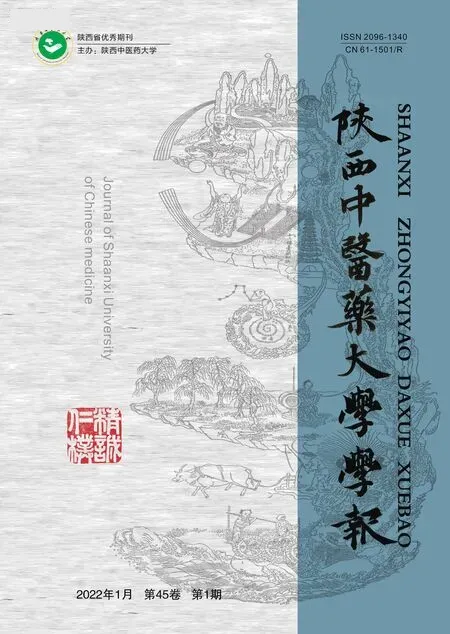吕志平教授辨治肝胆病学术经验*
黄少慧 陈炜聪 孙海涛 高磊 张国华 张绪富 安海燕 庞杰 贺松其,2
(1.南方医科大学,广东 广州 510515;2.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广东 广州 510315)
吕志平(1956年—),男,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中医教学名师,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专家,第五批、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传承工作指导老师,广东省名中医。从事中医教学、临床、科研工作40年,擅长应用中医理论及治疗方法防治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脂肪肝、胆囊炎、胆石症及肝郁证等肝胆疾病,临床经验丰富,诊疗思路独特,创新性提出:①肝胆病属于肝脾同病而以肝郁脾虚为主,治疗当注重疏肝理气、健脾补虚、扶土抑木。②岭南肝病,多湿多瘀,当分期分证、审因论治。③肝炎后肝纤维化的病机关键是肝郁脾虚、湿热内阻挟瘀毒,提出隐证型患者同样存在治疗必要性。④对慢性乙肝的防治提出了执简驭繁,以内外辨病因,以虚实分证型,多法联用求治疗的新观点。研制的保肝宁、养肝降酶丸、熊胆清肝胶囊、熊胆利胆胶囊等院内制剂,取得较好疗效。笔者师从吕志平教授临证,现将其辨治肝胆病的学术经验总结如下:
1 肝胆病首重疏肝健脾调气机的学术渊源与传承
1.1求学明师得真传,论治诸病重调肝 吕志平教授早年求学于广州中医学院,在校期间得到广东省名老中医关汝耀先生的悉心指导。吕教授学习关老的“理肝疗法[1]”,并掌握其经验方“调肝汤”的运用要领,体会到诸多内科杂病的发生、变化、发展均与肝气失调有关,故治疗许多内科杂病都应考虑到调肝理气。之后,吕教授赴山东中医学院攻读中医学硕士,师承刘承才教授。因勤奋好学、天资聪颖,深得老师的赏识,在老师的倾囊相授下,尽得真传,对“黄连温胆汤”“逍遥散”“柴胡疏肝散”“茵陈蒿汤”“四逆散”等方剂治疗肝胆内科疑难病的领悟尤为深刻。同时,吕教授亦得到山东省名老中医张珍玉先生的指教,受其“诸病皆可从肝论治[2]”等学术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行医过程中每遇疑难杂症,均重视调理肝气。吕教授在长期中医肝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勤求古训,衷中参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方法。
1.2肝主疏泄,为气机之中枢,属于中焦 肝与人体全身气机最为密切,吕教授提出“肝主疏泄,为气机之中枢,位于中焦”的学术观点。肝主疏泄,最早见于朱丹溪的《格致余论》,是指肝具有维持全身气机通畅的作用[3]。肝使全身气机通而不滞,散而不郁,故为气机之中枢。肝主疏泄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维持气、血、津液的运行,促进消化吸收等方面。肝主疏泄,能调畅全身的气机,气机调畅则气之运行通畅。气能运血,气行则血行,故肝气的疏泄作用使气血运行畅达无滞。气行则水行,保持水道的畅通,促进津液输布于全身。肝助消化的作用,与胆汁的生成和排泄和维持脾胃气机的正常升降相关。肝气疏泄,分泌胆汁;胆附于肝,藏泄胆汁。肝气疏泄正常,则胆汁藏泻有度,胆汁顺利排泄于肠道,促进脾胃消化食物。脾胃升降: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肝得疏泄,气机通畅,则脾胃升降无滞,生化与受纳无碍,饮食得下水谷得消而腑气通畅。又肝属木,脾胃属土,故古人有“土得木则达”之说[4]。
中医“肝”的本体和现代解剖学的肝脏基本一致[5],从部位上看属于中焦,可以从古籍中找到佐证。如《灵枢经》说:“阙……在下者肝也”,这里“阙”指的是胸廓,在下即指季肋部,可见古人已经认识到肝的位置在季肋。“肝独有两叶”“隔膜之下有肝,隔膜下有胃,其左有脾,与胃同膜”“中焦在胃中脘,以包肝裹胃也”等。中西医对肝认识的差异,归根到底是由两种医学体系不同的认知方法论决定的。从认识来源来看,中医学侧重从临床观察、经验总结中获取认识;西医学主要从解剖、生理、生化等微观研究中获得认识。吕教授认为肝属于中焦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本体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临床上与脾胃密切关系。临床常见“肝脾同病”“肝病传脾”,以肝脾同治为要。
1.3肝胆病属于肝脾同病而以肝郁脾虚为主 《难经·七十七难》云:“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此句提示医者,在临床上治疗肝脏病,应同时调理脾胃,使脾气充实旺盛不受肝脏邪气的侵犯。可见肝病要先“实脾”的原因,在于预防肝脏之邪传之于脾,也说明由肝病及脾的传变是一个过程,存在病变的先后性。吕教授借鉴此宝贵理论,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了“肝胆病属于肝脾同病而以肝郁脾虚为主”的经验学说。吕教授认为肝胆发病的同时,常伴有脾胃的失调,表现为“肝脾同病”,其中肝郁脾虚证最为多见,故治疗注重疏肝健脾、扶土抑木。从生理上看,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肝主疏泄,调畅气机,协调脾胃,并排泄胆汁于小肠,促进饮食的消化吸收及对精微的吸收和输布功能,脾的运化健旺有赖于肝的疏泄正常,脾气健旺,运化正常,水谷精微充足,气血生化有源,肝气得以濡养而使肝气冲和条达,有利于疏泄功能的发挥。又肝与脾胃共居中焦,肝为气机之中枢,调节全身之气机,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司气机运行之升降。肝气疏泄正常,则中焦气机升降得宜。从病理上看,肝脾同病。肝失疏泄,横逆脾土致脾失健运,而脾虚不运易致木郁土壅,消化功能失常。从临床表现上看,慢性肝胆病患者多表现出倦怠乏力、肢体困重、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及腹胀便溏等一系列脾虚不运之症,亦有胁痛、胁部不适、头晕失眠等肝郁的症状。故治疗注重健脾补气,扶土抑木。
2 辨治肝胆病
肝胆病病因复杂多变,不同的疾病或同一疾病的不同病变发展阶段,常表现出不同的病因病理特征,故而在临床实践中应注意审查病因及证候,为临床的辨证施治提供依据。结合中医学对肝病的认识,以西医对疾病病变发展不同阶段为切入点,以期较为完整科学地论述吕教授辨治肝胆病的学术思想。肝炎病毒、酒精、药物与毒物、血吸虫、代谢和遗传、胆汁淤积等病因引起的慢性肝脏疾病常伴有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进展为肝癌,严重影响患者健康与生命[6-7]。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理论指导下,吕教授认为肝胆病的病机关键是肝郁脾虚、湿热内阻挟瘀毒。尤其是岭南地区肝胆病,多湿多瘀,当分期分证、审因论治。在防治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肝硬化腹水、自身免疫性肝病等肝胆疾病,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2.1病毒性肝炎 岭南为多湿多热之地,湿热的气候因素使岭南人群易感外邪之气[8]。岭南地区气候炎热,多雨多湿,暑热期长,释继洪《岭南卫生方》:“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因此,岭南地区多暑、湿、火(热)三种淫邪之气,暑、湿、热三邪最易相兼[9]。病毒性肝炎诊治应结合岭南地理特点,分期分证、审因论治。吕教授认为病毒性肝炎的病因病机当归纳为毒、痰、瘀、虚四方面,正虚(主要指肝、脾、肾虚)是发病内因,是发病根本所在。整个病变的发展由气及血,由阳入阴,由中焦到下焦,同时“湿毒”之邪贯穿于疾病的始终。初起(活动期)多以湿热为主,湿热邪毒交蒸常贯穿于肝病的始终,湿热较盛,病邪可直入心肝营血,发生重症肝炎,即中医之急黄重症[10],病毒复制活跃,ALT明显升高,甚至血清胆红素升高。
治疗过程中,除了西医的对症治疗,中医治宜清热利湿(退黄)、解毒,用茵桅清肝汤,方药中的药物具有解毒燥湿,退黄通便,泄肝火、除湿热,还能平肝散郁,止吐健脾,取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应视湿热之孰重孰轻而权衡清热解毒与利湿退黄之轻重。正气不足则毒邪难去,毒邪不去则正气难扶;郁不解则血难通,血不行则气必滞。病毒性肝炎的发生发展,亦经历由急性到慢性的过程。肝炎慢性期,多以肝郁脾虚、挟瘀,治宜疏肝理气健脾,祛瘀解毒除湿,治宜白丹软肝汤。主要由白背叶根、丹参、鳖甲、黄芪、白术、枳实等药物组成,该方药可疏肝解郁,协调脏腑气机升降,健脾而使脾土不受肝邪乘侮,使脾的运化功能恢复健全,消除脾虚证候,白背叶根、丹参化瘀,则可达到治疗目的。在肝病整个病变过程中,湿热毒邪入血,这是肝病病程长、病情重、变化多端的病机关键所在。因湿热蕴毒,深伏营血,使病情反复发作,缠绵难愈,故应运用一些直入血分的药物,活血化瘀,以遏制病邪深入,达到清理肝脏的目的。治宜祛瘀解毒,健脾补肾,益气养血,用灵甲护肝汤,并随症加减。临床诊治中,识别邪正虚实;辨清在气在血;洞察阴阳偏盛;分清症候主次,注意主证转化;详查病症标本,分清轻重缓急;注重八纲、气血、脏腑三大辨证互参。
2.2肝纤维化 中医学并无肝纤维化这一概念,基于对肝纤维化临床表现,可归属与“胁”“肝着”“黄疸”等范畴[11]。肝炎肝纤维化病位虽在肝,但其病机转化及临床表现均与脾有关。吕教授阐明了肝炎后肝纤维化主要病因是湿热疫毒入侵和正气不足,病机关键是肝郁脾虚、湿热内阻挟瘀毒,反映了广东地区慢性乙型肝炎的证候特点。肝炎合并肝纤维化患者常出现肝气郁结及脾气虚弱的证候,表现为胁痛、情志抑郁、乏力、纳差、肢体困重。同时伴有湿热内阻的证候,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岭南地区气候炎热,多雨多湿;另一方面是脾失健运,湿滞中焦,郁而化热,临床上可见尿黄苔黄腻等症。
治疗上,吕教授自创新方保肝宁,方中用柴胡、枳壳、白芍疏肝解郁,黄芪增强益气健脾之功,黄芩、白背叶根清泄邪热,深得仲景“治肝补脾之要妙”。《灵枢·五邪》云:“邪在肝,则两胁中痛……恶血在内”,指出肝病可致瘀血。血瘀既是肝纤维化的病理产物也是加重肝纤维化的病因,配伍丹参、桃仁活血化瘀。全方配伍使用,肝郁得解则不至横逆犯脾伤胃,气机调畅血运正常不至血瘀[12],临床使用保肝宁方加减用药,疗效满意[13]。此外提出隐证型患者肝组织呈现出由轻微病变至肝硬化的系列肝病谱,同样存在治疗必要性的新观点,这一类患者人体免疫功能不全,呈低反应状态,临床上谷丙转氨酶长期轻度升高,HBsAg和HBV-DNA持续阳性者[14],但是这些患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不适症状,多是因为体检发现。但是可以辨病选药,根据肝炎后肝纤维化肝郁脾虚、湿热内阻挟瘀毒的病机特点,常用柴胡、郁金疏肝解郁,配以茵陈、白花蛇舌草、黄芩等清热解毒祛湿,并加四君子汤健脾益气,扶正祛邪。此外,使用自研方养肝降酶丸,疗效理想[15]。
2.3肝硬化 未经抗病毒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肝硬化年发生率为2%~10%[16],当纤维化患者病情进展,肝郁、脾虚迁延恶化,湿热瘀毒内阻严重,血热互结,患者可见黄疸,脾胃运化水谷失常而消瘦、肌肉软弱无力,脾虚水湿不运溢于肌肤出现全身浮肿,提示病情进展为肝硬化阶段。吕教授开展肝炎后肝硬化的优化治疗方案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对慢性乙肝的防治提出了执简驭繁,以内外辨病因,以虚实分证型,宏微结合,多法联用求治疗的新观点。西医常规疗法加促肝细胞生长素或干扰素治疗,能进一步稳定病情,防止复发[17]。肝硬化患者瘀血证较为严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血实宜决(破),气虚宜掣(导)引之。”《素问·离合真邪论》云:“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复其真气。”但化瘀易伤正气,补气又留邪,而肝硬化患者脾虚尤甚。
治疗上,吕教授善用化瘀方药,力倡缓攻其瘀的方法,配伍健脾补肾之品。精选鳖甲、桃仁、莪术、丹参、丹皮逐瘀血,峻药缓攻,在治疗瘀血证时,常配伍补气黄芪、山药、芡实、茯苓等健脾补肾药兼顾正气,防止伤正,厚朴、郁金行气提高疗效,肝硬化患者体质个体差异性大,所患疾病亦错综复杂,临床上可巧妙配伍使用清肝胆之热、温经散寒、养血、消痰、利水之药。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肝肝硬化的具有明显优势。
2.4肝癌及肝胆病晚期 在解决疑难、复杂、危重疾病方面,吕教授团队选择以肝癌作为重点防治病种,探索“肝炎、肝硬化、肝癌”发展进程及肝癌系统性治疗的有效手段。建立肝癌预防评价体系,区域内肝癌高发人群健康管理探索,开展亚健康干预及肝癌早期筛查,探讨肝癌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指标并研发肝癌早期诊断新方法,初步建立肝癌预防评价体系,获得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共识,拟向全国推广。同时对肝癌的不同类型,采取中西医结合方法,拟定肝癌术前、术后,结合化疗、放疗及保守治疗的不同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拟定相应方剂,取得较好临床疗效,提高区域肝癌诊治水平。传统的中医理论上并无肝癌的名称,但相似的症状体征,肝癌可归为积聚、癥瘕、膨胀、肝积等范畴[18]。肝癌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正虚邪实,气血、湿热、瘀毒搏结渐成积块。《难经·五十五难》云:“气之所积者曰积,气之所聚者曰聚,故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积者,阴气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始终,左右有所穷处。”《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肝癌患者虚实错杂,“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治疗上,肝癌患者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患者邪盛,临床上多见该类患者发病较为年轻,伴有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可口服靶向药物,进行化疗、或免疫治疗等西医系统性抗癌治疗后[19],同时进行中医药物治疗。此时,机体正气较盛,以破血化瘀消癥为主。中期当扶正祛邪,标本兼顾,攻多补少。而在晚期,以正虚为主,患者多为老年患者,或者经过多次的化疗、放疗等身体消瘦严重,此类患者治疗上不宜攻伐,治疗用药应当平和,化癥不伤气血,补益不碍消癥。肝癌的基本病变为瘀、毒、虚并存,不同时期、不同体质的患者,只是在扶正祛邪,攻补兼施的侧重点上稍有差异,临床上根据患者个体差异性,辨证论治,结合现代的抗癌方法,中西医结合,可使肝癌的疗效得以提高。
3 病案举例
余某某,男,71岁,初诊日期2017年11月17日。主诉:肝脏肿瘤微波消融治疗2日余。
初诊: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携带40余年,患者右胁隐痛一月余,伴有全身乏力,加重7 d,遂到当地医院门诊就诊,于2017-08-15行腹部磁共振示:肝右叶肝门部异常信号,考虑肝癌。无恶心、呕吐、无发热、无便血,查体:未见蜘蛛痣、肝掌、腹壁静脉曲张,未扪及腹部肿块,脾肋下未及。査乙肝两对半:HBsAg(+)、余项阴性。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遂到我院就诊,入院完善检查,上腹部增强CT示:①肝左右叶交界近肝门区原发性结节型肝癌;②双肾多发囊肿。于2017-08-21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于2017-11-15在超声引导下行肝脏肿瘤微波消融治疗,治疗后,患者要求口服中药治疗。遂到吕教授门诊就诊
诊查:证见头晕、乏力,口干,眠差,腹胀,食则胀甚,纳呆,消瘦,便秘尿赤,面色灰暗,舌暗红苔白,舌底脉瘀,脉弦。
中医诊断:肝积,证属肝脾失调,瘀阻脉络。
西医诊断:①原发性肝癌;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③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患者起病时由于肝气郁结,气滞血瘀,不通则疼,故有协疼,气不能行、脾运失健,加上年老,脾气虚弱,出现乏力症状。又经过化疗栓塞术、肿瘤微波消融等创伤损耗机体正气,头晕乏力、纳呆、消瘦,乃脾虚之证;瘀血导致新血不生,失于濡养,故患者形体消瘦,阴液干枯,不能滋润,故见口干,便秘。舌暗红苔白,舌底脉瘀,乃肝脉瘀阻之象。
治则:行气活血化瘀,佐以甘补。处方:鳖甲20 g,桃仁15 g,莪术10 g,白背叶根20 g,白花蛇舌草20 g,山慈姑15 g,猕猴桃根15 g,穿破石15 g,薏米20 g,白术10 g,茯苓10 g,丹皮15 g,党参15 g,郁金15 g,28剂,水煎服,日1剂。
二诊(2017年12月20日):患者症状有所缓解,仍有疲倦乏力,偶有口干口苦,纳一般,大便质较硬,面色灰暗,舌暗红苔白,舌底脉瘀,脉弦。在上方基础上,去穿破石,加炒莱菔子、鸡内金各10 g,何首乌、远志各15 g安神,火麻仁、郁李仁各10 g润肠通便,28剂,水煎服,日1剂。
三诊(2018年1月27日):服上述药后,患者头晕、乏力改善明显,大便质地软,睡眠良好。在上方基础上,加生地、麦冬、枸杞各15 g滋阴柔肝,14剂,水煎服,日1剂。
按语:肝癌患者多伴由感染慢性乙型肝炎病毒后发展而来,肝癌临床多见上腹肿块、右胁疼痛、食欲不振、全身消瘦,并可见腹水、便血等多种变证[20]。中医辨证治疗对于改善患者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有良好效果。患者起病时,以胁疼为主要症状,经过西医辅助检查,确诊为原发性肝细胞癌,又经过局部治疗,病情迁延,故中医可诊断为:肝积。脾之运化,有赖于肝之疏泄。肝中有瘀血,瘀血日久,脾不能运化水谷,新血不生,机体失于滋养。吕志平教授以行气活血化瘀消积,并配伍健补脾肾之品。患者无肝硬化、无静脉曲张,故治之首以鳖甲、桃仁、莪术活血,消积,并加以白术、党参、茯苓补脾以免后天之气伤甚,寓有“见肝之病,当先实脾”之意,使用郁金之类,疏肝理气,此后即大致以此方为基础,或加滋阴养肝之枸杞、桑葚、女贞子,加麦冬、玉竹、生地滋养肝胃之阴,或加枳壳、柴胡疏肝解郁,治疗上攻补兼施,“坚者攻之”“衰者补之”,但扶正、祛邪轻重有别,标本缓急不乱,在临床上疗效良好。
4 小结
本文初步探讨了吕教授中西医结合防治肝胆病的学术思想,并以西医对疾病病变发展不同阶段为切入点,阐述“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临床经验及诊疗特点。可以丰富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胆病的理论体系,为临床上中西医结合防治肝胆病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