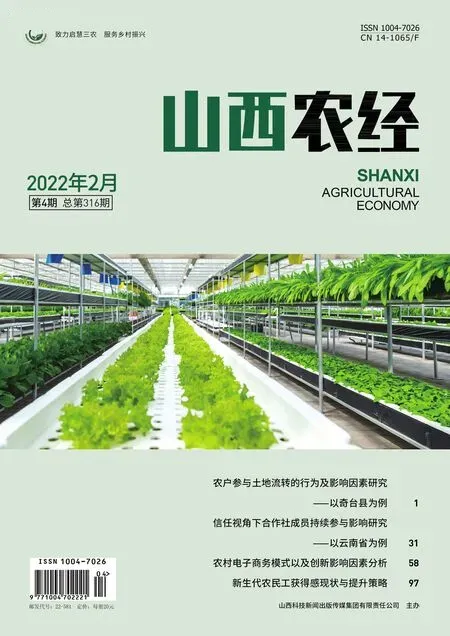多元共治理念下的乡村柔性治理路径分析
□陆伟同
(太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结合国家治理,并改变在治理层级中的“中央-地方-乡村”单向模式,体现“共治”理念。
1 多元共治与乡村柔性治理的概念
1.1 多元共治
“共治”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尹文子》:“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在《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代的共治思想需要在治理方式上做到“兼听则明”,在治理过程中“民贵君轻”,强调的是一种朴素的政治统治处理方式。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共治”一词出现在党的重要会议和报告当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推进社会当中的治理创新,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1]。在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数次提到,比如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提到的“共治和共享”。国内学者侧重从多元化的角度理解,王名等(2014)[2]认为,“多元共治包括以下特征:多元主体,开放、复杂的共治系统,是一种小政府、强政府、大社会共同治理模式”。江必新(2019)[3]认为,“多元共治不仅是治理主体的多元,还是共治方式的多元,多元共治还意味着治理体制和结构的多元”。综合以上观点,本文所述多元共治,指的是在治理的过程中,基于共同一致的目标,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方参与治理进程,采用多种治理方式,最终实现共同利益的一种治理新方式。
1.2 乡村柔性治理
在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城镇化治理表述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柔性化治理”[4]。在国内的研究中,乡村柔性治理与乡村软治理的命题一致,刘祖云和孔德斌(2013)[5]首先提出“乡村中的软治理”的概念,将“乡村中的软治理”看作共同协商平台下的软法治理手段。曹召胜(2018)[6]则将“柔治从力治中分离”,将柔性治理和农村中的多元性的治理技术相结合。胡卫卫等(2019)[7]侧重分析了柔性治理的概念、权力路径、技术构成,认为“权力、话语和技术构成了乡村柔性治理的基本概念体系和逻辑主线”。本文认为乡村柔性治理是一种多元共治模式,体现了在乡村治理层面的国家、社会和村民的互动影响,强调“以人为本”,运用多元化的治理方式,达到乡村治理秩序的平衡,最终实现乡村善治。
2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现状
2.1 治理体系现代化下的乡村治理滞后化
现行乡村治理不同于原有的单一维度治理格局,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个人”多个层面的参与主体,但是乡村治理处于最基层的一环受到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影响,乡村中主要表现为治理体制在“乡政村治”格局中的乡镇管理和村委之间的行政体制性矛盾;治理主体在“村民自治”格局中出现的村两委和村级组织之间的内部管理矛盾,乡村治理的矛盾说明了在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滞后性,使得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和过程环节不能适应乡村的现实改变,阻碍了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
2.2 治理观念多样化下的文化价值同化
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接受了大量外来文化价值的侵袭,乡村治理观念随之呈现出时代化的特征。在乡村价值的塑造过程中,随着政策性的推行,大量乡村向着同质化的方向发展,乡村呈现出千村一面、万村一貌,维系着原有的乡村情感基调的传统文化引领被不断同化。同时,乡村文化价值代际化传承随着乡村“空巢化”的现象难以为继,乡村中的共鸣化理念逐渐消失,文化对乡村建设的积极作用被削弱。
2.3 治理空间缩小下的乡村治理“空心化”
乡村治理空间随着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影响而呈现出“空心化”现实特征。一方面,这些现实情况源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进一步同化,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动增加了治理过程中的“空心化”现象;另一方面,自然村以及乡镇之间的合并速度加快,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相对封闭的边界环境,使得治理空间向社区化方向发展,乡村治理难度加大。
3 多元共治与乡村柔性治理的耦合作用
3.1 共治主体多元化下的乡村柔性参与主体
多元共治就是坚持多个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柔性治理强调治理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回应性、自愿性和共治性,而非单一性、命令性和管控性的治理方式。乡村柔性治理源于乡村治理的推进以及“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形成,使得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制度层面的落实和保障。在政治生活中,农民成为主体,当前的农村社会秩序发生明显变化,国家和农村社会的关系不再是单方面的强制嵌入,更多地表现出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互为条件和相互影响的关系[8]”。乡村治理形成了“国家-农民”这种简约化治理模式,通过外部权力嵌入将国家治理的权力授予全部参与治理的主体即农民,《村民自治法》的实施使得村民的参与有了合法的基础,村民在这种条件下,内生整合式的柔性参与治理机制就成为了乡村治理的必要。所有村民能合法、合理参与平台,形成了主体多元参与治理的乡村治理模式。
3.2 共治方式多样化下的乡村文化柔性治理
多元共治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多元性的特征,在体现“人民观”的基础上,在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同时避免多元机制下的“多数人的暴政”,“多中心理论”的提出者奥斯特罗姆提出“多层级系统内”[9],需要结合自治权的相对下放。这种共治是通过对话、竞争、妥协与合作等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得到实现,并且实现了每个参与者的意见从分歧到一致的过程。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结构,在费孝通先生的“人际关系网络化”[10]情景之下,农村中形成了由熟人联接的网络。这就是乡村中的熟悉化格局,乡村治理形成杜赞奇所提出的“权力文化网络”,即“文化网络构成地方社会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11],在这种乡村情感文化氛围中,伦理、价值、乡俗、民约等乡村文化价值体现出了在乡村治理当中的“软约束”,深入挖掘治理理念中人本核心理念所体现出的包容、关怀、温暖、情感、灵活的一面,最终实现在多元共治下的柔性价值治理。
3.3 共治空间网格化下的乡村治理边界柔化
多元共治并非多元参与下的自治权限最大化,而是改变了单一治理决策模式,由原来的线性治理方式以及沟通决策模式,转变为多个主体的互动式交流。在治理的进程中,所有治理个体处于一个公共的领域之下,参与治理的环境实现了治理空间的网格化。
乡村柔性化治理则集中体现在这种网格化空间下所体现出的治理“边界柔化”特点,城乡边界虚化,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边界柔化就体现了城乡空间治理中的“城乡边界柔化”,即城乡融合、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治理。城乡融合体现在空间治理层面上需要将治理地域纳入到全社会治理的共同方式中,破除城乡二元壁垒和乡村原本的角色认知,实现共治理念下的区域性共治。
3.4 共治系统多层化下的乡村柔性高效治理
在多元共治的多层级系统中,打破了原有乡村治理的单一诉求表达方式,通过多元化的主体自由参与、多样化的协商机制以及网格化的平等对话方式,形成了村庄当中的公共开放治理领域。多元共治通过开放的公共治理系统方式,在系统内外不断吸纳各种高效治理机制。一方面,在以公共性为基础的引领下,在治理过程中,通过自由对话、公开竞争、协商合作的机制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在以开放性为前提的指导下,通过乡村中的集体决策、集体行动,改变了原有的村庄强权、村庄资源配置垄断的方式,形成了村庄共同利益体,以这样的方式实现村庄高效柔性治理。
4 多元共治下的乡村柔性治理路径
4.1 多元包容:理性自治
乡村柔性治理的实现,是要将外部性的嵌入和自身内部的所有资源进行整合,以便于实现乡村中的治理多元化。首先,需要充分发挥外部嵌入机制,实行乡村理性自治,激发乡村自治的活力。村民自治要实现多元包容,不能局限在有限的民主选举层面,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完善“党治+自治”的领导自治,加强村民小组组织,建立“村小组+自治”合作自治,加强其他群众性组织作用,建立“妇联+自治”“经济合作社+自治”等形式的协同共治机制,实现自治权限多元化、自治群体微型化,形成“党小组、村小组、村委会、村社组织、村民个人”广泛参与的农村基层治理新格局。其次,充分发挥乡村内生的建设力量,注重发挥乡村内生力量,内生于乡土社会当中的“新乡贤”群体能够有效弥补现有乡村治理下出现的农村治理人才“空心化”和乡村治理“碎片化”的困境,探索“村两委+乡贤理事会”的新治理模式,在治理的进程中,“村两委与新乡贤组织应是“主”与“辅”“断”与“谋”的关系”[12],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充分挖掘出曾经有乡村情结、有乡土情怀、有奉献精神的乡贤参与到乡村内部治理中,发挥知识治村、技术治村和模范治村的作用,促进基础性权力的强化。
乡村治理要实现理性自治,多元自治不是否定村民自治,而是要回归自治本质,提升自治能力,拓宽自治层面。在发挥党在村民自治中的利益整合功能的同时,要加强在乡村治理中乡村利益整合机制,注重国家各个层级之间、各级机构之间、各个自治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充分发挥每一次治理主体的自治作用。结合当前乡村治理中的主要矛盾需求,充分鼓励农民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自治的方式和方法,开展“群策群力”的群治方式,突出村民自治的自主性,实现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4.2 文化塑造:道德引领
乡村治理要着重文化重塑,乡村的产生伴随着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作为一种稳定的、有特色的、深层次的和不易改变的记忆象征,乡村文化认同体现的是一种“社会中的软治理”理念,侧重于从“每个人的心灵出发”[13],心灵的共性价值以及人们的乡村文化规约维持着乡村中的基本行为。因此,乡村中柔性治理的基础依托于乡村,并且形成村庄中的文化认同,体现出的“村庄是一个共同体,它不仅是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共同体,更是一个有着共同规范并承担众多公共事务的功能性共同体”。
在文化价值契合下要注重道德引领,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宗族观和家族观为单位所建构起来的道德体系,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家长制、宗祠制、会首制”等为主的乡村权威结构和“血亲制、婚姻观、继承观等”为主的乡村伦理规范以及“邻里观、孝义观、诚信观”为主的乡村行为准则,维系起了村民对村庄共体的认同感。乡村治理培育乡村认同感,用道德引领村民,弘扬“崇德向善”的风俗,开展良好家风、乡风建设,培育淳朴民风。评选农村道德模范,弘扬道德新风,传承传播优良家训,培育新型乡村治理模式。
4.3 “力”“柔”结合:法治重构
乡村治理要实现多元共治下的“力治”,随着“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14],并伴随着“共治”理念的提出,乡村治理需要遵循“自治为本、德治为基”的前提,理顺村民自治过程中组织要素、制度要义和规则框架。将乡村治理限定在一定的村庄治理共同体范围之内,推行国家有关乡村治理的文件和规范,推行《村民自治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范对乡村治理的约束性作用,使乡村治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各级治理主体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有序地开展各种治理活动。规范在乡村中的小微权力,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地执政。
在“力治”的同时,结合“柔治”,建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乡村矛盾调解体系,处理有乡村特色的“软法”与国家法治之间的矛盾,根据乡村治理特色,建立适应乡村本色的“红白喜事会”“村务监督小组”“村民调解员”等制度,维护法律的权威,增强村治过程中的法律信仰。
5 结束语
乡村柔性治理符合多元共治的特征和规范,在多元化的主体和多样化的方式层面,乡村柔性治理将在硬性的制度规范“力治”角度下,将平等互利、合作共治、利益共赢的乡村自身的认同感聚合起来,用理性自主自治、人文价值关怀和法治外部规范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管理乡村治理领域。柔性治理要体现出治理本质,结合治理体系要求,最终实现在乡村治理当中参与主体的话语主导权和政治意愿表达权,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