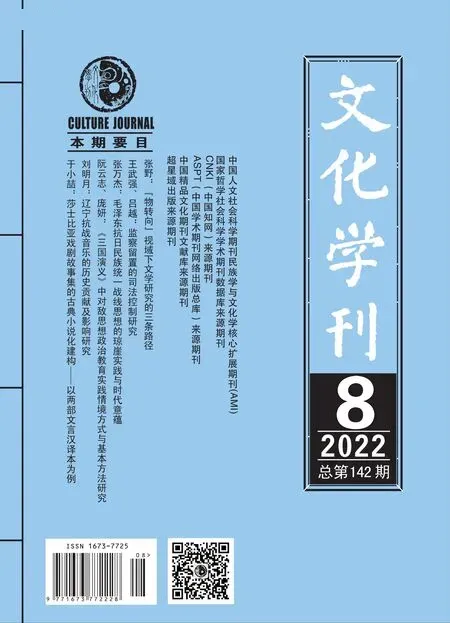山东金代碑刻整理指瑕举例
刘赛飞
自宋代起,便有学者开始了对金石文献的整理,如赵明诚的《金石录》、欧阳修的《集古录》、洪适的《隶释》及《隶续》等。到清代时,在乾嘉考据学的兴盛背景之下,学者们掀起了对金石学研究的热潮,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以著录为主的金石学专著。例如,王昶的《金石萃编》、阮元的《山左金石志》、张金吾的《金文最》、罗振玉的《山左冢墓遗文》、段松苓的《益都金石记》、孙葆田的《山东通志》、吴式芬的《金石汇目分编》,等等。尤其是各省编修的地方志,不仅在《艺文志》中收录当地碑刻,有的还设《金石》《碑碣》《墓志》等类目专门著录。清代金石学家还注重实地考察,以原碑、拓本为依据,整理碑文时并附跋语考证,真实性高,且颇具史料价值,为后世查阅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现代出版的金石学专著亦数量众多,如王新英的《金代石刻辑校》和《全金石刻文辑校》、阎凤梧的《全辽金文》、唐圭章的《全金元词》等。无论地方志,还是古今金石学著作,都对山东金代碑刻的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民国以前各类汇集山东金代碑刻的著作中,金石学家所录碑文多考证严谨,讹误较少,方志录文则缺乏考证,错字、漏字较多,近年出版的金石学著作亦多不注重实地考察,常摘取另一书录文直接整理,同样缺乏考证,因此,常出现碑刻存地记载及文字辨识错误等问题,如《全金石刻文辑校》。依照原碑或拓本校对金石著作录文可以提升碑文本准确性,同时能正方志讹误,现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所收录碑刻拓本为例,对七则山东金代碑刻录文予以校对。
一、所选碑刻简介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收录多种山东金碑拓本,但有部分残损、磨泐,而《满庭芳词并跋》《郑公墓志》《塔河院碑》《天封寺记》《博州庙学记》《蒙山祈雨记碑》《兴国寺碑》七种拓本尚为清晰,能够为我们提供较准确的碑文信息。故以此为例,对碑文进行校正。《满庭芳词并跋》,大定二十八年(1188)立石,属道家碑刻,现存山东潍坊,碑文见于陈垣的《道家金石略》、唐圭章的《全金元词》、王新英的《全金石刻文辑校》中,具体存地玉清宫;《郑公墓志》,大安二年(1210)立石,现存山东青州,但拓本记载此碑现存山东寿光,故碑具体存地有待实地考察,碑文见于清段松苓的《益都金石记》、清阮元的《山左金石志》、清张金吾的《金文最》、罗振玉的《山左冢墓遗文》及王新英的《全金石刻文辑校》中,其中,《山左金石志》未辑碑正文,《全金石刻文辑校》录文讹阙较多;《塔河院碑》,大定二十一年(1181)立石,现存山东临沂,碑文见于光绪《费县志》。拓本记载:“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闰三月二十二日刻。碑在山东费县。拓本高度为184厘米,宽度为76厘米。正书。碑两截刻,上刻二十年十月公据,下刻记。此本为陆和九旧藏清光绪年间拓本。”[1]150碑额题“圣旨存留塔河院额”八字;《天封寺记》,大定二十四年(1184)立石,现存山东泰安,碑文见于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张金吾的《金文最》及王新英的《全金石刻文辑校》;《博州庙学记》,大定二十一年(1181)立石,现存山东聊城,碑文见于阮元的《山左金石志》、宣统《聊城县志》、清王昶的《金石萃编》、张金吾的《金文最》、王新英的《全金石刻文辑校》中,其中,《金文最》仅收录碑阴,宣统《聊城县志》不录正文,仅存目;《蒙山祈雨记碑》,承安五年(1200)立石,现存山东临沂,碑文见于光绪《费县志》;《兴国寺碑》,大定五年(1165)立石,现存山东滕州,碑文见于王新英的《全金石刻文辑校》。
二、碑刻录文校正
(一)《满庭芳词并跋》
对于《满庭芳词并跋》现存地,各书记载有异。《道家金石略》记载碑现存山东潍县玉清宫,《全金元词》第390页也注明这首词“有石刻在潍县玉清宫”[2]390,然而《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记载此碑现存山东潍县昆嵛山[1]190,昆嵛山在今山东烟台境内,因此,确认拓本记载有误。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辑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记载《满庭芳词并跋》“在山东潍坊昆仑山”[3]312,该文据拓本录文,所以应该和《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一样描述错误。有关《满庭芳词并跋》录文,唐圭章《全金元词》引文不确,其部分原文如下:
“全性命,紫书来诏,直赴大罗宫。”[2]390
“来诏”二字,在陈垣《道家金石略》和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辑校》中皆作“诏去”,拓本作“诏去”,是。《全金元词》引文错误。
(二)《郑公墓志》
第一,正文第二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因遭宋季兵火,携家西来”[3]499,《益都金石记》作“因遭宋季兵火,挈家西来”[4]14864,“携”字原作“挈”,今据《益都金石记》及拓本改。
第二,正文第六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不幸夫殁守义□有二子三女”[3]499,《金文最》作“不幸夫殁守义。而有二子三女”[5]1273,阙字原作“而”,今据《金文最》及拓本补。
第三,正文第八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尚勤俭训子”,《益都金石记》作“尚勤家训子”,“俭”字原作“家”,今据《益都金石记》及拓本改。
第四,正文第十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尔之祖父母,我之姑舅”[3]499,《益都金石记》作“尔之祖父母,我之舅姑”[4]14864,《全金石刻文辑校》“姑舅”二字互倒,今据《益都金石记》及拓本正,《益都金石记》及拓本作“舅姑”,是。
第五,正文第十二行,按:“我祖我父率□□土未能□卜敬从母命”[5]1273。《全金石刻文辑校》作“我祖我父□□□□未□□。敬从母命”[3]499-500,《金文最》作“我祖我父率□□土未能□卜敬从母命”[5]1273,补“率”“土”“卜”三字,拓本磨泐难辨,对照其他行字数,“父”到“未”缺四字,“未”到“敬”缺三字,参照《金文最》改。
第六,正文第十三行,按:“择其良师卜其□□□安厝之”[5]1273。《全金石刻文辑校》作“择其良师卜□□□□□安厝之”[3]500,缺五字,《益都金石记》作“择其良师卜□□□□安厝之”[4]14864,缺四字,《金文最》作“择其良师卜其□□□安厝之”[5]1273,补两字,拓本磨泐难辨,辨“择”到“安”间缺八字,故参照《金文最》改。
第七,正文第十三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岁次庚午立□四月十有三日”[3]500,“有”字原脱,今据拓本补。
第八,正文第十四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命工刻石于灵侧”[3]500,《金文最》在“石”字之后多一“□”,辨拓本疑“石”与“于”间缺两字,亦不缺,此处难以确定。
(三)《塔河院碑》
第一,上层碑文第四行,光绪《费县志》作“大含乎元气下缺河院建立已来”[6]369,“院”下拓本有“者”字,当据补。
第二,上层碑文第五行,光绪《费县志》作“天德一年”,误,若第一年,当写作“元年”。“天德一年”当依拓本作“天德二年(1150)”。
第三,上层碑文第六行,光绪《费县志》作“大垂戒沙门善明上足法门嗣下缺住持以迄与今此者特奉”[6]369,“门”字拓本无,当系衍文;“嗣”下拓本疑有“行”字,当据补;“奉”字当依拓本作“遇”。
第四,上层碑文第八行,光绪《费县志》作“圣朝崇奉真风,阐扬要道”[6]369,“扬”下拓本有“佛”字,当据补;“道”字当依拓本作“遂”。
第五,上层碑文第十一行,光绪《费县志》作“遂使双林之道愈光下缺广智道”[6]369,“光”下拓本有“之流浸”三字,当据补。
第六,上层碑文第十二行,光绪《费县志》作“时下缺一年太岁辛丑閏三月丁丑朔二十二日戊戍”[6]369,“时”下拓本疑有“大定二十”四字,当据补。且结合原碑文“大定二十年(1180)十月日给”[6]369,则大定二十一年(1181)立石应合理。
(四)《天封寺记》
第一,《全金石刻文辑校》作“承直郎、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云骑尉、赐绯鱼袋党怀英撰并书”[3]274,“书”下拓本有“篆”字,当据补。
第二,正文第九行,“落成□明年”,按:阙字当作“于”字。阙处拓本完全磨泐不能辨,《全金石刻文辑校》不录此字,《金文最》作“于”,结合上下文,“于”字合理。
(五)《博州庙学记》
第一,关于《博州庙学记》碑刻尺寸,《山左金石志》与《金石萃编》记载差异较大,《山左金石志》云“碑高七尺七寸,广三尺二寸”[7]14682,《金石萃编》云“碑高八尺五分,广四尺二寸”[8]2879,因未查看原碑,故此处存疑。
第二,碑阳第二行,拓本作“乃修六经以诒后人”[1]152,《全金石刻文辑校》“诒”原作“诏”,今据拓本改。
第三,碑阳第四行,拓本作“莫不敦尚经术、开设学校为先务”[1]152,《全金石刻文辑校》“不”下原有“以”字,今据拓本及《金石萃编》删。
第四,碑阳第十六行,“从祀画像之广”中“广”字,拓本模糊,疑有四点,应为“广”,《全金石刻文辑校》原作“院”,今据拓本改。
第五,碑阳第十九行,拓本作“岁贡士与内州等”[1]152,《全金石刻文辑校》“岁”字原脱,今据拓本补。
(六)《蒙山祈雨记碑》
第一,碑额题“蒙山祈雨記”五字,下方“白云嵓洞主白云居士皇希永撰并书篆额”[1]54十七字在光绪《费县志》中原未收录,今据拓本补。
第二,正文第一行,光绪《费县志》作“巍然敦犬”,“犬”字拓本作“大”,是。
第三,正文第二行,按:阙处当作“相”字。光绪《费县志》原作“东浮云气(接于蓬莱”[6]372,拓本所示阙字疑为左右结构,左木右目,类“相”,将“相”字填入句中,“相接”亦合文意。
第四,正文第二、三行,按:阙处当作“南”字。光绪《费县志》原作“东浮云气(接于蓬莱,西根连于三宮空洞之天(隶衡岳为佐命,北重艮坎为蒙卦”[6]372,据拓本“天”字之后疑为“南”或“西”字,结合该段文字,东西南北恰缺一南,故此阙字应为“南”。
第五,正文第八行,光绪《费县志》“千”字原作“干”,今据拓本改。但不排除此处为印刷错误。
第六,正文第十三行,光绪《费县志》“灯”字原作“烛”,今据拓本改。
第七,正文第十三行,光绪《费县志》“之上”二字原脱,今据拓本补。
第八,正文第十四行,“旱乾”二字光绪《费县志》作“乾旱”,当据拓本。
第九,正文第十四行,光绪《费县志》“村”字原脱,今据拓本补。
第十,正文第十四、十五行,光绪《费县志》“众村”二字原脱,今据拓本补。
第十一,正文第十六行,光绪《费县志》“龜”字原作“蒙”,今据拓本改。
第十二,正文第十九行,光绪《费县志》作“刊二銘”,“诸”字原脱,今据拓本补。
此外,光绪《费县志》载此碑文“后有题名二行”,但未录题名内容,兹据拓本补题名如下:
“□□村纠首杨政,妻张氏,张氏,张氏,男杨珪,新妇张氏,男乡贡进士杨□□,新妇栢氏,男杨,新妇玉氏。维首杨震,妻赵氏,乡贡进士杨□□,妻管氏,妻李氏,进义副尉靳□□□□□李策。蒙阳魏绪,杜真,杜成,刊。”[1]54
(七)《兴国寺碑》
第一,正文第二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示生贤□之师”,拓本阙处作“智”,是。
第二,正文第三行,《全金石刻文辑校》原作“□未达真理”,按:阙处当作“纵”字。拓本阙处疑“纵”,“纵”有“纵然、纵使”之意,合句意。
第三,正文第六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在今滕邑之古二十五里”[3]125,“古”字当依拓本作“有”。
第四,正文第七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或碑志存□□□□休相□数里”[3]125,“相”下拓本有“望”字,当据补。
第五,正文第八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村之正中□□寺庙”[3]125,拓本作“村之正中□置寺庙”[1]83,今据拓本补。
第六,正文第九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因存留为大圣□”[3]125,阙处当依拓本作“院”。
第七,正文第十三行,“郡”字《全金石刻文辑校》原作“乡”,今据拓本改。
第八,正文第十五行,“共”字《全金石刻文辑校》原作“为”,今据拓本改。
第九,正文第十五行,“修进”二字《全金石刻文辑校》作“进修”,当据拓本。
第十,正文第十七行,《全金石刻文辑校》作“□而遭遇恩诏”,拓本阙处作“既”,是。
三、结语
以上对七则山东金代碑文的校补皆以拓片为依据,基本上对有关著作录文讹误之处都能准确更正。此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尚有许多山东金代碑刻拓本,藉此可对勘更多相关碑文。总的来说,前人已在山东金代碑刻整理及考证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这就为我们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继续深入对山东金代碑刻的篇目整理和文字释读工作提供了方便。同时,通过对更多山东金代碑刻的整理研究,也可以继续展开对《金史》、山东省地方志等史志及相关古籍的校补工作,深入发掘山东金代碑刻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