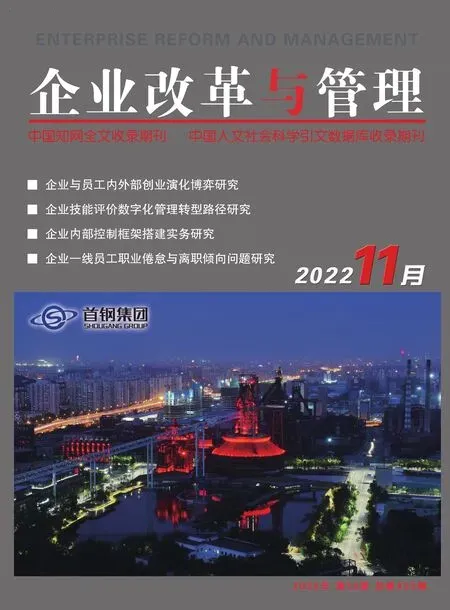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
张 俊 杨迎亚
(1.中共六安市委党校,安徽 六安 237000;2.安阳工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可以说,数字经济不仅是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现有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助于提高学者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学者们主要从概念、涵义、量化、属性、现实表现以及理论研究等方面对数字经济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全面、清晰地认识数字经济。陈晓红等(2022)在对梳理归纳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科学问题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数字经济的基本规律或属性,例如,核心理论、基本概念、内涵、典型特征等;刘军等(2020)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2015-2018年我国各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则在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搭建数字经济的规模核算框架,并核算2007-2017年我国整体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
另一类是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等其他研究对象的影响。例如,王宁和胡乐明(2022)指出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能带来改善收入分配的“数字红利”,也会带来恶化收入分配的“数字鸿沟”;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多是从理论或实证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其影响的内在逻辑、作用机制以及实现路径等。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采用“微观—宏观”的研究视角,剖析了该影响的内在逻辑,并指出发展数字经济能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颁布相应政策的落地实施提供大力支持;赵涛等(2020)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此外,这种作用效果具有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即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就“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这一热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鲜有学者分析该影响的具体特征。本文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恰当的指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分别测算2011-2020年省域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基于异质性视角,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效应,期望为后续研究与政策制定提供些许实证支持。
二、研究基础假设
1.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具有降成本、融合性强、覆盖性广、信息共享以及颠覆性创新等新型特征。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解决传统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不均衡、时空限制以及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并且数字技术的普遍使用能有效地提升社会生产力,缩小收入差距。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数字经济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能有效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提升区域间经济活动的关联度,拓宽其深度与广度,实现经济跨区域协同发展,进而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国内外均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互联网对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例如,我国学者张俊英等(2019)立足我国实际,发现互联网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溢出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3.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
我国地域广阔,各省份在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也会因此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而不同发展水平的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对这一情况进行深入讨论,并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1.计量模型设定
建立如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同时,本文引入此数字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其他控制变量集的交互项以验证假设“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省份、年份,Ehqi,t、Digi,t分别表示省份i在t年的经济高质量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表示控制变量集合,、、分别表示省份、时间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扰动项;λ、W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权重矩阵,、分别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空间交互项的弹性系数。
2.变量测度与指标说明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暂无统一标准,本文参考魏修建等(2020)、黄群慧等(2019)做法,选取合适的衡量指标,构建省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同时,在参考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财政分权(gov)、基础设施(tra)、人均劳动生产率(lf)、人力资本(edu)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qy)等可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的变量作为其他控制变量。
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选取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本文所用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全文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经网数据库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表1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分析
表2为基准回归结果。实证表明,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证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省域经济发展质量,即假设1成立。此外,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2)至(6)中,财政分权程度不利于地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对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越大,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财政分权会制约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进而抑制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刘成奎和王玉琴,2022)。交通基础设施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有效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人均劳动生产率为负,但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2.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为验证假设2,先对两变量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再采用莫兰指数法计算两变量在各类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效应,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两变量的莫兰指数均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各省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样本期内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即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表3 空间相关性检验
建立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模型的结果保持一致。此外,数字经济的空间交互项系数为正,且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表明其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邻近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即假设2成立(赵涛等,2020)。

表4 空间效应回归结果
3.异质性检验
为检验假设3,将样本分为东部、中西部区域。表5为异质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两区域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优于中西部地区,有利于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促进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证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即假设3成立。

表5 异质性检验
五、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选取合适的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各省域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建立相应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且能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对其他地区产生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东部、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即区域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