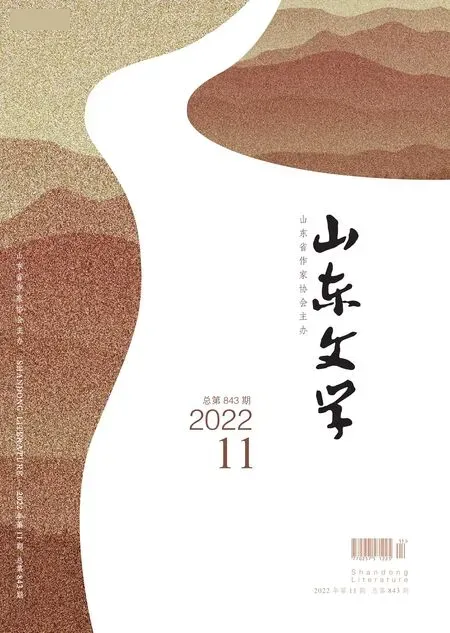寿光往事
孙鹏飞
堤里村
第一次撒谎是六岁半。
村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去了乡里,唯独他,当天就让老师赶回来了。
他跟爸爸说:“打架,因为打架。”
爸爸是个头脑单纯的屠夫,在太阳底下的堤里村,亲手结果了无数头黑猪的生命。爸爸扯着围裙擦额角亮晶晶的汗,擦完看看脑袋冒着青茬的儿子,照例问他:“那你打输了打赢了?”捆着的四蹄倒挂的黑猪,突然桀骜不驯地嗷嗷叫。
他说:“当然是打赢了。”
猪两只眼睛充血,奋力挣扎。爸爸咬紧牙口,一刀捅向猪的肚子。
他蹲着看了会儿,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偶尔问一两句讨爸爸喜欢的话。“爸爸呀,猪到了你手里,为什么都这么听话?”
爸爸络腮胡子,矮个子,浑身黝黑、通亮,裹挟着一身的戾气。周边孩童看见了他爸爸,吓得直哭。
爸爸也试探着问他:“跟我学杀猪?”
他若是当真点头说好,爸爸便抡圆了膀子,一巴掌扇到他肉乎乎的嘴脸上。爸爸得说他没出息。所以,他得拼命摇头,他还得急得跺脚,他说:“我才不要呢,又累又脏。我以后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爸爸朗声大笑,跟邻里搭话,“你看看这崽子,倒是有出息呀!嫌他老子的工作脏,不知道老子一天一沓子钞票挣得容易。”
邻里也会讨喜,观摩着这孩子,说给他爸爸听,“眉眼间都是一副官相,局长的料。”
到了下午,他面对幼儿园的李玉萍老师,没了机灵劲儿。
李玉萍安排几个圆头圆脸的娃娃,去乡里学广播操,赶上六一儿童节,乡里派得上用场。他因为不守纪律,让带头的老师用教鞭打了脑门,咣咣咣,打得他那叫一个清脆爽亮。打完,老师说,“你下午不用来了。”
所以,李玉萍老师揪着他问:“为啥打你,不打别人,为啥把你赶回来了,不把别人赶回来?”他均答不上来。见问住了他,李玉萍囔着嗓子说了句,“三脚踢不出个屁。”
李玉萍全然不知,他眉眼官相,是干局长的料。背着无知的李玉萍,他放了个响屁。此后的很多年,他都在一些场合,绘声绘色地描述童年时代打架的场面。当然,第一架,是六岁半的小脑袋里想出来的。是拿来骗他爸爸的。爸爸由头到尾听完,竟然听不出任何破绽。
他姥姥家在乡里。他在乡里有个玩伴,叫国子平。模样同他一模一样。赶上赶集,国子平妈妈还抱错过他几次。后来,又听姥姥说起,原来国子平的妈妈,要嫁给他爸爸来着。只是介意他爸爸是个杀猪佬。终于在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下午,同杀猪佬讲清楚利弊关系,自此情尽缘清。
杀猪佬从不提这段往事,但是杀猪佬有意无意引导着孩子,一定得比那个国子平强。杀猪佬说,“你得比他强一百倍,强一万倍。对了,你能不能打过他?”
孩子望着身高、模样同样周正的国子平,猛点头。
“那好,国子平,你敢不敢跟我儿子打一架?”杀猪佬吆喝道。
国子平蹲下系鞋带,头使劲往上探着说,“我当然敢,你得等我系好鞋带吧。”国子平系好了鞋带,像老鹰抓小鸡似的铺展开两臂,双目放出酷似猎食的光芒。
待国子平逼近,孩子蹦蹦跳跳,学着电视里打拳击的步伐,一路倒退着跳。国子平看不明白了,只看着好玩,也学着他的模样,蹩脚地跳恰恰舞。俩孩子你来我往在地球上玩了一下午跳跳床,只有杀猪佬看得分明,孩子是有心让着国子平,孩子几次三番闯到了国子平眼皮子底下,只要挥挥拳头,什么都解决了。一再为孩子本性善良扼腕叹息。
对于没有技术性的打倒对方,杀猪佬当然耿耿于怀。“打赢了,我看看国子平妈妈怎么说,承认不承认我儿子强,呔,就是血性。”孩子便活络着一张小嘴,在这张嘴里,六岁半的他打架了,而且是狠狠揍了国子平一顿。
“你打得多狠呢?”爸爸乜眼瞅他。
“打破了头。对,我把他围在了墙角,一拳打得他东倒西歪,接着又一拳。”孩子拳击手的姿态,大跳着比画。
“那你们老师没有管?不得了,你这是到乡里打人。”
“老师也不敢管。那时谁敢管?我把他堵在墙角,一拳,又这样一拳。他求饶,我说晚了,直到把他揍趴下,揍得起不来。”
“妈妈的,你真狠。”爸爸听到兴处下死手拍腿,浓郁的腿毛在阳光中战栗。待腿毛波浪平静,爸爸追问一句,“那国子平起不来了?”
“你说他敢起来吗?”
“不敢,他起来,你还不是接着揍他?当他傻呀。没那么傻。对了儿子,你说,他破了头,你还没说呢,到底怎么破的头?”
儿子挠挠鬓角,摸摸耳朵,转转眼珠子,也不蹦也不跳,忽然大吸一口气,瞪圆了眼睛。他说:“爸爸呀,他是一下子躺地上的,磕破了头呗。”
胡营乡
孩子身上不胖,从胯骨往上能一根根数清肋骨。胸骨、锁骨一律凹陷,称得上瘦骨嶙峋,唯独一张大头肉脸迷惑别人。有一年夏天,孩子穿着背心到乡里买馒头,让姥姥家一个村民揪住,说你这也不胖啊。村民一把掀了他背心,一看,啥都明白了。自此,乡里传开了,一张大脸,干柴禾身子。有感性的逢年过节,堵上姥姥家的门,把闺女、女婿、孩子一并堵住,大嗓门喊,你这一年到头杀猪也不行,你们家没钱,你看看孩子瘦的。
到底是灭了杀猪佬的威风。杀猪佬走街串巷,再不散布自己挣大发了的谣言。知情的国子平妈妈才算心里踏实。
但是还有一个事,孩子压国子平一头,就是功课。
孩子九岁在屯里上学,同班同学皆八岁,小的七岁,个别的六岁。独他,九岁,智商超群。
第一年摸底考试,语文、数学双百。他怀抱着奖状一路小跑,到了堤里村的界限,弯腰使劲喘气。就是借着喘息的工夫,冬风一吹,奖状脱离了孩子皲了的双手,流向村口的蔬菜市场。有大老粗一脚踩住,看着字样,艰难地辨认一阵,逐字逐句说,了不得,全乡第一。
这股风也传到了乡里。在窗户前做针线活的国子平妈妈也知道了,杀猪佬的儿子全乡第一。
到了三年级,孩子不管是学习上、体育上,均不再占优势。他自己分析原因是同班同学身高、智力已经长开了。五年级的春节,班里下发了十八张奖状,孩子一张都没有得到。那个西北风呼啸的下午,孩子假装失手打碎了班里一块玻璃。老师揪住他耳朵训了一阵,训够了,勒令孩子回家,把玻璃钱带来。
杀猪佬的一张大脸是皲裂的,像菩提根、象牙果盘玩开了片,像窑烧的冰裂纹杯盏、茶洗,军大衣的领子高高竖着,在西北风中养成的职业习惯是紧缩着脖子,本来身子不高,再缩脖子,便时时刻刻矮人一等。杀猪佬灌了口冻透了的茶水,问他儿子:“奎文啊,你跟爸说实在话,你考得咋样?”
“第一名。”孩子给自己竖大拇指。
“那你这,连个奖状都没有?”
“我去老师办公室谈的,我说今年别给我发奖状了,我要学习用品。我见他桌子上摆着盖了大红章的学习本,就说要这个。”
“那你的学习用品呢?”
“年后发。”
“我问你老师去。”
“问去吧。”
杀猪佬早已信不过孩子的解释,打听了孩子几个同学,得知今年下发了十八张奖状。又问,“那你班里发了多少奖状?”
“十八张。”
杀猪佬瞅着风平浪静的集市,咬咬后槽牙,握紧起了厚茧的手指,随后摊开短粗的巴掌,随后再一次握紧,这一次手里多了一把剔骨刀。冷飕飕,银灿灿,滴答着殷红的猪血。“嘿哈——”他一脚踢翻了肉案子,把尖刀逼向了儿子。“我要你一句实话,你为啥没发到奖状。”
“我把班里的玻璃打碎了,因为这个,老师对我意见很大,把奖状撤了。”孩子双手抄兜,眉目倒是清澈。
漫长的暑假计划泡汤,孩子转眼间就要只身闯荡胡营乡的大联中。最后的胡营大集上,孩子垂着头,踩着印象中满大街萧瑟的落叶。而孩子的妈妈颇费力气地拉扯着时常痴呆的孩子,买了书包,买了被罩,要买牙刷时,孩子打断妈妈,说是自己多嚼嚼口香糖就行,刷牙耽误了时间,影响学习进步。妈妈点头同意,还是给孩子选了把劣质的硬毛牙刷。其间,孩子见一个身材魁梧的身影,在一堆凡夫俗子中晃荡个不停。同他仅有的目光交汇,孩子知道不好,国子平长成了大个子。
另一件不好的事,验证在了国子平身上。是孩子在联中第一次如厕,孩子跟不相识的面孔蹲成一排,旁边的同学在那聊一次坐席吃肉的经历,厕所的味道熏着同学龇出的一口黄牙,同学还恬不知耻地嘻嘻笑。孩子吸一口凉气,思考了一会儿人生,这时眼瞅着国子平站到尿池前,褪了裤子,像跟谁赌气似的撒尿斗远。厕所墙上描了半幅世界地图。
这时,正抽着烟的染了头发的少年,把烟头弹到地上,嘶嘶冒着尿渣子气。少年已经九年级了,他走近国子平,拍拍国子平肩膀,问道:“你会打仗吗?想跟着我们吗?想的话留下姓名班级,我们找你。不想,我们扒了你裤子,扔尿池。”国子平说:“你等我弄好。”国子平收紧了腰带,像是回到了小时候,跟还是孩子的奎文跳恰恰舞,国子平蹦蹦跳跳地同他们三人战斗。
为首的少年一拳打破了国子平鼻子,剩下的俩少年抬着国子平,往孩子蹲坑的地方一扔。“噗通”一声巨响,孩子和国子平先后泡进了茅坑。“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孩子仰天长啸。
“奎文,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报仇。”国子平带着孩子来到他家屋后的树林,梧桐树林里有摞高的砖头摆成的梅花桩,树杈子上挂着填了沙的化肥袋子,沿着屋墙摆了一溜长短不一的烧火棍。“你没事就来这里练功,练成神功我们报仇雪恨。”国子平也拍拍孩子的小肩膀。
国子平还带孩子到他家的大棚里。光鲜亮丽的紫皮茄子,往咯吱窝里蹭蹭,递给孩子一个。孩子一口咬去大半,咂嘴咂舌评价,香甜、多汁。国子平皱眉说,“不行不行,昨天我爸用茄子砸我妈,还把两根茄子同时赛我妈嘴里,说我妈没有脑子,只知道吃,不知道怎么种茄子。”
大棚是国子平妈妈一个人种,国子平爸爸在外地当建筑工人。问及奎文爸爸妈妈的职业,奎文说,“爸爸在县城开门头,妈妈在国营企业上班。”奎文特别强调,爸爸妈妈结交了县城的很多关系,因此也从来不过问他学习上的事,因此他完全不必为了学习和未来担忧。
事实上,他妈妈在村里卖农药,爸爸在集上有一个猪肉的摊位。
时有练功没了头绪,国子平买了武打的盗版光碟,邀奎文去看。洪拳的招牌架势,蔡李佛,八卦掌手黑,迷踪拳,三板斧的咏春,这些靠影视传播、千篇一律的南北拳种,国子平和奎文如数家珍。跟着电影打一趟太极拳,国子平扎稳了马步问奎文,“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破绽没有?”仅有的一次阴差阳错放错了片子,该说盗版商走心还是不走心,把成龙的警察形象印在了碟片上,填充的内容却是三级片。奎文取出碟片,一手持着碟片然后一掌击穿。
奎文的各科成绩相较练功之前,都是节节败退。学校新出的督促孩子学习的政策是,考试后每一科的成绩,都需要签上家长的大名。孩子练了武功什么都不怕,孩子自己代表家长签上姓名。班主任问时,孩子说,我们家长没文化,就这个水平。惹得老师气歪了鼻子。
孩子问国子平,“谁签的字?”国子平直言是自己的爸爸。孩子又问,“那你考成这样你不挨揍吗?”国子平说,“挨揍就挨揍啊,这次考差了,下次长进就行啦。”孩子便哀求国子平,把自己的成绩单委托给国子平爸爸,一并签好了。孩子最后一个上交签过字的成绩单,上交时他在一堆成绩单中发现了国子平爸爸,一个资深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字体,和他手中的签名一模一样,任谁也忘不了这扎眼的字。他只好悄默声地抽走了国子平的,只留下自己的。
为此,孩子很气闷。生气自己,违背了兄弟的情谊。尤其是当天下午,老师说,“很多同学都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们,很多同学不是太听话,这样——”老师喊懵然无知的国子平起立,然后一脚踹了国子平一个大跟头。不待无辜的国子平站起来,老师便宣布道:“谁不听话,谁这个下场。”
后面几次考试,国子平确有进步。孩子没进步,孩子觉得气闷时,找上幼儿园老师李玉萍的家,把一块红砖断作两截儿,一截儿砸向李玉萍家的窗玻璃。李玉萍老公从猪栏抄了根长竹竿,追着打孩子,孩子也不慌,把另一截儿红砖砸向了李玉萍家的另一块窗玻璃。
夏至未至,上一茬染头发的少年毕业了。秋分时节,跟奎文、国子平同级的同学也染了头发,牛仔裤上耷拉着铁链子,也成群结队去低年级招收小弟。让校长劈手夺了链子,指名道姓说:“这玩意儿在农村拴狗合适。”校长开大会的目的是动员一部分学生,选择寿光县城的技校,宣布这是咱们自己地界的大学。
国子平想上高中。班主任找国子平谈话,“你跟奎文保持距离吧,在他,是无所谓的事。在你,不一样,你还有机会,别轻易放弃。”
奎文不想上高中,就算想上,自己也考不上。
所以两兄弟该并肩行走江湖、锄强扶弱的,仅剩下奎文一人了。就算结伴去厕所,从厕所再到教室的路上,国子平也要说一句,“老师对我期望很高,不要让他看见咱俩在一起。你先走,我再走。”奎文心里酸酸的,嘴上还是说,“了然了然,兄弟不挡兄弟的路,中国人不骗中国人,你一定要加油。”
分流的当天,天空阴冷的异乎寻常,奎文自己搬着桌子,桌面上倒立着椅子,椅子上挂着书包。教室前面的草坪久无人践踏,却同样是破铜烂铁的色彩。奎文踩着影子在门口驻足,国子平隔窗挥手,奎文怀抱着桌椅所以无法挥手。在学校门口浪潮般的二道贩子里,奎文精挑细选了最看得顺眼的一位,桌子五十,椅子三十,一并卖了。
他知道,青春的故事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
寿光县
那晚,杀猪佬盘腿坐在失去弹力的沙发上,乐呵呵地觑着自小带大的孩子。两指间的烟越缩越短,总是着急忙慌抢救下最后一口烟,脸上不无得意之色。并肩而坐的孩子垂着头,只有在表示反对意见时才会抬头,目光坚毅地锁着杀猪佬。杀猪佬说:“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屠夫,所谓一刀定乾坤,既然父亲从了武,你就得从文,我们霍家才能一文一武,文武双全。”孩子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孩儿的志向从来不在学习上,将来要在考试之外,另闯出一番天地。”杀猪佬咧嘴大笑,爽朗的共振,像年底炮仗震得房梁下落阵阵灰尘,“村里几个念了技校的,都是远近闻名的无赖疣子。你学他们吗?他们是你的榜样?我们霍家只出栋梁之材,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所谓自古侯门出将相,所谓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孩子一脚踢翻了跟前茶几子,在杀猪佬的诧异中,孩子双膝跪地,规规矩矩地磕了三个头。“爸呀,你当我是个不孝子,你放过我吧。”
杀猪佬面皮颤动着,连同着嘴唇一并颤动。他打量了一圈奋斗了十余年,亲手打造的几间瓦屋,最后视线定格在东屋。东屋的水泥地早让老鼠洞糟蹋得没了样貌,几块摞高的红砖上盖满了小麦、玉米袋子,袋子上面拴着尼龙绳,杀猪佬抽出一根长绳,在没通电、漆黑一片的东屋里挥舞起来。这条长绳最终反剪了不孝子的双臂,人同长绳吊挂在梧桐树枝杈间。
杀猪佬搬来了茶桌,倒上清茶。杀猪佬在蚊蝇萦绕中一口口品着茶,苦等着绵绵不绝的黑夜散尽,黑夜的尽头总是日出。“我他妈是给你脸了,小畜生。”
小畜生个子不高,甚至比发育早些的女生矮半个头。小畜生的爸爸交了一万二的委培费,小畜生稳当当地坐在县城第一中学一班的第一排。迂腐的班主任是按照传统的身高模式,给寿光境内七洲四洋的兄弟姐妹分的座位。班主任白衬衣掖在牛仔裤里,胸前当啷着红领带。班主任下巴打理得干净,说是从没有过胡子都说得过去。班主任说:“不许给女孩子写情书,别不要脸,你们还没到那个年纪。”小畜生也就记住了这些话,时常回望身后的漂亮女孩,并把最漂亮的一个记在了心里。
孩子的第一封情书,就是写给这个女生。他自称同这个女生的关系是小溪和大海,是铅笔和铅笔刀,是许仙和白娘子。女生也交口称赞孩子有才华有前途。“林万红。”他无数次躲进细雨中的小树林,在孔子石像下呼喊这个美妙异常的名姓。林万红。他在网吧的键盘上打字,在偷钱买来的小灵通上打字,在平白如洗的作业本上写字。林万红。这个名字最终让一双粗糙大手当场擒获。大手的主人,也拥有着一双肥大的脚,宽敞的鞋底子一下落到孩子的胸口。
“不害臊的东西,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大手的主人再一次在孩子眼前晃晃剔骨刀,孩子一个巴掌把刀打到黄土路上,划出尘土飞扬的一道纹路。
这双失去剔骨刀的大手,把一个月见一次的孩子锁在房间里。杀猪佬隔着房门说:“你哪也别去,在家好好学习,就趁着这一日,大家都放松的时候,你好好学习,一下子赶超了他们,我看他们怎么说。全班面对你突飞猛进的成绩,一准都抓瞎。”
孩子困在东屋改建的闭塞书屋里,孩子却没有抓瞎。孩子从集上买的印着光屁股女人的杂志,上面除了影楼风格的艳图,还有一些诡异小故事,还有港台明星八卦,还有《小说月报》,孩子只挑出黄段子,一目十行地看。看着看着睡着了,恰好午睡时刻。想来,人也是稀里糊涂地进入到书本故事中。
故事讲的也是一个男孩子午睡,睡眼惺忪间,一身白衣的女子撩门帘进来。女子三十多岁,脸色浮肿,来回徘徊。逐渐逼近卧床,很自然地揭衣上床,压在男孩子的雪白肚子上。女子的细腰、肚脐也是尽收眼底。男孩子只觉千斤重,胸口闷,苦苦发不出声音。一着急,手如绑缚,脚如瘫痪,全身能动弹的只有小细腰,便使足了劲儿往上顶。顶了几下,也就一股一股释放出来了。
孩子臊眉耷眼地坐起来,茫然四顾,肚皮上娱乐杂志封面印着妖娆的张柏芝,一行黑体加粗字:张柏芝的小儿子是刘德华的,刘德华不敢承认。烈日正旺,窗玻璃五彩缤纷的,玻璃外是五彩缤纷的十七岁的天空。
晚自习之后,孩子把林万红约到操场。给林万红护手霜,给一张林万红的素描像,有时候是首尾呼应的一首小情诗,还给过奶茶、豆浆、馅饼、咖啡糖。林万红问孩子:“为啥叫奎文,是不是《超生游击队》里说的,是在潍坊市奎文区生的?”奎文说,“是生他那年,爸爸的第一套房子,在奎文区买的。”林万红感兴趣,“那第二套呢?”一中在县城边缘,时有断电。黑灯瞎火的,孩子壮着胆子亲了林万红,亲完只是说:“坏了坏了,一断电,刚提的一箱雪糕又得化了。”其实孩子家里唯一的电器是,爸妈结婚备的一台彩电。孩子走路只顾看自己鞋子,林万红倒是大方,劝孩子得放开,跟个小姑娘似的,忸忸怩怩多拧巴。
孩子同样看见,其他男孩子约林万红到操场。也是黄昏时分手拉着手。孩子不上课,跑回宿舍用被子蒙着头大哭。孩子还跟着高年级的学长翻墙上网,还跟着看午夜电影。孩子留长头发,因为不符合校规,班主任问他:“你这脑袋上长了金条吗,说你多少次还不去理发。”气不过,用剪子给他绞,绞出一头炸毛,让他看着办。“像精细打理的草坪,来了牛,来了羊。还来了什么,还来了猪。”
猪是骑摩托车来的。把摩托车停在教学楼前面,人穿着紧实的皮衣,脚蹬着大号皮靴子。林万红的几个女同学都围着他看。他说:“你们看啥看,把我当动物看呢,当什么,当猪呀?”惹得女同学哈哈大笑,夸赞着他的风趣幽默、知冷知热。他把林万红带出了西门岗,然后拐弯上了笔直的大马路。路是漫长的,没有尽头,大概在马路上疾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的同样时间,疲惫的旅人才从地球的另一端穿越回来。回到了原点。
只是猪没有下车,在西门口丢下林万红,摩托车轰隆隆的油门声,车屁股喷着稀薄的烟,烟散了,人也消失了。
穿运动衣都显苗条、婀娜的林万红,哪怕是上个厕所,身后都跟着一大群指手画脚的男男女女。“猪拱了白菜。”嘴贱的这样说。孩子理论:“采花不败花,败花皆可杀。”嘴贱的说,“拉倒吧,还杀个凉鞋呀,破了处了,小痴子。”
林万红顶不住压力,最终退学了。孩子握紧了拳头,孩子在心里定了魔鬼训练的计划,照他的思路,练成了就是中国的洛奇,中国的兰博,再组建一支中国的敢死队。他要继承杀猪佬的手艺,最好是照着嘴脸,一刀下去,把猪头猪身劈成两半。
有大半年时间,孩子的正经事是跑步,是单双杠,是铅球,是标枪,是散打,是通背拳,是摔跤,是自由搏击。除了频繁的淘汰球鞋,孩子倒是长高了,茁壮了,眉眼间有英武之气,举手投足带着起义的斯巴达克斯的神韵。脑子里演练的是一声令下,攻城略地的战争剧。
孩子是在塑胶跑道,见到的正上体育课的国子平。当时国子平的同学在讲,从实战出发,李连杰能不能打过甄子丹。高谈阔论吸引到了孩子,孩子探头探脑扎进人堆一看,国子平也在其中。国子平没考上高中,国子平的建筑工人爸爸给学校交了八千块钱,作为落榜生的委培费。国子平爸爸一个月,只给国子平六十块钱。国子平黑了瘦了,说是业余时间勤工俭学,去工地上和泥巴、搬红砖。一日三餐是自带的榨菜,馒头是工地上攒下来的。
孩子拉着国子平到孔子石像下,孩子一一诉说着自己的平生不得志,说到心爱的女孩辍学时,潸然泪下。孩子说:“如果孔子有灵,看着如今莘莘学子这样艰难,真不知作何感想。”命运是覆水难收。当年落榜的消息,是和秋天的第一批落叶一起来的。一夜之间席卷了胡营乡的大街小巷。彼时的孩子同国子平爬到屋顶,二人喝啤酒像喝白酒,小口抿着喝。喝了一个白天,酒还剩下大半。乌鸦或者干脆是报喜的喜鹊四处盘旋,声声鸣叫。国子平紧抿着嘴唇,抿得嘴巴是一道担着千斤重物的扁担。国子平说:“好兄弟,看来我们得去寿光的大学打拼了。”
孩子宽慰道“你看成龙,也没有学历,但是一双拳头打拼了多少荣耀。我们年轻,有闯劲,我们到哪里都不怕。”
孩子和国子平自诩还算年轻,有闯劲,什么都不怕。顶着一打架就开除、一点商量余地没有的校规,孩子再一次见到摩托男。孩子招手把国子平喊到身边,孩子心里是有了无限的底气。孩子说:“猪,你别走了,你今天走不了。”猪看看孩子,看看国子平,猪从兜里摸出手机,猪打电话,猪说:“哥呀,我让几个人物劫道了,县一中西门,快来。”猪说话时一只手摸着肚子,许是紧张,或是天气炎热,天干物燥,猪的鬓角一直流冷汗。
猪的哥带着兄弟来的。孩子并不怕,即使人多势众,孩子也全然不怕。孩子说:“我叫霍奎文,他叫国子平,我们可不怕你们。”猪的哥哈哈大笑,哥笑的时候,猪一个箭步上来,亲自扇了孩子两个嘴巴。孩子的脸孔先是扭向左边,接着扭向右边。接着猪的哥把一个没打开的弹簧刀戳在孩子胸口,他说:“就你,劫道。”
孩子呐喊一声,像是杀猪佬跟猪血拼之前做的准备,孩子只一下足以把猪的哥顶翻在地。只是,没有人看到,孩子是哪个时刻,是怎样夺过了弹簧刀。
猪的哥招呼着俩兄弟,一边一个把挥起弹簧刀的孩子架空,孩子两脚离了地,徒劳地蹬腿,“妈妈的。”
猪冲着孩子的肚子踢了两脚,像是只两脚便把充气娃娃踢得没了气。充气娃娃嘶嘶嘶撒着气,瘪了,缩成一团。
猪的哥是后知后觉。他看了会儿众人,自己坐到地上,随后乖乖地躺倒,他使劲儿睁开又合上眼睛。
国子平木偶人一般远远看着,目光里是不解、疑惑,像是没想明白,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潍坊市
奎文从长途车上下来,呛着风吸着烟往龙城市场方向走。见了熟人,从后面拍拍人家,等人家反应过来,奎文早就消融在无数个晃动的背影中。这次在批发站要了两大包里脊肉,过秤时还是无休止地跟人讨价还价,贩肉的都认识他,看看秤,再看看奎文,还是决定给他个便宜。
“肉不好卖了,一只猪宰了,四脚朝天挂着,你割一刀,我割一刀,都他妈要里脊,要后肘,要精的,我他妈哪儿来那么多里脊,那么多后肘,那么多瘦肉,剩下的叫我怎么卖?我还有什么,就剩个猪脸。”贩肉的替他扛着一包里脊,出了市场,贩肉还叨叨个不休。“对了,看你年纪不大,有三十了?”
“今天刚好三十岁生日。”
“你这么小,今天不回家过中秋节?”
出了市场,他肩膀担一包肉,嘴巴咬着烟,大步往长途车站走。不等走到车站,冻肉会化开一部分,弄得大衣黏乎乎的,到了车上,肉会化得更快,混着血水流淌。上次司机以为他运尸呢,闹了个笑话。路过潍坊市职业学院时,他加快了脚步,几乎没正眼看南门口拥挤的学生,但是穿过门口,又往前走一段上坡路,快走到栅栏的头了,还是驻足,细细观望着里面。
有几个身影像林万红,有几个像国子平,还有像他的。也只是像而已。没别的了。回程的路要经过最漫长的黄沙路,沙子噼里啪啦痛快地拍打着车玻璃,车身急剧地摇晃中,他歪着头睡着了。又是梦到那年夏天,一人午睡,一身白衣的女子撩门帘进来。女子三十多岁,腰系麻裙,揭衣上床。女子亲吻他的额头、眉眼、颧骨、脸颊、鼻子、嘴巴,一点点、一寸寸往下,他只觉手如绑缚,脚如瘫痪,窘迫难挨。他突然用尽了全身力气,恶狠狠地咬住了她的嘴。牙齿深咬进肉里,血液流淌到脸上,湿淋淋地连枕头都打湿了。奎文平静地睁开眼睛,深呼吸,车子四平八稳地碾压着黄沙路,前面是重重叠叠的树林,似乎一切永无尽头。
一年前盛夏,杀猪佬突然两眼一黑,栽倒在集市上。
“中风?脑血栓?你爸这个怪突然的。这二年真累了你啦,工没得上,钱没得挣,一天到晚伺候个杀猪的。”
再出现在乡亲面前的杀猪佬坐在轮椅上,儿子推着他走街过巷。直把杀猪佬推到猪肉档前,儿子系上围裙,围裙带子勒出了他腰上、肚子上新添的赘肉印子。乡亲在他猪肉档前面立住时,他脸上堆着笑散烟。一包烟拆开,很快散得只剩下一支,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冲着乡亲傻笑。待人离开,他才张开五指拢上火苗,点火深嘬一大口,一丝细烟迎风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