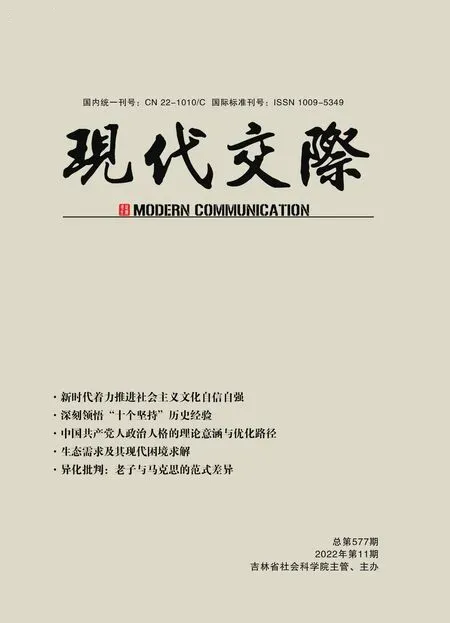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的立体透析
□邓小玲 庞 清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6)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泛起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生态危机、探讨解决生态危机途径的社会思潮,技术批判思想是其思潮的重要内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思想以技术异化为批判对象,将技术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统一起来,而后提出克服技术异化以防止生态危机爆发的途径,这为我国新时代理性运用和发展技术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启示。
一、思想表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的主要内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控制自然”理念、“异化生产”方式、“异化消费”观念导致技术异化,从而触发了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从这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技术进行批判,进而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
1.“控制自然”理念之维的技术批判
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欧洲,人文主义精神盛行一时。人文主义精神极力主张以人类为中心,主张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翁,确认人的主体性地位,高歌人的价值作用。随着人类解放思想影响的不断扩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运用技术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逐渐增强,由此人类不再敬畏自然,而开始转向征服自然、占有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成功欲和获取经济利益的物质欲在这一过程中均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控制自然”这一思想理念伴随产生,而后在启蒙运动中得以加速发展,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主导思想之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威廉·莱斯认为,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在“控制自然”思想意识形态的支配下,“社会成为唯一有意义的和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的支撑结构”[1]5。技术被单纯视为满足人类现实社会价值而舍弃自然价值的工具,逐渐走向了“以人类为中心”“技术为人类服务”“自然向人类低头”的非理性极端,出现“技术越进步、自然越糟糕”的怪象。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技术越被人类控制,人类越被技术控制”的怪病。诊断其怪病发现,资产阶级“对自然的技术控制通过操纵需求转化为对人的控制”[1]141。威廉·莱斯认为,这种违反生态发展规律和人类本性发展规律的所谓“控制自然”的思想意识形态必须转变,应当向“生态道德观”转变,这样才能阻断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才能阻止技术的异化,才能推动技术本质与功能的生态复归,继而实现技术价值的返魅。生态道德观,“它的主旨在于伦理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或技术的革新”[1]168。生态伦理或道德的发展致力于消除人与自然之间不对等的“主仆”关系,重构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从而打造人与自然的命运利益共同体;它否决精致利己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从全局意识和长远眼光出发,摒弃短视的固我利益,合乎理性地运用技术在人类与生态自然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此来实现造福人类社会和保护生态自然环境的“双赢”。
2.“异化生产”本质之维的技术批判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为了获取更多的、更大的经济利润,必然会想方设法地推动技术进步来扩大生产规模,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技术越是进步,越是容易异化为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机械工具,异化为资本不断向自然生态环境索取经济利益的一把无情利刃。异化生产引起技术异化,而技术异化的后果将会愈发激起自然生态环境的“愤怒”,然后以愈发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对人类进行“报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与生态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有限自然资源的限制,注定是走不远的。他在批判这种短视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异化带来的不良生态影响,指出这会导致自然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污染范围越来越大,生态危机形势越来越严峻,“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了问题”[2]。最后,福斯特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异化制造出来的污染垃圾物、工业污水、有毒废气向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输送、排放的可恶行为。这种转嫁生态危机的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来说是不公平的,是非正义的,是不道德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没能吃上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却要吞下他国强制塞给的污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康纳与福斯特的观点大致一样。奥康纳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从而更进一步地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家必然对技术进行改良,由此对自然界的自然资源需求更大,从而加速了自然资源衰竭的速度,逐渐超出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负荷,使生态环境系统失调失衡,最终引发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异化引发生态危机的不良后果来论证异化生产造成了生态危机。
3.“异化消费”观念之维的技术批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本·阿格尔坚持此立场和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消费即幸福”的思想意识形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将幸福与消费挂钩,用消费能力高低去衡量幸福程度。这种消费观与“异化消费”无异,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3]5。这种“异化消费”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运作的固有逻辑,当代西方人受资本支配和控制产生的“假需求”让人们沉醉在“越消费越快乐”的泡沫城堡里而难以正视现实生活;这种“异化消费”观念也是资本主义异化生产带来的产物,资本主义异化生产所造成的“劳动—闲暇二元论”,使人们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3]5。由此看来,为了消费而劳动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将会使劳动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被覆盖直至消亡,另一方面也会使消费活动被资本主义异化,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将这种异化消费与技术异化相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社会以实现更多的经济利益作为最终目标和最高准则,费尽心思地运用技术生产出各式各样的商品,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在于能否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要,而更多地是为了迎合消费者“消费即幸福”的异化消费理念。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之下的消费者是“为了消费而消费的”。随着资本主义市场“无形之手”的控制和技术的不断升级改良,异化消费的势头越发猛烈,主要表现为资本家生产质量次、寿命短的商品,即“商品的破坏或废弃就构成商品自身,它们的快速磨损是被设计好的”[4]。如此一来,消费者只能增加对此类商品的购买次数或者购买价格更高、质量更佳的同类商品。由此,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商品不仅具有它本身固有的物理属性,即在发挥使用价值时会磨损、老化直至被淘汰,而且在资本和异化的技术操控下,在商品身上还呈现出社会性被淘汰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市场不断向消费者鼓吹新商品的新功能,从而令消费者被迫“心甘情愿”地淘汰掉原有商品,转而去购买新商品,以此来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目的。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显然易见的,主要表现为资本家为了节约成本,谋求更多的经济利润而大规模地生产破坏生态环境的商品。综合来看,消费异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异化、技术异化对生态的依赖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严峻的症结所在。
二、克服途径:推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以克服技术异化
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异化生产”“异化消费”以及“控制自然”思想价值观是技术异化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诊断出问题根源所在之后方可“对症下药”。因此,克服技术异化、避免生态危机频发的途径在于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双重变革。
1.破除资本主义制度是治本之策
生态危机的当下,技术乐观主义者坚信技术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的生态危机问题还不能得以解决,是当前技术还不够发达所导致的;如果技术足够发达,那么一切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将迎刃而解,如开发和使用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空气能等高新技术便可减少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生态危机。与此观点截然不同的是技术悲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则认为技术是一种控制自然,进而控制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怕力量,因此主张通过给技术画上“终结符”来降低技术异化发生的概率,以此来遏制技术异化带来的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赞同上述两种观点,他们认为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都没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去深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寄托于技术身上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引起技术异化才引发生态危机的。无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是资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既然技术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的,那么整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技术完全是由资产阶级来决定的,这也就意味着技术的类型、使用方式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契合,因而资产阶级只会实施那些有利于榨取经济利益、维护自身政治统治的技术,而那些无经济利润或者低经济利润、高生态保护成本的技术就自然而然地被淘汰、被舍弃。因此,破除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克服技术异化、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先“破”旧资本主义制度,后“立”生态社会主义新制度。生态社会主义新制度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按需生产、供需平衡”的稳态,因而与此相对应发展的是小规模的分散技术。这种技术以“小”和“散”为主要特征,以“清洁化技术”“人性化技术”“软技术”为主要表现形式,以生产与消费需求相一致为运用导向,以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为宗旨,致力于去除资本主义“异化生产”“异化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弊端。高兹、奥康纳、阿格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技术进行了阐述。高兹认为,这种技术能够让人类社会实现“更少地生产而更好地生活”;奥康纳认为,这种技术有利于让商品的“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阿格尔认为,这种技术能够让工人实现“生产者”与“管理者”的统一,在极大程度上实现民主化,从而推翻“劳动—闲暇”二元论。
2.塑建技术运用伦理道德观是重要之法
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控制自然”理念深入人心,“向钱看齐”思想蔓延四周。在这种技术理性导向观的影响下,资产阶级疯狂地运用技术向自然界掠夺资源,运用技术大批量地向社会输送破坏生态平衡的商品,技术异化成为生态危机发生的“间接凶手”。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思想意识主导地位,如果不塑建新的技术运用伦理道德观,那么生态危机将对人类社会发起更无情的“报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莱斯、高兹、佩珀对塑建什么样的技术运用伦理道德观进行了阐述。莱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遵循着平等、和谐的伦理道德,而技术的运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也应遵循这样的伦理道德。由此看来,“控制自然”显然不符合平等、和谐的伦理道德,因为置于此理念之下的“自然”处于被主导地位,而人类处于主导地位,人与自然不对等的关系难以实现这两者的和谐相处。如果促使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那么就应该消退人运用技术的非理性欲望,约束人非理性运用技术的行为,即将“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5]。高兹认为,技术运用应该遵循生态理性而非经济理性的伦理道德,在生态理性的伦理道德引领下,人们开始向清洁生产、低碳生活、绿色消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佩珀认为,技术运用的主体是人,那么技术运用应遵循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伦理道德着眼于全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以“造福人类社会,改善生态环境,创造美好生活”为价值准则。虽然资本主义技术主张的也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道德,但维护的只是资产阶级少部分人的利益。为了保证这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生态环境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技术运用伦理道德观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那么技术必然异化为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类的工具,资本主义技术运用伦理道德必然从人类中心主义沦为资产阶级中心主义。在此影响下,生态危机必然会发生。由此看来,克服技术异化,除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还需塑建技术运用伦理道德观,前者为克服技术异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后者为克服技术异化筑牢思想共识。
三、影响辨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思想的积极意义与不足之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技术批判思想为化解生态危机、端正技术运用方式提供了许多有益思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因缺乏实践基础而带有局限性。
1.积极意义
第一,有利于树立辩证的技术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深深扎根人类脑海里的“控制自然”的思想观念。在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类借助技术的强大力量来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发生异化,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人类要转变传统的“控制自然”的思想,强调技术的理性运用,限制人的欲望的非理性膨胀,要求做到“人要控制其科学技术的创造力,就必须首先不对它感到惊奇和企求它所不能赐予他们的福祉”[6]。对于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如果技术能够理性运用,那么就能缓解生态危机,就能较好地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使这两者实现和谐、平衡发展,进而提出的“清洁化技术”“人性化技术”“软技术”是其技术理性运用的核心内容。这些技术体现的是一种辩证的技术观,既肯定了技术能够造福人类的社会价值,又能够看到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消极影响。“清洁化技术”以节能环保为宗旨,强调运用技术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所产生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环境来说是无害的,甚至是有利的,这能够解决技术非理性运用产生消极影响的问题。“人性化技术”则认为,人与自然需求是一致的,技术的发展与人的需要是相统一的。这种技术观辩证地看待人的现实需要、自然的生态需要、技术的发展需要,从这三者中找准需要的融合点,而融合的阻挠因素在于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只有改变反人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才能解决反生态技术异化的问题。它认为“软技术”是一种既肯定技术经济价值又看到技术生态价值的技术观,它与唯经济增长的大规模集中生产的“硬技术”不同,与“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硬技术”相对,“软技术”更偏向实现“小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更侧重追求“精准消费”的生活理念,主张人类社会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这样就会尽可能地减少了自然资源的浪费,降低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弱化了技术异化的程度,同时人类社会精准化需求得以满足,生产与消费得以维持和谐平衡,这就能实现技术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统一。综合来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思想让我们正确、辩证地审视技术的两面性,让我们全面反思控制自然的非法性和技术运用的非理性,让我们看到了技术价值的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创造技术多重价值的理论思路。
第二,有利于理性地运用技术造福人类社会和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为我们提供了辩证的技术观指引,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理性运用技术的方法与手段,为造福人类社会和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一些有益思考。首先,“清洁化技术”主张开发和使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这些清洁能源的使用能够实现和谐的生态循环,也能够节约自然能源和减少环境污染,还有利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和提升生活水平,创造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共赢”的局面。其次,“人性化技术”即技术的人性化,认为运用技术的目的不在于控制自然、支配自然、统治自然,而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注重在保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维护人类整体的、长期的利益,反对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制度,提倡增强具有公益性质和体现人类整体利益的生态道德意识和生态责任感。“人性化技术”深入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异化展开批判,把自然从技术的征服下解放出来,也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了自然与技术、自然与人的双重解放,明确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异化的不良后果,将生态危机“后果”与资本主义制度“前因”挂钩,为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视域提供新视角,同时为构建社会主义技术提供新思路。最后,“软技术”通过重塑理性的消费主义文化与价值观,把人们从盲目生产、疯狂消费的泥潭里解救出来,有助于生产者克服盲目大规模生产的弊端,有助于消费者摆脱异化消费的枷锁,让生产者与消费者均从中受益,也让生态环境得以“喘息”,恢复生机与活力。
2.不足之处
第一,错误判断了社会基本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愈发严峻的现状来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与自然的矛盾代替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判断脱离了唯物历史主义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这样的判断没有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始终受这一基本矛盾的制约与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必然受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制约与影响,由此生态危机必然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相关,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现实基础去对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技术异化进行批判,这样的批判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缺乏实践基础。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却只是“一种带着田园牧歌式余响的批判”。[7]
第二,理论构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体现在“稳态经济”模式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小规模分散技术”的做法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生产,借用缪勒的经济理论,提出了“稳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倡缩小工业规模,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建立分散化的小规模生产。这一主张并不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漠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工业化建设,而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正方兴未艾,正是需要依靠技术的力量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而“稳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来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另一方面,“小规模分散技术”的做法也是不现实的,片面追求小规模技术,只会陷入主观主义境地。当代技术大规模生产、快速发展的趋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对于一些造福人类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要大规模运用,如为人类社会交流沟通提供了便利条件的电信技术,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提供坚强保障的医疗技术,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强有力支持的新能源技术。总而言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或者低估了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生态功能及其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技术大小规模与生态危机无必然关系,大技术不一定就会造成生态危机,而小技术不一定不造成生态危机。
四、结语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思想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为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带来了许多启发,也为我国新时代理性运用和发展技术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启示。一是明确技术是为造福人类社会、改善生态环境服务的。全面理解技术的本质,深刻把握技术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拒绝仅仅具有经济价值的技术,否决偏离“造福人类社会、改善生态环境”宗旨的技术,充分地让技术发挥它应有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真正地做到造福人类社会,改善生态环境。二是重视开发新能源,运用和发展“清洁化技术”。清洁化技术最大的特点是节能环保。这种技术与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相契合,与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相耦合,为我国正确引导技术、规范技术、应用技术、发展技术提供了思想支撑,为正确处理人与技术、人与自然、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想遵循,有利于促进我国技术快速健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