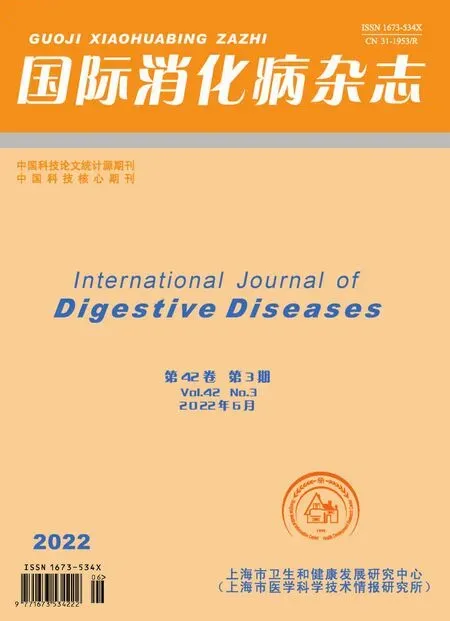溃疡性结肠炎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
陈 鸣 张 靖 朱金水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肠病(IBD),主要累及直肠和结肠,其发病率在国内外均呈逐年升高趋势[1]。遗传易感性、上皮屏障缺陷、免疫反应失调、环境等多种因素在UC 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UC 的主要临床症状为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及里急后重等,治疗目标是诱导并维持缓解,表现为症状消退和内镜下黏膜愈合[2]。非特异性抗炎药物(如5-氨基水杨酸类药物、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是治疗UC 的主要药物。针对细胞因子或其受体的药物(即生物制剂)的发展,代表了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治疗的里程碑式进步,这些药物主要包括靶向细胞因子或细胞因子受体的单克隆抗体和重组蛋白。这类药物可以阻断T 淋巴细胞向肠道炎性反应部位迁移或者抑制促炎细胞因子表达,从而减轻肠道黏膜损伤[3-4]。英夫利西单抗(IFX)是最早被用于UC 治疗的靶向制剂,在此之后新的治疗靶点及治疗药物也不断被发现。本文就UC 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靶向治疗的原理
UC 发病的病理、生理机制复杂,这一过程由Th2 细胞驱动,当肠道上皮屏障被破坏后,巨噬细胞和抗原递呈细胞被激活,浸润性单核细胞成熟为巨噬细胞并产生TNF、IL-12、IL-23 和IL-6 等多种促炎细胞因子,导致可以吸引中性粒细胞的趋化因子表达水平升高,从而促进肠道炎性反应的发展[1]。当肠道存在炎性反应时,免疫细胞发挥抗原递呈作用,上调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表达,适应性免疫被激活后诱导外周循环中T 淋巴细胞迁移至炎性反应部位。T 淋巴细胞的肠道归巢在UC 的发病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肠道归巢的T 淋巴细胞表达肠道特异性α4β7 整合素,其与胃肠道内皮细胞表达的黏膜地址素细胞黏附分子-1(MAdCAM-1)相结合,T 淋巴细胞选择性地迁移至肠道,分泌过量趋化因子和炎性因子,从而导致肠道黏膜持续性损伤[5]。Janus 激酶(JAK)属于酪氨酸激酶家族,包括JAK1、JAK2、JAK3 和酪氨酸激酶2。肠道免疫细胞和基质细胞维持稳态所必需的细胞因子(如IL-6、IL-10、IL-2、IL-22、γ-干扰素、IL-12 和IL-23 等)的表达,均依赖于JAK/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STAT)介导的信号转导。因此,JAK/STAT 信号通路在IBD 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阻断JAK 信号通路可以抑制黏膜免疫细胞生成的炎性细胞因子的信号转导[3]。鞘氨醇-1-磷酸(S1P)信号转导是UC 发病过程中免疫细胞迁移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具备生物活性的S1P可以通过结合G 蛋白偶联受体1-磷酸鞘氨醇受体1~5(S1PR1~S1PR5)激 活STAT3 和NF-κB,且限制外周淋巴器官中淋巴细胞的迁移能力[6-7]。
新型生物制剂的治疗原理主要基于UC 发病的免疫病理机制,由此衍生的靶向治疗药物包括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表达进而抑制免疫反应,从而减轻肠道黏膜损伤的药物,如抗TNF-α 单克隆抗体、IL-12/IL-23 拮抗剂;也包括通过阻断T 淋巴细胞向肠道炎性反应部位迁移而减轻肠道炎性反应的药物,如整合素拮抗剂、S1P 受体激动剂;此外,还包括细胞因子信号转导阻滞剂,如JAK 抑制 剂等[6]。
2 UC 靶向治疗药物的分类及应用
2.1 抗TNF-α 单克隆抗体
TNF 主要由UC 患者肠道中的各种免疫和非免疫细胞产生,包括巨噬细胞、T 细胞、树突状细胞、成纤维细胞和脂肪细胞,这些细胞通过产生促炎细胞因子以加重炎性反应程度,引起肠道损伤。对皮质类固醇和(或)免疫抑制剂不耐受或产生耐药性的UC 患者,其治疗需要应用靶向TNF-α 的生物制剂。目前被批准用于UC 治疗的抗TNF 药物包括IFX、阿达木单抗(ADA)和戈利木单抗。与IFX 单药相比,IFX 与硫唑嘌呤联合治疗的患者更有可能实现无皮质类固醇临床缓解和黏膜愈合[8-9]。与静脉滴注IFX 相比,每2 周皮下注射ADA 的治疗方案效果更佳;与安慰剂组相比,ADA 治疗组在诱导治疗第8 周和维持治疗第52 周的治疗有效率和黏膜愈合率更高[10]。临床研究显示,戈利木单抗治疗可以作为IFX 和ADA 难治性UC 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法[11]。抗TNF-α 单克隆抗体具有高度免疫原性,导致中和抗体形成,影响药物疗效和安全性。因此,需要定期监测患者血液中的药物水平,以期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疗效果并降低药物毒性[10]。
2.2 整合素拮抗剂
整合素是白细胞表面的一种跨膜受体,由α和β 亚基组成,可与特定配体结合。整合素拮抗剂主要包括维得利珠单抗(VDZ)、依曲利组单抗等。VDZ 是一种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可选择性阻断MAdCAM-1 与整合素α4β7 的结合,有效诱导和维持UC 患者症状缓解,避免应用那他珠单抗时可能对机体中枢神经系统造成的影响[12]。Favale 等[13]在经IFX 治疗失败的患者中比较了VDZ 与ADA 的疗效,结果显示在第52 周ADA 的治疗失败率更高,提示VDZ 可能是经IFX 治疗失败的UC 患者的首选治疗药物。此外,在第5 周皮下注射VDZ 作为维持治疗,其疗效与静脉注射方案的疗效一致[14]。临床试验结果显示,VDZ 的免疫原性较弱,引起的输液不良反应较少,患者发生严重或机会性感染的风险较低,但存在发生肠道感染的风险[15]。 依曲利组单抗可双向抑制α4β7/MAdCAM-1 和αEβ7/上皮性钙黏附蛋白信号通路的β7 亚基[15]。一项Ⅱ期试验评估了依曲利组单抗的疗效和安全性,该试验纳入了经TNF-α 抑制剂或免疫调节剂治疗无效的中重度UC 患者,结果显示依曲利组单抗100 mg 组中有21%患者在第10 周出现临床缓解,但发生了UC 病情恶化、鼻咽炎和头痛等不良事件[16]。 因此,依曲利组单抗的安全性及应用前景需在Ⅲ期临床试验中进行进一步评价。整合素拮抗剂通过阻断T 淋巴细胞向肠道炎性反应部位迁移,从而减轻肠道炎性反应,该类药物在UC 治疗中显示出较好的应用前景。
2.3 IL-12/IL-23 拮抗剂
IL-12/IL-23 拮抗剂主要包括乌司奴单抗、Mirikizumab、Risankizumab、Brazikumab 和Guselkumab 等。乌司奴单抗是一种全人源化免疫球蛋白G1(IgG1)单克隆抗体,通过靶向IL-12 和IL-23 的p40 亚基发挥治疗作用,其在多种免疫介导的炎性疾病(银屑病关节炎、银屑病和IBD)发生的病理、生理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与安慰剂组相比,乌司奴单抗组在诱导治疗第8周和维持治疗第44 周的黏膜愈合率更高[17]。此外,另有一项研究纳入了95 例活动性UC 患者(部分患者的梅奥评分>2 分),这些患者接受至少1 剂乌司奴单抗静脉注射,在第16 周、第24 周和第52 周, 分别有53%、39%和33%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该研究证实了乌司奴单抗在短期和长期均具有降低疾病活动度的作用,也表明了该药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与VDZ 相当[18]。但是与其他大部分生物制剂一样,乌司奴单抗在抗TNF 治疗失败的UC患者中表现出较低的疾病缓解率[1]。目前,多种选择性的抗IL-23 单克隆抗体(靶向IL-23 的p19亚 基)如Mirikizumab、Risankizumab、Brazikumab和Guselkumab 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19]。有关Mirikizumab 的Ⅱ期试验结果显示,在第12 周患者未达到临床缓解,但该药在诱导期的临床有效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59.7%比20.6%)[20]。另外3种选择性的抗IL-23 单克隆抗体在UC 治疗中的效果需要更多试验支持。IL-12/IL-23 拮抗剂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表达进而减轻肠道黏膜损伤,其中乌司奴单抗的良好疗效已在多项临床试验中得以证实。
2.4 JAK 抑制剂
JAK 抑制剂包括非选择性抑制剂(如托法替布)和选择性抑制剂(如非戈替尼、乌帕替尼)。托法替布是一种口服小分子JAK1/JAK3 抑制剂,对治疗中重度UC、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等疾病均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已被批准用于UC 治疗[21]。多项Ⅲ期临床试验结果发现,接受托法替布治疗的患者在诱导治疗第8 周和维持治疗第52 周的临床缓解率和黏膜愈合率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22-23]。一项纳入260 例UC 患者的临床研究评估了托法替布的安全性,该研究发现有15.7%的患者发生了不良反应(多数为感染);此外,该研究结果显示在接受大剂量托法替布治疗(每日2 次,每次10 mg)的患者中,发生静脉血栓栓塞和带状疱疹的风险增高[24]。一项荟萃分析的结果表明,接受托法替布治疗的患者在使用该药期间血脂水平升高,但在停药后血脂水平降低,并且血脂水平与高敏C 反应蛋白水平呈负相关[25]。近年来还出现了多种选择性JAK1 抑制剂,如非戈替尼、乌帕替尼。关于非戈替尼的一项Ⅲ期临床试验纳入了中重度活动期UC 患者,其中659 例未使用过生物制剂,另有689 例使用过生物制剂(抗TNF 药物或维得利珠单抗);所有患者均经非戈替尼(每日1 次,每次 200 mg)治疗10 周后,未使用过生物制剂者的临床缓解率为26.1%,而使用过生物制剂者的临床缓解率为11.5%,且两者与安慰剂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该研究结果提示对于中重度活动期的UC 患者,非戈替尼(每日1 次,每次200 mg)在诱导临床缓解方面有效,且患者耐受性良好[26-27]。此外,与托法替布相比,经非戈替尼治疗的患者感染带状疱疹的风险较低[28]。以上研究结果提示,非选择性抑制剂(如托法替布)是相对安全有效的,而选择性JAK1 抑制剂的远期疗效及不良反应仍需进一步评估。
2.5 S1P 受体激动剂
S1P 可以通过结合G 蛋白偶联受体S1PR1~S1PR5 限制外周淋巴器官中淋巴细胞的迁移能力,从而减轻肠黏膜损伤,由此衍生的治疗药物包括Ozanimod 和Etrasimod。Ozanimod 是一种新型的口服小分子S1PR1 和S1PR5 激动剂。2021年5 月Ozanimod 被美国FDA 批准用于治疗中重度UC[29]。该药的获批基于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Ⅲ期试验,该试验结果显示接受Ozanimod 治疗的患者第10 周的诱导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接受安慰剂治疗者(18.4%比6.0%),同时第52 周的维持治疗有效率也显著高于安慰剂组(37.0%比18.5%);在安全性方面,治疗组在诱导缓解期内常见的不良事件包括贫血、鼻咽炎和头痛,而在维持期内常出现患者体内ALT 水平升高及头痛等不良反应[30]。除了Ozanimod 外,Etrasimod 是另一种选择性S1P 受体激动剂,该药物通过靶向S1PR1、S1PR4、S1PR5起到对全身和局部细胞的调节作用[31]。 一项Ⅱ期临床试验的结果显示,中重度活动期UC患者应用Etrasimod(每日1 次,每次2 mg,持续12 周)后,临床疗效较好,并且内镜下黏膜愈合率较安慰剂组更高[32]。针对Etrasimod 的Ⅲ期临床试验有待进一步展开。S1P 受体激动剂是一类用于治疗免疫介导的炎性疾病的小分子合成药物,具有起效快、使用方便等特点,可作为治疗UC 的新选择,其长期疗效及不良反应有待于在实际临床应用中进一步随访观察。
3 小结与展望
在过去几十年中,以抗TNF-α 单克隆抗体为代表的靶向治疗药物为UC 治疗带来了曙光。随着对免疫系统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治疗靶点不断被发现,整合素拮抗剂、IL-12/IL-23 拮抗剂、JAK抑制剂等药物均显示出对UC 较好的疗效。这有助于减少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提高疾病的临床缓解率。靶向治疗为提高UC 疗效带来了新的希望,具备良好的应用前景。其中抗MAdCAM-1 抗体(PF-00547659)和抗β7-整合素抗体(依曲利组单抗)等已进入Ⅱ期临床试验阶段,其具体疗效尚待进一步评估[15,33];非选择性JAK 抑制剂(如托法替布)已被证明是相对安全有效的,一些新型选择性JAK1 抑制剂如非戈替尼、乌帕替尼将进入Ⅲ期临床试验阶段[21]。已被研发出来的选择性JAK2 抑制剂尚存在一些潜在的不良反应,如抑制促血小板生成素及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从而影响患者的造血功能[34],其安全性有待今后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