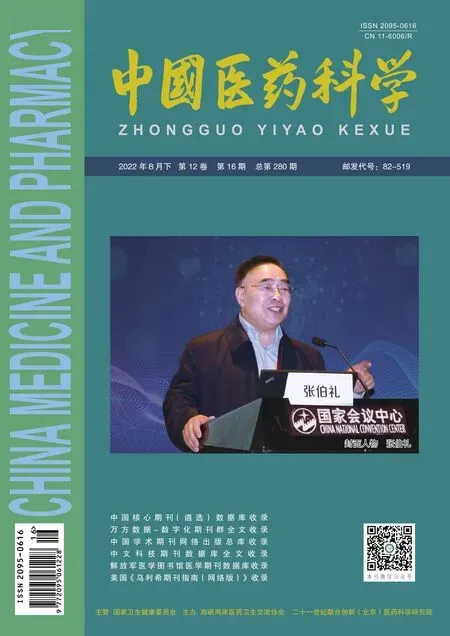黏膜免疫系统对肠-肺轴影响的研究进展
郭斌丹 董文婷 霍金海 王伟明 张碧海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6
免疫系统是人体的重要防线,多数呼吸系统疾病与免疫相关,在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中“肺肠合治”法具有显著的效果[1],此法源于传统中医基础理论之一“肺与大肠相表里”。现代研究表明消化系统与呼吸系统的大多数器官均由原始消化管内胚层分化发育而来,通过血液和淋巴循环将两者联系[2]。消化系统与呼吸系统具有共同的黏膜免疫系统,肠道和呼吸道黏膜是黏膜免疫的一部分,同时具有微生态菌群变化的同步性等,是“肺肠相表里”的重要机制[3-4]。其中黏膜是机体95%以上的感染发生或者入侵处,呼吸道黏膜是所有黏膜中与外界接触最多的[5-6],肠道作为最大的免疫器官,是黏膜免疫系统中占据表面积最大的器官,发挥重要且复杂的作用。除此之外,肠黏膜屏障还介导了共生肠道微生物和宿主免疫之间的联系,并构成了抵御腔内致病性抗原和潜在有害微生物的第一道防线[7]。所以,以黏膜为基础,肠道与肺可作为“共同轴系”去研究。本文从黏膜免疫、肠-肺菌群层面阐明肠-肺轴的联系,以期阐明肺病肠治的科学依据。
1 黏膜免疫系统与肠-肺轴
黏膜免疫系统(mucosal immune system,MIS)是由胃肠道、呼吸道及某些外分泌腺的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组成[8]。机体50%以上的淋巴组织和80%以上的免疫细胞在MIS[9],在MIS中免疫细胞以及细胞因子在肠-肺轴的联系起到重要作用。
1.1 免疫细胞的迁移与相互作用
研究发现,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pulmonary obstruction,COPD)等病理过程相关的2型 天 然 淋 巴 细 胞(type 2 innate lymphoid cells,ILC2)会通过血液循环从肠道迁徙至肺部发生免疫反应[10]。肥大细胞(mast cells,MCs)属于固有免疫细胞,其中骨髓来源的肥大细胞又称骨髓单核细胞(bone marrow mononuclear cells,BMMCs)[11],研究[12]发现在肺炎模型中MCs缺陷小鼠与野生小鼠相比肠道菌群发生紊乱,当把模型小鼠肺中给予BMMCs悬液后其可恢复肺炎引起的肠菌紊乱且肠道有害菌显著减少,说明MCs细胞在肺炎期间保持宿主防御和肠道微生态平衡方面有重要作用。Kim等[13]研究表明,香烟暴露的短期肺部模型小鼠通过肠道辅助性T细胞17(helper T cell 17,Th17)、3型天然淋巴细胞(type 3 innate lymphoid cells,ILC3)和中性粒细胞反应升高增强了肠道炎症,说明Th17细胞-中性粒细胞轴在香烟暴露后驱动小鼠肠道炎症起到关键作用。现有研究表明黏膜淋巴细胞表面的归巢受体与黏膜地址素之间的识别可能是肺、肠黏膜组织间建立共同黏膜免疫防御的基础[14]。
1.2 细胞因子及其相互影响
细胞因子是一类大多由免疫细胞分泌的具有免疫调节和效应功能的低分子蛋白或多肽[15],其能在细胞间传递信息、促使各种细胞进行生长、防御等生理活动。肠道是人体最复杂和最大的内分泌器官,肠道和呼吸道通过黏膜及细胞因子发挥着重要的免疫应答作用。研究表明高氧刺激下大鼠肺泡灌洗液以及肠黏膜灌洗液中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白 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细胞因子的变化具有一致性[16],且在哮喘疾病模型中发现模型大鼠的分泌性免疫球蛋白A(secreted immunoglobulin A,SIgA)同时在肺部和肠道中表达[17]。Mateer等[18]研究发现靶向抑制IL-6分泌可减少由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引起的肺部中性粒细胞浸润却不会引起IBD症状减轻,说明IL-6是IBD引起肺部炎症的重要细胞因子,Shi等[19]研究发现鱼腥草多糖通过调控肠道趋化因子受体6/趋化因子受体20(chemokine receptor 6/Chemokine receptor 20,CCR6/CCR20)进而调节Th17/Treg平衡,进而治疗甲型流感病毒诱导小鼠急性肺损伤。以上研究表明细胞因子可通过一定的信号途径影响肠-肺轴,但对于具体的信号途径,以及不同信号途径的交叉联系仍需探索。
2 菌群与肠-肺轴
肠道和呼吸道的微生物群在人出生后同时发育,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彼此影响[20]。此外,病理下许多细菌的波动在呼吸道及肠道间相似[21]。早期研究发现婴儿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增加了哮喘的风险[22]。研究表明在不同造模时间段的溃疡性结肠炎大鼠(ulcerative colon,UC)中需氧菌总数和葡萄球菌在呼吸道和肠道同步增多或减少[23]。
2.1 肠道菌群与肠-肺轴
肠道菌群可促进肠黏膜免疫系统的发育和维持肠道内环境稳态[24],其主要通过微生物组分和代谢物诸如细菌代谢物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细菌分泌物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脱氨基酪氨酸(deamination tyrosine,DAT)等物质通过肠-血屏障(gut blood barrier,GBB)[25],进入体循环,进而调节肺的免疫应答[26-28]。
2.1.1 SCFAs的作用 SCFAs主要由乳酸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在结肠酵解膳食纤维等不易消化的糖类产生[29]。研究表明COPD患者中SCFAs菌属繁殖有抑制现象[22],且增加COPD患者膳食纤维的摄入可以减少气道炎症的产生,说明肠道产生的SCFAs具有减少肺部炎症的作用[30]。董盈妹[31]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乙酸是治疗哮喘缓解期(asthmatic remission,ARS)小 鼠的重要机制。国外研究表明在辅助性T细胞2(helper T cell 2,Th2)细胞介导的过敏性气道炎症(allergic airway inflammation,AAI)期间,循环乙酸或丙酸调节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造血和骨髓功能,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的共同前体(macrophage/DC Progenitors,MDPs)显著增加,随后这些DC细胞局聚集在肺部分化为分化抗原簇分子11B(CD11B+DCs)细胞,进而抑制Th2反应,因此AAI被迅速解决[32-33]。现有研究表明,SCFAs主要是通过免疫细胞上G蛋白偶联受体41、43、109A(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GPR41、GPR43和GPR109A)等影响细胞因子的分泌[34],随着血液循环影响肺部免疫。
2.1.2 其他 胃肠道是致病性内毒素、病原菌的重要来源,而胃肠黏膜构成的屏障,使内毒素不能进入机体,但严重的肺系疾病又可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破坏、导致细菌及LPS转移[35]。肠道菌群失调使革兰阴性菌在肠道中占比升高,释放大量LPS入血,沿着体循环和肺循环进入肺脏,引起肺组织炎症及损伤,引发肺部感染[36],由此可见LPS是肺、肠之间病理影响的关键介质。研究表明结肠炎会导致小鼠肺部LPS水平升高[18],且肺中注入LPS又会导致血液和盲肠中的微生物变化[37],进一步说明了LPS与肠-肺轴的相关性。
DAT源自类黄酮和氨基酸代谢,Steed等[38]研究表明由专性梭状厌氧菌消化黄酮类成分产生的脱氨基酪氨酸能扩散到血液中,到达肺部,并改善免疫系统,防止流感感染。
2.2 肺部菌群与肠-肺轴
关于肺部菌群的研究较少,一直以来肺部都被认为是无菌的[39],直到2010年Hilty等[40]利用16S rRNA基因测序才发现了肺部菌群。下呼吸道支气管以及微支气管通过“微抽吸”,把上呼吸道的细菌抽吸到下呼吸道,但由于肺部的黏膜免疫防御及黏液和纤毛的摆动清除,使下呼吸道微生物的数量少于上呼吸道,正常状态上、下呼吸道菌群多样性基本是一致的,随着肺部出现病变菌群也呈现动态变化[41],但对其微生物群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大量研究集中在呼吸系统疾病条件下肺部菌群的变化以及其菌群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或肺部菌群与肠道菌群变化的一致性[42-43],极少有更深入的研究,比如肺部屏障和免疫功能是否由下呼吸道微生物群或远端上皮细胞抑或两者共同决定、呼吸道微生物群是如何代谢的等问题[2]。相对肠道菌群来说肺部菌群的研究尚处空白阶段。
3 结论与展望
慢性咳嗽、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免疫息息相关,因此免疫在预防以及治疗疾病中至关重要。以往研究多认为肺、肠黏膜都是独立的免疫系统,未重视二者之间的整体性,随着16S rRNA高通量测序等前沿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多技术、多学科的综合应用,针对肺、肠黏膜免疫特点的研究以及相关机制探索的热度日渐提高,肠-肺轴可成为未来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的关键所在。但到目前为止,针对肠-肺轴的双向传导机制的研究不够准确深入,大都是集中在肠道菌群以及其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但目前的研究过于单一且相关的信号通路不够清晰、靶点不够精准等使其机制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导致无法针对性地应用于临床,所以仍需更佳完善的实验方案、充足的试验数据、更合理的数据处理方式、更先进的仪器来进一步精确探索肠-肺轴的联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