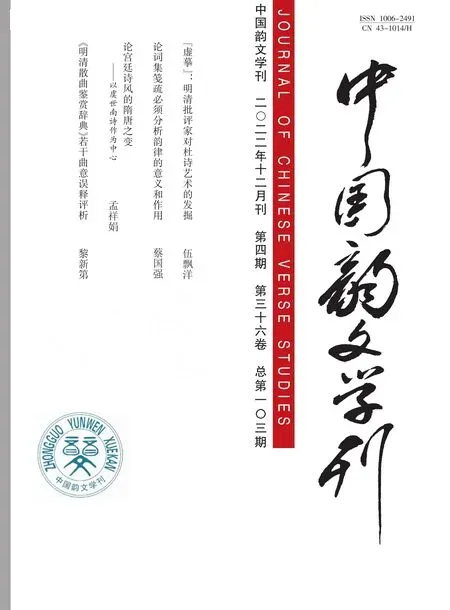论宫廷诗风的隋唐之变
——以虞世南诗作为中心
孟祥娟
(北华大学 文学院 ,吉林 吉林 132013)
虞世南历仕陈、隋、唐三朝,均以诗文成就为时人称赞。在陈,他以诗文并擅而见称于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徐陵,“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1](P2565);陈亡,与其兄虞世基共同入隋,因才学出众被方之于在东吴灭亡后入晋的陆机、陆云兄弟;隋亡入唐,又为李世民“秦府十八学士”之一,其文辞更被唐太宗评为一绝。作为隋唐两代宫廷诗创作群体中的重要成员,虞世南的诗歌体现了宫廷诗风的隋唐之变。本文即以《全唐诗》中标明为其在隋所作的七首诗歌以及在唐所作的六首应令、应诏、应教、应制诗和两首“赋得”诗为中心,考察隋唐之际宫廷诗风的变化。
为论述方便,先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全唐诗》所录隋代与唐初的应制、赋得诗分别按内容题材分类列表如下:

表1 隋代与唐初的应制、赋得诗

续表

续表
从表1对比大体可见,在现存数量上,武德与贞观两朝宫廷唱和诗的数量要超过隋代。隋代宫廷诗创作的核心人物是杨广,唐初宫廷诗创作的核心人物是李世民。所以,可以说李世民倡导下的宫廷诗留存数量超过了杨广倡导的宫廷诗创作。从各种题材占比来看,与隋时的奉和多集中于出行与宴饮的场合不同,初唐早期宫廷诗中的时令与其他纪事诗增多,宴饮与出行诗占比减少,同时,对具体事物的赋咏以及因前代名篇而起的创作日渐增多。具体而言,宫廷诗的隋唐之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由自然而政教——“赋得”诗的题材新变
“赋得”诗始于南朝梁代,萧纲、萧绎、刘孝绰、刘孝威、庾肩吾、庾信以及陈代的张正见,都留有数首“赋得”之作,其中尤以张正见存诗最多。所赋得之内容,有翠石、曲涧、山等自然景观;雾、露等自然现象;有雁、鹤、蝉、马等动物,而以雁居多;也有烛、扇等器物,还有萍、竹、荷等植物,也有前人诗句,如“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名都一何绮”等,以及历史人物,如荆轲、韩信、司马相如等。
从表1可见,杨广时期的“赋得”,仍以具体的物品为多,如珠帘、镜、笛、石、鹤、燕等,或者是前代的名篇名句,并没有超出梁代“赋得”的范围,所赋之内容仍不外以上诸种类别。到了唐初,“赋得”不仅有柳、竹、菊、李、樱桃等植物,雁、莺、蝉等动物,露、云、雾等自然现象,浮桥一类的建筑,更有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李百药、褚亮和虞世南分别赋得魏都、蜀都、吴都,当即本于《三都赋》,而虞世南《赋得慎罚》语出《尚书》,明显与施政原则相关。可见,虽然创作的环境大致相同,但李世民倡导下的初唐分题创作的着眼点更加开阔,不再局限于眼前的自然景物,而是加入了历史和人文的内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中还融入了对政治与治国的思考。《旧唐书·文苑传》曰:“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巍巍济济,辉烁古今。”[1](P4982)诚不虚也。
二 分字限韵——“赋得”诗用韵新变
宴游赋诗,在建安时即已流行,那时往往只是简单的同题共作,并没有用韵的限制。到了梁代,赋诗限韵已经存在,《南史》所载曹景宗赋“况”“病”韵诗的故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但在今存的作品中,庾肩吾《暮游山水应令赋得碛字诗》是唯一可见的隋前指定以某字为韵的“赋得”之作。而遍检隋诗,并没有这种指明用某字为韵的限韵诗,在宫廷唱和中也未见分韵赋诗的情况,仅薛昉有一首《巢王座韵得余诗》,规定了以“余”字为韵。此诗见存于唐玄宗时期徐坚所编的《初学记》,曰隋薛昉,然薛昉生平无考,而隋唐时期的巢王,可知者唯有死于玄武门之变的齐王李元吉,于贞观十六年(642)被追封为巢王。据此,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很可能是入唐之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之前,题目为后来编者所加。另薛道衡有一首《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提到了用韵问题,许善心的原诗已经不存,从薛氏之作看,诗中的确存在转韵的情况,是否用许作之韵,或规定应用何韵,不得而知。
到了唐代,分字限韵赋诗的情况明显增多了。虞世南《侍宴应诏赋韵得前字》即以“前”字为韵,杨师道《赋终南山用风字韵应诏》则以“风”字为韵。另外,初唐时,于志宁、令狐德棻、封行高、杜正伦、岑文本、许敬宗、刘孝孙等多人参与的在于志宁宅邸举行的一次宴集作诗,各赋一字为韵,所得有杯、趣、色、节、平、归、鲜等字,表明了分字限韵作诗方式的推广。既然从陈、隋时代的现存作品中找不到这种指明用某字为韵的限韵诗,在宫廷唱和中也未见分韵的情况,而初唐时的“赋得”诗又明显可以见到这种创作的发展过程,由此可以认为,分字限韵作诗以增加诗歌创作的难度,是唐代宫廷诗创作中出现的新要求——至少是在唐初才日渐兴起的。
另外,用来“赋得”的前代名篇名句,隋时以古诗十九首、曹植、刘桢、左思居多,初唐时期则只见阮籍诗一句(1)《全唐诗》中收录有刘孝孙《送刘散员同赋陈思王诗游人久不归》、杨濬《送刘散员赋得陈思王诗明月照高楼》、许敬宗《送刘散员赋得陈思王诗山树郁苍苍》,然《全隋诗》中有刘斌《送刘员外同赋陈思王诗得好鸟鸣高枝诗》,四诗应是同时之作。考刘斌与孔德绍、庾自直、虞世南、蔡君和等人曾登临山水,结为文会,时在隋代,故将这几首诗系之于隋。。可见,魏晋名篇是隋唐间“赋得”的主要对象。而这种赋得,从内容而言,是敷衍原诗句之意,将一句诗扩展成一篇,这与后世将赋得诗句中的每个字作为韵脚而创作多首诗的方式亦有所区别。
三 由铺陈到节制——颂圣内容的减少
如前文所述,隋朝的应制诗以杨广出行或宫廷宴会相关的内容居多,在这些诗中,有许多对杨广的称美颂扬,如《奉和幸江都应诏》:
南国行周化,稽山秘夏图。
百王岂殊轨,千载协前谟。
肆觐遵时豫,顺动悦来苏。
安流进玉轴,戒道翼金吾。
龙旂焕辰象,凤吹溢川涂。
封唐昔敷锡,分陕被荆吴。
沐道咸知让,慕义久成都。
冬律初飞管,阳鸟正衔芦。
严飙肃林薄,暖景澹江湖。
鸿私浃幽远,厚泽润凋枯。
虞琴起歌咏,汉筑动巴歈。
多幸沾行苇,无庸类散樗。[2](卷三六,P476)
此诗运用了许多典故,“南国行周化”,语出《诗经·召南·甘棠》毛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3](卷第一,P91)“稽山秘夏图”出自《吴越春秋》卷六,说夏禹东巡,至会稽,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这是以召伯与夏禹之事对炀帝出游表示赞誉。“顺动”语出《周易》“豫”卦:“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4](P64)“来苏”语出《尚书·仲虺之诰》:“徯予后,后来其苏。”[5](卷第八,P235)意指从疾苦中获得再生。这是说在炀帝的治理下,百姓获得了幸福。“封唐”,是用周成王剪桐叶为圭以与叔虞,后遂封叔虞于唐的典故。“分陕”是用周初周公旦和召公奭分陕而治之典,以指平陈后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管理东南军政达十年之久的经历。“冬律”指候气之法,出自《后汉书·律历志》。“衔芦”出自《淮南子·修务训》,谓雁衔芦飞行以防矰弋。“虞琴”出自《孔子家语·辨乐解》:“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6](P374)“汉筑”用汉高祖刘邦之典,《史记·高祖本纪》记汉高祖还乡:“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7](P389)“行苇”为《大雅》篇名,传为公刘而作,言公刘和睦九族,尊事耆老,周家忠厚,仁及草木。这是说炀帝巡游故地,心系百姓,得到百姓的拥戴。“散樗”语出《庄子·逍遥游》,指一株大而无用之樗树,是诗人用以自谦之语。
他如《奉和月夜观星应令》中的“休光灼前曜,瑞彩接重轮”[2](卷三六,P475),《和銮舆顿戏下》中的“瑶山盛风乐,抽简荐徒谣”[2](卷三六,P475),《奉和至寿春应令》中的“瑶山盛风乐,南巡务逸游。如何事巡抚,民瘼谅斯求”[2](卷三六,P475),等等,都可以感受到对杨广的称颂。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虞世南对唐王朝以及唐太宗直接给予称颂的诗作比例并不高,最明显的一首是《赋得慎罚》:
帝图光往册,上德表鸿名。
道冠二仪始,风高三代英。
乐和知化洽,讼息表刑清。
罚轻犹在念,勿喜尚留情。
明慎全无枉,哀矜在好生。
五疵过亦察,二辟理弥精。
幪巾示廉耻,嘉石务详平。
每削繁苛性,常深恻隐诚。
政宽思济猛,疑罪必从轻。
于张惩不滥,陈郭宪无倾。
刑措谅斯在,欢然仰颂声。[2](卷三六,P473)
重德慎罚,是儒家礼乐教化的政治主张。“慎罚”一词,语出《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5](卷第十四,P425)在这首诗的开篇,作者即予唐王朝以高度的礼赞。通篇写来,是说唐王朝乐和讼息,明慎哀矜,政宽刑措,是以风高三代,颂声远播。
另外,也就是《奉和咏日午》中的“再中良表瑞,共仰璧晖赊”[2](卷三六,P473)和《发营逢雨应诏》中的“豫游欣胜地,皇泽乃先天”[2](卷三六,P473),含有称颂的意味,这个比例明显低于在隋时对杨广的称颂。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唐太宗喜纳谏言、不喜阿谀的行事作风的影响。《资治通鉴》载,虞世南上《圣德论》,李世民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8](卷一百九十四,P6098)《圣德论》全文已佚,但《上圣德论表》尚存,在表文中,他不仅说唐太宗“有汉高之度”“有光武之仁”,更说太宗“将四三王而同盛,六五帝而匹休”[9](P110),确有吹捧谄谀之嫌。这样一篇以颂美为主的文章,并没有让李世民飘飘然,而是遭到了他的批评。另一方面,唐太宗唯恐臣下不进谏谠言,多次要求群臣切谏、极谏,“导之使言”[1](P2549),对直言进谏之臣加以褒奖。两相对照,自然会让诗人在创作时有所考虑。二是虞世南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反思——他曾经多次称颂的隋炀帝,不就是未能慎终、身死国灭吗?想一想曾经的诗文中的那些颂美,对照一下炀帝最后的下场与名声,他完全可以预想到自己会被后世嗤笑的后果。反思之后,在创作中自然也会对这一类内容有所节制。三是诗作题材改变的结果。虞世南在隋所作应制应令诗,多是与杨广出行相关的叙事记行之作,在唐所作则多闲暇时的风景与咏物诗之作,并不与君王的行为直接相关,“赋得”体的诗作尤其如此。
不过,在诗歌的结尾表达自己有幸侍从君主的感激、对自己才华的自谦,似乎是虞世南应诏诗创作的一个套路。他在唐所作《侍宴应诏赋韵得前字》中的“滥陪终宴赏,握管类窥天”[2](卷三六,P473-474),《侍宴归雁堂》中的“刷羽同栖集,怀恩愧稻粱”[2](卷三六,P474),与在隋所作《奉和月夜观星应令》中的“宿草诚渝滥,吹嘘偶搢绅”[2](卷三六,P475),《和銮舆顿戏下》中的“抚己惭龙干,承恩集凤条”[2](卷三六,P475),《奉和至寿春应令》中的“天文徒可仰,何以厕琳球”[2](卷三六,P475),《奉和幸江都应诏》中的“多幸沾行苇,无庸类散樗”[2](卷三六,P476),《奉和献岁宴宫臣》中的“微臣同滥吹,谬得仰钧天”[2](卷三六,P476)并无二致。考虑到虞世南入唐之后深得李世民赏识,与入隋之后的前期,即杨广为太子时期或践祚之初,深受杨广器重非常相似,而虞世南在隋诗基本作于彼时,从他多次参与当时的创作活动就可以推测其境遇并不差。从这点来看,前后两期诗中大致相同的情感也就可以理解了。
四 由场面到景物——描写重点的新变
如前文所述,隋朝的应制诗以杨广出行或宫廷宴会相关的内容居多,虞世南在的此类诗作中除对杨广的称赞外,还用大量笔墨描写出行的场面、宴会的奢华,对自然景物的关注相对较少。如:
《奉和献岁宴宫臣》:履端初起节,长苑命高筵。肆夏喧金奏,重润响朱弦。春光催柳色,日彩泛槐烟。微臣同滥吹,谬得仰钧天。[2](卷三六,P476)
《奉和至寿春应令》:瑶山盛风乐,南巡务逸游。如何事巡抚,民瘼谅斯求。文鹤扬轻盖,苍龙饰桂舟。泛沬萦沙屿,寒澌拥急流。路指八仙馆,途经百尺楼。眷言昔游践,回驾且淹留。后车喧凤吹,前旌映彩旒。龙骖驻六马,飞阁上三休。调谐金石奏,欢洽羽觞浮。天文徒可仰,何以厕琳球。[2](卷三六,P475)
入唐后,虞世南的应制诗基本都是以写景或咏物为主。诗人的视野更多地转向了自然景物。如:
《侍宴应诏赋韵得前字》:芬芳禁林晚,容与桂舟前。横空一鸟度,照水百花然。绿野明斜日,青山澹晚烟。滥陪终宴赏,握管类窥天。[2](卷三六,P473-474)
《侍宴归雁堂》:歌堂面渌水,舞馆接金塘。竹开霜后翠,梅动雪前香。凫归初命侣,雁起欲分行。刷羽同栖集,怀恩愧稻粱。[2](卷三六,P474)
《凌晨早朝》:万瓦宵光曙,重檐夕雾收。玉花停夜烛,金壶送晓筹。日晖青琐殿,霞生结绮楼。重门应启路,通籍引王侯。[2](卷三六,P474)
《初晴应教》:初日明燕馆,新溜满梁池。归云半入岭,残滴尚悬枝。[2](卷三六,P474)
《春夜》:春苑月裴回,竹堂侵夜开。惊鸟排林度,风花隔水来。[2](卷三六,P474)
《奉和咏日午》:高天净秋色,长汉转曦车。玉树阴初正,桐圭影未斜。翠盖飞圆彩,明镜发轻花。再中良表瑞,共仰璧晖赊。[2](卷三六,P473)
《发营逢雨应诏》:豫游欣胜地,皇泽乃先天。油云阴御道,膏雨润公田。陇麦沾逾翠,山花湿更然。稼穑良所重,方复悦丰年。[2](卷三六,P473)
《奉和幽山雨后应令》:肃城邻上苑,黄山迩桂宫。雨歇连峰翠,烟开竟野通。排虚翔戏鸟,跨水落长虹。日下林全暗,云收岭半空。山泉鸣石涧,地籁响岩风。[2](卷三六,P472)
在这些诗中,诗人减少了叙事的成分,更多地表现出对自然景物的细致观察和敏锐捕捉,并用生动的笔墨将其描绘出来。他用准确的动词描写景物的变化与特点,如“高天净秋色”(《奉和咏正午》)用一个“净”字写出了高阔天空映衬之下的景物显得更为清晰纯净,“横空一鸟度”(《侍宴应诏赋韵得前字》)用一个“度”字写出一只飞鸟横空掠过的迅疾。诗人还善于捕捉最能体现自然景物特色的瞬间状态,“归云半入岭,残滴尚悬枝”(《初晴应教》)用树枝上悬着的一滴雨来表现初晴的景物特色。或者,运用颜色的对比和增强来产生精彩的对句,如《发营逢雨应诏》中的“陇麦沾逾翠,山花湿更然”两句,写陇上麦子雨后显得更加青翠,山花经雨水冲洗后红艳如同燃烧的烈火,色彩对比强烈。《侍宴归雁堂》中的“竹开霜后翠,梅动雪前香”两句,也是类似的手法。《侍宴应诏赋韵得前字》中的“照水百花然”一句,也是用跳动的火焰比喻怒放的花朵,并将“花”放在“水”边,清平如镜的水面和鲜艳似火的红花产生了很强的画面冲击感,令人称赞。杜甫后来就模仿了这种色彩对比增强的写法,在《绝句二首(其二)》中写出了“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10](卷十三,P1135)的著名诗句。
五 由婉缛而清新——诗歌风格的新变
上述内容上的改变和语言上的成就,使虞世南的诗风显得清新、明丽而又活泼起来。如《奉和幽山雨后应令》,写雨后的青山、彩虹、翔鸟、山风,清新优美,明丽如画。而且,这些作品在篇幅上也大多较隋时所作为更为精简。胡震亨《唐音癸签》云:“虞永兴师资野王,嗜慕徐、庾,而意存砥柱,拟浣宫艳之旧。故其诗洗濯浮夸,兴寄独远,虽藻彩萦纡,不乏雅道。”[11](卷五,P43-44)就是说虞世南的这些诗作无论是题材的选取还是内容的安排上都超越了同时代的宫廷诗人,洗去宫体诗的铅华,完成了对宫体诗浮艳诗风的超越和突破。
虞世南对淫靡轻薄有过明确的反对,《大唐新语》载李世民尝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12](P41)乃是出于敦厚风俗的考虑,对轻薄的艳诗加以批判。他本人的诗歌创作践行了他的上述主张,虽仍偶有堆砌辞藻的现象,如《赋得临池竹》中,“龙鳞”“凤翅”之比,以及“波泛”“流摇”“漾”“拂涟漪”等词语的堆砌,但总体看说,由隋至唐,虞世南的应制诗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内容趋向于政教,诗风渐去婉缛,趋向于清新与明丽,为贞观诗坛带来一股新的气息。虽然体制不脱传统宫廷诗的苑囿,但精神气质已经有所超拔,体现出大唐肇始的新气象。
结论
《旧唐书》卷七十二“史臣曰”有云:“二虞昆仲,文章炳蔚于隋、唐之际。”[1](P2585)无论是从立意之高远、气格之雅正还是内容之广泛等方面考虑,虞世南都是隋唐间一位不容忽视的诗人。
就应制诗而言,虞世南在隋之作虽以婉缛为主要特色,但已呈现出“洗濯浮夸,兴寄已远”的特色[13](P25),如《奉和出颍应令》,就显示出由婉缛向疏秀转化的趋向。入唐之后,其诗风由于时代气象的影响又呈现出新的趋向,表现出疏朗秀雅、清新明丽的风貌,褪净宫体诗的淫靡趣味,提升了应制诗的品格。他不同于其他宫廷诗人一味堆砌陈词故典而导致诗歌生涩累重,而能于细致深入的体察之后加以精工的描写,体现出娴雅明丽的艺术个性。如《侍宴应诏赋韵得前字》诗中间四句“横空一鸟度,照水百花然。绿野明斜日,青山澹晚烟。”鸟横空与花照水,一高一下;“一”和“百”,一少一多; “一鸟度”与“百花然”,一淡远萧瑟,一绚烂夺目,写出俯仰之间的不同观感。绿野与青山,延绵相接;斜日与晚烟,萦纡缭绕;“明”与“淡”,光影摇曳,写出极目四野之所见。于侍宴的背景之下能写出如此富于意蕴的广远景致与闲雅意态,足见功力。这无疑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含思婉转、意蕴浑成的范本。
另外,虞世南还有《赋得弱柳鸣秋蝉》《咏萤》《秋雁》等几首歌咏动物的小诗,均为五言四句,虽体制短小,但颇有特色。由语言的省净精练而表现出风格的疏朗秀雅,又努力将典雅的形式和雅正的思想熔于一炉,于咏物时遗貌取神,以抒发自我的高情远志,发扬了古诗兴寄的传统,寄寓深远。沈德潜评其咏蝉诗曰:“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14](卷十九,P249)《诗法易简录》云:“咏物诗固须确切此物,尤贵遗貌得神,然必有命意寄托之处,方得诗人风旨。此诗三、四品地甚高,隐然自写怀抱。”[13](P27)可谓的评。其创作实践,为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诗人的咏物兴寄诗提供了借鉴,引导了唐代咏物诗重归雅正。
而且,虞世南的乐府边塞诗虽然尚未完全摆脱宫体积习,但已经有了英俊精爽、豪壮超迈的气韵。不少诗句因为构思别致、意象精警而被盛唐诗人袭用。如李白《塞下曲》(其五)“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15](P287),就可以看到虞诗《从军行》“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的痕迹;王维《使至塞上》“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16](P133),明显借鉴了虞诗《拟饮马长城窟》“前逢锦车使,都护在楼兰”。知名的盛唐诗人从虞世南的边塞诗中汲取养料,足见对虞世南作品的熟悉及认可。沈德潜评虞世南《从军行》曰:“犹存陈、隋体格,而追琢精警,渐开唐风。”[14](卷一,P7)便指出了虞世南在边塞诗歌方面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总之,虞世南留存至今的诗歌作品虽不算多,却体现了诗歌发展的隋唐之变,但因其为隋唐之交的代表性诗人,其诗歌颇有以小见大、以点及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