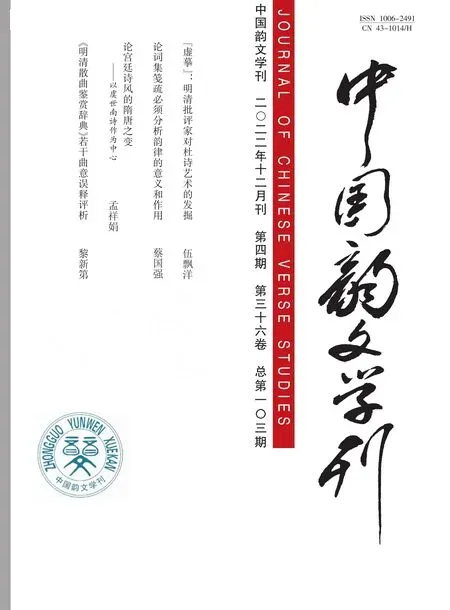“虚摹”:明清批评家对杜诗艺术的发掘
伍飘洋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虚摹”是明清杜诗批评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用语。陆时雍在《唐诗镜》中首先用以概括杜诗“吞吐含情,神行象外”的艺术效果。其后何焯、浦起龙、仇兆鳌、翁方纲等人亦多用“虚摹”来评论杜诗。而他们使用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内涵与陆时雍并不相同,其中涉及批评者诗学观念的差异,“虚摹”一词内涵的迁移与固定,以及明清人对杜诗艺术特色的发掘逐渐深入等具体问题,值得思考与探究,但目前尚未有见专文论述。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一概念使用的情况做一个相对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考察。
一 “虚摹”与经义阐发“凿空驾虚”之弊
“虚摹”作为一个批评用语被频繁地使用,大概首先是在明代儒学家阐发经义之时。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人们主要用这一概念批评士人对儒家义理阐发过虚无实之弊。如孙慎行(1)孙慎行(1564—1635),字闻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及第,累擢礼部侍郎。曾说:
“下学而上达”,《中庸》便是法程。始由庸德、庸言,素位、居易,而行远、登高,终至合鬼神、格天命,何其有渐而不易。即至诚、尽性,能化如神矣,而犹待不息、久、征,方悠远、高厚,如天、配天。此岂可虚摹妄拟者也?且夫子志学、而立是“下学”,不惑、知天命是“上达”,然前后亦且历数十年之久。今说者乃谓下学便是上达,如此直捷,其初不过虚见自悟入者耳,其流至增浅见之高谈,而无益近理之实用,此有志所宜痛戒者也。[1](P280)
《论语》中“下学而上达”指一个循序渐进的为学过程,不可“虚摹妄拟”。何为“虚摹妄拟”?在孙慎行看来,今人解说以“下学”为“上达”,背离了孔子为学“有渐”的意旨,因此不过是“虚见”,是为“虚摹”。他还说道:“欲老师宿学舍古人二十岁后学礼惇行、博学无方之实事,而徒索影响之见解于洒扫应对间,自以为精义入神,其凿空驾虚尤为可虑。”[1](P280)圣贤之学本为近理、实用之学,今人只求应付于宾客酬答之见解,而不知进一步体贴博学、笃行之实事,“自以为精义入神”,实则空言无用,此为“凿空驾虚”,亦即“虚摹”。可见孙慎行所言“虚摹”意在批评那些故作姿态,空谈义理而不切事理之人。
除了强调虚见、虚发之外,或者说“凿空驾虚”的弊病,明人在阐发义理时所言“虚摹”还多与文学性想象有关。如周宗建(2)周宗建(1582—1626),字季侯,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及第,历任知县、御史。曾对《论语》中“何如斯可谓之士”一章解释道:
“切切偲偲怡怡如”,是想象出一段中和的意象来告之。下二语却又实体贴两项来,须索要“切偲”“怡怡”也。“切偲”以尽委曲,“怡怡”以致浃洽。“切切偲偲怡怡”一句要实实摹写,讲不得只落“如”字虚摹之套。[2](P484)
这里的“想象”“实体贴”,应当分别与“虚摹”“实实摹写”相对应。在周宗建看来,“切切偲偲怡怡”“实体贴两项”,即与朋友“切切偲偲”,与兄弟“怡怡”。如此解经是真切地体贴了经文,“实实摹写”了经义。如若只是将“切切偲偲怡怡”看作“意象”,简单地理解为形容修饰、想象之语,这便是落入了“虚摹之套”。又如,葛寅亮(3)葛寅亮,字水鉴,号屺瞻,万历二十九年中进士,历任南京礼部郎中、湖广提学副使等。弟子以为,《孟子》中“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二句是曾子为了称赞孔子无人能及而作的一个比喻,因此,“字义似只宜虚虚摹写,不该将‘心体’‘道德’等语填入”。葛寅亮则指出:“语气原不该填实,但字义既是借来相形,若究其实,则既非道德,又非心体,更何所指!”[3](P376)可见葛寅亮也反对“虚摹”经义,认为应当把握“意象”当中的实际内涵。而且,葛氏所言“虚摹”之笔与周宗建一样,都与经文当中的形容修饰之语或是形象的比喻有关。再如,沈长卿(4)沈长卿,字幼宰,万历举人。论“齐人乞墦”一章云:“孟子所云齐人,盖阴有所指,非虚摹者。圣贤宅心长厚,不忍直斥,后世反以为寓言耳。”[4](P222)在沈长卿看来,圣贤决非凭空想象、泛泛而言者,因而经文中微旨当切实地体贴。这里的“虚摹”与“寓言”相对应,显然带有文学虚构、虚拟之意。由此可见,“虚摹”除阐发经义过虚无实外,也兼具文学想象的内涵。
与阐发儒家经义直接相关的是,“虚摹”一词还出现在时文批评之中,批评的主要也是“凿空驾虚”的弊病。如明末学者陈龙正(5)陈龙正(1585—1645),字惕龙,号几亭,崇祯七年中进士,任中书舍人。在《举业素语》中曾两次使用“虚摹”,批评当时八股文写作中用虚过度的行文方式。他说:
今日习气有三种:一是假造子书,如颠如醉;二是才短者妆娇作隽,自贵虚摹;三是气浮者粗谈壳语,自负雄骏。若守其陈腐,反无几人,人亦不齿。吾今特定“新、切”二字为救时之的。新则陈言近套并从捐除,直须浚发巧心,不经人道;切则一切假古色、假摹神、假阔论,但不着脉者,皆扫去无用矣,直须洞达题髓,目击道存。[5](P2577-2578)
他还说:
“去套”二字为铁门关,为玉钥匙。但所云套,亦自多变。如题易平衍,则平衍为套;题中易着气概,或易布淋漓,或易涉凌驾,或易妆虚摹,则举士子所自喜警策处、快心处、传神处,皆习气,皆滥套,皆厌态也。[5](P2582)
八股文有其基本的写作原则和规范,如尊题、肖题,从立意到语气处处都尊奉题旨(儒经),不得与理背离或别出己意,不说出题外话[6](清代卷,P34-35)。在陈龙正看来,“造子书”“虚摹”“粗谈”者,不讲题旨,不着题脉,故以其文为“假古色、假摹神、假阔论”,以此气习为“滥套”“厌态”。而“虚摹”与“摹神”“传神”相对而言,又主要指写作者不能体认题中精神、阐发题中义理,而又装腔作势、放言空谈。“或绝非此题话头,无端扯入,或近似而非题本意,翩翩发挥”[5](P2578),“丢开题面,悬空扯闲”[5](P2580),都是“虚摹”的一些表现。其实,陈龙正并不反对八股文用“虚”,只是认为应当在虚实相济中神色俱备。他曾说:“古人所贵镜花水月,必有实解得处,但用之虚融圆远,使无迹可求,盖滓去而神存也。若胸存滑(笔者注:当为‘鹘’)突,故为影似之言,令其自解,终不可得,是直无神,何名无滓?”[5](P2575)用“虚”的前提是“有实解”,否则,它最终只能沦为一种“假摹神”。由此可见,陈龙正在使用“虚摹”一词时,亦将侧重点放在了“虚”字上,主要批评时文不讲题旨、不实解经义,用虚过度之病。
总之,以上所谈到的孙慎行、周宗建、陈龙正等,皆为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之人。他们使用“虚摹”一词主要是批评那些不能切实体会、阐发经文的学者。此外,他们所言“虚摹”往往还与比喻、虚构等文学修辞或文学的特征联系在一起,具有文学性想象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周宗建等人批评“虚摹”经义,其实也是在反对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解读经文。这或许与当时士人“普遍地不遵经文和传注,远离现实,放言空谈”,以及八股文“全面去经学化,更趋文学化”[6](明代卷,P595、594)的风气有关。而这种与义理阐发的疏离,以及与文学审美的关联,或许也是“虚摹”一词后来更广泛运用于诗歌艺术批评之中的重要原因。
二 “虚摹”与陆时雍含蓄自然的审美趣味
就笔者所见材料而言,明代陆时雍最早将经义阐发中更常见的“虚摹”一词运用到杜诗批评之中,概括杜诗的艺术特征,肯定杜诗抒情写意的艺术手法。他在《唐诗镜》中说:
摩诘七律与杜少陵争驰。杜好虚摹,吞吐含情,神行象外。王用实写,神色冥会,意妙言先。[7](P532)
古人论诗,多以景为“实”,以情、意为“虚”。《唐诗从绳》中所云“凡诗写景为实,叙事述意为虚”[8](P1682)是诗文批评者一般性的看法。陆时雍此处所使用的“虚摹”一词,与“实写”相对,又与“情”相联系,侧重强调的应当是抒情写意这一层内涵。陆时雍比较欣赏杜诗(尤其是七律)所表现出的以情为主、字字写意抒情的艺术效果,这从他称赞盛唐人中“惟杜子美长于言情”[7](总论,P12),以及所言“五七律诗,他人每以情景相和而成,本色不足者,往往景饶情乏;子美直抒本怀,借景入情,点镕成相,最为老手”[7](P678)可见。陆时雍还多赞美杜甫七律中“率怀抒写”的“漫兴”之笔,这类作品也以情为主。(6)有关陆时雍对杜甫七律中“漫兴”之作评点的分析,可参孙学堂《论陆时雍的杜诗接受》,《中国诗歌研究》2014年第10辑。除此之外,即便陆时雍认为杜甫的五言古诗大体上“苦于刻”[7](P403),即或是“苦意摹情”,或是“穷工造景,逼于险而不括”[7](总论P9),他也会肯定其中的遣情抒怀之作。如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云:“登高望远,一往寄情无限。”[7](P687)称赏的便是该诗写景而情横溢,即杨伦(7)今学者皆因该评语前有“何义门云:此下意有所托”而将其视为何焯所言。检《义门读书记》,何焯仅云“回首以下。或有所托”,则此句当为杨伦借何焯话头所作之评点。(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95页。)所言“身世之感,无所不包,却只是说塔前所见”[9](P36)。由此可知,陆时雍所言“虚摹”首先作为一个正面的评价,更多关注的是杜甫以抒情为主,善化景物为情思的诗歌作品。具体而言,“虚摹”指的是杜诗“抒情气息之浓郁畅快”,而“吞吐含情,神行象外”则是“诗歌展开过程中呈现的动态形象,即流贯于诗歌动态形象中的‘神理’”[10](P469)。
陆时雍虽然高度肯定了杜甫善用“虚摹”抒情写意的艺术手法,但在写景状物方面,他对于“虚摹”“过形”的作品又是否定的。首先,“虚摹”作为一个否定性的评价曾出现在陆时雍对曹丕《于盟津作》的评语中:
“遥遥山上亭,皎皎云间星。远望使心怀,游子恋所生。”随境自成,不烦专设。……后人却撮入一语一字见奇,又以虚摹巧绘逼其意象,便拙。[7](P36)
此处“虚摹”与“巧绘”合说,分明地表达了陆时雍对于“后人”有意刻画景象的否定态度。而这种“虚摹巧绘”落实于创作则具体表现为对意象的经营安排,陆时雍以为“拙”。
其次,陆时雍曾批评杜甫“虚境过形”。他在评韩愈《山石》一诗时说:“李、杜虚境过形,昌黎当境实写。”[7](P972)此处的“虚境过形”虽然也与“实写”对举,但很显然它并非一个正面的评价。这与陆时雍对于诗歌在写景状物之时应当如何处理虚实关系的认识有关。陆氏认为“诗须实际具象,虚里含神。沈约病于死实”[7](P202)。所谓“虚里含神”,当如他评江总《赋得三五明月满》中“只轮非战反,团扇少歌声”句“生韵流动,所谓死者活之,实者虚之,点铁成金,借形出相,一往神行乎其间”[7](P291),又如他评庾肩吾《奉使江州舟中七夕》云“‘织女欲攀舟’,写得生动。所谓死者活之,实者虚之,诗家作用,端在等处”[7](P224),即诗人在“当境实写”之下,又能不拘泥于实地实景,通过虚拟摹写使月夜之景活现。也就是说,陆时雍并不反对用虚,“虚境过形”所批评的是写景状物方面过分地虚拟形容。陆时雍这里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虚摹”这一概念,但“虚境过形”所传达的意思实际上与“虚摹巧绘”大致相同。
再者,对于后来批评者以为写景状物入神的《登岳阳楼》,陆时雍亦是不喜的。他说道: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自宋人推尊至今,六七百年矣。今直不解其趣,“吴楚东南坼”,此句原不得景,但虚形之耳,安见得洞庭在彼,东南吴楚遂坼为两耶?且将何以咏江也。至“乾坤日夜浮”,便悬虚之极,以之咏海庶可耳,其意欲驾孟浩然而过之。譬之于射,仰天弯弓,高则高矣,而矢过的矣。[7](P752)
而清人沈德潜称赞道:
孟襄阳三四语实写洞庭,此只用空写,却移他处不得,本领更大。[11](P360)
杜甫登岳阳楼而言“吴楚”“乾坤”,则“目之所见,心之所思,已不在岳阳矣”[12](P7),这确实是“空写”“虚形”,与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摹写实地、实景不同。但面对杜甫的“空写”,沈德潜与陆时雍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沈德潜认为杜甫写出了洞庭湖的精神,也写出了自己身处岳阳楼的真感觉,故言“移他处不得”“本领大”,即写景状物传神。而陆时雍以为杜甫“虚写”过头,反失其真,所谓“悬虚之极”,“弯弓高”而“矢过的”正是上文所说的“虚境过形”,这在他看来是一种刻意的经营安排,亦即“虚摹巧绘”。
总之,就写景状物而言,陆时雍使用“虚摹”一词意在批评诗歌中有意的刻画与经营安排。在他看来,杜诗往往虚拟摹写景物,容易走向“虚摹”“过形”的极端,这是他所否定的。但从抒情的角度而言,陆时雍也用“虚摹”来概括肯定杜诗抒情浑沦自然的艺术。陆时雍对“虚摹”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解,反映了他诗学思想的矛盾性,以及在接受杜诗上矛盾的态度。而这归根结底又与他本人把含蓄自然之美视为诗歌创作最高的审美理想有关。因此,无论是“虚摹”概念的使用,还是对杜诗艺术的理解和阐释,都更多地带有其个人色彩。
从回护中寓感慨,字字排空,却字字跖实。其妙多端,不可名状。今人求其说而不得,遂以虚摹为绝诣,恐境地全隔。[13](P438)


三 “虚摹”与杜诗传神写照的艺术境界
“虚摹”的概念到了清代基本清晰起来。特别是在杜诗评论中,批评者使用“虚摹”普遍观照的是杜甫想象、虚拟的艺术手法,且开始强调虚与实的辩证性。他们最终的落脚点已不再是“虚”,而在“实”与“真”上,由此深入发掘并高度肯定了杜诗描绘物象入神的艺术境界。
1.化实为虚——想象揣度之语
“虚摹”一词中的“摹”本身是中国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中较为常见的概念术语,最初常运用于书画领域。作为一种书迹复制的方法和学书的技巧,“对着底本摹写或画”,或是通过“拓”“影写”等具体方法“覆在范本上摹制”,是“摹”这一概念的主要内涵。[19](P169)无论是“传移模(通‘摹’)写”[20](P17),或是“摹拓妙法”[21](P38),“摹”“摹写”都具有模仿、试图再现事物形象的含义。这也是“摹”运用在诗文创作、批评中所具有的基本内涵。(10)“摹”运用在诗文创作中,还具有对其他文学作品进行模仿、摹拟的内涵。本文所论“虚摹”手法主要以客体自然世界与主体内心世界为观照对象,不关涉此种含义。如仇兆鳌评杜甫《湘夫人祠》中“虫书玉佩藓,燕舞翠帷尘”句“摹写祠中景物,自见庄雅”[22](P2369),又如浦起龙评杜甫《万丈潭》中“黑知湾澴底,清见光炯碎。孤云到来深,飞鸟不在外”四句“摹写潭身。‘黑知’‘清见’‘孤云’‘飞鸟’,两实写,两虚摹”[23](P81),他们使用“摹”“摹写”这些概念的含义大致相同,都表示为杜甫对庙宇、山川等实地景物的形貌或是状态进行描写、摹画。因此,“虚摹”它首先属于对现实事物进行观照后的一种“摹写”。
但“摹”有虚、实之分别。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虚摹”作为与“实写”相对而言的概念,含有想象之意,这也是清代杜诗批评者所使用“虚摹”概念的基本内涵,即经过想象、揣度后对现实事物进行描写、叙述。“实”指实际的事物,而“虚”则往往非实际所见、所历,有时亦略带虚幻的成分。如浦起龙评杜甫《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云:
前八,就“稻畦”写,中八,就“行官归”后写,后八,就秋成写。全首总属虚摹,时未亲阅东屯也。[23](P175)
据黄鹤所言,该诗乃杜甫还未迁居东屯时所作(时居瀼西)。[24](P225)东屯补水之事、稻畦之景杜甫并没有亲历、亲阅,只能是听闻、想见,因而浦起龙言“全首总属虚摹”。诗中“虚摹”之笔即如“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摹写补水前稻秧无浸润之情景,“芊芊炯翠羽,剡剡生银汉”,摹写补水后稻秧之青葱、畦水之明净,皆为“分明”之想见;又如“秋菰成黑米,精凿傅白粲。玉粒足晨炊,红鲜任霞散”,摹写畦中收获的丰富壮观,也不过是秋成之预想。浦起龙用“虚摹”概括杜诗想象、揣度之笔还见于他评《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之时。该诗作于杜甫携家居白水,舅崔氏设宴于高斋之际。诗中自“坐久风颇怒,晚来山更碧”以下十四句,摹写了傍晚远望之景象,浦起龙评其中“兵气涨林峦,川光杂锋镝。知是相公军,铁马云雾积”四句云:
白水去潼关且四百里,安得云近?亦遥相(笔者注:“想”)虚摹之词耳。[23](P26)
“安得云近”针对的是朱鹤龄提出的“时翰统兵二十万守潼关。潼关属华州,与白水近,故见兵气之盛如此”[23](P26)的说法,浦起龙并不认同。在他看来,杜甫傍晚于高轩望岳,“前轩颓反照,巉绝华岳赤”可实见,为“实写”。“兵气”“锋镝”“铁马”遥不可见,应为杜甫想象、摹拟之词。而且,此前的“相对十丈蛟,欻翻盘涡坼。何得空里雷,殷殷寻地脉”,摹写蛟龙翻盘涡、涧水寻地脉,与“兵气”一样亦非实景,实际上也是杜甫因坐久风怒想象、“虚摹”而来,所以浦起龙评论“兵气”四句时才有“亦”“虚摹之词”的说法。除此之外,仇兆鳌亦曾以“虚摹”评说杜诗。他评《望岳》“岱宗夫如何”以下六句为“实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二句为“虚摹”[22](P5)。“虚摹”指登绝顶、览众山乃“身在岳麓”的杜甫“神游岳顶”“冥搜而得”,亦即非即目亲见之摹写。
从非实景描写,想象、揣度这一层意义而言,“虚拟”“摹拟”等可视为“虚摹”的同义词。如浦起龙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起就新障作虚摹势。”又云:“‘野亭’六句,才写画中景物。前皆虚拟,此乃实描也。”[23](P244)“虚摹”“虚拟”指杜甫摹画之词——“生枫树”“起烟雾”,“元圃裂”“潇湘翻”,坐“天姥”、“闻清猿”,“风雨急”“鬼神入”,障湿、天泣,都是他因眼前新画山水屏障所发之奇想。又如浦起龙评《草阁》“鱼龙回夜水,星月动秋山”二句前为“虚拟”,后为“实拈”[23](P503)。这里的“虚拟”与前所用“虚摹”“虚拟”含义也基本相同,意在说明“鱼龙”潜游乃杜甫秋夜临阁观水时产生的想象。
2.由虚入实——传神写照之境
事实上,李白也经常使用这种“虚摹”“摹拟”的手法。浦起龙评杜甫《龙门阁》时曾指出:“太白《蜀道难》,亦未免虚摹多,实际少。”[23](P86)正是看到了二人在通过想象虚拟景物方面具有相似性。但杜诗的“虚摹”又不同于一般的想象、虚拟以追求玄幻之境,它保持了“摹”本身所具有的求真内涵,“虚”非玄虚。杜甫最终通过“虚摹”创造了一种更高的“实”,即批评者所褒扬的杜诗“神境”“神理”。也就是说,“虚摹”不仅指化实为虚,还指能由虚而实,即杜甫能通过想象、揣度体贴现实事物之性情,最终使有限、固定的景物、形象变为无限流动、生动鲜活的形象。这是清代杜诗批评者所使用“虚摹”概念的重要内涵。
何焯评杜甫《孤雁》一诗十分具有代表性。他评颈联“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云:
遥遥一雁在前,又隐隐一群在后,虚摹“孤”字入神。[12](P1228)
我们可以结合整首诗来理解何氏此处所言“虚摹”之义。该诗乃摹写一孤飞之雁。首、颔联“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以及尾联杜甫借以相形的“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都是作者可见、可闻之实景。而“望尽”二句,摹写大雁似见、如闻其群,显然已经是杜甫想象、揣度的情景了,即浦起龙所言“惟念故飞,‘望断’矣而飞不止,似犹见其群而逐之者;惟念故鸣,‘哀多’矣而鸣不绝,如更闻其群而呼之者”[23](P523)。也就是说,杜甫由“雁”“飞”“鸣”之实,揣度、虚拟了其逐群、呼群之势。他所摹画的已不仅仅是大雁可见的样貌与姿态,而是形态之下所含敛的鲜活的精神。由此可见,何焯说的“虚摹”“入神”指杜甫能摹写出孤雁念群之精神、心境,这使得诗歌中雁的形象流飞、生动了起来。浦起龙“写生至此,天雨泣矣”[23](P523)称叹的正是该句能“虚摹”“入神”。杨伦亦评该诗云:“公诗每善于空处传神。”[9](P829)“空”即“虚”,非实景,而“空处传神”,其实也就是“虚摹”“入神”。
又如翁方纲评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云:
“上云”内之“数公”“此人”皆实也。“下云”内之“风云”“龙虎”则虚摹写也。所以又必加“下云”四句之虚摹写,而后上云云之神乃足也。[25](P653)
“上云”即诗中“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即“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这两部分其实都是在追叙房、杜、王先世之交谊,简括识主、开国之事。翁方纲认为,英俊相交,少年为首是实写,即叙述君臣遇合之实际。而“风云合”“龙虎吟吼”是“虚摹写”,即是从现实中虚拟出来的话,为了使“数公”之形象神完气足。可见翁方纲使用“虚摹”一词关注的同样是杜诗传神写照的艺术手法。
再如,浦起龙评杜甫《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罗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为毛骨有异他鹰,恐腊后春生,骞飞避暖,劲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见,请余赋诗二首》云:
须知二鹰在山,本非王监所有,亦非公所亲见,自不应在毛色着想,正须凌空摹拟,以表其奇,此超与滞之辨也。[23](P661)
这里浦起龙没有直接使用“虚摹”一词,但“凌空摹拟”亦可作为“虚摹”的同义词与“虚摹”互释。该诗意在摹写山中白、黑二鹰。从诗题“见王监兵马使说”可知,鹰为实物,但杜甫并未亲见,所言皆为想象、揣度。但想象也有“滞”与“超”之别。浦起龙所言“滞”,当即摹写鹰之毛色体态,而所谓“超”,称赏的是杜甫能够“凌空摹拟”,亦即摹写二鹰之精神、风度。通览全诗,除“雪飞玉立尽清秋”“黑鹰不省人间有”“金眸玉爪不凡材”乃通过推想摹写鹰之毛色外,“不惜奇毛恣远游”,“一生自猎知无敌”,“正翮抟风超紫塞,玄冬几夜宿阳台”云云皆从鹰之精神、品性着想。正如仇兆鳌所云:“黑白其形色也。题中罗取未得,劲翮思秋,此鹰之精神骨力也。诗从神力上摹写其迅捷英奇,正深于体物者。”[22](P1923)仇氏、浦氏一致认为,杜甫正是通过“虚摹”实物,写出了鹰的真精神。
从摹写入神这一内涵来看,杜诗批评者所言“摹神”亦可视为“虚摹”的近义词。如杜甫《反照》云:“反照开巫峡,寒空半有无。已低鱼复暗,不尽白盐孤。荻岸如秋水,松门似画图。牛羊识僮仆,既夕应传呼。”仇兆鳌(11)仇氏自注此句引自《杜臆》。今检此书,其文云:“中四句半有半无各分,而尾句在有无之间。”由此可知“写影”“摹神”乃仇氏之语。(王嗣奭《杜臆》,《续修四库全书》第1307册,第572页。)以为:“中四写影,各分有无之半。末二摹神,想入有无之间。”[22](P2103)“已低”“不尽”“如”“似”描绘的都是夕阳之下物色在若有若无之间的实景,故仇氏曰“写影”,亦即实写。末二句云“既夕”,“则光全敛矣”,“牛羊”其实未见,杜甫却“能于无形中写出有声”[9](P866),故仇氏谓之“摹神”,亦即“虚摹”“入神”,它是对“反照”之景更真实生动的一种写照。又如仇兆鳌指出,《登高》一诗中“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两句“多用实字写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则“多用虚字摹神”。[22](P2138)这里的“摹神”称赏的也是“无边”“萧萧”“不尽”“滚滚”等描写形容,生动刻画出了秋日登高所见“落木”“长江”的声色与神态。
另外,黄生曾评《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中“暗度南楼月,寒深北渚云”二句“写彼地之雪,意中想象”,“不写雪之意,而写雪之神”(12)仇氏《杜诗详注》引黄生注,“写雪之意”作“摹雪之状”。[26](P198),浦起龙评《万丈潭》中“孤云到来深,飞鸟不在外”为“虚摹”潭身之笔[23](P81),王嗣奭也指出该句写出了潭水“虚明空洞,无底无边神妙”[27](P445),他们有的虽然没有使用“虚摹”的概念,但其实都关注到了杜诗“虚摹”之笔有远神,即能写出人物、景物之气韵、精神的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从写景状物的角度而言,清代杜诗批评者所言“虚摹”非“规规传神写照”,亦非“泛然驾虚立空”[22](P850),他们使用这一概念是试图将诗歌审美向深处延伸,欣赏的是杜诗所创造出的有别于所观照对象(实景、实物)而又生动活泼的,具有独特的、鲜活的精神或品格的审美意象。正如张方在论艺术审美“由实而虚”(即“从外在的形貌和声采转向了内在的精神和韵味”)时所言:“相貌和景观本身是固定、机械的,而它的特有的精神和风韵却是灵动、活泼和悠远的。就审美而言,这显然是非一般的视听可以抵及的虚境。”[28](P13、15)清人“虚摹”概念所揭示出的正是杜诗中非一般视听可以抵及的审美虚境,这是一种更高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