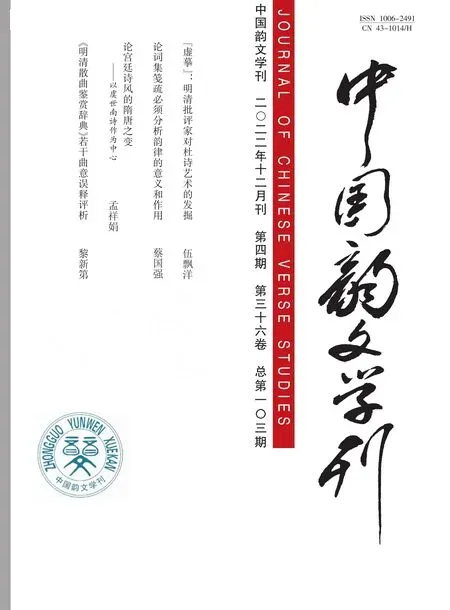论姜夔“峭拔”词风的营造
吴亚萍
(深圳大学 中文系,广东 深圳 518061)
张炎《词源》谓姜夔词“清空则古雅峭拔”[1](P259),戈载在《宋七家词选》中说白石词“其高远峭拔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2](P309),唐圭璋亦谓其“清空峭拔之致,求之两宋,实罕其俦”[3](P970)。关于姜夔的“清空”词风,学界已多有论述(1)参见袁向彤《南宋“清空”词风辨——兼论拗峭句式和音律的运用》,《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智凯聪《以“清空骚雅”为美——姜夔词乐美学探究之二》,《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赵维江、谷卿《“清空”“骚雅”内涵新释——以张炎与姜夔之词学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郭锋《论姜夔词的“清空”》,《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至于“峭拔”,“峭”本意为“山峻拔峭绝”[4](P239),“峭拔”指山高而陡、险峭,借指劲健、有骨力的词风,有研究者从姜夔词的结构、用笔和受越文化影响方面考察了他用峭劲救软媚的词风特点(2)参见庞维跃《试论白石清空峭拔的词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杨万里《越文化对姜夔“古雅峭拔”审美意识的影响》,《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但忽略了形成其“峭拔”词风的其他方面。姜夔“峭拔”词风的形成,与他对词中环境的营设、字眼的锤炼、意象的选择、句法的设计及音乐的配置都有密切关系。
一 造高峭之物境
姜夔常在词中设置高峭之景,熔铸天地山川来表达情思,使词的境界更为高挺、阔大,这是形成其峭拔词风的因素之一。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姜夔游览处州括苍山,登临范成大主持修建的烟雨楼,追和范之题词作《虞美人》,其序云:“括苍烟雨楼,石湖居士所造也,风景似越之蓬莱阁,而山势环绕、峰岭高秀过之。”[5](P117)以“山势环绕、峰岭高秀”来突显烟雨楼的位置、环境,词起首云:“阑干表立苍龙背,三面巉天翠。东游才上小蓬莱,不见此楼烟雨未应回。”[5](P117)烟雨楼高立于山冈之上,三面危崖、翠意连天,显出一派陡峭高险之象,叶绍钧曾在《周姜词绪言》中指出:“《虞美人》里的‘东游才上小蓬莱,不见此楼烟雨未应回。而今指点来时路,却是冥濛处’。尤其有辛词的豪放的神韵。”(3)按:文中所引白石词,据唐圭璋《全宋词》对其句读有修订,韵脚用句号,非韵脚用逗号或顿号,下文同例。[6](P142)词开篇营造的高峭环境,则为这种豪放神韵打下了基调。又如《虞美人·赋牡丹》(其二)起句便写南岳山势:“摩挲紫盖峰头石,下瞰苍厓立。”[7](P126)营造出苍崖高悬、壁立千仞的景象。再如《汉宫春·次韵稼轩蓬莱阁》云:“更坐待千岩月落,城头眇眇啼乌。”[7](P110)千岩高峙,月落乌啼,凄清高峭之景如在眼前。《法曲献仙音》也是如此,此词赋张彦功官舍,小序云:“张彦功官舍在铁冶岭上,即昔之教坊使宅。高斋下瞰湖山,光景奇绝。”[7](P130)交代出官舍所处的高峭环境。词起首曰:“虚阁笼寒,小帘通月,暮色偏怜高处。树鬲离宫,水平驰道,湖山尽入尊俎。”[7](P130)楼阁高与月齐,可鸟瞰湖光山色,展现了一幅“暮色偏怜高处”的绝妙图景。
清末诗人陈曾寿受到姜夔《法曲献清音》词境的启发,取此词首句之意,为林则徐侄孙林葆恒作《讱庵填词图》。姚达兑曾在《清遗民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林葆恒和六幅〈讱庵填词图〉》一文中对此图画进行研究。他影印了陈曾寿所绘之图,陈曾寿在画上的落款云:“子有老兄,属绘填词图,经年未作。偶忆白石‘虚阁笼寒,小帘通月,暮色偏怜高处’之句,真乃词中妙境。因取真意为图,聊以应命,即祈正之。”(4)按:144页引文“小廉通月”之“廉”字有误,据《讱庵填词图》题跋原文和姜夔词修订为“帘”。[7](P144)姚达兑将此画描述为:“上面的楼阁,由巍然的山崖托起。下方则由松柏和杂石相衬。……从阁楼上眺望,可见月色下,远山依稀、江景迷离。”[7](P145)他指出陈曾寿创作此画的意图是以山水来烘托和衬染遗民形象。从《讱庵填词图》和姚达兑的描述可见,画上图景完全是姜夔《法曲献仙音》景观的再现,那么这种环境和陈曾寿要塑造的遗民形象有什么关系呢?南宋柴望在《凉州鼓吹自序》中对白石词的评述或可解释这一点,他说:“唯白石词登高眺远,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兴之思,殆与古《西河》《桂枝香》同风致,视《青楼歌》《红窗曲》万万矣。”[8](P1104)意谓姜夔设置高峭之景,“登高眺远”以“感今悼往”、托物抒怀,呈现出新的风格特征,远胜《青楼歌》《红窗曲》类的绮靡词风,肯定了高峭物境对姜夔开创新词风的作用。清代王鸣盛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评《巏堥山人词》时说:“如姜、张之多作登临山水、怀古咏物、送别酬唱语。”[9](P639)陈曾寿正是取姜夔词登临高处、怀古悼往之意为画境,来展现遗民群体面对江山改、人物异的内心苦痛。这说明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都对姜夔在词中设置高峭之境的情况深有体认。
姜夔在词中设置峭拔之境,不只是为了“登高眺远”和“感今悼往”,还有表达高蹈之志的作用。如《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姜夔用“使君心在,苍厓绿嶂”[5](P114)来赞誉辛弃疾的品格——虽然辛弃疾在上饶带湖、铅山瓢泉的归隐生活是被朝廷冷落的无奈之举,但此处的“苍厓绿嶂”代表了一种高逸、远离政治的品格和态度。
姜夔不仅将山岩崖嶂之景写得危危然而高峭,普通的花木,他也描写得十分峻拔。如《玉梅令》咏梅,“有玉梅几树,背立怨东风,高花未吐,暗香已远”[5](P59),梅树并不顺应风势,而是倔强地“背立”东风,且“高花”未许攀折,显出梅树的孤傲、挺峭。姜夔写柳树也多以“高”来形容——他当然也写过“细柳”“残柳”,可需要突出柳的峭拔时,就说“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惜红衣》)[5](P27),为品性高洁的蝉配上可栖的高木。《念奴娇》(闹红一舸)也用“高”形容柳,云:“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5](P38)除“高柳”外,该词还有两处写花木之高峭,词前小序云“古城野水,乔木参天”,不仅乔木高大,连荷叶也高得不同寻常:“秋水且涸,荷叶出地寻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5](P38)水涸荷露,离地“寻丈”,“寻丈”在八尺到一丈间,按宋代的度量衡来计算,高达3米。咏荷而将荷叶写得如此高举、峭拔是很少见的。瞿佑曾评姜夔诗曰:“姜尧章诗云:‘小山不能云,大山半为天。’造语奇特。”[10](P31)谓姜夔诗将常见景物刻画得奇绝脱俗,实际上其词亦如此,时以奇语摹奇景。《砚北杂志》云:“近世以笔墨为事者,无如姜尧章、赵子固。二公人品高,故所录皆绝俗。”[2](P62)虽然这说的是书法,但反映了姜夔的审美情趣,姜夔词中多峭拔、绝俗之景,正是其孤高人品在造景上的折射和外化。
二 炼健峭之字眼
姜夔曾“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后“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11](自叙1),但江西诗派作诗之法影响到了其词的创作。姜夔在创作中注重炼字,尤其是在动词的使用上,常有惊心动魄之感。陆辅之《词旨》将姜夔的“波心荡、冷月无声”“千树压、西湖寒碧”“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等都列为“警句”[2](P67),这当然与姜夔的炼字有关。除陆辅之列出的“荡”“压”“惯”“说”等字眼外,姜夔词中还有“唤”“逐”“洒”“立”“点”“佩”“湿”“舞”“打”“商略”等诸多炼字,它们本身就是动词,呈现出趋向性、动作性和力量性;而且这些字几乎都是仄声字,从语音学的角度看,上、去声是降调,发音时舌体的姿势先拱起,再下降,发声就显得有力;入声字发音方式多数是先塞或擦,再阻塞,发音急而短促,顿挫中更显力度,词是歌唱文学,文字的发音方式自然会影响到演唱效果,歌者演唱、听者聆听和读者吟诵时,均会感受到这种发音带来的力量感。历代词评家对其炼字均有体认,如《词综·序》云“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12](P1),《词坛丛话》谓姜夔“琢句炼字,归于纯雅”[2](P438),《词洁》评姜词曰“‘无奈苕溪月,又唤我扁舟东下’,是‘唤’字着力。‘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是‘荡’字着力。所谓一字得力,通首光采,非炼字不能然,炼亦未易到”[13](P146),指出姜夔炼字之精妙。姜夔亦颇为自得,如“荡”字他会反复使用,除《扬州慢》的“波心荡”[5](P1)外,《一萼红》云“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5](P5),《庆宫春》也有“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5](P77)之句,三个“荡”均为摇荡之意,但有细微差别,“波心荡”是水波荡漾的泠泠之意,“荡湘云楚水”“荡云雪”是以楫摇荡,但都带来心境上的波动、飘荡和不稳定感,这或许反映了姜夔四处游历、干谒权贵的境遇和心态,这在其词乐中也有体现,如杨荫浏、阴法鲁二人和丘琼荪对其自度曲《扬州慢》的译谱中,“荡”字皆以大六度作下跳处理,曲调突然跌宕,突出了这种不稳定感。再如“逐”字,《踏莎行》云“离魂暗逐郎行远”[5](P25),《醉吟商小品》亦云“梦逐金鞍去”[5](P47),都是以幻笔刻画对意中人的依恋,“逐”字有倩女离魂的“鬼语”之感。姜夔使用频次最多的还是“压”字。邓廷桢的《双砚斋笔记》云:“朱希真之‘引魂枝,消瘦一如无,但空里疏花数点’,姜石帚之‘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一状梅之少,一状梅之多,皆神情超越,不可思议,写生独步也。”[14](P392)“压”字是“状梅之多”的点睛之笔,凸显了树之挺拔、枝之繁盛、花之厚密,也展现出梅枝逼向湖面的势能与动感,梅树的高拔峭劲之态全出。除梅花外,在书写其他花木时,姜夔也会用到“压”字,如《洞仙歌·黄木香赠辛稼轩》云:“花中惯识,压架玲珑雪。”[5](P111)用“压”字写花朵的茂盛和沉重。《虞美人·赋牡丹》其一云:“娉娉袅袅教谁惜,空压纱巾侧。”[5](P126)以“压”突出牡丹的硕大,娇柔的花朵立时有了骨力。同样以健笔写花朵,韩愈用的是“芭蕉叶大栀子肥”[15](P145),韩愈的刚健之气从描摹物状中来,姜夔却用动词来表现花的形态与劲力。当然,姜夔对“压”字的使用不限于花木,如《阮郎归》云:“红云低压碧玻璃,惺愡花上啼。”[5](P73)用“压”突出西湖上云层之低重。《庆宫春》则以“压”来写意中人的愁态,“伤心重见,依约眉山,黛痕低压”[5](P77),“黛痕低压”使哀愁有了不能承受的重感。诗词对字词尤其是动词的使用,是带着主观情感的,“压”字体现了姜夔笔下物、景、人的情态,也间接流露出其心境,不难看出,倦游江湖和四处旅食的人生境遇、所处时代政治气象的低迷,给姜夔带来的沉重压迫感。对于姜夔的炼字,唐圭璋曾云:“白石词重音律,崇典雅。语语精炼,敲打俱响。”[3](P970)铿然有声,字字敲打得响,这是对姜夔炼字艺术的高度评价。
我们还可以从清代词人蒋春霖对姜夔“压”字的借鉴与使用上,体会其炼字为作品带来的健峭骨力。蒋春霖身世际遇与姜夔相似,《清史稿》评其词云:“彷徨沉郁,高者直逼姜夔。”[16](P13362)言其词风与姜夔类同。蒋春霖对姜夔词的体认相当深刻,对其炼字炼意也多有摹仿,如果要拈出蒋春霖词作中最具代表性的炼字,当是他从姜夔处借来的“压”字。如《瑶华·败荷》的“罗衣叶叶寒未剪、乱压一湖深翠”[17](P39),明显是来源于姜夔的“红云低压碧玻璃”;《鹧鸪天》的“屏间山压眉心翠”[17](P70),用意也与姜夔的“伤心重见,依约眉山,黛痕低压”相仿。又如《一萼红》的“压雪檐低,垂萝径窄,红萼开、倩谁簪”[17](P47),以“压”写雪重寒深,反衬梅之傲骨。《扫花游》云“压春潮、一船幽恨”[17](P9),“压”将幽愁暗恨具象化,喻写愁之深重。最典型的是《凄凉犯》一词,蒋在词中两次用到“压”字,词前小序云:“十二月十七日夜,大寒。读书至漏三下,屋小如舟,虚窗生白,不知是月是雪。因忆江南野泊,雪压篷背时光景,正复似之。”以“雪压篷背”来比拟其居所,因换头处有“回首垂虹夜,瘦舻摇波,一枝箫咽”[17](P32)句,当知“雪压篷背”为白石过垂虹之事,蒋明显是以姜夔之境自拟,这个“境”是处境,也是心境;另一“压”字在下阕收尾处:“却开门、树影满地,压冻月。”[17](P32)居所如压,月色如压,压抑摧迫之情和沉郁健峭之境顿出。陈廷焯曾以“才气甚雄,亦铁中之铮铮者”[18](120)评价蒋春霖之词,唐圭璋也认为其词格“峭拔像白石”[3](P1009),这种“铮铮”“峭拔”之气自然与宗法姜夔有关。
“炼字”使姜夔的词“硬语盘空,时露锋芒”[19](P1477),具有劲峭的骨力,这正是《藏一话腴》所说的:“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20](P548)这是白石词形成其峭拔词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择高洁之意象
姜夔词中最多的意象是梅和荷,他有18首咏梅词和多首咏荷词,代表作《暗香》《疏影》更被张炎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1](P266)。姜夔赋予了梅、荷隐曲而高洁的寓意,前人对此多有研究,但对其他意象则比较忽视。事实上,即使是姜夔词中用作背景和点缀的景物,也是精心选择的具有节操、高洁峭劲的意象,如竹、松、苔藓等。
如姜夔赋范村梅花的《玉梅令》,词序描述了“梅开雪落,竹院深静”[5](P58-59)的景象,这固然是范成大的园林中植有竹,但与姜夔的意象选择也分不开,他将竹设置为“玉梅几树”[5](P59)的背景,以竹的环境来显梅之绝俗、清峭。《暗香》也是如此,“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5](P60),不直呼梅,而代以“竹外疏花”,梅邻于竹、映于竹,更显梅之清雅高洁。《疏影》写竹则更巧妙,“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5](P61),化用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21](P670)之句,将梅比作空谷佳人,斜倚修竹,显梅之瘦硬。在描写范村以外的梅花时,也缀以竹,如咏西湖梅花的组词《卜算子·吏部梅花八咏,夔次韵》,其二云“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5](P120),以竹引出梅,显出清逸的标格。
松也是姜夔词中常用的陪衬意象。如《卜算子·吏部梅花八咏,夔次韵》其三云“玉蕊松低覆”[5](P120),其八有“御苑接湖波,松下春风细”[5](P121)句,高松覆梅,松风吹梅,呈现出健峭之气。又《喜迁莺慢·功父新第落成》云:“高卧未成,且种松千树。”[5](P90)张镃在苍寒堂植有松树数百株,姜夔撷松入词正好应景,且松寓高洁超逸之意,与“高卧”并置,体现了姜夔和张镃共同爱赏的“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22](P2462-2463)的晋人风神。在《汉宫春·次韵稼轩蓬莱阁》中,姜夔同样以松来表达高蹈之志,词云:“小丛解唱,倩松风、为我吹竽。”[5](P110)这用到了《南史》中陶弘景的典故:“(陶弘景)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23](P771)姜夔在怀古咏史的兴亡感慨中,借“松风”之音来协奏,是表达其高洁的归隐之志。又《洞仙歌·黄木香赠稼轩》云“自种古松根,待看黄龙,乱飞上、苍髯五鬣”[5](P111-112),“苍髯五鬣”典出段成式《酉阳杂俎》:“松,凡言两粒、五粒,粒当言鬣。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两株。”[24](P1273)谓黄木香枝蔓爬上古松,以松衬花,藤本的黄木香顿时有了高峭、苍劲和奇艳之气,用来喻辛弃疾才恰如其分。
姜夔词中用作配角的意象除松、竹外,还有苔藓,且使用“苔”“藓”的频次比松、竹还高。如《疏影》起首便云“苔枝缀绿”[5](P61),《清波引》云“岁华如许,野梅弄眉妩。屐齿印苍藓,渐为寻花来去”[5](P14),《卜算子·吏部梅花八咏,夔次韵》其三、七、八分别云“藓干石斜妨”[5](P120)、“折得青须碧藓花,持向人间说”、“此树婆娑一惘然,苔藓生春意”[5](P121)。姜夔频繁使用“苔藓”是有深意的:其一,苔藓的颜色是“绿”“苍”“青”“碧”色,营造出了冷色调的氛围,显出梅枝的老硬苍劲,也与红梅形成“破色”效果,呈现强烈的质感和画面感;其二,苔是起兴之物,引起观赏者清逸绝尘的“野兴”;其三,苔表明梅生长在孤清幽僻、人迹罕至之处,隐喻了作者不遇于时、为人冷落的境遇。“苔枝”“青须碧藓花”等苔梅意象的共构,实际是姜夔自身的隐喻符号,是作者追求的狷洁、孤峭人格的象征。苔藓是一种比德之物,虽然它生活在阴暗潮湿处,形体纤小、微末,但传统文化中的比兴和托物言志的传统赋予了苔很高的品格。江淹有《青苔赋》,谓青苔“必居闲而就寂,以幽意之深伤”[25](P58),“视青蘼之杳杳,痛百代兮恨多”[25](P59),寄兴于苔,既抒发身处僻远之地的幽恨,又寄寓人生短暂的感慨。杨炯有《青苔赋》云:“苔之为物也贱,苔之为德也深。夫其为让也,每违燥而居湿;其为谦也,常背阳而即阴。重扃秘宇兮不以为显,幽山穷水兮不以为沉。有达人卷舒之意,君子行藏之心。”[26](P59)将苔人格化,喻指君子的处幽不显、舍之则藏的高尚德操。王勃的《青苔赋并序》云:“宜其背阳就阴,违喧处静,不根不蒂,无华无影。耻桃李之暂芳,笑兰桂之不永。故顺时而不竞,每乘幽而自整。”[27](P14)谓苔能处僻地、不哗众、不竞时,具有洁身自好、怡然自乐的理想品格。姜夔笔下的苔藓,不仅涵盖了传统苔意象的所有内含,还有进一步的延展和发挥,如《八归·湘中送胡德华》云:“无端抱影销魂处,还见筱墙萤暗,藓阶蛩切。”[5](P16-17)用“藓”的景语表达与友人别离时幽寂的心境,《词综偶评》评此词云:“历叙离别之情,而终以室家之乐,即《豳风·东山》诗意也。”[2](P187)谓“藓”等意象具有和《豳风·东山》的“伊威”“蟏蛸”[28](P206)等类同的比兴作用;又《鹧鸪天》云“曾共君侯历聘来,去年今日踏莓苔”[5](P71),以“踏莓苔”代指去岁与张平甫共游西山之事,“莓苔”体现出其寻幽探僻、“尝遇溪山清绝处,纵情深诣,人莫知其所入”[2](P88)的烟霞癖好;《水调歌头·富览亭永嘉作》云“不问王郎五马,颇忆谢生双屐,处处长青苔”[5](P119),表达愿效谢灵运徜徉山水的高隐之志;“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齐天乐》)[5](P74),以井苔衬蟋蟀声,书写失意人的冷寂、愁苦;甚至还以“苔”来表现历史的沧桑巨变,“云鬲迷楼,苔封很石”[5](P114),“沈香亭北又青苔”[5](P126)。姜夔既以苔藓类比自身不遇于时、浪迹江湖的居闲境遇,抒发郁郁不得志的幽意愁绪,也以其指代林泉生涯,寄寓高蹈之志,更以之书写朝代兴亡。苔形体虽小,但它具有清逸远尘、孤高自得的内在品格和节操,并蕴含有深沉的历史感,因而和梅、荷、松、竹一样显骨力和峭劲。
四 设挺异之句法
正如张炎所说,姜白石等数家“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1](P255),白石词行文折宕劲峭,形成“挺异”的句法。
其一,起句的兀立。沈雄曰:“起句言景者多,言情者少,叙事者更少。”[29](P123)姜夔打破了此种惯例,起句多有“言情者”“叙事者”,如以“言情”起句的《解连环》:“玉鞭重倚,却沈吟未上,又萦离思。”[5](P57)又《江梅引》云:“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5](P80)再如《侧犯·咏芍药》云:“恨春易去,甚春却向扬州住。”[5](P131)以“叙事”起句,如《湘月》云:“五湖旧约,问经年底事,长负清景。”[5](P11)又《鹧鸪天》云:“曾共君侯历聘来,去年今日踏莓苔。”[5](P71)《念奴娇·毁舍后作》开篇云:“昔游未远,记湘皋闻瑟,澧浦捐褋。”[5](P11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反浅,曲者反直。”[19](P1489)周济所说的“浅”“直”可以理解为手法,词开篇不以叙景铺垫、渐行渐入,而是直抒胸臆或劈头叙事,有奇峭兀立和笼罩全篇之效。姜夔追求的是“如兵家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11](P328),起句常出入于“正奇”之间,如咏物词《虞美人·赋牡丹》,起句云“西园曾为梅花醉,叶剪春云细”[5](P126),又如《洞仙歌·黄木香赠辛稼轩》起首云“花中惯识,压架玲珑雪”[5](P111),两首词皆咏花卉但不直接写景赋物,而以叙事起句,此为一奇;《虞美人·赋牡丹》赋牡丹反从梅花写起,《洞仙歌·黄木香赠辛稼轩》赋黄木香却以白木香入笔,起笔皆不写所赋之本物,而从他物入手,此又为一奇。这种“正奇”变化,是在读者的既定阅读期待与词人的突破性创造中产生的,有出人意料的新奇与突兀感。陆辅《词旨》云:“起句好难得(谋篇难凑巧)。收拾全藉出场。”[1](P302)起句上的突兀“挺异”,使词开篇就有了奇峭之气,并笼罩全场。
其二,声律上的拗怒峭切。姜夔喜押仄韵、多用拗句,以声调的拗怒不谐突出笔风的劲健,这在其自度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姜夔17首自度曲,只有《扬州慢》《鬲溪梅令》2首押平声韵,其他15首皆押仄声韵,其中又有6首押入声韵。韵脚押平、仄声韵在声情表现上是不同的,平声韵音调舒徐,声情和缓悠婉;仄声韵音调转折,上声抑扬、去声劲切、入声顿促,具有内在的张力而重硬、刚劲,声情也显得或郁怒或幽怨或激切。姜夔还喜用拗句,如《霓裳中序第一》上下阕的末句“仿佛照颜色”和“醉卧酒垆侧”[5](P7),每句四个仄声字,仄声连用构成拗怒的音节,正适宜表现商调曲凄怆怨慕的情绪。再如《翠楼吟》押仄声韵,又拗句连用,逼仄短促,一显顿挫劲切之气。此外,姜夔还打破句子的常规节奏,喜用尖头句,避熟滑而求生涩,显出硬涩的声情特点。如《淡黄柳》[5](P44)的“看尽鹅黄嫩绿”和“唯有池塘自碧”用“二、四”句法,“都是江南旧相识”用“二、五”句法,“怕梨花落尽成秋色”是“一、七”句法,“问春何在”是“一、三”句法,皆为尖头句,上轻下重,节奏涩硬,显出奇峭之气。《暗香》《疏影》也多用尖头句,尤其是《疏影》,全词除四字句外,无一例外都是尖头句,郑文焯品评《疏影》时称其“出以清健之笔”[30](P101),“清”是姜夔的“清空”特色,“健”当是他认为该词有寄托:“此盖伤心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发言哀断。”[30](P101)言其兴感哀凄,内具骨力。实则“健”也从句法上来,仅以《疏影》上阕为例 ,“有翠禽小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5](P61)全为尖头句,节奏上生涩峭劲,的为健笔。

五 谱陡拔之旋律
为配合词句的“挺异”、情绪的转换,姜夔在自度曲的谱曲上,常有平地陡拔的旋律音程的设计。
旋律音程体现了两个音在时间上先后鸣响的横向关系,按照音程的大小,旋律音程分为狭音程和广音程。狭音程指三度和三度以下的音程,广音程是四度和四度以上的音程,在音乐行进上,狭音程是级进的,由狭音程构成的旋律一般较平和、宁静;广音程是跳进的,由广音程构成的旋律起伏跌宕较大。参照杨荫浏、阴法鲁和丘琼荪对姜夔自度曲管色谱的译谱,可以看到,姜夔常利用广音程达到跌宕高拔的音乐效果,这在其代表词作《暗香》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姜夔自度曲的音乐和文本应视为一个整体,关注音乐的振起之处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词作。如前所述,《暗香》中八度的旋律跳进有四处,这是音乐中的小高潮,也反映了作者的情绪变化:“不管清寒与攀折”,请佳人为攀摘梅花,词人是激动的,这是美好事物带给词人的心灵震颤;“何逊而今渐老”,是年华已逝却仍飘零江湖的悲慨;“红萼无言耿相忆”,“红萼”是双关语,既指梅花,也指合肥恋人,这在《长亭怨慢》中有句为证——“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5](P46)夏承焘曾评说“予又疑白石此词亦与合肥别情有关”,如“红萼无言耿相忆”等句“皆可作怀人体会”[5](P62),此种情绪也用音乐上的高潮来凸显;“长记曾携手处”是仍沉浸在回忆中不能自拔而带来的情绪波动。更多的词评家认为姜夔是有寄托的,如宋翔凤《乐府余论》云:“《暗香》《疏影》,恨偏安也。”[1](P2503)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其感慨。不独《暗香》《疏影》二章,发二帝之幽愤,伤在位之无人也。”[18](P29)邓廷桢亦云:“词家之有白石,犹书家之有逸少,诗家之有浣花。盖缘识趣既高,兴象自别。其时临安半壁,相率恬熙,白石来往江淮,缘情触绪,百端交集,托意哀丝,故舞席歌场,时有击碎唾壶之意。”[14](P407)“发二帝之幽愤”“击碎唾壶”的情绪自然是激越劲切的,《暗香》使用多处八度音程跳进,形成峭拔的旋律,以表达这种情感和意旨,这是音乐设计配合作品内容的必然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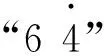
姜夔的词因“清空峭拔”的风格而自成面目,在婉约和豪放派之外别开一路,其词风沈义父称“清劲”[35](P48),周济称“清刚”[36](P3),朱庸斋称“幽劲”[37](P110),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称“幽峭”[38](P489),它们是同一内涵的词学批评术语,指“清空”中又用笔瘦硬、气格劲健、高远峭拔的词风。对“峭拔”词风的成因进行考察,能充分揭示白石词的美学意义及词学价值。且从现象学的角度,“峭拔”是姜夔作品“呈现于知觉”[39](P43)的产物,是读者和历代词评家综合感观体验的结果,尚有美学和心理机制上的深层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