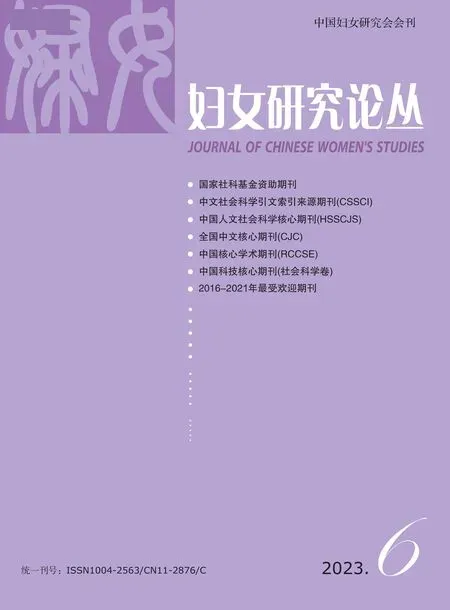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性别平等、技术革新与“翻身”叙事*
——以郝建秀的工作法及其生命历程为例
原璐璐 Nicola Spakowski 周晓虹
(1.3.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弗莱堡大学 汉学研究所,巴登-符腾堡州 弗莱堡 79095)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占据重要位置。由某一时期的物质生产力奠定的经济基础,不仅是上层建筑的决定性要素,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依靠人力与畜力的投入,其后则有赖技术的进步推动生产的发展。而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同样的劳动概念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涵。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不仅是物质产出的途径,还具有国家政治自主、社会关系变革和主体身份建构的多重作用,因此成为共产主义理论分析的核心。对这一理论的中国化应用也体现在共产党主导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之中,其中包括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使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工农业生产实践。而对占据一半人口基数的女性的劳动或工作动员的研究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研究的重要内容[1]。通过动员促成的“广泛的劳动参与”不仅可以使女性成为“国家建设事业的生力军”,也与“家务劳动社会化”及“儿童公育”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付诸实践的关键举措[2]。在此过程中,妇女劳动模范的引领作用值得重视。作为重要的社会动员和影响机制,妇女劳动模范无论是作为妇女通过生产获得解放的新宣言之范例,还是作为重新理解以劳动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切入点,都很重要。因此这一议题也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一、性别平等与技术革新:研究的缘起
以往有关妇女劳动模范的代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其中史明(Nicola Spakowski)对新中国成立前延安妇女劳动英雄的形象进行了分析[3]。通过论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想象下对国家和民族建设的考量,史明分析了延安妇女劳动英雄现象的形成、作为“新中国妇女诞生”的意义象征及其产生的广泛社会效应。在讨论了延安时期对“妇女通过劳动获得解放”这一新理念的成功形塑之后,史明将视野继续延展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女性劳动模范(或女劳动英雄)是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参与者,是社会主义转型的展演和象征[1]。通过追溯在农业领域争取同工同酬权益的申纪兰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三重情境下的活动,史明揭示了女性参与生产对传统性别秩序的颠覆作用,同时分析了作为不同行动者的国家、地方干部和农村妇女的特殊理想和不同利益如何汇聚到“同工同酬”的统一需求中。无独有偶,宋少鹏对申纪兰动员妇女参加劳动与西沟妇女们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历史展开了独到分析,呈现了劳动与性别作为新社会的两种组织方式如何帮助普通妇女在劳动过程中生成了自我主体性[4]。除了对全国著名的榜样性人物的分析,贺萧(Gail Hershatter)、高小贤和金一虹等学者对“银花赛”[5][6]和“铁姑娘”[7]中的普通妇女劳模群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重点探讨了妇女解放和农业革命的深层复杂关系,在各个议题上都具有开创性的奠基意义。
与农业领域相比,工业领域妇女劳动模范的议题在中外学界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不多的研究涉及“铁姑娘”群体[7]和“摩登劳模”黄宝妹[8]及另一位纺织女工劳模裔式娟[9]等典型人物。这些研究的对比分析显示了女性特质的隐蔽和彰显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对妇女劳动模范塑造的不同意义,以及从中凸显出的国家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多重维度和彼此间的显著张力。综上所述,以上所有深厚而细致的研究均显示女性受到“变革”着的现实以及与当时的地方、国家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的妇女政策的多重影响[1][3]。这也有助于我们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妇女解放的具体路径,避免空泛的概括和简单线性的“妇女史”研究。
妇女在工农业领域广泛地参与劳动和争取同工同酬的权利之后,其解放道路如何推进?社会地位如何进一步提升?这就涉及生产力演进的路径。显然,要促进生产发展,劳动的组织、管理以及劳动者的技能提升成为首要的考虑因素,是否掌握方法和技术也成为劳动领域分化、劳动价值分野以及劳动的阶级和性别分工的重要区隔。然而,以往对“妇女掌握技术”“妇女技术发明”等性别劳动与技术创新的关联及其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尚不够深广。有研究者曾对西方相关理论流派和观点进行梳理,指出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经历了从重新发现技术史领域的妇女身影和女性成就的“技术中的妇女问题”,到在社会与文化结构中探讨“性别—技术”相互形塑过程的“女性主义的技术问题”的理论转向[10]。其中涉及中国历史场域的著述并不多见,卓越的研究当属白馥兰(Francesca Bray)的著作《技术与性别:晚清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通过打破传统的技术史研究范式,白馥兰创新性地提出“女性技术”(gynotechnics)这一分析概念,将妇女纳入更宏观的技术体系(technical system)中去理解性别与技术的关系,继而论述了技术与性别是相互形塑和建构的动态过程[11]。
回眸国内当代妇女史研究也能够发现长久以来存在技术劳动视角缺席的问题。在集体主义时期的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普遍存在着男性执掌技术而女性大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助性工作的现象。即使在工业实践中部分女性典型在工作上有突出表现,也通常反映在工时与工作量上,而非技术创新方面[12]。针对这种现象,也有学者提出过反思。金一虹认为“铁姑娘运动”的最大局限是对平等权利的理解仅限于“男女同工同酬”,既没有推动女性争取平等学习和掌握核心技术、平等分享资源,也没有鼓励女性提出争取平等管理权和参政权的诉求[7]。针对“技术中缺少性别,性别中缺少技术”的双重缺位,新近的研究增加了对20世纪50年代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中妇女参与的讨论。例如,李如瓛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业技术革新中的妇女动员、性别实践和身份重构的系列分析,将技术革新运动看作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路径,指出通过动员妇女掌握技术推动了社会分工格局和性别秩序的重建[13][14][15]。这些研究重新发现了妇女与技术革新运动的历史关系,具有一定开创性。工厂生产场域之外,孔煜也同样以“性别—技术”视角对“大跃进”时期妇女参与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典型案例“三八饭店”进行了考察,指出国家通过发展具有集体生活福利设施性质的自动化设备来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对妇女史论域中如何处理妇女承担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双重负担”这一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解答。与此同时,其在对妇女劳动过程的探讨中引入的技术政治脉络和历史变迁视角也很有启发[16]。农业生产领域,张华、颜衡则以重庆璧山为例,梳理了合作化前后劳动性别分工的嬗变,指出在使妇女劳动进入水稻生产的核心环节中,技术革新和推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而突破“男田女土”的格局和逻辑,形成“男女共耕”的面貌,在农业劳动性别分工意义上开始了真正的平等[17]。
而在妇女广泛参与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之前,即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妇女与技术的关系如何?新中国的工业如何进行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奠基和发展?妇女技术劳动模范在其中的意义又为何?这些追问涉及本文要补充探究和继续推进的研究内容。通过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郝建秀及其工作法的采访、专题报道和口述史等文本材料,我们对郝建秀工作法的核心内容、创造和总结过程、宣传和推广以及产生的多重效益进行了解读,进而对郝建秀个人的生命历程及其经济、政治、社会和主体性意义进行了全方位解析,以此回应以郝建秀为代表的妇女技术劳动模范和新中国工业发展关系的现实问题,并进一步探讨性别、阶级和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相互型构作用。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技能习得与性别平等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着力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陆续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将此视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之两翼(1)最初,毛泽东估计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18年,即三年恢复时期(1949-1952)加上三个“五年计划”,但实际的发展要大大快于这个估计。从1951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历经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到1956年底已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与此同时,1953年11月开始的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大体完成。最后,通过“赎买政策”到1956年底同样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背景下,单就工业化而言,如何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大工业”,在承袭和推广延安时期已有的劳动观念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劳动模式[18]并使之引领工业化的转型,就成为这一时期的发展要义。具体目标则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由依靠时间、体力的投入提升为工艺和组织管理流程的改进;生产关系由“剥削与被剥削”改变为“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生产所得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整体战略推进。
首先,就生产力的提升路径而言,根据唯物史观,物质生产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力的技能提升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掌握技术能够促进体力劳动的升级和机器的迭代更新。延安时期,在蒋介石经济封锁和抗日战争的紧张局势下,根据地开始提倡人人参与的劳动竞赛,此时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以“大生产运动”增加农业产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落后不仅表现为先进机器等物质生产资料的匮乏,更表现为劳动工人数量和质量(技能)的双重不足。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发展策略中,除了继续强调和动员以人力体力增加为主的劳动时间和强度的投入外,同时在苏联援建和“向苏联学习”的号召下,不仅大力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设备,还十分注重操作技术提升、工作方法改进以及劳动的组织和管理制度的增强[2]。国家希望通过对新旧阶段劳动观念进行区别和改造的系列举措,把劳动力从传统手工生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高技能型劳动生产效率,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建设。
其次,除客观的迭代规律外,由技能带动的生产力提升还具有促进政治自主和变革社会关系的双重作用。显然,通过生产关系的系统改造,方能建立国家、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新的社会主义主体性。具体言之,集体主义时期中国的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国际政局上,受制于战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国家对于独立和主权的需求使得发展技术从一开始就被冠以自力更生的希冀。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以蔑视欧美为主的一切“洋权威”为要义,宣扬青年积极分子要敢于冲破任何教条和迷信、热烈追求一切最新的创造,并指称这是“共产主义劳动精神”的又一个表现[19]。而在国内的社会变革与改造中,则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群众观点,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此指引下,工业领域1960年确立了体现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三结合的“鞍钢宪法”[20]和“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21]。通过强调工人掌握技术的重要性,改变以往知识、官僚和资本精英阶层垄断文化教育和技术习得的权力后通过脑体之间的“剪刀差”收割底层工人体力劳动的局面,从而在阶级平等的革命追求下,以群众路线颠覆传统阶层格局、打破阶级壁垒,进而实现阶级身份转换。
再次,工人自身的价值认同、劳动的动力源泉及其对于理想人生的期盼也来自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双重满足。从延安时期到国家工业化初期,对劳动参与和技能提升奖励的制度变迁,体现了特殊历史情境变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激励手段由物质奖励到阶级地位提升、权利赋予再到精神塑造的转变过程。激励方式整体流变路径为由农业重要工具“牛”(2)见《晋察冀日报》报道中为奖励劳动英雄而举办的政治聚会及农民观众对于牛的反应。参见《政府奖给韩凤龄一条黑牛——涞源妇女劳动英雄受奖记》,《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4日,载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611-612页。的奖励到按劳取酬的“工资”(3)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进一步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党在政治教育之外也十分注重物质奖励,把对职工的思想教育和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结合起来,贯彻“按劳取酬”的工资政策,并认为“劳动得好,生产得多,就应该得到较多的报酬,这是十分合理的要求”。参见《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中必须合理地解决工资问题》,《人民日报》1952年4月26日。增加再到“无私奉献”不求所得,整体上表现为物质层面的逐渐弱化;劳动意义的锻造则经历了由“阶级翻身”到做“国家主人翁”[18]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逐步强化历程。
最后,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技能型劳动英雄或模范的数量发展、宣传报道形式及其带动作用视为党在改造和发展工业的现实主义目标下进行劳动重组和激励、施行群众路线和实现阶级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复合实践,具体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权力地位赋予和政治秩序的调整。不仅男女劳动模范都可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和社会影响范围也经历了从个别高山仰止的“劳动英雄”到许多日常可及的“劳动模范”再到每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这样逐步的扩展过程。
中国的妇女解放道路不同于西方,主要是由其自身所处的特殊政治社会环境决定的。在中国革命中,妇女问题总是与阶级问题相连,妇女解放也一直被认为是阶级压迫的终结,进而成为全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22]。早在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就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23](P84)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追求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实践[13],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双重作用。因此毛泽东说:“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4]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动员妇女广泛地参与社会劳动自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具有重要意义。妇女参与劳动不仅能够助推工农业发展,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内在要求。因而在以往的国家话语系统中,妇女解放以“生产劳动”为中心,“劳动”是实现女性身份转变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妇女解放”基本等同于“劳动解放”,妇女的身份认同也是在生产劳动领域中建立的[15]。其实,这一理念早在1943年2月2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就被系统宣扬,在1952年《新中国妇女》杂志《为完成增产节约任务促进妇女彻底解放而奋斗》的社论中又得到进一步弘扬:“妇女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妇女都参加社会劳动,也就是使全体妇女都变成工人,只有这样,妇女才能彻底解放。”[25]
然而在普遍参与生产劳动的目标实现之后,就经济领域来说,由于传统观念的禁锢、家务劳动的掣肘以及妇女自身文化知识和技能结构的欠缺,妇女职业的低层次化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女性参与的工业劳动大部分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女工在部门中主要起辅助性作用,难以涉足高技术领域,这就极大地阻碍了妇女解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与“铁姑娘”运动宣扬的“男女都一样”的体力比拼做法不同,新中国工业化初期动员妇女参与技术革新不乏试图破除技术的性别界域、打破男性对技术领域的垄断、鼓励妇女努力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技术核心的意图。通过让妇女在技术革新中学习、掌握、运用技术,成为技术的掌握者和“主人”,不仅能改变男女智力有差异的错误认知,承认女性的智力和创造性,还能促使女性迎来职业生涯的转折,从中获得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拓宽自己的活动空间和关系网络,彰显自身的社会价值,并进一步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除此之外,国家在技术革命运动中建立起的同工同酬制度,也能真正消弭男女在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给予两性同等发展的机会及保障,从而奠定妇女解放的经济基础并从根本上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格局[13]。
为了适应工业化和生产建设的需要,自20世纪50年代起,党和国家就开始鼓励女工积极参加各种职业教育,学习文化技术,还有部分女工进入大中专院校继续深造。对于关键的技术革新领域,更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红勤巧俭”竞赛运动、物质激励、评先晋升和后方保障等各种方式进行动员[14]。到1960年,全国各地已经有不少女职工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们发扬实事求是和敢想敢干相结合的共产主义风格,大胆创造,大胆革新,出现了许多优秀人物”[26]。在多种动员方式中,妇女劳动典型的塑造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报刊、广播等主流媒体的报道,配合漫画、电影、戏曲等艺术形式,宣传妇女劳动模范的人物形象和典型事件,以“先进旁边无落后,巧姑娘左右皆英雄”的口号实现对女工群体的激励。在此影响下,全国出现了许多一人先进带动整个小组、车间、企业实现满堂红的事迹。如“天津棉纺四厂相玉兰小组帮助后进女工,使全组二十二人都达到市纺织能手的标准,被誉为‘集体主义之花’”[26];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器厂在同一时期也涌现出诸多因参与技术革新而受到表彰的女工群体,如“红霞姑娘组”“冲压三八红旗组”“刘玉华姑娘组”等[27][28],其中“刘玉华姑娘组”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功效数十倍[29]。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誉为“劳动英雄”或“劳动模范”,彰显了新中国妇女在参与经济、获得社会认同方面的潜质[3]。
三、“郝建秀工作法”:一位女工是如何成为技术革新能手的?
在20世纪50年代的众多妇女群英榜中,最夺目的当有两人:农业领域为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动员妇女参加初级社生产劳动、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申纪兰;工业战线则当属因创立“郝建秀工作法”而名闻遐迩的纺织女工郝建秀。郝建秀出生于1935年,山东即墨大翁村人[30]。因村子被日本人拆了建飞机场,全家流浪到青岛沧口,依赖父亲赶大车和母亲烙煎饼度日。郝建秀仅读过一年多书,后辍学捡煤渣帮助家庭维持生计。1949年青岛解放后,生产百废待兴,纱厂也开始大量招工,年仅14岁的郝建秀成为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4)国棉六厂的前身为始建于1921年的日商钟渊纱厂,1923年开工投产,先后被改名为钟纺公大第五厂、中纺青岛六厂,1949年6月被定名为“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细纱车间的挡车工。细纱车间的挡车工工作繁琐,对手、眼、脑的协调性要求较高。纺纱过程中要求防疵、捉疵,棉线线头若接不好就会变成疙瘩似的皮辊花(又称“白花”),只能被当作边角料清理。显然,皮辊花越多,纱线产量越低。因此,工厂在细纱质量上会严格把关,监管细纱挡车工提高原料的利用率,以“少出白花、多纺纱”为目标。
经过3个月的培训,1950年春节前郝建秀结业,随后开始独立值车。值车第一天,因另一女工请假,郝建秀被分配了300个纱锭,且又在两个不同的组,工作量陡增。手脚兼顾不到,自然出现了很多落纱造成的断线头。为此,她受到车间领导严厉的批评。经历这场挫折后,郝建秀开始认真琢磨纺纱技术,同时仔细观察老工人的操作,技能提升很快。肯动脑筋的郝建秀很快发现了断线头和皮辊花之间的关联,而断线头又与车面不洁时的花毛有关。通过随时而不是常规的定期清洁,工龄不过两年的郝建秀终于发明了一种可以防止断线的新方法[31],即后来被时任中华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称为“郝建秀工作法”[32]的“三勤三快”操作技术。郝建秀使用这一技术连续7个月将皮辊花率控制在0.25%以内,创造了全国纪录。她不仅被车间里的同事称之为“纺纱天才”,而且引起全国纺织工会和纺织工业部的关注。1951年8月,在陈少敏的推动下,年轻的郝建秀和她的工作法为中国的纺织行业乃至整个工业领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波”[32](PP20-22,PP36-38)。
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后,1952年郝建秀进入山东大学工农速成中学短期补习,第二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1958年,郝建秀中学毕业后旋即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纺织工程系,完成四年的本科教育后,1962年回到青岛国棉六厂工程师室任技术员,两年后晋升为工程师。此后,这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步入人生坦途:1965年起任青岛国棉八厂副厂长、青岛市委副书记、山东省总工会副主任、省妇联主任、省委常委;1977年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1982-1998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直至2003年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5)参见《郝建秀》,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gjjg/2008-10/22/content_1127272.htm。。
郝建秀之所以能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劳模典型,最初的原因自然在于“郝建秀工作法”的创立。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整体国力十分贫弱的背景下,这一工作法符合“增产节约”的基本方针。如果总结这一工作法,具体内容大致有三:其一,工作主动,有规律、计划和预见性;其二,生产合理化,能够把几种工作结合起来做;其三,抓住了细纱工作的主要环节——清洁工作,这样断头就少,产量高、质量好,“打破了一向认为‘车管人’的老规矩,创造了‘人管车’的科学工作法”[30]。在新中国工业发展初期,相比于技术领域突飞猛进的高要求,这种方法侧重于工作流程的精细管理,更易快速掌握和操作,因此被作为范本予以推广,并被认为“不仅适用于细纱生产方面,同时也适用于其他生产部门”[31]。
那么,郝建秀工作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或者说,一位女工是如何成为技术革新能手的?在郝建秀本人的叙事中,一开始其创新的动因是为了克服打盹,继而为提高工效自我钻研;接下来转变为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了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力量”,从而提高了自我意识,“下决心要好好生产”并“虚心努力地向老工人学习”[33]。上述劳模的成长叙事,体现了“党领导的动员”与“从群众中来”的双向形塑路径。当然,这位普通女工最终成为技术革新能手,与那个时代塑造典型的独特方式密切相关:在郝建秀创造全国最低皮辊花率的新纪录后,同样在青岛纱厂做过童工、被毛泽东称为“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6)在发现和培养郝建秀的过程中,证实了毛泽东对陈少敏的称赞。在叶帆撰写的《郝建秀与火车头班组》中,描写了陈少敏去国棉六厂第一次看到工作中的郝建秀的情形:“郝建秀神定气闲的样子让陈少敏看呆了,这个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女将,被眼前这个面色黝黑、淳朴憨厚的小姑娘感动了,仿佛一道灵光闪过,历尽沧桑的心头蓦地温热起来,甚至,连眼睛都有些潮润,也许,这就是母爱。”的陈少敏敏锐地意识到郝建秀作为典型的意义,并立刻成立了工作组,协同国棉六厂党、政、工、团一道总结郝建秀的经验并予以推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郝建秀的“实践才被提到理论原则上来,大家才公认郝建秀创造了一套科学的细纱工作法”[31]。
20世纪50年代中苏正处在“蜜月期”,“向苏联学习”也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工业化领域最火爆和流行的口号,各个领域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力争以苏联为榜样建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2],因此作为劳模的郝建秀及其工作法的树立和推进,十分自然地被嵌入“学习老大哥”的时空背景之中。显然,这种学习不仅包括从“老大哥”那里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设备,也包括学习“苏联‘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的生产’的先进经验”[34]。一如郝建秀工作法研究委员会主任门宏所言:“这次总结的成功,是与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分不开的。”具体说,通过学习“苏联棉纺厂中斯塔哈(汉)诺夫的劳动方法”(7)阿列克塞·斯塔哈诺夫(一译斯塔汉诺夫,Alexey G.Stakhanov,1906-1977),出生于奥勒尔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35年8月30日,时任顿涅茨克矿区采煤工人的斯塔汉诺夫创造了一班工作时间内用风镐采煤102吨的记录,超过定额13倍(一说实际上是三人的产量算在斯塔汉诺夫一人头上实现的),由此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大力神”,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获得广泛宣传,并开展了以斯塔汉诺夫命名的广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Stakhanovite Movement)。1938年,陕北公学最早在中国宣传斯塔汉诺夫,1942年陕北边区农具厂涌现出“模范工人”赵占魁,并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式的斯塔汉诺夫”;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工业化早期,也曾大力开展过学习斯塔汉诺夫运动。参见周海燕发表于《新闻记者》2012年第1期的文章《赵占魁运动:新闻生产中工人模范的社会记忆重构》。,清楚了如何计划与组织工作时间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35]。此外,郝建秀工作法还强调了工程师的理论知识与工人的技术经验相结合的重要性,这庶几可以视为后来作为“鞍钢宪法”之精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的早期同类探索(8)在郝建秀工作法的总结中,曾提及“有的工程师在总结前认为日本、英国的纺织工作法好,对于在共产党领导培育下一个不足二年工龄、十七岁的青年女工,就感到有些微不足道。可是经过这次总结,他们这种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的思想就被打破了”。参见门宏:《郝建秀工作法是怎样总结出来的?》,《人民日报》1951年9月3日。。
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劳模典范,郝建秀工作法很快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宣传和推广。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确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郝建秀工作法。随后《人民日报》指明这是每个工厂的党支部和宣传员的责任,要把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提高到爱国主义的高度,与党和人民当前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工厂的党支部及宣传员开始向工友进行政治宣传,把学习郝建秀工作法与完成突击增产任务、支援抗美援朝相联系。同时在经济层面突出了生产对国家发展与个体生活的同价意义,如在宣传中将工厂赚的钱化作三等份:一份用于国防建设;一份用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工人福利事业(如新建“工人宿舍、通风设备、医院、托儿所等”);一份作为工资发给工人个人。如此一来,十分自然的是“咱们增加生产就是为了增强国家建设,就是为了咱们自己过好日子”[36]。于是抗美援朝、增产捐献的思想在各个支部形成了热潮,工人们都认识到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郝建秀工作法的顺利推广。
伴随着大面积的宣传和推广,各地也开展了及时的跟进和检查工作,并发现各企业在政治思想、经济激励和社会团结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如“有的单位推广工作和政治教育结合不够;所有单位没有建立奖励制度,或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时没有相应地增加工人工资;而特别严重的是个别单位的领导干部还存在着保守思想和自满情绪,因而助长了某些技术人员和工人对郝建秀工作法的对抗态度,甚至打击了郝建秀工作者”[37]。进一步的原因则是,他们还未认识到“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是一个新旧思想的斗争过程,必须不断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把学习先进经验变成广大工人自觉的行动”[38]。
经过上述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推广和应用,郝建秀工作法显现出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青岛纺织工人不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学习高潮,而且通过郝建秀小组向全国细纱工人发出的爱国增产节约竞赛挑战书[39]鼓舞了广大纺织工人的生产热情,使得各纺织厂的工人学会了科学的操作技术,“由机器的奴隶变成了机器的主人”[38],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还提升了劳动力素质。
在生产成效方面,郝建秀工作法因操作更合理,从而使得产量增加、质量提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假若全国各棉纺织厂的皮辊花率都能降低到郝建秀的水平,至少可以多生产四万四千四百六十件纱,以每人每年用布四丈计,可供四百万人一年的衣料”[40]。除此之外,党组织的行政管理和工厂的工作关系也因此得以改变,如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陈少敏在《郝建秀工作法的好处——在青岛市棉纺细纱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言,青岛工会和企业行政经过总结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不仅“教育了自己”,还密切了工会和生产的、群众的以及行政的关系,密切了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更“改变了技术人员轻视工人创造的观点,打破了职工思想中的保守性,因而工会和行政的威信都提高了”[31]。
综上所述,“郝建秀工作法”的创立、总结、宣传和推广,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工业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实施的一套组合拳式的历史实践。正如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郝建秀小组实行科学管理二十六年》一文所总结的:“1951年,郝建秀同志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创造了科学的细纱工作法,为我国纺织工业总结、推广一系列先进操作技术开辟了道路。”[41]郝建秀工作法不仅在“增产节约”的时段性生产目标下减少了浪费、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客观上增加了物质产出和国家财富,还在保持工人生产热情的基础上激发了工人劳动意识的转变,提高了劳动组织能力和技能,减轻了体力劳动强度,提升了生产力效率,同时实现了工厂管理法和生产关系的改造,促进了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42],长远来看也促进了工业进程的迭代和升级。
四、“翻身”叙事:地位转换与妇女解放
除了推广技术革新与增产节约,郝建秀工作法的进一步推广中还包括对家庭出身、性别平等、主体思想、社会关系和阶级地位转换方面的叙事与报道。当然,不同的形象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表征。细纱工作法推广后,郝建秀在短期内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解放”前后堪称典型的“翻身”叙事,不仅表现在通过女性工作机会的增加体现出的性别平等、“新社会”工人的权利和地位赋予上,还通过家庭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表征出新中国工人都和郝建秀一样,在党的领导下从过去被奴役、被剥削的状态和贫苦生活中被解放出来。他们开始追求自己无限美好的前程,并用劳动报答党的恩情、建设伟大的国家。在郝建秀撰写的《保卫我们和平的幸福的生活》一文中,其“家庭改变了过去穷苦的面貌,收入大大增加了,三餐吃白面,经常吃鱼吃肉。全家大小都穿(戴)整齐。两个弟弟都上了学。人民政府和工厂还帮助盖起了六间向阳的新屋子”。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使得其一家人有说不出的喜悦,尤其父亲母亲整天笑逐颜开,并时常叮嘱郝建秀“好好干活,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给咱的恩情”[33]。
超越物质激励的是郝建秀获得了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机会,并被赋予相应的政治身份,这一切给予这位普通女工“最大的荣誉”。郝建秀1951年到首都北京参加了国庆节典礼,列席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1952年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去苏联参加了莫斯科“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亲眼看到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世界和平的旗帜斯大林同志”[33],“他身体又胖又健康”[30](P19)。随后郝建秀又到苏联几个大城市参观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这成为其“一生中永远忘不了的两件大事”[33]。此外她还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等给予的物质奖励和共青团中央授予的模范团员奖状。对于这些经历和荣誉,郝建秀做出的反馈与党和国家倡导的集体主义的工作价值观十分吻合:“所有这些光荣,我要归诸于党,归诸于毛主席,归诸于我们全体工人阶级。”[33]
从更长的时段来看,作为典型的技术革新模范,郝建秀在政治地位上实现了跨越式的“阶级跃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贫苦阶级翻身求解放的理想以及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郝建秀并非个案。在教育资源极其稀缺的新中国,为提升典型模范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全国各地的1900名产业工人和工农出身的干部分别于1954年进入北京6所高等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学习,1958年毕业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被保送到高等学校继续深造[43]。郝建秀作为其中的重要成员,其学习经历也被重点宣传。这位过去仅初识文墨的普通纺纱女工,接受过专门教育后成为纺织工业方面的技术人才。在1962年的大学毕业答辩上,“面对着许多教授和讲师,郝建秀详细地叙述了自己设计的棉纺织厂所选用的工艺、设备、工程设计直至整个厂的生产组织和成本,并且逐一作了论述和证明”[44]。学成归来后,郝建秀被分配到总工程师室担任技术员。此时获得技术精英身份的郝建秀展现了自觉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政治觉悟,如当有人称她为大学生时,她会不好意思地说在生产实践面前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呢!而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生产实习后,她更深刻地体会到必须继续向老工人学习的重要性。而老工人也十分珍爱自己的大学生,如车间里的一位队长高兴地说:“来吧,建秀,你给我理论,我给你经验,凡我知道的,都端给你。”[45]
在这里,阶级乃至性别地位的转变都是当时流行的“翻身”叙事的典型议题。在中国,“翻身”一词从1920年开始被用于表述阶级解放,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末成为中共边区新的革命词汇,并因“更具口语化的特征”[46]在1946年“土改”后流行开来,甚至成为“土改”的同义语[47]。1948年,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1919-2004)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山西长治张庄“土改”,他后来撰写的反映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翻身》中准确地写道:“每一次革命都会创造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词就是‘翻身’。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翻过身来’,而对中国的几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它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48]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在内的反映“土改”的小说主题都是“翻身”叙事[49]。在某种程度上,“翻身”成为动员贫苦农民及工人投身革命的重要情感诉求。按照袁光锋的研究,尽管“翻身”和“解放”两词在1949年后使用频率有下降趋势,但“依然是执政党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中“翻身”在1951-1952年的使用频率仍相对较高[46]。
沿着“翻身”和阶级平等的终极逻辑,劳动人民出身的劳模成为领导干部后,是否能坚持参加“劳动”,不脱离“群众”、不脱离火热的社会主义实践,成为一个人身份转变后是否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试金石。具体在郝建秀的案例中,作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她不仅于1954年顺利入党[50],回原厂工作3年后职位迅速晋升,历任副厂长、市委副书记和省委常委等重要职务,但是并没有完全脱离一线的体力劳动。当了领导干部,怎样继续保持劳动模范的本色,在郝建秀那里依旧是需要认真考量的重大问题。在当时,党和国家一直强调:“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51]
作为一位女性劳模典型,郝建秀的“翻身”叙事不仅意味着其个人阶级地位的跃升,她的成长所产生的性别效益和示范作用也是巨大的。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后,其所在的青岛国棉六厂很快于1952年4月成立了由23名女工组成的“郝建秀小组”。以一个先进个体为基础打造一个小组,说明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有纪律的、稳定的工作队伍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有意识地铸造而成的[52],也同样说明劳动模范具有“桥梁、骨干与带头作用”,因此以某个劳动模范的名字来命名,可以带动背后一个集体[6]。正如同一时期的裔式娟通过自身模范行为和“思想工作”为其小组成员树立正确的态度一样,以团队为基本单位的工作过程不是一个匿名的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人际关系问题(9)参见史明于2016年7月在上海大学参加“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与现状”学术会议时的工作论文“Female Labor Models and the Microworlds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第11-12页。。在这种情境下,工厂作为一个道德世界出现,由愿意接受教育和开放理性的人组成。因此除了发扬郝建秀的劳动精神以促进整体操作技能的提高外,“郝建秀小组”还树立了“又赛又帮”的生产效率与群体互助兼具的集体主义工作风格。到郝建秀回厂时为止,组内的女工们在126个月中有123个月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当时郝建秀小组的女工个个都是一级操作能手。9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小组累计输送了12名女工当干部,并为厂内外训练了150多名技术工人[45]。
不仅如此,随着以郝建秀为代表的女性技术劳动模范的事迹为世人熟知,整个社会对妇女的看法也开始发生改变,妇女在工业劳动中的成就快速得到肯定。1956年底,全国各工厂企业中,就有11万多名女职工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53]。伴随着社会层面的认可,也让工作及家庭场域中的男性对妇女有了新的认识,这不仅改变了妇女在公领域的生存空间,也改进了私领域内的家庭关系。女性群体自身在此过程中也逐步实现着主体身份的建构,改变着传统的性别文化和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并使这种改变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54]。
五、结语:性别、阶级与社会主义改造
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地位的获取有先赋与自致两种基本途径。不同于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下的阶级理论强调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或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从而获得执政地位。而无产阶级成功执政之后,如何治国理政以巩固阶级地位,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1949年后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基于此,本文将这一命题置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解析,以著名劳动模范郝建秀的工作法及其生命历程为例,试图探求共产党成功执政后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顺利实现工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层动因。
整体来看,郝建秀的生命历程展现了集体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维逻辑,即促进客观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在工业领域,则体现为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系统性提升和改造。具体而言,以操作技术为内核的“郝建秀工作法”在短时期内经过组织力量的强劲宣传和推广,有效提升了工人的劳动热情、劳动技能,从劳动态度和能力的综合维度增强了工业劳动力的素质,借以达致有效提高生产力、增加物质产出之目标。而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领域效率和利益优先原则下工人的螺丝钉角色或工具色彩,以及工人和技术精英、管理精英之间因利益分裂割据和等级地位差异,从而无法有效联合对抗资本主义秩序的状态。从较长的时段来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初期通过“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手段进行阶级斗争、直接实现阶级颠覆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阶级内部工农兵和技术、官僚阶级之间的翻转和结合。通过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及一系列涉及“阶级跃迁”(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阶级反哺”(强调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继续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和“阶级融合”(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具体策略,建立起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初期的社会整合机制。
具象到生产实践的场域,其社会建构方法可进一步总结为“典型个体—集体—阶级—社会—国家”的系统性循环模式。具体机制可逐步细化为三个层面。(1)典型模范的塑造和社会影响机制。这需要以劳动投入和技术革新等特定事件为目的,善于发现、寻找相关典型,通过组织的力量进行有结构的总结和塑造,而后宣传推广并解决诸如新旧思想斗争和反对势力的阻碍等问题,从而使其顺利应用并产生社会效应。(2)鼓励形成“又赛又帮”的集体主义工作氛围。这种工作氛围不仅与强调个人成就的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同,也与苏联模式及早期延安模式中仅强调“劳动英雄”的个人突出作用有异,当然也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所提倡的“韬光养晦”或“出头椽子先烂”的所谓生存智慧。具体来说,这种“又赛又帮”的集体主义是对单纯强调“效率”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单纯强调“世故”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双重改造和智慧化运用。如果说“赛”强调效率,那么“帮”则兼有传统师徒制中的“传、帮、带”和新时代阶级话语中的“千亲万亲阶级亲”的双重精神内核。这就将因师徒或业缘而形成的“拟态(血缘)关系”[18],与新型的阶级关系成功地加以“嫁接”改造,进而发挥了榜样示范和社会整合功效[55]。(3)国家—集体—典型个人—群众个体的利益关系捆绑机制。通过塑造一个典型劳模,宣传其劳动产出和为国家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同时给予其极高的荣誉激励和巨大的身份地位转变机会,从而将整体的国家发展愿景通过典型模范所获得的社会利益分配,对阶级集体和群众个体进行了有效激励,从而促成和巩固了个体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主人翁”意识、效仿行为以及相应的奋斗实践。
最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妇女解放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妇女地位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在此理论指引下,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既从属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性别与国家、社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亦是彼此调和与相互促进的。伴随着农业中国到工业中国的历程转变[56],现代化发展历程下的工业强国目标提出了“妇女掌握技术”的新要求,即在实现妇女参加劳动和男女同工同酬之后,通过劳动技能的提高打破性别界域,拓宽妇女生产的路径、渠道和内容[14],使妇女掌握地位提升的核心要素,获得最高政治荣誉,实现教育机会、阶级身份和性别地位的转换,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解放的崭新逻辑,这也进一步促成了集体主义时期“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特征。尽管郝建秀仅是新中国妇女技术劳动模范中为数不多的典型案例,技术领域的从业妇女迄今为止也没有发展到半数之多,但郝建秀的工作法及其生命历程却是妇女打破性别区隔“天花板”和实现自我解放的代表,其所具有的重要经济性、政治性、社会性和主体性意涵,都伴随新中国艰难困苦的工业化进程和社会主义转型历程而得以彰显。在此过程中,妇女不论作为客体与主体,不论是“党领导的动员”还是“妇女主导的变革”,阶级、集体和妇女个体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妇女解放的本身意义,在国家独立自主、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未来想象中,成为更高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追求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