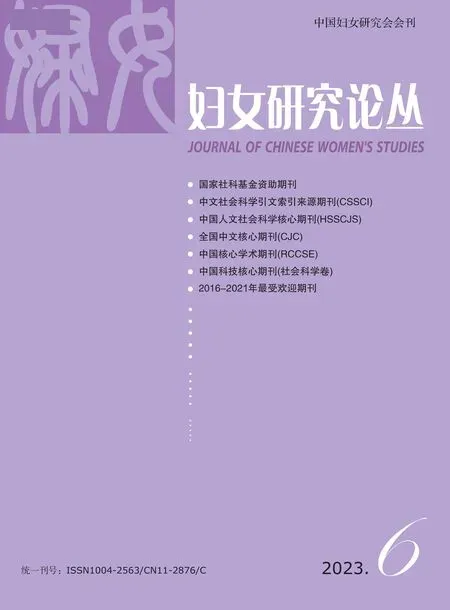论“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意义、局限及其在中国的接受
——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郭晓飞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88)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其中“姚某某故意杀人案”引人注目,这个案件首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5年共同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的相关规定,将受暴妇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杀死施暴人的,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本案的基本案情是:被告人姚某某(女)和被害人方某某(男)结婚十余年来,方某某在不顺意时即对姚某某拳打脚踢。2014年8月16日中午,方某某因琐事再次殴打姚某某,次日凌晨,姚某某在绝望无助、心生怨恨的情况下产生杀害方某某的想法。姚某某趁方某某熟睡之际,持屋内的螺纹钢管猛击其头部数下,又用菜刀砍切其颈部,致方某某当场死亡。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姚某某长期以来对被害人方某某实施的家庭暴力默默忍受,终因方某某逼迫其离婚并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子女而产生反抗的念头,其杀人动机并非卑劣;姚某某在杀人的过程中虽然使用了两种凶器并加害在被害人的要害部位,且承认有泄愤、报复的心理,但结合家暴问题专家的意见,姚某某属于家庭暴力中的受暴妇女,其采取杀害被害人这种外人看来残忍的行为,实际上有其内在意识:是为了避免遭受更严重家暴的报复。姚某某具有自首、认罪、悔罪情节,作案手段并非特别残忍、犯罪情节并非特别恶劣,被害人父母对姚某某表示谅解,姚某某尚有四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因此,对被告人姚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
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典型案例的同时,还提到了这一案例的典型意义,认为系全国首例家暴问题中“专家证人意见”被法院判决采纳的案件:本案开庭时聘请具有法学和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人员出庭并向法庭提供专家意见,在庭审中,专家证人出庭接受了控、辩双方的质询并就家庭暴力的特征、表现形式、受暴人与施暴人在亲密关系中的互动模式以及受暴妇女、施暴人特殊的心理、行为模式等家庭暴力方面的专业知识向法庭进行了客观、充分的解释。本案专家证人在证言中也描述了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对受害人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长期家暴可能给家暴受害人带来严重的身心影响,如个体在长期遭受无法逃脱的负面刺激或困境后,逐渐丧失对改变自身状况的信念和动力,产生无助和无能为力的心态,称为“习得性无助”,这些影响在家庭暴力事件发生时,有可能会影响家暴受害人对暴力程度、危险性和预期结果的认知,以及影响他们所采取的对策、行为的判断力[1]。
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的材料中认定,在涉及家暴的刑事案件中,本案引入专家证人证言,这对地方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严格来说,本案不是全国首例家暴问题专家证人意见被判决采纳的案件,而是2015年《意见》发布以来全国首例在“受虐妇女杀夫案”刑事判决中采纳了专家对受虐妇女心理出具的专业意见。尽管在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的材料中,始终没有出现“受虐妇女综合症”(Battered women’s syndrome),但是熟悉这一领域的学者很容易从字里行间读出这一内容。例如,在反家暴的知识框架下,“习得性无助”是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案的专家证人同时具有法学和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强调长期家暴对受虐女性产生的严重心理影响,分析受暴人与施暴人的互动模式,从而影响定罪和量刑,这都是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典型特征和在一些国家司法实践中的日常运用。
在典型案例发布的内容中,强调了长期家暴对受虐妇女的心理影响,在受虐妇女杀夫案件的判决中采纳了专家证人证言,并对杀夫的妇女进行刑罚轻缓化处理,但是又不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甚至没有出现这个字眼,或许从中可以读出中国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既有借鉴,又有疑虑。即使在诞生此理论的美国,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评价也有着复杂的面向,学术界既承认其积极意义,也提出了很多批评。本文试图从比较法的角度,通过研究这一舶来品在其起源地的运作实践和理论争议,同时描述性分析中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出于何种理由、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或者拒斥这一概念,并对这种接受程度的现状进行评价性分析。最后,本文建议中国应该用“受虐妇女社会调查报告”来代替“受虐妇女综合症”,既避免了病理化效应,又可以进行更加全面的调查,同时也与刑诉法中既有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一致性。
二、“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含义
“受虐妇女综合症”起初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这个概念由心理学家雷诺儿·沃克(Lenore Walker)提出,常用来指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亲密关系暴力的女性所表现出的心理创伤或者特定行为模式。沃克对受虐女性的定义为:“一个女性被一个男人反复施加任何的身体或精神暴力行为,以强迫她做他想让她做的事情,而豪不关心她的权利。”[2](P54)沃克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主要有“暴力循环”和“习得性无助”两部分内容,中国学者对此已经有非常精准的译介,所以此处仅做简要介绍。
沃克用“暴力循环”来指称家庭暴力的周期性。第一个阶段是“紧张累积”(tention building)阶段,在这个阶段,妇女在亲密关系中经受了施暴者轻微的身体暴力和语言攻击,她试图把暴力事件的严重程度最小化,并往往把暴力事件的发生归咎于自己。第二个阶段是“严重殴打事件”(acute battering incident)阶段,在这个阶段,暴力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受虐者无力再安抚施暴者。同时,暴力的程度升级,受虐妇女常常会担心自己遭受严重身体伤害甚至死亡,暴力处在完全失控的状态。第三个阶段是“带有爱意的悔过行为”(contrite loving behavior)阶段,也称暴力的“蜜月期”,施暴者充满魅力地向受虐者道歉,忏悔自己的过错,并承诺不再有暴力行为[2](PP56-66)。然而,“重归于好”之后,暴力周期重启,并且暴力更加残酷。
沃克用“习得性无助”来指称经过“暴力循环”的受虐女性的心理状况:即便妇女事实上有可能逃离所处的遭受虐待的关系,她也往往“感觉”对自己遭受虐待无能为力[2](PP47-48)。“习得性无助”一词起源于心理学家马丁·沙利格文(Martin Seligman)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实验,他将几只狗用绳子拴住放在铁笼子里,每天电击铁笼子的各个部位,一开始狗左躲右闪,但很快发现无处可躲,于是停止了闪躲,默默忍受。后来,研究人员打开笼子,解开绳子,狗却不知道可以逃跑了。沃克认为,受虐妇女对家暴的反应,与狗不知道逃跑的反应原理上是相似的。因为“暴力循环”反反复复,受虐妇女变得顺从、被动、无助[3](P137)。
中国学术界对“受虐妇女综合症”概念的精髓基本上已经有了精准的掌握,可是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概念最初属于社会心理学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成为一个法律概念”[4](P565),但这个判断值得商榷。事实上,当下美国各个司法辖区通过判例或者立法的形式,在法庭上接受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但是这个概念仍然只是用来佐证受虐妇女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并没有“受虐妇女综合症辩护”这一独特的类型,也没有在既有的防卫学说之外添加的一种新的法律学说,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法律概念,不如说它是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社会科学概念:“受虐妇女综合症”在美国的运用恰恰是在既有的法律规范学说框架下来进行,并非在实体法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范式转换,仅仅是挑战并纠正了一些既有规范适用中的刻板印象,并在证据层面注入了女性主义的视角。
三、“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意义
我们首先探究一下“受虐妇女综合症”在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下的运作以了解一些基本概念。美国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具体分为四类:自身防卫(self-defense)、防卫他人、防卫财产和执法防卫。其中与本文最相关的是自身防卫,也就是如果一个人合理地认为自己处在遭受非法身体侵害的紧迫危险中,法律许可受侵害者对侵害者本人运用适度暴力[5](P77)。一般来说,有两种案件类型会关涉到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对抗性案件和非对抗性案件。前者指的是妇女在受到伴侣对她身体攻击时立即杀死或者回击对方;后者指的是长期被虐待的女性在伴侣没有攻击她的时候,比如在伴侣睡觉的时候,攻击或者杀死伴侣[6](P338)。而受虐妇女在非对抗性案件中杀死伴侣的行为,是否可以因为“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而满足法律规范关于自身防卫的要求,从而达到出罪的结果,这在目前具有最大的论证难度,引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
(一)回答“她为什么不离开”这个问题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大众舆论对于长期受家暴虐待的妇女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为什么不离开?反家暴研究者或者是较为关注这一议题的人会强调这个问题是刻板印象的一部分,只有昧于现实情况者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问题和刑法的法教义学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基本上也不太会成为刑法学研究的问题,而在美国,“她为什么不离开”直接和法律规范的解释相关,所以在“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研究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美国大多数州规定自身防卫的成立必须满足几个要件:其一,围绕案件的证据必须证明自身防卫的抗辩是理性的;其二,防卫人必须诚实并且合理地相信自己面临死亡或迫在眉睫的威胁;其三,防卫者必须使用合乎比例的武力进行防卫。最后,有些州还规定,被告必须证明他们无法逃离或从袭击现场撤退。如果可以避免,就没有理由使用致命武力[7](P926)。最后的这个要件也就是“避让规则”。但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认为,长期受虐待的妇女形成了无助、被动的心理特点,就像实验中处在笼子中的狗不断遭受电击后,哪怕笼子已经打开也已经失去了逃跑的能力和欲望,长期受虐待的妇女已经没有能力识别和选择“可以逃离”。由此,在美国这个证据的目的是为了说服陪审团,“避让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如今美国只有很少的州要求自身防卫需要满足“避让规则”,而那些存在避让要件的州在经过一些挫折之后,认可城堡主义原则(Castle Doctrine)——古老的法律谚语说“每个人的家都是一座城堡”,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被攻击,没有义务撤退——作为避让要件的例外。1982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在State v.Bobbitt[8]一案中认为,受虐的妻子在家中面临丈夫的攻击,仍然适用避让规则,而不是城堡主义原则,因为双方是同一所房子的合法居住者,并且有平等的居住权利。显然,这个判决对于受虐妇女是不利的。不过这个先例在1999年被另外一个案件推翻了,那就是Weiand v.State[9]案,一名佛罗里达州女性凯瑟琳·维兰德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她使用了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为自己辩护,没有成功,因为陪审得到了这样的指示:如果她撤退就可以避免使用武力,那么她使用武力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就不具有正当性。最后她因二级谋杀罪被判18年有期徒刑。她提出上诉,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认定防卫者和防卫对象住在同一所房子里,防卫者没有避让义务,可以适用“城堡原则”,原因是认为对陪审团进行关于“避让”义务的指示会合法化和强化关于家庭暴力的“神话”和刻板印象。围绕家庭暴力最普遍的“神话”之一是,女性可能随时离开虐待的关系。也就是说,在1999年Weiand v.State案件判决之前,佛罗里达州允许在法庭上提出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但是同时法庭又指示陪审团关于“避让”的义务,而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最终对此进行了纠正,认识到避让义务会架空“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运用效果。
所以看起来,美国存在“避让”义务要件的州已经很少,而且在这很少的存在避让要件的州,也都接受了城堡主义的例外,即在自己家里遭受攻击时进行防卫不需要避让。于是,似乎已经不需要专家证据来解释为什么受虐妇女不离开虐待关系,其实不然。按照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提出者沃克的看法,陪审员关于家暴的刻板印象并不仅仅与法律规定的避让义务有关,甚至在那些没有正式规定避让义务的司法管辖区,陪审员也会认为被告没有离开虐待关系是不合理的。有一些关于家暴的“大众迷思”会认为:“被虐待的女性是受虐狂,她们与伴侣在一起是因为她们喜欢被殴打,暴力满足了这对伴侣内心深处的需求,或者如果她们真正想离开,她们可以自由地离开这种关系。”[10](PP1-2)陪审员关于家暴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会对受虐妇女的诚信产生质疑,她长期受家暴的历史都将受到质疑,说服陪审团自己在防卫那一刻感受到身体和生命被威胁,也将变得更加艰难。于是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受虐妇女综合症”固然是部分地针对避让义务的法律规范,然而在避让规则式微、城堡主义得以承认的今天,关于“习得性无助”的观念仍然被期待能够破除陪审团成员关于“为什么不离开施暴者”的刻板印象。
“她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刻板印象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研究家暴法律问题的学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新的学术词汇来概括与分离有关的暴力——“分手攻击”(separation attacks)。对这个概念的界定如下:是发生在她决定分手或开始准备分手的那一刻或之后的一种特定类型的攻击……过程中的各种暴力和胁迫行为可以称为“分手攻击”[11](P65)。“习得性无助”和“分手攻击”并不矛盾,前者是感知到分开很困难,后者证实了要抽身而退的确不容易,尽管受虐女性有些时候的确会高估离开虐待关系的困难,但是“分手攻击”证实了受虐女性对危险的感知是理性的,支持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这个层面,即强调妇女的理性和她对暴力的反应是正常的[11](P81)。“分手攻击”这个概念揭示了对女性身体和意志的控制,是一场争夺控制权的斗争,施暴者阻止受虐者离开,或者对分手进行暴力威胁,把自己的意愿凌驾于女性愿意同谁一起生活的意志之上,于是,本来是强调免于干涉的谚语——“一个人的家是自己的城堡”,也可能在某些时刻成为禁锢人的一座监狱,理解这一点,才能回应这一常见的问题——“她为什么不离开”,也才能对受虐女性在某些时候的反杀行为有更多的同情理解。
(二)对迫近危险之合理确信的证明
在普通法之下,被告要想提出自身防卫的抗辩,必须证明自己真诚合理地相信面对迫近的危险(imminent danger)。关于紧迫性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紧迫性意思是“危急”(imminent),是“即将发生”;二是认为紧迫性的意思是“立刻”(immediate),乃“即时发生”。如果把紧迫性理解为“即将发生”,为非对抗性杀夫成立正当防卫扫除了障碍[12](P70)。尽管美国也有学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界限,只要即将发生的不法侵害具有必然性,同样构成防卫的紧迫性[13](P88)。美国大多数州的确不是在“立即发生”的意义上来理解紧迫性,而是取“即将发生”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语境里,如果把imminent翻译为“迫在眉睫”,可能不如翻译为“即将发生”,更能体现出与“立刻发生”的区别。
在美国法语境下,对于“即将发生”的判断建立在合理感知(reasonable perception)的基础上,被告人必须说服陪审团,自己对于即将发生的严重危险的确信以及所采取的暴力措施是合乎理性的。如何判断这种确信的合理性,美国不同的司法辖区采取不同的判断标准,有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分。客观标准又称理性人标准(reasonable person test),被认为是客观普遍的标准,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来看,对危险的恐惧和需要防卫的信念必须是合理的,所有人都应遵循相同的标准。批评者认为这个标准在受虐妇女反杀案件中有缺陷,没有考虑到受虐妇女为何要使用致命武力来防卫的特殊情况,所以主观标准要求考虑被告的特殊情况,倾听被控告的妇女对案件发生时相关状况的解释,以判断被告是否诚实地相信有必要采取防卫行为[7](PP929-930)。如今,越来越多的州在判断是否合乎理性的时候,纳入了主观性因素。如在State v.Leidholm一案中,北达科他州一名女性趁丈夫睡着的时候杀死了他,此前他们发生了纠纷,丈夫用暴力阻止她使用电话报警,并且有证据证明丈夫长期虐待她。初审法院对陪审团的指示体现了客观标准:“她采取行动的情境必须是能够使合理谨慎的人,无论其性别,在类似情况下都会产生合理的信念,即对方当时即将杀害她或对她造成严重身体伤害。”[7](P932)北达科他州最高法院裁定这个指示错误理解了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向陪审团作出的正确指示应该是这样的:“被告的行为不应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人在类似情况下可能会做或可能不会做,或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来判断,而应以他本人真诚地相信并有合理理由相信,为保护自己免于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而必须做的事情来判断。”[7](P932)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仍然需要谨慎对待这样一个事实:相同的语言在不同语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大陆法系国家,在非对抗性案件中,受虐妇女杀死正在睡觉的丈夫,不能满足正当防卫的紧迫性要件,因为没有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种判断标准必须是客观的。也就是说,普通法系国家所强调的合理确信侵害即将发生的所谓客观、主观标准,在大陆法系视角下都是主观的,这种合理确信在大陆法系国家很容易被认定为“假想防卫”,而不是正当防卫。
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试图说服陪审团,受虐妇女在非对抗性案件中的杀夫行为也构成自身防卫,因为她诚实地相信自己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危险或严重身体伤害,必须保护自己。这个带有病理化色彩的心理学术语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在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低下的情况下阻却责任,恰恰相反,是为了证明受虐妇女杀害施暴者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而且只要了解了更多受虐妇女的特殊心理,就能证明她的合理确信是真诚的。
然而对合理性的证明,的确是通过一定程度的病理话语实现的。美国精神病学会并没有将“受虐妇女综合症”明确定性为精神障碍,而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个大的病症之下的创伤经历之一。沃克认为,一个人经历了可怕的事件之后,会产生一系列的感觉、想法和行动,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出现典型的三种症状:认知紊乱、高度警觉(high arousal symptoms)和高度回避症状。受虐妇女的认知紊乱体现在重复性、不由自主对受暴经历的回忆,使得她们重新体验受虐经历,并且会将以前的受虐经历与现状混淆,增加了她们对危险的感知。高度警觉状态是指受虐女性对任何潜在的危险和即将到来的攻击高度敏感,从而准备发起反击。高度回避症状指受虐女性使用回避技巧,否认、最小化自己的危险处境[14](PP327-328)。沃克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特别是持续性的高度警觉状态,证明了受虐女性即使在没有与施虐者直接对抗的情况下,也会感受到持续的威胁和恐惧。随着虐待的循环在关系中继续确立,受害者学会了预测随后发生的虐待事件的可能时间和严重程度[14](PP326-330)。
沃克的暴力循环理论试图说明,受虐妇女此前的受虐经历,使得她陷入了恐惧和焦虑,即使在虐待事件停止之后,这种恐惧仍在继续,因为她经历了暴力的循环,知道暴力还会继续降临,她必须抓住暴力的间歇期进行正当防卫。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度警觉症状,使得她有时候对危险的感知超越了受虐事件本身,经常遭受严重的身体虐待可能造成施暴者的一个眼神,或者将会杀死她的威胁,都使她确信这一次自己可能真的会被杀害。充分考虑受虐女性的特殊心理特征,也就是舍弃“事后诸葛亮”客观、冷静的一般理性人标准而采取主观标准,可能会更加认同她对危险即将发生的确信是合理的,实施致命的手段进行防卫也是“高度警觉”心理的顺理成章的反应。“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介入,使得自身防卫的认定加入了历史和未来的双重考量。一是历史因素,即反复出现的暴力的累积影响;二是未来因素,即考虑到对即将发生的暴力的预测。
有的学者和律师用“习得性无助”来回答“她为什么不离开”这一常见问题,这个问题和普通法上成立自身防卫的“避让要件”相关;学者和律师也常常用“暴力循环”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来证明危险迫近之合理确信。但是,这两个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非亲密关系里,法律要求紧迫性,是因为法律要求防卫者尽量在能不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下逃离这段关系,而事实上一个人很难从持续性的亲密关系中轻易脱离。法学教授维多利亚·诺尔斯(Victoria Nourse)质疑在某些案件中,法庭将危险迫近之合理确信要件,直接等同于避让要件。看起来是在问被告是否具有危险即将发生的合理确信,实际上在问的却是被告采取的防卫手段是否是逃避严重身体伤害和死亡的唯一手段[15](P1263)。在诺尔斯看来,有一些模糊的法律概念,里面隐藏着还没有被解决的社会潜规则,这些社会潜规则有时候会否认或者违背法律的公开承诺。尽管如今法律已经不要求受虐妇女必须行使避让义务才能够进行防卫,可是避让义务却在潜规则里继续存在,这些潜规则虽然没有被明文规定,却伪装潜藏在“紧迫性和必要性”要件中继续发挥作用[16](P976)。这样的洞见启发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受虐妇女综合症”究竟是挑战了正式的法律规范、先例、教义学说,还是挑战了这些规范和学说在适用中的刻板印象?“受虐妇女综合症”是专门为女性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恩惠”,还是与传统的防卫学说本身并不冲突,只是试图在传统规范的适用中去除性别偏见?
(三)移步不换形:在既有的防卫学说中纳入性别视角
普通法传统上成立自身防卫的要件是:危险必须是迫在眉睫,防卫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合乎比例地使用武力。这种理解很常见,于是,先发制人地防卫行动很难被认定为正当。女性主义法学认为这种防卫学说缺乏性别视角,没有意识到这种所谓理性一般人的标准只是男性的标准,正如英文中用“男人”(man)来指代所有性别的人。有学者分析,普通法的自身防卫规定是围绕着两种场景发展起来的:要么一个个体被另一个陌生个体严重袭击,这可以称之为“黑暗小巷中的陌生人”场景;要么是一个个体卷入“过失杀伤”事件,这可以称之为“酒吧斗殴”场景。防卫者想要辩护成功,必须证明自己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并且使用了与袭击者相称的必要武力。而上述自身防卫标准根本没有考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经历;相反,在普通法限制已婚妇女独立性的庇护(coverture)原则之下,允许丈夫对妻子进行身体上的管教,并且特别禁止妇女对这样的暴力进行防卫。英国普通法大师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对法律的理解是,如果妻子杀死了丈夫,相当于摆脱了对丈夫权威的一切服从,因此法律将她的行为定为叛国罪,并判处她与杀害国王一样的惩罚,这个妇女将会被烧死[17](P1753)。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法学开始把“家庭暴力”问题凸显出来,为传统自卫学说的研究注入性别视角。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下,产生了“受虐妇女综合症”概念,指出防卫条件中严格的“即刻”概念不适用于重复发生的暴力关系,家庭暴力中的受虐妇女能够合乎情理地感受自己正面临致命人身伤害的威胁,并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对付施暴者[18](P217)。女性主义法学还揭示了传统防卫学说中的“合乎情理”的行为标准是男性的标准,“并不适合于一个合乎情理下的女性的防卫特征,尤其不适合于那些长期遭受男性配偶在身体、心理及情感上虐待的女性的情形。”[19](P17)甚至,西方的reasonableness(合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带有社会性别色彩,行为标准建基于“理性”(rationality)这个概念,排除了情感和道德[20](P1405)。
普通法下对于自身防卫的最初预设是两个陌生男子之间的一次性暴力冲突,这两个男子块头差不多,因此,当受虐女性在非对抗性案件中以暴抗暴,杀死正在睡觉的丈夫的时候,可能她确信这是唯一的防卫机会。女性用致命武器来进行防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知道很难用拳头制服对方,除了生理上常常处于弱势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女性很少被社会鼓励学习拳击格斗,正如法官在一个判决中所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明显缺乏获得培训的机会,也缺乏发展必要技能的手段,无法在不使用致命武器的情况下有效击退男性袭击者。”[21]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强调,因为存在持续多次受虐待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一个女人会害怕熟睡或者手无寸铁的男人,并为了保护自己必须进行致命的身体攻击。对于一个受虐女性来说,伴侣的一个眼神,都使得她相信使用致命的武力是必需的,没有遭受过殴打经历的女性可能不会这样想[22](P870)。因此,严格地要求防卫者只能使用合乎比例的武力,缺乏性别因素的考量,且没有注意到家庭暴力中防卫情节的特殊性。
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受虐妇女综合症”挑战了法律界传统的防卫学说,但并没有重新定义自身防卫的概念,对受虐待妇女进行公平审判的最常见障碍不是现行法本身的内容出现了问题,而仅仅是裁判者对法律的适用出现了问题。在美国大多数司法辖区,衡量防卫者行为合理性的标准是防卫者自己的看法和经验,危险紧迫性要件也不要求危险必须迫在眉睫,也要考虑语境,包括行动时的环境和过去的事件。要求防卫者合乎比例的使用武力也是在个案的基础上衡量,要考虑防卫者和死者的体型、年龄、身体状况和他们之间以往发生的暴力事件。而且,不能说刑法预设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一次性暴力,几十年的犯罪统计表明,在绝大多数凶杀案中,当事人很多是熟人[23](PP382-407)。
曼斯泰勒(Robert P.Mosteller)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关于防卫的实体法已经改变,虽然他也承认这样的说法在技术上不正确,因为大多数司法辖区的自身防卫标准并没有改变,但是这一变化是通过修改证据规则,而不是修改防卫法来实现的。他认为,法院和立法机构正在通过承认一种新的证据类型来改变实体法,最大的改变在于:在受虐妇女作为被告时,几乎自动地承认受虐经历这一“背景信息”(contextual information)[24](PP488-489)。
一种很常见的批评是,“受虐妇女综合症”是女权主义者在为受到家庭暴力从而杀死施暴者的女性寻求特殊对待,然而,在女性主义刑法学家金波斯特(Kit Kinports)看来,根本就没有所谓独特的“受虐妇女综合症辩护”,相关案件只是引入了被虐待的证据来支持传统上的自身防卫主张。即使受虐妇女在非对抗性的案件中杀死正在睡觉的施暴者,也可能符合传统的自身防卫要件,研究表明,2/3到3/4的受虐女性能够准确预测她们面临的施暴伴侣施加危险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自身防卫中的客观标准,也是采纳“被告是所处特定情境下的理性人”(the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defendant’s circumstances)视角。传统上,自身防卫所要采纳的证据标准完全可以在今天涵盖家暴经历。早在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就承认,可以用不法侵害者的暴力行为和名誉来支持正当防卫的主张。在某一著名的纽约地铁枪击案中,纽约上诉法院认为,被告先前遭受的经历和对死者先前暴力行为的了解是评估被告恐惧合理性的相关因素。同理,“合理的受虐妇女”标准只是对传统标准中“被告所处特定情境下的理性人”的简略描述[25](PP313-318)。相当一部分学者支持这一观点,即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没有改变传统自身防卫标准。因为,19世纪以来,被告遭受过的威胁和暴力,包括受害者的暴力行为特征,被认为与被告自身防卫的主张高度相关。1888年,就有法院对陪审团作出指示,一般理性人标准不应该以某种“理想”的标准来评判,陪审团应将心比心,以案发时遭遇不法侵害者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以及其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影响,作为标准。而且,很久以来,普通法强调的威胁不是实际的威胁,而是防卫者的感知,只要这种感知是合理的,就足以认定为自身防卫。这就是“外观规则”(appearances rule)[16](PP971-972)。
这些论述充分证实了一个结论,“受虐妇女综合症”并没有改变实体法上的自身防卫要件,也不是在寻求对受虐妇女的特殊“恩惠”,传统上关于防卫的经典学说,从来都不排斥考虑不法侵害者施暴的历史,以及陪审团一贯被指示要站在被告的立场考虑案发时的具体状况。这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受虐妇女综合症”在科学上争议很大,却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大获成功,因为这个证据的引入没有颠覆防卫传统,只是挑战了以往家暴领域刑事案件对于受虐女性受暴经历的忽视。
美国传统的防卫学说并非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对性别视角的分析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洞见。例如,当有人指责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是企图为女性寻求法律上的特殊“恩惠”时,忽视了防卫学说在实践中的运作,这本身就渗透了男性视角。例如,对紧迫性的严格要求,对防卫者合乎比例的武力的认定,都忽视了女性整体上在力量方面处于弱势,很难在侵害正在发生时进行防卫。女性平时疏于擒拿格斗的训练,很难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有效对付施暴者。刑法的男性视角因为行之有年,人们甚至看不出某些实践做法是男性视角的体现。例如,在美国,如果一个男子发现自己的妻子与人通奸进而杀人,人们会普遍认为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激情犯罪,是激情之下的故意杀人,属于“自然失控”而并非有预谋的杀人。诺尔斯曾提到,在刑法中,群体概括(group generalizations)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当陪审团普遍认为,在妻子出轨时,丈夫自然地会失去控制,那么他们就是在进行群体概括。而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并不需要专家证人解释,并不需要依赖“男性排斥综合症”为自己“辩护”,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当妻子出轨时一个理智的男人就是会失去自制力[26](PP1443-1451),这种特殊心理状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定罪量刑的考量因素。然而,受虐妇女的特殊心理状态却需要专家证人专门向裁判者进行解释,这不仅不是寻求对妇女的特殊“恩惠”,反而是妇女费尽心力地去纠偏。
当然,我们分析防卫学说在运作中对妇女的不公,不能简单地以男人“厌女”来解释,还要看到一个重要的因素——人们很难理解在家庭暴力存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家庭可能成为类似于一个“绑架的场所”,受虐妇女很难随意地选择离开。人们对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刻板印象,往往会影响审判。有学者指出,尽管传统的防卫学说和“受虐妇女综合症”并不冲突,都不强调威胁实际存在,而是强调防卫者对威胁的合理感知,而且也会考虑不法侵害者过往的暴力行为,但是,裁判者有一种模糊的直觉,即传统防卫教义学说中的这些考量,仅仅对陌生人适用,对亲密关系中的人不适用。这些亲密关系中的一些刻板印象,压倒了正式的法律规范[16](PP971-973)。与家庭和亲密关系有关的潜规则,影响了正式规则的运作,以至于需要专家证人来“拨乱反正”。
“移步不换形”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戏曲改革思想[27](P275),可以借用这句话来概括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和传统的关系:这个理论没有挑战美国教义学说本身,因为防卫学说也重视不法侵害者过往的暴力经历,也强调陪审团站在防卫者的立场考量紧迫威胁的合理感知,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各个司法辖区都接受了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此之谓“不换形”;然而,传统的防卫教义学说在实践中的运作,的确对于受虐女性的心理状态是忽视的,附着在亲密关系之上的刻板印象带来的潜规则,也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陪审团和法官,需要专家证人来纠正,此之谓“移步”。这样看来,“受虐妇女综合症”很少挑战传统防卫教义学说本身,而是着重批判了传统教义学说在实践运作中的性别偏见。
四、关于“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批评”
(一)“常识”视角的批评
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一种常见批评认为,这种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是一种“减轻虐杀责任的借口”,授予受虐妇女一种“杀人的许可证”(license to kill)[28](P232)。这种观点担心“受虐妇女综合症”会削弱“作为刑法核心的个人责任”,并把责任从被告身上转移到被杀死的受害人身上,充满同情的陪审团会认为死者死有余辜并且对杀人的妇女无罪释放[29](PP5-7)。美国著名刑法学家和人权律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认为,减轻虐杀责任的借口是普遍推卸责任的表现,这对民主原则本身是危险的,因为民主原则以个人对行动和选择负责为前提。事实上大部分有过被虐待经历的人,都没有从事暴力犯罪[30](PP4-6)。德肖维茨甚至追溯普遍推卸责任的起源,认为“这一切都是从所谓的受虐妇女综合症开始的”[30](P45)。
这些批评其实和美国的“文化战争”紧密相关,“结构”和“个人”的二元对立在此也有呈现。偏重结构的观点认为,犯罪行为的产生与社会制度结构相关,个人责任不是主要原因,惩罚已经过时了,犯罪人应该作为病人得到治疗。而强调个人责任的观点认为,上述观点是道德相对主义,是不断强调“受害文化”从而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借口,应该强调个人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而不是不断讲述受害的故事以博取同情。
“受虐妇女综合症”是为杀人者开脱罪责、为一种私刑辩护——这个批评观点看起来是一种“常识”视角的批判,但是这个问题还牵涉到正当(justification)辩护和宽恕(excuse)辩护之争:正当辩护强调受虐妇女杀死施暴者的行为是一种正当的防卫,是正确的行为;宽恕辩护认为受虐妇女杀人行为本身是错误的,只是因为受虐妇女特殊的心理状态而可以使其免于承担责任。采纳宽恕辩护立场的学者认为,尽管杀人是错误的,但这名被殴打的妇女对她的杀人行为不应该承担责任,因为就她面临的情况而言,任何人都可能会像她一样行事,希望陪审团宽恕她[31](P1493)。事实上,正当辩护与宽恕辩护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的,大量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论证是在自身防卫的框架下进行,是对防卫正当性的论证,自然遭遇了生命权不容随意剥夺的“常识”视角的批评,尤其是杀夫行为发生在非对抗性情境下的时候。
(二)科学视角的批评
199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一案中确立了证据法上著名的“道伯特法则”(Daubert Test),要求与科学有关的证词必须满足以下特征,才能被容许和接受:“结论是否可以通过实证检验,结论是否经过同行评议,已知或潜在的错误率,控制运作标准的存在与维持以及理论和技术是否被科学界普遍接受。”[32](P486)《默克诊断和治疗手册》被公认为疾病和伤害的主要医学文本,它没有将“受虐妇女综合症”列为公认的疾病。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是精神障碍的主要文本,也没有将“受虐妇女综合症”列为公认的精神障碍[32](P486)。
大卫·费格曼(David L.Faigman)虽然赞扬“受虐妇女综合症”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揭露美国家庭暴力存在的普遍性,并使家庭暴力受害者获得的资源急剧增加,但和一些学者一样,费格曼对沃克在《受虐妇女》和《受虐妇女综合症》书中的研究进行了批判并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从一开始就不是科学问题,但它却被法院视为科学事实[33](PP68-69)。费格曼还对沃克的方法论进行了批评:沃克的访谈技巧让受试者很容易猜到研究人员希望在研究中验证什么,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通过掩饰他们的预设从而避免“猜测预设”(hypothesis guessing)的现象,而沃克的做法加剧了猜测预设现象,例如在描述了每一次事件之后,受试者会根据开放式描述和殴打者在施暴前的行为等封闭式问题来做出判断。例如,“你会称之为……易怒、挑衅、攻击性、敌意、威胁吗?”访谈主持者会根据回答来记录是否有证据证明存在“紧张累积”阶段和“带有爱意的悔过行为”阶段。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沃克组织的这些访谈主持者不仅知道“正确的”结果,还报告了他们对受试者是否证实了结果的估计。受试者的回答没有被记录下来,只记录了访谈主持者对受试者答案的解释,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会通过不了解研究预设的访谈主持者来避免这个问题[33](PP76-77)。也就是说,沃克应该向访谈主持者隐瞒自己家庭暴力三阶段周期的预设,根据访谈的实际结果来验证或者纠正自己的预设,这样才能避免研究结果是研究预期的重复。恰恰相反,沃克让访谈主持者对受试者的回答进行概括,而这个概括又是根据研究预设的三阶段周期来进行,所以结果就是通过研究发现的是早已“埋藏”进去的。
沃克研究的另外一个缺陷在于没有表明“暴力循环”的经历时间是几分钟、几个小时还是几个星期,也忽略了任何关于第三阶段结束和新周期开始之间是否出现正常期的讨论。如果有正常期,这个循环周期实际上包含四个阶段,而不是三个阶段。沃克研究最为重大的缺陷在于,她如果要证明存在一个连贯的暴力循环周期,应该是在一个单一的暴力关系中经历三个阶段:紧张累积阶段、严重殴打事件阶段、带有爱意的悔过行为阶段。然而,书中数据显示,在所有受试者当中,65%的个案经历了殴打事件之前的紧张累积阶段,58%的个案有经历殴打事件后悔过的阶段。于是,她得出的结论为大多数家庭暴力的表现都证明了暴力循环理论[33](P77)。费格曼认为,沃克没有提供数据显示她的受试者当中有多大比例的人完整经历了三个周期的循环,根据沃克的数据来猜测,经历所有阶段的女性人数可能低至23%,无论如何不会超过58%[34](PP639-640)。
还有一些评论者指出沃克研究的其他缺陷,例如她的研究对象都是亲密关系中的受虐待女性,缺乏没有受虐待的女性作为对照组来进行比较研究。她的受试者当中很少有人杀害了施虐者,而且显然也没有人被指控与施虐者共同实施犯罪行为[35](PP236-237)。
不过,尽管费格曼指出沃克研究中方法论方面的种种问题,但是他有一个判断显然是错误的。他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里说,虽然预测“受虐妇女综合症”概念的消失还为时尚早,但这一消失却是意料之中的,并且确实是热切期待的[33](P70)。事实上,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另外一副面貌,美国如今各个司法辖区都接受了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有些是通过判例的方式,有些是通过立法的方式。逻辑和历史并不统一,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缺陷并没有成为障碍,“道伯特法则”也没有阻挡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被接受,是因为这个证据有着重大意义,在相关案件的辩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学者给这个问题提供了解释:美国司法对“受虐妇女综合症”广泛接受是出于政治因素,美国社会已经达成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即在诉讼中,天平应该转向对施暴者做出暴力回击的被殴打女性身上[36](P485)。因为虐待关系的社会现实严重失衡,法律程序没有适当的应对妇女为了进行自我救助而实施的暴力。因此,尽管科学上不确定是否存在真正的“受虐妇女综合症”,但决策者认为陪审员仍应接受此类证据,以帮助纠正失衡[36](PP490-491)。
科学视角的批评有价值,但是走向科学主义就不可取了。在一些人看来,因为某项研究有着方法论的诸种问题,所以这个研究所提出的概念就将没有生命力,或者应该期待它消失。这种主张和判断常常和历史背道而驰,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被司法上普遍接受一定是对解决真正的法律难题有帮助,直击靶心,而这种解决方案又和社会的政治判断一拍即合。传统防卫学说忽视了妇女所面临的防卫困境,陪审团关于家庭暴力又有着大量的性别刻板印象,裁判者对亲密关系暴力又有隔膜,而沃克的研究在性别问题上一定有不少洞见,这种洞见对裁判者的刻板印象有一种纠偏的效果,这种效果正好和社会下决心要纠正女性在防卫辩护中的弱势一致,于是也就不必纠结于这个概念本身是否真正符合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三)女性主义视角的批评
科学视角的批评常常举出的例证是,很多精神病学领域的权威文本并没有认定“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存在,而女权主义视角的批评恰恰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是对女性的一种病理化压迫,本来就不该在精神病学的权威文本中出现这样一种诊断分类。因此,尽管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致力于纠正裁判者的性别偏见,但是女性主义对此概念的批评也不假辞色,值得认真对待。
一项关于模拟陪审员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没有专家制约相比,专家证据的存在提供了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诊断,导致陪审员认为被告的思维更加扭曲,做出负责任的选择的能力较弱,对其行为所负的法律责任也较轻。”[37](P169)1984年轰动美国的电影《燃烧的床》描述了一个受家庭暴力多年的女性放火烧床,烧死了正在睡觉的丈夫。这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这名杀人的女性被判无罪,理由是暂时精神错乱,而不是自身防卫,电影中这个女性成了杀害施虐者的受虐妇女的典型形象。在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产生之前,杀死施虐者的受虐妇女常常以精神错乱影响刑事责任能力为理由进行辩护。著名女性主义法学家麦金农认为,如果一个辩护律师同时又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就会面临严重的冲突:“对于一名被指控的女性来说,激起法官和陪审团的性别歧视可能是她获得无罪释放的唯一机会。监禁是为原则付出的巨大代价。”[38](P721)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辩护律师,并不希望对自己的当事人——一个受虐女性进行病理化,但是如果她要坚持原则,自己的当事人就可能锒铛入狱,因为曾几何时,用病理化女性这一歧视女性的方式才能有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但事实上,因病理化而无罪的效果并不好,有一些用精神疾病辩护而得到无罪判决的女性被长期关在精神病院。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极力强调自己属于支持自身防卫辩护的专家证词,与精神错乱导致刑事责任能力下降这一辩护有所区别。虽然将其命名为“综合症”,但并不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而是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为了证明威胁迫近的合理确信,从而证明特定背景下的杀人是合乎理性的一种正当防卫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司法辖区对此的理解有所不同,例如路易斯安那州有些法院明确禁止在没有精神错乱辩护的案件中接受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但有些法院却允许,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8年Stata v.Curley案判决后才得以改变。在这个判决中,州最高法院判决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和相关专家证词在被告辩称精神错乱或自身防卫的案件中都是允许被接受的,而不仅仅限于精神错乱辩护。被告的辩护律师没有将此类证据纳入辩护,侵犯了被告关于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中获得有效律师协助的权利。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都预设“受虐妇女综合症”只与“精神错乱”相关,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称这是一个错误[39]。这个案件承认“受虐妇女综合症”不是一个可辨别的精神疾病,而是一种受虐妇女特殊心理状态,符合今天美国法学界和司法领域的主流见解,但是“综合症”这一命名所带来的病理化负面效应不可小觑。有些陪审团成员仍然从精神错乱的角度看待,从而很难理解受虐妇女的杀人行为是合理的选择、正当的防卫。在一些与监护权有关的案件中,受虐妇女也会因为被贴上“综合症”的标签而处于不利地位。
事实上,对旧有概念的不满和对新命名的追求在美国已经行之有年。1996年,美国司法部、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等机构发布了《刑事审判中殴打及其效应相关证据使用的有效性》的报告,报告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过度病态化了女性的经验,不能体现家庭暴力的本质和复杂性。如果将其命名为“殴打及其效应”,就去除了附着在“综合症”上面的病理化效应。也有学者建议用“有关暴力及其后果的专家证词”来命名,才可以体现有关家庭暴力知识的丰厚性[40](P144)。这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而是希望实现一种范式的转换,即“受虐妇女综合症”过于强调医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而应该转向结构和社会的因素,如不是从受虐妇女的“习得性无助”来解释为什么难以逃离施虐人,而是强调经济的依靠、求助于法律的困难、家暴受害者庇护所的缺失或者不足、施暴者对于受虐者分手或逃离表示进行暴力威胁等。总之,专家证词的内容应该更多地关注妇女所处的社会现实,而不是她的心理反应,否则就是把对家暴的社会病理学分析变成了对家暴受害者的病理化。然而,尽管重新命名的论述在各种文献里一再出现,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受虐妇女综合症”并没有被替代。有学者分析原因认为,美国是一个习惯于对异常行为进行病理化的社会,对医学术语的依赖为争论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性。在法庭上,恰恰需要解释特定被告犯下特定罪行,而社会逻辑的趋势化解释对审判来说没有什么用[41](PP97-98)。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用“综合症”命名,带着医学科学性的权威,在法庭上为证据的可接受性提供了基础,但是这种病理化的负面效应却始终挥之不去。
女性主义刑法学教授安妮·考芙琳(Anne M.Coughlin)批评沃克创造的“受虐妇女综合症”是父权制的产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沃克仍然执着于“科学”。沃克谴责法院在作出影响妇女生活的决定之前没有“倾听”妇女的意见,看起来是与法律女性主义者结盟,这些学者致力于揭露构建法律的父权视角,并在法律中引入一种基于女性生活的视角和价值观。不幸的是,沃克的女性主义项目妥协了,她承认她的调查结果符合她所在学科的普遍原则,是科学方法的产物,客观数据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真理。沃克要说服法庭和她的潜在客户,她的发现基于可接受的科学根据。沃克没能认识到,心理学的方法论对女性也是不友好的,特别是她认为科学客观性能够产生价值中立的结果,女性主义认为这种客观主义存在认识论缺陷,预设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彻底分离,并没有认识到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情境中的建构[42](PP73-74)。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疾病话语,显然增加了“综合症”话语的科学性,有利于通过证据法上的“道伯特法则”,事实上也纠正了陪审团的一些偏见,杀死施暴者的受虐女性因此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然而,女性主义批评者确实也指出这种代价是对受虐女性的病理化,而且这种病理化话语越“科学”,越让人难以反抗。只要想象西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历史上相当长时期把同性性行为病理化,就可以知道某些病症总是在某种社会情境下的建构,而并没有科学基础。另外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歇斯底里症”,这个词源于希腊语hystera,意为“子宫游走”,由此可知这个病症建构中的性别歧视因素。
女性主义者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批判不仅仅是在思想认识领域,这个专家证据在法律实务上也有其缺陷,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制造了一种单一的受虐妇女形象,这种“一刀切”的模式并没有准确地描述所有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有些受虐女性在被虐待的时候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反击,不是被动的或者无助的。而“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习得性无助”,所以每个被虐待妇女都必须满足这种刻板形象,才能成功地进行自身防卫辩护,这就不成比例地使得某些妇女群体处于不利地位,包括有色人种妇女和经济独立的妇女,陪审团不太可能认为她们是“无助的”。而且这个单一模式通过支持“无助”和“被动”,助长了性别刻板印象,像是“奖励”了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妇女[43](PP172-173)。考芙琳教授对沃克的批评非常严厉,认为她是一个“极度反女性主义者”,是一个“厌女者”(misogynist)[42](P87)。这么严厉的批评对沃克其实并不公平,沃克当然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并且“受虐妇女综合症”成功地使得无数受虐女性获得更加公平的判决,也在自身防卫规范的运作中去除了一些性别偏见。然而,这个概念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的确带来了另一些问题,在去除刻板印象的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刻板印象。例如,在State v.Anaya一案中,一名受虐女性被控告杀了她的丈夫,一名专家证人作证称,被殴打的妻子通常出于经济依赖而与丈夫呆在一起,他们对伴侣的暴力行为最常见的……反应是被动的。检方利用幸存者姐姐的证词反驳了辩方关于“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证据,被受虐女性杀死的男性处于失业状态,而这名女性在之前一个冲突事件中刺伤他。这一证词取代了许多其他证词,而这些其他证词是要证明这名女性是亲密关系暴力的幸存者[44](PP276-277)。正如一位学者所总结的:“如果女性在杀死施暴者后想要成功地进行自身防卫的辩护,她们成功的机会可能取决于她们是否完全被施暴者支配。”[33](P113)也就是说,受虐女性杀死施虐者,要想成功运用“受虐妇女综合症”进行自身防卫的辩护,她们在长期的受虐过程中,必须一贯保持“习得性无助”的刻板形象。一旦她们曾经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反击,陪审团就不会相信她们是无助的,也就失去了“受虐女性”正当防卫的资格。正如某位评论者所说,“好的”受虐女性受害者似乎是一个无助、被动、没有暴力或对抗行为史的受害者[45](P169)。也就是说,“受虐妇女综合症”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且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只有少数符合这种陈规定型的妇女才能作为合法的受害者,而这种彻底无助的形象恰恰把具有能动性的、积极反抗的女性排除在外,难怪女性主义者对这个概念提出了严厉批评。
五、“受虐妇女综合症”在中国的接受
从20世纪90年代起,“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概念被学者译介到中国,后来通过对一些热点案件的讨论,学术界对这一术语已经不再陌生。然而,从美国到中国“概念旅行”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明显的不同。例如,美国学术界参与这一话题讨论的是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刑法学家以及证据法学家,而中国除了有个别倡导女性权利的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译介之外,主要是刑法学家对受虐妇女杀夫案件进行研究,而在这些研究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受虐妇女综合症”概念并没有得到深入分析,尽管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这一概念开启了这些研究。更让人意外的是,鲜有证据法学家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几乎只有《妇女研究论丛》上的一篇相关论文属于证据法领域[46](P75),这与“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专家证据的地位很不相称。另外一个不同点也让人印象深刻,美国学者普遍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的存在价值在于说服陪审团成员,受虐妇女没有离开施虐者,不是享受被殴打的受虐狂,弱化陪审员形形色色关于性别和亲密关系的刻板印象,为受虐妇女争取有利的判决结果;而中国虽然没有陪审团制度,但是在无数的受虐妇女杀夫案件中,屡屡出现“百名群众联名向法院为杀人者求情”,以至于何家弘教授建议此类案件可以引入陪审团制度,把社区民众的温情带入法律[47]。甚至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在102例受虐妇女杀夫案件中,“有56例案件,被害人亲属对被告人表示了谅解”[48](P33)。尽管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受虐妇女杀夫的正当性似乎能够被认可,但这些现象的确为中国司法实践和学术上为受虐妇女寻求轻判甚至出罪的努力提供了一定的民意基础,正如“于某故意伤害案”[49](P89)中的民情为推动“正当防卫如何才能避免沦为僵尸条款”这一专业思考提供了助力。中国的特殊性还在于,中国司法实践基本上还不太接受“婚内有奸”,只有在夫妻双方处于分居或离婚诉讼等非正常婚姻状态下,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发生性关系的,才构成强奸。如果妻子在所谓正常婚姻状态下遭受强奸,很难属于刑法所赋予的特殊防卫权范畴。当中国有学者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是专门为妇女寻求特殊对待的时候,对于婚姻内妻子面临丈夫强奸不能行使特殊防卫权的现状却安之若素,这就是亲密关系的“潜规则”压倒了正式的刑法规范。在将来的司法解释中,笔者认为应该明确规定受虐妇女在此类案件中的特殊防卫权。本文接下来就制度建构和学术话语等角度来展开比较法学的分析,以增进对这一概念接受问题的理解。
(一)“有实无名”的部分接受——制度移植的维度
与“有名无实”相反,笔者试图论证,尽管中国在规范中并没有出现“受虐妇女综合症”概念,但无论是在实体法领域,还是在证据法领域,事实上已经部分接受了这一概念所开创的理论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在展开论述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何在美国饱受争议的概念却在中国能够得以部分接受?原因在于,尽管理论上有争议,但中国有学者积极译介了这一概念,并且认为这一概念对于打破性别刻板印象有积极意义,且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在内的不少普通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都接受了这一专家证据。中国即使不完全接受这一概念的学者也在探索受虐妇女杀夫的出罪理由,且一旦认清了“受虐妇女综合症”不是一个法律学说,而仅仅是与事实认定有关的证据种类,接受起来也就不难突破法系的障碍。为什么是“部分”接受呢?是因为中国有着不同的刑法教义学脉络,同时对于这一概念的“病理化”效应有所警惕,再加上中国对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建制正在探索,这种情况对于避免病理化效应也或许是个优势。
就实体法领域而言,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意见》第20条规定,“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对于因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体、精神受到重大损害而故意杀害施暴人;或者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较轻’。”这个司法解释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部分接受:强调了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的激愤恐惧这一特殊心理状态;强调站在事发当时被告人的角度来判断其主观心理状态;“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这一点部分体现了“暴力循环”说;强调了被告人行为具有防卫因素。但是与美国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主要用于自身防卫不同,中国更多是承认“具有防卫因素”。有学者认为,这种规定语焉不详:“如果受虐妇女杀害丈夫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当然成立正当防卫而阻却违法;如果不符合出罪事由的成立条件,司法机关在否定正当化事由之适用后又承认行为具有防卫因素会显得矛盾,且违背刑法理论与规定。”[48](PP31-32)这的确是个问题,做出这种矛盾表述的原因就和“部分接受”有关:一方面,规范的制定者受到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中自身防卫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却也意识到在非对抗性状态下受虐妇女杀害施暴人不符合“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一要件。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一庭课题组对《意见》的解释提到的,家庭暴力间歇期间实施的行为,不符合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所以没有采纳正当防卫的观点,而是酌定从宽处罚[50](P78)。这种矛盾描述也体现了法教义学和“常识、常情、常理”的冲突,这个“防卫因素”的说法与朴素民情相通,却未必符合法教义学,明明看着像防卫,却不能称作正当防卫。我们不妨把《意见》中这个所谓矛盾看作法律教义和民情在表述上的一个磕绊。
有学者认为尽管《意见》第20条重视了受虐妇女地位,具有进步性,但是处理此类案件仅限于量刑情节的考虑并不妥当,剥夺了出罪事由的讨论空间[51](P131)。类似的批评很常见。例如,陈璇教授认为只在量刑阶段而非定罪阶段考虑防卫因素并不合理,“同样可以在定罪环节的各类违法和责任阻却事由中得到体现”[52](P14)。学者们大多不满足在此类案件中只能以酌定从宽情节来对受虐妇女带有防卫因素的行为进行评价,而是积极寻求出罪的可能性。
2020年9月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尽管并非专门针对有关家庭暴力的犯罪,却在更大程度上为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的使用提供了空间。《指导意见》第2条规定:“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越是强调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和心理特征,性别、亲密关系暴力的特殊性等这些因素越容易被纳入定罪量刑的考量。《指导意见》关于正当防卫时间条件上的规定尤为重要:“对于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在彭文化教授看来,这里的“现实紧迫危险”已经不同于传统刑法理论所要求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而根据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这个危险不仅指现实的即时危险,还包括即将到来的危险。如何理解“不法侵害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根据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不能将暂时理解为短时间内,如果不法侵害具有持续的可能性,即使时间较长也可以认定为暂时中断或被暂时制止[12](PP75-76)。笔者整体上赞同彭文化教授的实质判断,但是并不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本身提供了这些洞见,作为来源于社会心理学的这一概念,在美国并没有对传统的防卫理论进行改造,更不可能对时间条件施加了什么创造性的影响,充其量是激活了对紧迫性要件的讨论,英美法系传统的防卫教义学说本来就不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而是强调防卫者合理确信面临即将到来的危险就可以进行防卫。受到大陆法系影响的中国则有所不同,尽管《指导意见》的确延伸了不法侵害的紧迫性,但是《指导意见》仍然重申了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以《指导意见》能够提供的出罪事由仍然相当有限。
不过,正如彭文化教授所言,尽管没有明确提及这个概念,《意见》和《指导意见》这两个司法解释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12](P74)。笔者把这个称之为“有实无名”的部分接受,尽管这些司法解释还有待改善,但是其“不用其名”的积极意义不容小觑。事实上,在美国,无论从事实维度上的科学批判,还是从价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批判,都使得“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个名字备受争议,所以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学术讨论,都有不少声音希望能用“殴打及其效应”来进行替换。当然,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已经被美国各个司法辖区普遍接受,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功挑战了传统防卫学说在性别和亲密关系里的刻板印象,并为作为受虐女性的刑事被告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这种“综合症”的命名病理化了女性,而且“习得性无助”等术语也制造了单一的受虐妇女形象,中国在借鉴的过程中一定要谨慎。事情的复杂度就在于,“受虐综合症”的命名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传播,因为它正好迎合了美国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学科的强势,习惯于把很多社会问题病理化。这种强势甚至在跨国传播中也有所体现。正如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像我们一样疯狂》(CrazyLikeUs),这个“Us”,既是指作者所说的“美国人”,也是指美国这个国家。作者想说的是,为什么全球的心理疾病越来越“美国化”,美国人以规模批发的方式出口自己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作者批判了美国文化对其他文化中独特的心理和疗愈方式的铲除效应[53](PP1-3)。尽管“受虐妇女综合症”概念并非一种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可是这种命名依然带来了病理化的负面效果,以至于中国有学者认为翻译为“受虐妇女综合征”更合适[54](P88)。这体现了大家对于病理化效应的恐惧,所以“有实无名”的借鉴也就有了必要性。
就程序法领域而言,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有证据法学者指出了这一法条适用的困境。专家辅助人只能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而“受虐妇女综合症”不是精神疾病,在现有框架下很难启动鉴定程序,于是专家辅助人就没有参与庭审的空间,因此建议对专家辅助人的角色进行扩张,以解决证据资格问题[46](PP82-84)。如今,这一证据资格问题已经通过司法解释部分地得到解决。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0条第1款规定,因无鉴定机构,或者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出具的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龙宗智教授认为,这条规定与相关的刑事诉讼法规范有明显冲突,但是确立有专门知识的人作证的证据地位有实践上的必要性,因为有些专业性问题不需要鉴定和检验,只需要专家的解读和判断,以促成法官心证[55](PP256-257)。在此前的司法解释中,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检验报告只是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而如今专家辅助人出具的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司法解释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惜与刑事诉讼法规范产生冲突,尽管解释者的原意不一定是专门针对受虐妇女的专家证据,却使得这一领域的弱势群体深深受益。从长期来看,可能还是需要相关立法修订来消弭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冲突。笔者建议参考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有必要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明确与家暴有关的刑事案件,需要受虐妇女社会调查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借鉴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一些洞见,又避免了病理化的污名,也可以纠正这个概念中偏重精神心理因素而忽视社会结构调查的弊病。事实上,美国也有学者建议应该用“关于受虐妇女经历的专家证词”来代替“受虐妇女综合症”,证词的范围应该涉及解释妇女暴力的总体社会背景,不应局限于对习得性无助、创伤后应激障碍或任何其他单一反应的调查[56](P1201)。在中国,用“受虐妇女社会调查报告”来代替“受虐妇女综合症”,与这样的整体性思维是暗合的,更重要的是,也符合我国不单一看待心理状况而重视社会调查报告的传统。
(二)聚讼纷纭的法教义学方案——学术争鸣的维度
针对受虐妇女杀夫案件,中国司法实践中一般都是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只是在量刑阶段考虑到受害人过错、受害人家属谅解等因素酌定从宽处罚,忽视了出罪事由的适用空间。只有极少数妻子在对抗过程中杀夫,因制止了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不负刑事责任[57](PP111-114)。针对这一普遍定罪的现象,极个别的学者甚至悲观地认为,“放弃出罪的尝试而在量刑方面寻求轻刑化才是值得追求的务实方案”[58](P418)。但是,大量学者不是这样的看法,纷纷给出刑法教义学的方案,为受虐妇女提供可能的出罪事由,哪怕是针对难度极大的非对抗性案件。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当下刑法学界主流已经对司法实践中只是在量刑阶段考虑受虐妇女特殊状况的现状不满,而是积极研究出罪的方案,受虐妇女调查报告一定会为这些努力提供证据上的帮助。
第一种方案是正当防卫。陈兴良教授认为:“在受虐妇女杀夫案中,虐待行为本身属于继续犯,而且间隔一段时间实施的虐待行为具有可预期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虐待行为理解为持续侵害。”[59](P85)因此,陈教授认为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虐待而实施的制止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在陈教授的论述中,吸收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一些洞见,例如家庭暴力长期巡回实施,具有规律性,如只要喝酒后就会施暴,受虐妇女杀夫是制止具有一定必然性或高度或然性的家庭暴力。但是陈兴良教授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回避了防卫行为的时间条件,以此作为认定正当防卫的依据有一些牵强[59](P84)。这个论述或许可能有一些误解,陈教授在文章中把正当防卫和“受虐妇女综合症”等并列作为受虐妇女杀夫案的出罪路径,而“受虐妇女综合症”不是一种独立的抗辩事由,它主要是作为一种专家证据来说服裁判者避免一些性别和亲密关系暴力的刻板印象,必须要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期待可能性等刑法教义学说结合起来适用。在美国,这个专家证据是和自身防卫结合起来论证受虐妇女对于紧迫危险的合理确信;在中国,如果陈教授对正当防卫适用于受虐妇女杀夫案的论述被司法实践接受,很可能也离不开揭示家庭暴力规律的专家证据。
第二种方案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张明楷教授认为,当施虐者处于熟睡状态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要件很难满足。否则,受虐妇女雇请其他人杀害熟睡中的丈夫,也构成正当防卫,这个结论很难成立[60](PP14-15)。张教授的出罪方案是,对非对抗性的受虐妇女杀夫案来说,只能认定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在少数案件中,受虐妇女确实缺乏期待可能性的,应当宣告无罪;在此外的案件中,受虐妇女并不完全缺乏期待可能性时,可以承认不可避免的期待可能性的积极错误,因而没有责任,否认犯罪的成立。”[60](P25)期待可能性理论是大陆法系的教义学说,美国司法实践中并不适用这样的学说,可是美国司法实践也会用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来论证“胁迫”(duress)要件,例如一个受虐妇女因为受到丈夫的殴打逼迫或者胁迫而从事犯罪行为,也可能会被判决无罪,因为不能期待她在被暴力胁迫的情况下还能够奉公守法。就像日本学者所说,“想对在强大的国家规范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脆弱的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61](P68)。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不能强人所难”,我们很难期待受虐妇女在某些特殊情境下仍然做守法公民。
在中国学者早些年的论证当中,期待可能性和“受虐妇女综合症”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屈学武教授就是选择前者[61](PP67-68)。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后者在美国主要服务于正当防卫理论,而中国的正当防卫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事实上,“受虐妇女综合症”非等同于正当防卫,它既可以服务于正当防卫,也可以服务于“期待可能性”学说。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中的积极错误指的是,原本并不存在丧失期待可能性的事情,行为人误以为存在。例如,由于特殊的心理状态,受虐妇女错误地认为只有杀死施虐者才能保护自己或子女的生命安全,这种错误认识不可避免,“受虐妇女综合症”可以成为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资料和理由[60](P26)。美国的“受虐妇女综合症”被用于论证自身防卫,而张教授把这个心理学所发明的概念用于论证期待可能性学说,这种巧妙的转换和勾连是概念在移植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处还有一个区别,在美国,成立正当防卫并不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只要防卫人合理确信危险的紧迫性,因此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极力论证这种确信的合理。而在中国传统的刑法学说中,强调侵害的客观性,所以即使支持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学者也在极力论证受虐妇女认识错误的“情有可原”。彭文化教授认为:“长期遭受丈夫暴力虐待的妻子,是不需要对丈夫的暴力虐待行为进行正确认识的,这是由其特殊的心理状态决定的。”[12](P76)张明楷教授也在用“受虐妇女综合症”概念来论证积极错误,只不过认为正当防卫没有为这种认识错误提供出罪的空间,转而求助于期待可能性理论中的认识错误。同样一个概念,在美国不断被用来论证“受虐妇女”的合理确信,在中国被不断用来论证“受虐妇女”的认识错误,尽管双方的目的都是寻求对于受虐妇女的有利结果,手段和表述却很不一样,这与两国的制度差异紧密相关。
第三种方案是防御性紧急避险。陈璇教授指出,“受虐妇女综合症”是不分国界的共享资源,但不同的法学制度和法学传统吸纳、消化这一成果的方式却可能大相径庭[52](P18)。有学者认为,针对危险引发者我们认为也可以进行紧急避险,施暴丈夫长期实施家庭暴力,可视为持续性危险,受虐妇女可以针对丈夫实施避险行为[51](P142)。陈璇教授支持这种防御性紧急避险的方案,但是认为必须满足“不得已”要件,即行为人只有在缺乏其他救济手段的情况下,才有权损害危险来源者的法益。德国学者认为对于家庭冲突,如果有制度化救助和回避可能性,则不允许紧急避险这种私力救济,所以陈教授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证目前在中国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针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途径是匮乏的[52](PP20-21)。相比于“受虐妇女综合症”偏重于受虐妇女个人的心理精神状况,这样论证的优势在于强调了制度这一结构性要素,对于受虐妇女为什么不离开施虐者这一常见的刻板问题,进行了更加完整的回答。即使在美国,也有学者批评沃克的“受虐妇女综合症”方案使人们不再关注被虐待妇女的集体困境和更大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是一种文化妥协[62](PP771-772)。但是不断论证“不得已”要件,就是在不断强调避让,是强调受虐妇女有一种在自己的家中撤退的义务,“受虐妇女综合症”被发明出来恰恰是要反对这一刻板的要求。当然,我们仍然不能离开语境进行简单的类比,毕竟制度差异甚大。如果“受虐妇女综合症”服务于正当防卫的论证,不需要论证避让义务,而如果采纳防御性紧急避险方案,就要论证“不得已要件”。
中国司法实践应该选择哪一种刑法教义学方案?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没有能力也无意回答。唯一清晰的是,刑法学界主流已经积极在为某些情境下受虐妇女“以暴制暴”的行为寻找出罪的方案,“受虐妇女综合症”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这样的努力,并且这个概念需要被批判性继受,它全可以和上述三个教义学方案中的任何一个相结合。作为一种专家证据的方式,它并不必然与“正当防卫”论证捆绑在一起,可以和“紧急避险”和“期待可能性”相结合。我们可以用“受虐妇女社会调查报告”的方式,去除“综合症”概念里的病理化弊病,同时详细甄别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不同,但是又不偏执地理解法教义学,以适度的实用主义态度,以问题为导向,真正解决受虐妇女的困境。
六、余论
科学性上面临重重争议,让女性主义者爱恨交加的“受虐妇女综合症”概念能够在美国司法领域大获成功,并不是偶然的,除了文中所列举的那些去除性别刻板的重要意义之外,“英雄造时势”的个人努力也不可小觑。同理,中国对于这个理论中洞见的部分接受和创造性转换,也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最后,本文简要论述一下两国两位先行者的贡献:美国的沃克和中国的陈敏。
除了社会结构性因素之外,有学者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成功离不开沃克个人因素。沃克特别擅长向不同的受众传播她的观点,从而使她的名字在各个领域都很突出。1979年她出版了《受虐妇女》一书,提出了“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假设,书中充满了受虐妇女经历的一些轶闻证据,这是她最具可读性和引用最多的作品。1984年沃克又出版了《受虐妇女综合症》一书,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确立了她工作的“科学有效性”,该书主要面向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1989年她出版了《可怕的爱》一书,讲述了她作为专家证人为受虐妇女作证的经历,为帮助受虐妇女辩护的人提供了建议。这都使得沃克所创造的这个概念具有“可检索性”,可供各个领域的受众使用[41](P96)。沃克经常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为受虐妇女的辩护提供帮助,在早期的一项调查中,在她的当事人中,25%获无罪释放,2/3没有坐过一天牢[3](P138)。无论是在学术界、大众舆论还是在司法实践中,沃克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是“受虐妇女综合症”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陈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杀夫的受虐妇女受到更公平的审判。她很早就在中国译介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也经常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帮助受虐妇女获得轻判。她被认为是一名家庭暴力问题专家,是家庭暴力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首位倡导者,是人民法院审理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第一个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迄今为止已经出庭十余次,始终坚持把学术研究写在法庭里,写在案例里。在一个受虐妇女杀夫并分尸烹尸的案件中,陈敏写了一份报告报给最高人民法院后被得到重视,最后,被告因长期受虐而毁尸的行为没有被认定为“手段残忍”,所以没有核准死刑。另外一个案件是发生在马鞍山的涉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陈敏在媒体上看到之后,通过最高法院与马鞍山中级法院的联络,得以在此案中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使得专家证人证言第一次被写入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并使得这项改革在全国法院开枝散叶[57](P5)。
陈敏还详细介绍了第一次将受虐妇女综合症导入我国司法实践的尝试,那就是发生在2003年轰动一时的“刘某霞杀夫案”,刘某霞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长期家暴,用毒鼠强毒死了丈夫。陈敏在当地妇联和检察院的配合下,在看守所会见了刘某霞,并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在确定了刘某霞具有典型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症状之后,陈敏决定以鉴定人的身份再次去看守所会见她。当地妇联和政法委提供了帮助,建议由县检察院委托陈敏作为专家为刘某霞做鉴定,但是上级检察院认为,由检察院委托专家为被告人做“罪轻”的鉴定于法无据。刘某霞一审被判12年有期徒刑,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该案承办法官表示,委托专家做受虐妇女综合症鉴定于法无据,法院不会考虑采纳这种证据,于是在个案中导入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鉴定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结束。陈敏认为,这种失败的理由之一在于没有好的合适的律师为刘某霞提供法律援助。例如陈敏和妇联一再向辩护律师说明,受虐妇女综合症的鉴定不是精神病鉴定,辩护律师依然在给法院的申请书中,要求法院委托专家为刘某霞做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精神病鉴定,以至于法院轻而易举以“于法无据”驳回了辩护律师的要求[3](160-164)。如果说受虐妇女综合症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破除性别和亲密关系中的刻板印象,那么这个概念自诞生以来,就要不断和精神疾病进行区隔,这个概念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更是如此,刘某霞的辩护律师即使在专家的不断解释下,仍然搞不清楚这个“症状”不是精神疾病,不需要走精神疾病鉴定的程序,有时也存在法官可能不了解这两者的不同脉络的情况。
同时,这第一次尝试的失败也证明了明确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重要性,法院和检察院会以“于法无据”作为拒绝接受此类专家辅助人意见的理由,然而外来的概念要落地,必须与我国的制度语境进行磨合,批判性借鉴,如今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制度上“有实无名”的部分接受,已经使得有专门知识的人所出具的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作为最高法院反家暴典型案件的“姚某某故意杀人案”,也是陈敏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为受虐女性获得较轻的处罚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在将来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还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受虐妇女社会调查报告”在此类案件中的证据地位,不再使用“综合症”这一病理化的概念,但是又借鉴了此一概念对性别刻板的纠正功能。与美国不同的是,陈敏的身份主要不是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专家,尽管她也有心理学的知识,但主要是法学研究人员,因此可以不必纠结于“受虐妇女综合症”概念先天具有的病理化色彩。更重要的是,陈敏推广专家证人出庭的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得益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这也是与中国重视顶层设计这一背景所契合的。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我们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接受绝不可以全盘接受,亦步亦趋,事实上中国也没有这样做。本文通过对这个概念之意义和局限的分析,以及考虑到两国具体制度语境的不同,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完全可以用“受虐妇女社会调查报告”来命名,不但可以去除美国概念中的病理化效应,也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同时也与中国刑诉中既有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