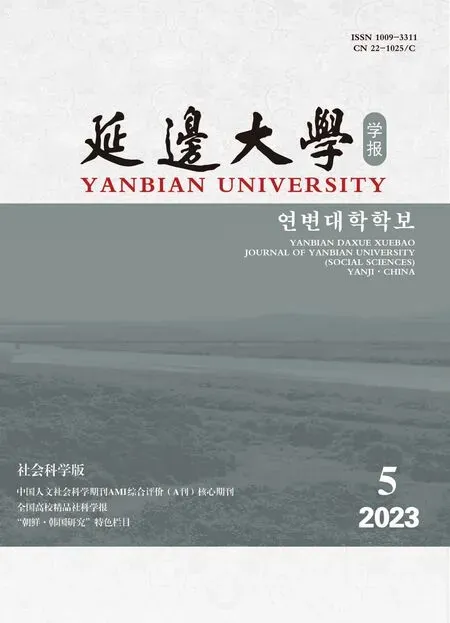东亚历史视域下的飞鸟奈良时代神道建设论析
刘艳文 徐天颖
日本飞鸟奈良时代同时也是东亚地区的大变动时期,朝鲜半岛上各国的冲突与融合成为牵动整个东亚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古代日本摄取大陆文明的主要来源便是朝鲜半岛,半岛的紧张局势成为推动日本由血缘氏族国家迈向律令制国家的重要原因,飞鸟奈良的神道建设实质上是律令建设的一环,由此开始,其国家原始巫术信仰得到系统的整合,成为制度化的神道发挥了作用。关于日本神道,迄今已有许多研究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宗教、艺术、思想、民俗等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则尝试从东亚历史视域出发,讨论飞鸟奈良时代神道的构建与东亚历史运行态势间的关系。
一、4-8世纪东亚国际政治中的日本
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相当于公元6世纪末至8世纪末,是其由氏族国家迈向律令制国家的转换期,同时也是整个东亚区域的变动期。这一时期,东亚各国围绕朝鲜半岛进行的政治博弈对古代东亚区域的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学界已有共识,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与整个东亚区域紧密相连,朝鲜半岛上的紧张局势深刻影响了飞鸟奈良时代日本社会的一系列变革。
朝鲜半岛上产生的政治博弈古已有之,自公元3世纪我国东北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高句丽南下以来,朝鲜半岛上的部落国家——辰韩、弁韩、马韩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1)陈寿著,章惠康编:《三国志文白对照》上,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700页。促使了新罗、百济建立,并由此引发了古代朝鲜半岛各国之间的生存竞争,为了在半岛上获得优势,各国之间或结盟或斗争,牵动了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政治往来。日本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关系密切,《日本书纪》中称朝鲜半岛为“财宝国”“金银之国”,(2)[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2、124页。显示出古代日本对朝鲜半岛丰富资源的依赖,日本早期部落联合国家邪马台国的形成也与对朝鲜半岛资源和先进文明的追求不无关系,对于古代日本人而言,朝鲜半岛不仅是财富、资源的供给地,而且是文明、信息、人才乃至政治权威的源地。(3)蔡凤林:《试论4-7世纪的朝鲜半岛与古代东亚国际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80-91页。由于本文的主旨在于厘清飞鸟奈良时代神道的发展形态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就该时期日本在东亚国际政治中所处的位置及采取的对策加以概述。
根据日本在围绕朝鲜半岛争端中所对抗的对象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可以大致把4-8世纪东亚国际中日本的行动划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一,4世纪中叶前,日本的主要对抗对象为新罗,采取相对平等的外交,尚未凸显宗主国意识。在《三国史记》中,早在公元1世纪便已经有倭人侵犯半岛的记录;(4)[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而2至4世纪期间,日本与新罗之间的冲突有14次之多。杨军指出日本与新罗的多次对抗与争夺朝鲜半岛南端的伽耶(日本称任那)诸地有关,至4世纪中叶,半岛上实质形成了两条大的对抗线,即东线新罗、日本之间的对抗和西线高句丽、百济之间的对抗。(5)杨军:《任那考论》,《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第53-63页。这一时期日本与朝鲜半岛存在既依赖又对抗的关系,依赖体现在当时的日本十分需要经朝鲜半岛传入的大陆文明和物质财富,视其为不可或缺的文明来源,而蚕食半岛领土是确保这一文明路径畅通无阻的武力手段,与新罗的对抗也由此而生。可以说,日本控制朝鲜半岛的企图就此萌芽,但此时的日本尚未形成一套完备的、可以凸显自身政治地位的外交体系,偏向于通过朴素的政治婚姻来处理外交关系,这点从《三国史记》中日本分别于312年和344年要求与新罗通婚,而非要求新罗朝贡可见一斑。(6)[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30页。
阶段二,4世纪末至6世纪,主要对抗对象为高句丽。在这一时期,诞生于中国的朝贡制度在古代东亚各国的交往中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外交形态,在正处于从部落联盟迈向统一的古代国家的动荡期的朝鲜半岛及日本,激烈的生存竞争和高涨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推动东亚各国在积极寻求参与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大的朝贡圈的同时,也在积极构筑以自身为中心的小型朝贡圈。日本开始正式由相对平等的外交而转为了一方面对半岛诸国自诩宗主,另一方面积极向中国朝贡,以事大原则谋求政治支持的外交方式,积极参与到整个东亚的国际政治活动中,并借此谋求以自身为中心的小型朝贡圈。好太王期间,高句丽加强了对百济的攻势,《三国史记》中记载,392年、394年、395年百济均战败于高句丽,(7)[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6页。为此百济不得不求援于日本,并于371年、396年与日本协同战胜了高句丽,自此“日济同盟”形成,百济对日本的示好给予了日本在半岛问题上的极大自信心和宗主国意识,而同时,为了与高句丽-新罗阵营对抗,日本也积极谋求与中国通交,加入朝贡体系,“倭五王遣使”便发生于此时。根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历代倭王遣使的表文中均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作出要求,有“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军事”“诏除安东大将军、倭国王”(8)[梁]沈约:《宋书》,上海:中华书局,2019年,第2627-2628页。的表述。同样,《广开土王碑》上记载:“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每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9)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0页。此记录虽有夸大之处,但可显示出高句丽和日本角力,均将新罗、百济视为藩国,而将自己置于宗主位置上的态度。而在《日本书纪》中,日本更是直接视三韩为“内官家”,且记录高句丽、新罗、百济都愿“永称西藩”。(10)[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4页。此条纪事虽然通常被认为是日本单方面地宣扬自身在朝鲜半岛所具有的利益的记录,不具有太高的可信度,但却可以从中清晰地读取出日本对半岛的政治意图以及对朝贡制度的模仿。此外,日本加入中国朝贡册封体系无异于一石二鸟,不仅对外增强了与高句丽对抗的砝码,对内也利用这些官爵加强倭王在国内的政治权威,促进了倭王和诸氏族之间隶属关系的形成,这也是古代日本国家的发展受到朝鲜半岛局势变动影响的重要体现。
阶段三,6世纪后,主要对抗对象为新罗,并且在着力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朝贡系统时,逐渐开始试图与位于东亚朝贡圈中心的隋、唐对抗来维持自己在半岛的利益。6世纪初新罗的崛起使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立足点——伽耶地区(任那)被新罗吞并,《日本书纪》中曾反复提及日本“重建”任那的意图,并且威胁新罗和任那使者朝贡或进献任那调,(11)[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60-276、281-284页。由此可以看出,于日本而言,在朝鲜半岛上可以获取的利益显然是不能放弃的。而新罗在594年加入隋朝的朝贡体系,在政治和文化上都越来越倾向于隋朝,并且日益在半岛上发展壮大,这自然不是日本乐于见到的结果。在此背景下,日本呈递给隋的国书中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12)魏征撰,马俊民校注:《隋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4954-4965页;[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07页均有记录。来表明双方君主的对等,鲜明地显露出日本力图与隋所建立的朝贡体系相对抗,凸显自己的地位,确立起自身对新罗的优势地位的意图。6世纪末至7世纪末,朝鲜半岛上的情况更为复杂,隋、唐相继北伐高句丽,高句丽与新罗、百济的对抗,百济与新罗的对抗都在客观上将日本推上了半岛三国所争取的结盟对象的位置,除了早有渊源的百济,高句丽、新罗也积极谋求与日本通交,更加催化了日本自认为是半岛宗主的自信心,加深了对故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对抗意识。直至白江村战役唐-新罗联军大败日-高句丽-百济联军,百济、高句丽相继灭国,日本才彻底丧失对半岛的话语权,这一结果也成为日本由氏族国家迈向律令国家的主要动力。而日本第一次对于神道的系统建设以及佛教的初传,正是基于上述的历史背景发生的。
二、神道的含义与6世纪前后神道教的基本状况
首先,在谈论飞鸟奈良时代的神道问题之前,有必要对“神道”一词加以说明。神道一语,最早的用例可以追溯至《日本书纪》,是相对于佛教对于本土固有信仰的总称。日本的神道教由于长期缺乏实质上的教义和与之相关的思想体系,至今在定义上仍存在分歧。较为知名的是津田左右吉对“神道”进行的界定,津田将日本“神道”一词的含义划分成五种:1.指日本古来作为日本民族风俗的宗教(含咒术)信仰;(13)[日]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页。2.指神的权威、力量、行动、伎俩、地位或神祇、神本身等,即传说中的神或者被称之为神的人物们的行动都被称之为神道;(14)[日]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页。3.对神代传说附会的“思想”和对其的解释,如两部神道、唯一神道和垂加神道;(15)[日]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页。4.以神社为中心形成的神道流派;(16)[日]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页。5.日本独特的政治或道德规范的“神之道”,实质上是近世受到儒学影响后,国学家为与之对抗而创造出的。(17)[日]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页。
笔者认为,基于津田的定义进一步进行归纳后,“神道”一词实际上存在两个大的层次:其一是脱胎自咒术性信仰的原始宗教的层次(包括上述1和2);其二是出于某种目的添加了外来的思想并且相对体系化的宗教的层次(包括上述3-5)。这样划分有助于解释神道定义上的分歧。譬如久米邦武指出的,“神道”本是在祭天古俗中产生,并非宗教,因而没有“劝善利生”的思想,只是攘灾招福的手段,(18)[日]久米邦武:《神道ハ祭天の古俗》,《史学会杂志》1891年第10-12卷,第230页。便指属于将神道视为上述的第一个层次的看法。而津田左右吉将汉学传入后的神道视为在中国思想影响下,仅在知识阶层之间传播的产物,则是趋向于第二个层次。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神道两个层次之间并非是前者自然发展成后者的关系,譬如两部神道便是以真言宗的密教思想来解释日本诸神而建立起的神道,神道的第二个层次,实质上是在受到外来的冲击(如佛教、儒学)后,为了对抗或调和外来的思想,而不得不借助外来思想并将其糅合在本民族的基层文化中而构筑起来的。
在明确神道的含义之后,为了方便对于飞鸟奈良时代神道建设的理解,还有必要对6世纪前后神道的基本状况作简要介绍。事实上,神道教虽然是日本的本土宗教,但其产生却相对较晚,尽管在绳文与弥生时代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就产生了如万物有灵、谷灵信仰等宗教的要素,但散落在各部族之间,并不成体系,也缺乏作为宗教的条件,只能被看作咒术信仰,主要依附于生产生活而存在。直至古坟时代中后期,随着大和朝廷的形成,从近畿到关东的大量古坟根据氏族部落、墓主人身份的不同而分成了不同的规格,显示出了一定的规范。这种古坟不仅仅是埋葬氏族中有权力者的坟墓,通常还被认为承载了祭坛的功能,(19)王金林:《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如此,日本的原始信仰才表现出了具有一定关联性的原始宗教的构造。通常日本固有信仰的基本形态,也被认为是在古坟时代形成。(20)[日]逵日出典:《神仏習合》,京都:临川书店,1986年,第25页。但即便如此,对于日后在日本神道教中显得尤为重要的有关农耕的各种仪制、祭祀仍然保持着氏族内部各自举行的分散、封闭的状态,甚至于“神道”的名称也是在6世纪初佛教东传日本后,出现了“藩神(佛)”与“国神”之分,才被逐渐应用起来。此时的神道教通常被日本的学者称为“古神道”或“原始神道”,也是符合上述定义中的第一个层次的神道。
进入6世纪之后,从推古朝改革开始到文武朝《大宝律令》颁布,日本完成了律令制国家的建设,神道处于从第一个层次向第二个层次转变的阶段。首先是佛教在日本的落地生根刺激了神道的发展。受到佛教中佛陀、菩萨等人格神的影响,日本固有信仰中的自然神与祖先神的融合进一步发展,展现出人格神的特征;而自推古朝佛教兴隆之后,各氏族竞相建造寺院,受到这一风潮的影响,原本将山体、森林等自然物视为神域的神道也开始建立固定的神社。
其次是律令建设对于神道的影响。正如前文所提及,日本深受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从争夺半岛利益到白江村战役的落败,其朝廷处在对邻国唐及不断唐化的新罗的危惧之下,旧有的氏族联盟的统制已经不能够满足对于强大的国力的需要,因此跨越氏族的障壁,建立在当时代表着先进的律令制度成了必然的选择。自此,日本从推古朝改革开始着手天皇集权的建设,直至《大宝律令》颁布才彻底完备。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为了向完全不同于旧有体制的律令制过渡,精神上的维系变得愈发重要,神道的建设正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可以说,在飞鸟奈良时代,神道的建设实际上是在佛教与律令的双重刺激,特别是在建立律令制国家的需要之下发生和进行的。与传入时已经具备严密的教义、经典、建筑乃至组织形态的佛教不同,当时的神道教仅仅是基于万物有灵、产灵信仰的朴素神观和用于祈祷的咒术、祭祀礼仪的朴素宗教,要作为维系整个律令国家的精神基底还过于稚嫩,十分缺乏通用的体系和制度。因此,基于律令的精神对民间的咒术信仰展开系统化,将固有的信仰整合到以天皇集权为主的律令的制度之下,成了飞鸟奈良时代神道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飞鸟奈良时代的神道教建设
古代日本深受整个东亚地区动态的影响,而飞鸟奈良时代的日本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面对强盛的隋唐和新兴的新罗,如何拯救自己、确保自己的立身之地的问题。因此,从氏族国家脱胎,迈向律令国家,以集权的力量来振兴国力成了当时日本的首要任务。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脱胎于古老咒术和祭祀的神道,实质上是伴随着律令制国家的建设被构建起来的,宗教成了律令国家建设中必要的一环,因此具有强烈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色彩。这一先决条件奠定了日本神道的基本性格,是“皇权神授、万世一系”融入神道教的源头。
这一时期的神道建设主要分成两条线展开:其一是神统谱的构建,其二是祭祀制度的再整理,目的均在于强化天皇的正统性,将固有的、分散的宗教权威收归皇室。因此,下文将以《记纪》的编纂和律令中的《职员令》《神祇令》作为切入点看飞鸟奈良时代的神道。
(一)修史与神统谱
事实上,上至古坟时代,在大和朝廷的势力范围之内应当存在一套简朴的祭祀神的系统。《日本书纪·崇神天皇卷》中记载,崇神天皇七年(前90)数有灾害,于是天皇驾临神浅茅原,会八十万神以卜问之,倭国域的大物主神凭依倭迹迹日白袭姬命告知天皇“若能祭我者,必当自平矣”。天皇随教而祭,但并不灵验,于是大物主神托梦天皇指出需要自己的子嗣大田田根子掌祭。于是天皇命物部连祖伊香色雄为神班物者,又以大田田根子为祭大物主大神之主,平息了灾害。(21)[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6页。这条记载反映出几个问题:其一,在古代氏族成立的过程中,豪族的祭祀权被收缴到大和朝廷手中,以此来确保大和朝廷的统治力。其二,神的身份实质上仍然是氏神,天皇祭祀豪族的氏神并不能得到相应的效果,仍需要将“神宝”归还给豪族的子孙令之祭祀。也就是说,对于神的祭祀实际上未被官方统合,是各氏族团体内部的行为。其三,大和朝廷中已有管理祭神的职位,物部氏作为“神班物者”,为中央掌管“神宝”的班收。此条还可以结合垂仁天皇二十六年(前4),天皇命物部氏前往出云国点校神宝来看。由此可以看出的是,在6世纪以前,氏族国家的祭祀虽然已经产生了统治阶级的祖神(氏神)与巫术信仰初步结合,神开始作为“人格神”被祭祀,但是皇室与各氏族所信奉的神灵应当尚未确立明确的血缘、上下和从属关系,也缺乏统一的祭祀系统,因此在实际举行祭祀时,由氏族在朝廷的监控下各祀其神。
氏族社会下的日本,同一氏族的人以血缘的关系通过祭祀共同的氏神而紧密团结在一起,尽管通过大和朝廷被统束起来,但神仍然是氏族的神,并不能为国家的凝聚力而服务,因此在整个国家需要置于天皇的统一治理之下时,仿照地上的皇室与氏族的关系,将氏族的神编入以皇祖神为中心的神谱当中就有了必要。
而神统谱的构建则是随着日本修史事业展开的。根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二十八年(620):“皇太子、嶋大臣共议之,录《天皇纪》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22)[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2页。这次史书的编纂应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出于自我意识的修史事业,(23)《日本书纪》中履中天皇四年置国史的事件仍待考证,但从目的上来说更多是出于与刘宋王朝的外交需要。详细可参看韩昇的《日本古代修史与〈古事记〉、〈日本书纪〉》(《史林》2011年第6期)。圣德太子深受隋朝文化的影响,在推行“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改革后,推行史书的编纂也在情理之中,这些都是加强国家统一、天皇集权的配套设施。从此条记述中可以看出,推动编撰的有天皇(倭王)世系、国史以及地方豪族史。根据《日本书纪》记载,《天皇纪》与《国纪》至皇极天皇四年(645)已经完成,但由于苏我虾夷遭到诛杀而被付之一炬,(24)[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42页。而代表地方豪族史的《本记》则无明显记述,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由于《本记》并非由当时承担朝廷修史学事业的苏我家编撰,而是交给各家贵族、豪族主笔,实际上尚未完成的缘故。(25)韩昇:《日本古代修史与〈古事记〉、〈日本书纪〉》,《史林》2011年第6期,第148-154、187-188页。尽管无法得知两册书中的具体内容,但从名称和编纂目的上看,对于神、皇、豪族的谱系构建已经开始。
日本的修史事业在推古朝遭遇挫折后便暂时被束之高阁,直至天武朝才重新启动,这恐怕与天智天皇时期日本在白江村一战受挫,自此加紧了律令制改革不无关系,此外也与“壬申之乱”后,有必要树立天武天皇统治的正统性有关。天武天皇时敕令编撰的《帝纪》“令纪帝纪及上古诸事”,(26)[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34页。是《记纪》直接的前身,经过持统、文武、元明和元正四代最终修成《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日本学者上田正昭指出,在《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有关神统谱的书写中,古事记的神统谱遵循了一祖多氏(诸氏族以血缘关系集中到以大和王权的神祖为中心的谱系下)的原则,而稍晚完成的《日本书纪》则比《古事记》中多了天武天皇赐姓后存在的氏族,采取了一祖代表氏(在记述氏族祖先时采用“某神为某氏等始祖也”的记述方式进行省略)的原则,因而与皇室直接存在血缘关系的氏族数量略有下降。(27)[日]上田正昭:《神統譜の展開:氏族系譜と神々の位置》,《史林》1956年第39卷1号,第5页。尽管《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在神统谱的记述上略有差别,但从成书目的上看,《记纪》实际上与前两次修史的目的是一脉相承的,撰写神代史的目的在于确立天皇统治的正统性,只不过《日本书纪》在记述中使皇室一脉的谱系更加独立而已。
神统谱的建立一方面使天皇与诸氏族的祖神在神统谱中得到与民间信仰的完全融合,成为人格神,如天照大神还有别号大日孁贵或也直接称作日神,属于将皇室的祖先神与农耕社会的太阳的崇拜相结合,确立的是天皇的神性——天皇即天照大神的血脉在人间的延续。其他氏神也有此类现象,如住吉神与“绵津见”神逐渐合一,又被记为阿云氏的祖先;而神代史中中臣氏的祖先“天儿屋命”则和鹿岛神社以及香取神社的祭神共同祭祀。(28)[日]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1页。另一方面,神统谱也是天皇与诸豪族关系的映射。贵族、豪族的氏神通过血缘或拟血缘、臣属关系建立与皇祖神的联系,由此从官方得到了身份上的承认,同时也确立了统属于皇室的关系。正如石田一良指出的,豪族的氏神被统合到高天原(即皇祖神的谱系),也意味着生活在地上的诸豪族的谱系也随之通过血缘或拟血缘的关系被统合到皇室的谱系中去了。(29)[日]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日本の心と形-》,东京:东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如此,各个氏族的祭祀体系被插入整个大的以天皇为中心的祭祀体系中去,宗教上的权威也就集中到天皇的身上,天皇作为天孙、现人神,延续了最高神天照大神的血脉,获得了无上的宗教权威,有权进一步控制和管理地方的祭祀。
(二)神道教的律令化、制度化
天皇所获得的宗教权威体现在制度上便是这一时期神道建设的另一条路线,即通过神祇官和《神祇令》的设置将神道作为核心的祭祀编入了律令的体制当中。
现存有关神祇官的内容和《神祇令》均属于《养老律令》,其中神祇官条在《职员令》内,其内容主要是通过律法规定了神祇官的官位、职责;《神祇令》的主要内容则是记载了一年四季各类需要举行的祭祀及其相关注意事项,共20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确定了一年的大小祭祀与相应时间之外,不同于古坟时期将收缴的神宝下发给地方自行祭祀,而是采取了班币制度,这显然是模仿了唐朝的做法。事实上,神祇官条和《神祇令》也是模仿了唐朝的祠部及大常寺的设置。(30)[日]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9页。神祇令中规定:“其祈年、月次祭者,百官集神祇官。中臣宣祝词,忌部班币帛。”《令集解》对此条注释:“班,谓班诸国也,时行事社社祝部,参神祇官受取尔”。(31)国书刊行会编:《令集解》第1,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第214页。即,每逢祈年和月次祭(事实上还有新尝祭),诸地方神社都需要派祝部到中央的神祇官厅,聆听中臣氏宣读祝词,再领取忌部氏所颁发的币帛,带回本国祭祀,这显然是为了将地方神社置于朝廷的管理之下。如此一来,地方的祭祀必须要领受神祇官厅的币帛,收缴豪族的“神宝”已无必要,因此才有了“元来诸家贮于神府宝物,令皆还子孙”一事。(32)[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19页。
此外,根据神祇官条中的内容,神祇官具有司掌名籍的职能,即管理地方祝部和神户(受神社管理的百姓)的名籍。地方神社的祝部由国司选定上报或者由神祇官遣使卜定,(33)国书刊行会编:《令集解》第1,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第32页。如此一来,地方神社的管理同样也受到神祇官厅的制约。而让朝廷任命的国造主持祭祀的做法,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经过神祇官体制的确立,曾经分散的祭神的权力和实际上祭祀的流程都受到朝廷的管控,在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的同时,地方豪族及其所掌管的地方神社的祭祀也被置于律令制度之下了。
同时,祭祀制度的重新整合也确实为律令的实际运行提供了便利。前文已多次提到,日本向律令国家的转变并非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受到东亚国际环境的影响而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问题。奈良时代的地方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前,仍处在由豪族统帅的、咒术性格浓厚的集体社会中,普通百姓难以明白繁杂的租庸调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祭祀制度还为朝廷加强对百姓的控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义江彰夫指出,神社颁发币帛的制度是一种征收租税的咒术性办法,通过将带有皇祖神灵力的“币帛”赋予地方,国家获得了以“初穗”的名义征收租税的权力。(34)[日]义江彰夫:《日本的佛教与神祇信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24页。这反映出在日本组建律令国家这一变动的过程中,神道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精神维系、精神支柱的作用。
综上所述,神道教的第一次整合——上述神统的构建与《神祇令》的颁布,充分体现了古代日本政事即祭事的特点,既是一种律令建设中的政治行为,又是一种宗教意味上的变革,是受到来自东亚国际形势刺激后的产物。从实际的效果上来说,飞鸟奈良时期的神道建设赋予古来的祭祀以律令制度的精神,是原始的、朦胧的巫术迈向系统化、体系化的关键性一步,经过这次建设,天皇作为宗教和世俗双重意义上的君主的身份同时得到信仰和律法上的确立,其存在甚至成了激励国家团结的一个文化符号,自此融入了神道的固有性格。
四、结语
由于朝鲜半岛一度成为日本摄取文明的主要途径,自公元4世纪开始,日本已经深度参与到东亚国际政治中,力争朝鲜半岛上的任那伽罗地区,试图保障自己的文明通道。从推古朝与隋的交往可以看出,自飞鸟时代起日本的对抗意识越来越强,一方面向中国学习先进的制度、引入大陆的文化,另一方面已经开始试图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然而,由于在白村江战役中落败,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加之百济与高句丽相继覆灭,强烈的危机意识推动了日本从古代氏族国家向律令制国家的转变。改革意味着变化与动荡,必须有精神上的维系和支撑,因而作为天皇权力来源的神道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该时代朝廷通过神统谱的构建和祭祀制度的法制化,使过去以氏族为中心的巫术信仰和祭祀被团结到以皇室为中心的谱系之下,倭王成为天皇,拥有了宗教和世俗双重意义上的君主的身份,而神道也被赋予了律令的精神,“万世一系”自此植入了神道的基因当中。在飞鸟奈良时代,除了神道,佛教同样对日本转变为律令国家给予了宗教和精神层面的支持,并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一时期,神道教的整合与佛教的接受和建设几乎是同步展开的,在《日本书纪》中,有时还会将天皇对佛教和神道的态度并列记录。(35)如记载明天皇纪“信佛法、尊神道”;孝德天皇“尊佛法,轻神道”。参见[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89、343页。这种神佛并行不悖的发展方式同样与建设律令国家的主要任务相关,并且这种神佛并重的做法还深刻影响了平安时代的神道与佛教的发展。因此,将飞鸟奈良时代的佛教置于东亚视域进行考察,探索神、佛如何在建设律令制国家的大背景下相互作用,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东亚国际环境给予日本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飞鸟奈良时代,而是贯穿了日本整体的历史进程。由于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特殊,对于日本来说既是通往大陆的交通要道,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因此近代以来日本对朝鲜半岛所采取的种种政策也绝非偶然的、突然产生的,而是存在历史必然性并且有迹可循的。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自古代开始,东亚各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摄取先进的文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古代中国,由于自身文明的发展程度较高,其动向对于东亚地区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东亚地区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其历史的、现在的乃至于未来的发展状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研究东亚各国的发展历程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时,无论古今,都不应当忽视以整体的东亚区域的视角切入、关注东亚国际政治环境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