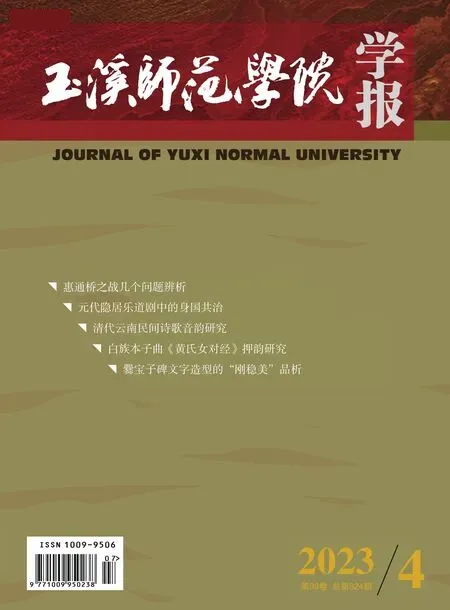杜甫《伤春五首》其二“兄弟”异解
王之意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杜甫《伤春五首》是其在阆州时期的名作,题下原注:“巴阆僻远,伤春罢,始知春前已收宫阙。”①(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1309.本文凡引用杜诗,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出注。这组诗感时伤世,既是代宗出奔之事的实录,亦为杜甫僻居巴阆而忧心京华的反映,在杜集中地位重要。《伤春五首》其二有句“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关于其中“兄弟”一词,历代注家并无异议,通行的权威注本均以为此处的“兄弟”应指杜甫兄弟而言。《九家集注杜诗》解“不是”二句曰:“言虽有兄弟,而为丧乱阻隔,不得相保耳。”②(宋)郭知达,编,陈广忠,校点.九家集注杜诗[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1217.仇兆鳌云:“且想兄弟别离,能无北望伤神乎?”浦起龙谓:“公弟颖、观、丰皆在他乡,惟占从入蜀,时又以检校草堂往成都。”③(清)浦起龙,著.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738.皆以此句为杜甫忧家之语。然而,这些解释都仅就“兄弟”一词的字面含义立论,而忽视了此句与全篇主旨的关联。曹慕樊对上述解释独标异见,否认“兄弟”所指为杜甫兄弟,因杜甫有弟无兄,作诗不会连用“兄弟”二字,而此联中“兄弟”确指玄宗诸子无疑④曹慕樊,著.杜诗杂说全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39.。此说有两点值得怀疑的地方:第一,杜甫可以用“兄”指代自己,以“弟”称呼诸弟;第二,杜甫除了同父同母的弟妹以外,尚有旁支的从兄。
遍搜杜集,可以发现杜诗中实有连用“兄弟”的例证。杜诗中的“兄弟”含义不一,其中“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兄弟分离苦,形容老病催”所指都是他自己的兄弟,而“岑参兄弟皆好奇”“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则显然是就他人兄弟而言,可见杜诗并非没有连用“兄弟”之时,且含义并无一定。探究杜甫《伤春五首》其二中的“不是无兄弟”所指究竟为何,应对“兄弟”一词的文化渊源予以追索。下文简要梳理“兄弟”除一般意义上的亲缘关系外,另一条与政治内涵发生紧密联系的发展脉络,以明其存在双重指代的可能性。
一、不同时代“兄弟”一词的文化内涵
周初分封七十一国,中有兄弟之国十五。授民授疆土之外,亦要求诸侯对王室承担屏藩保卫的义务。受封诸侯须朝觐述职,并在对外战争中响应军队征召,提供武备支持与军用供应。在此封建基础之上,建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结构,由此形成水乳交融与分封制的宗法制,共同构成周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①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87.此一时期形成的政治文化制度深刻且持久地影响了后世诸多政治形态的产生,而大量文化现象的出现亦有迹可循,当从其源观之。亲缘关系与宗法政治自诞生起便不可须臾或离,纵然在王朝更替中经历过剧烈变革,仍深植于方方面面。“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与家国同构的血缘政治,须置于相同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观照。“兄弟”一词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封建亲戚的宗法社会中,异性诸侯须通过联姻结缡,产生亲厚血缘关系以保障协同万邦的稳定性,此为“甥舅之国”;同姓诸侯则具有天然优势,作为“兄弟之国”活跃在政治中心,承担着拱卫王室的重要历史职责。
1.先秦两汉
在早期王官旧典中,由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特性,“兄弟”一词与王室手足具有自然关联。先秦文献中大量出现以“兄弟”一词指代王室宗亲、同姓诸侯的案例。《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②(清)阮元,校刻,蒋鹏翔,主编.阮刻尚书注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1081.由“友于兄弟”延伸至施政之上,成为血缘与政治联系的键钥。与之相近,《毛诗·大雅·思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③(清)阮元,校刻,蒋鹏翔,主编.阮刻毛诗注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2202.亦体现了从亲亲之义推广为政治秩序的典型儒家思想。汉代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分封与宗法制的走向仍甚明晰,其时《诗经》阐释往往与政治讽喻不可分割。《王风·葛藟》中重章复沓的“兄弟”一词被指实为周室亲族,全诗宗旨则为怨刺周平王不亲九族,“终远兄弟”④(清)阮元,校刻,蒋鹏翔,主编.阮刻毛诗注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600.。此为将“兄弟”一词与王室宗亲不睦相联系的早期文本。从《尚书》的“友于兄弟”,到《诗经》的“终远兄弟”,王室宗亲之间的关系逐渐得到展示,前者是美政的理想范式,治国施政需由此而来,后者则是讥讽怨刺的对象,因其会带来“争国”“道衰”的危险后果。战国时期,王官之学散于百家,《管子》将“明立宠设”作为君臣之道的重要内容,并阐发其政治意义——“兄弟无间隙,谗人不敢作”⑤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586.。手足宗亲之间明确等差,遵循礼义,国家的根基便稳固。《韩非子》提出了一致的论断:“兄弟不服,必危社稷。”⑥(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24.诸子希图将主张与思想应用于政治蓝图的构建中,为“兄弟”一事反复致意,可见当时各国同姓手足之间冲突频仍,对国家产生的动摇也不在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在记载当时各国政治事件的史籍中,“兄弟”为乱的问题更加突出。《国语》富辰谏周襄王曰:“郑在天子,兄弟也。”⑦徐元诰,集解,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44.以“兄弟”谓同姓诸侯国,并征引《棠棣》诗句,力谏不可以小忿弃兄弟之亲。《左传》呼吁“一二兄弟甥舅”⑧(清)阮元,校刻,蒋鹏翔,主编.春秋左传注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4591-4592.踵武贤迹,从先王之命,尊勤王之义,追溯周初封建亲戚的旧事,继而称引幽王、惠王时期诸侯兄弟急难故事,其中“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直以“兄弟”二字代指诸侯宗亲。
根据上述材料,可知先秦两汉时期,“兄弟”一词时常蕴含王室宗亲之义,尤其在早期的王官旧典中,家国一体的属性使血缘与政治自然结合,无需作特殊说明便身兼二职,亲属关系以外,更明确地指向政治权责。
2.魏晋南北朝
“兄弟”一词在魏晋南北朝的涵义绍续先秦,未见中断。曹魏时期,曹丕、曹植二人乃历代兄弟不睦的代表,且曹丕称帝后,二者的兄弟关系便蕴君臣之分,与本文所论要旨可谓严丝合缝。曹植的《求存问亲戚疏》自抒心志,为世所传诵,中云:“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绝。”①(三国魏)曹植.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649.曹丕在《诏报东阿王植》则一一回应:“恩泽衰薄,不亲九族,则《角弓》之章刺。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②(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571.可见“兄弟”一词在血缘关系以外兼具政治属性。曹丕更上溯《诗经·角弓》的文化史涵义,将“兄弟”与“九族”“诸国”等词相联系。曹冏《六代论》借古喻今,谏奏魏“亲亲之道未备”③(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592.,认为固同姓之辅、明亲亲之道乃国家安定的重中之重。虽以贤贤与亲亲并提,而实强调手足在急难御侮、宗盟藩卫上的作用。“兄弟”不仅能辅佐政事,建立功业,更重要的是能使国家“本枝百世”,统续始终在同姓宗族间承继。
同样看法与建议历代屡见不鲜。至南朝,裴子野《又明帝诛诸弟论》不仅枚举前代危亡之君的恶例,警告“先弃本枝”乃祸乱之始,将国家安危系于能否“友于兄弟”之上,更重要的是他将曹冏《六代论》所蕴含的潜文本明白揭示,且进一步阐发:“借使叔仲有国,犹不先配天;而它人入室,将七庙绝祀。”④(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21:4233.即对于国家宗庙而言,君主只要为同姓兄弟便可,在位之君是否能够永葆其位,相比之下则不甚要紧。这也是臣民不断强调“兄弟”的重要性,劝诫君主亲睦手足,而君主往往背道而驰,排斥甚至打击“兄弟”的关捩所在。
唐人诗文瓣香齐梁,破立之功虽大,在典故、符码的用法上却仍有大量祖述之处。杜甫提倡“熟精文选理”,对南朝诗文谙熟于心,并时常化用。这一段时期奏议书表中的“兄弟”一词,具有同于此前的政治内涵。梁元帝《又与武陵王纪书》云:“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⑤(唐)姚思廉,撰.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827.邵陵王纶《与湘东王书》云:“兄弟与湘雍,方须叶力。唯亲惟急,万倍于斯。”⑥(唐)姚思廉,撰.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23.侯景乱时,武帝诸子分散在外,父子兄弟之间既有地域阻隔,更有政治争斗,诸王彼此离心,不能团结一力勤劳王室,以至家国沦丧。故此时尤多“兄弟”一语,乃政治局势的直接反映。
此外,唐代距隋不远,相关语义多有沿袭,变化不大。隋炀帝《手诏劳杨素》论平汉王杨谅谋反之事,云“朕寡兄弟”“由朕不能和兄弟”⑦(唐)魏徵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289.,“兄弟”一词囊括同姓诸王、手足不睦、犯上作乱等政治内涵。而其上追经典,用《春秋》周公诛管蔡故事,下罪自身不能和睦兄弟,以致动乱荼毒,更为逐渐固定、沿袭套用的论述模式。
二、杜甫时代所见“兄弟”之含义
杜甫所处的唐代,“兄弟”一词的内涵延此理路继续推进。君王所下的诏书、册文中所见“兄弟”最能说明情况。杜甫生长于玄宗朝,唐玄宗尤其善用“兄弟”以睦亲叙好,维护统治。其《鹡鸰颂》中兄弟“载崇藩屏”与“有睽谈笑”⑧(宋)钱易,撰,梁太济笺证.南部新书溯源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3:6.正代表了天家手足的政治与亲缘两方面作用,前者乃自古藩王皆应躬行的义务,后者则更多在文化礼制与精神教化上结实,共同发挥襄辅中央的政治功能。《纪泰山铭》更在以盛德形容告山川神灵时将孝友兄弟之义与“锡类万国,时惟休哉”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902.的理想美政相合而荐。无论是托物喻志,还是登山纪铭,都时时敦叙手足之情,昭告“友于兄弟”之义。玄宗尤感其长兄李宪辞让储位之恩义,作《奠让皇帝文》,谓“一代兄弟,一朝存殁”②(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031.,对兄弟揖让一事反复致意。此外,花萼相辉楼的修建亦与其以宗室辅翼中央的政治思想相关,用《诗经·棠棣》典故昭示天家手足之情,可见玄宗对这一宗旨的重视。远取诸物,在天之羽翼与在地之花萼,兄弟亲情均未与承辅拱卫王室的政治内涵相疏离。
除帝王册书外,臣子为皇帝所写的章表奏议等亦多言“兄弟”,张九龄《惠庄太子哀册文》为玄宗二兄申王作哀册文,亦就血缘与政治两方面并言,于“分王子弟,藩卫京师”后既以少年亲爱的追怀:“昔在冲妙,具惟兄弟。四国并封,五王均体。”③(唐)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923.贾至《肃宗皇帝即位册文》嘉许肃宗:“尔有友爱之义,信于兄弟。”④(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2.对皇帝善友兄弟的屡屡提及和称道,可以反映其时士人的共识:和睦兄弟,以固本枝,乃评价圣明天子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之一。而皇帝在诏书中亦屡申“友于兄弟”,足见其对这一价值标准的接受与认可。南朝因兄弟不睦而国祚不永之事甚多,前论已详,殷鉴不远,故唐朝君王对此尤其注意。杜甫作为关心时政,且深谙历史兴衰的士人,对此更有深刻认识与领会。
“兄弟”一词的文化内涵从先秦发展到此,由于宗亲不能戮力同心、效忠王室,甚至兄弟争国,致使中央孤立、根基动摇的事件不胜枚举,杜甫同时人元结在论及政事时再三讨论王室兄弟,《时规》曰:“何不曰愿得如九州之地者亿万,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争国者,使人民免贼虐残酷者乎?”⑤(唐)元结,撰,孙望,校点.元次山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97.“兄弟”在指涉王室手足之时,常常一方面寄托其相互友于以固国本的期许,一方面蕴其彼此离心,或将造成国家危乱的政治隐喻。
三、杜甫《伤春五首》“兄弟”一词辨析
1.以庾解杜:外在文本的互文
前文谓唐代诗文瓣香齐梁,杜甫则是其中集大成者,而尤为服膺庾信。带有回顾总结性质的《戏为六绝句》中“庾信文章老更成”最具代表性,更可拆分为二层次予以理解:“庾信文章”谓其诗赋篇章艺术造诣之高,既慕其格调,云“清新庾开府”,亦赏其风力,称“凌云健笔意纵横”;“老更成”则着眼于庾信入北后,身历兵燹而境界一转的生命体验与文风趋向,即“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陈寅恪提出以庾解杜、以杜解庾,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中以古典字面与今典实指相证。在点明庾杜二者在文本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的相似性以外,其谓“杜公此诗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01.,更超越了前人以庾诗解杜诗的藩篱,打破了赋与诗之间的文体隔阂而以文义互释,予本文以庾赋解杜甫《伤春五首》其二“兄弟”一词重要启示。
除身世飘零的共同遭际外,安史之乱对杜甫及其同时人所产生的心灵创伤是重大而持久的,而其与侯景之乱的相似性,亦使杜甫拥有了与庾信相近的流离体验与战争记忆,或促使其对谙熟于心的庾信作品进行同调书写。《哀江南赋》作为凝聚庾信生平心事与沉恸反思之作,以其艺术性与影响力成为杜甫创作《伤春五首》时的心魂所寄。倪璠注《哀江南赋》云:“《哀江南赋》者,哀梁亡也。”⑦(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94.而作《伤春五首》的杜甫时在蜀中避寇,也面对着王室蒙尘,群凶百战的国乱,自身更经历着远离乡关的痛苦,与庾信不谋而合,二人于此有隔代知音之感。从诗题上看,杜甫《伤春》五首典出《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①(宋)洪兴祖,撰,白化文,校点.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15.仇兆鳌《杜诗详注》解此诗题曰:“因以发其感愤之意,遂名曰《伤春》。《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故以为题。”②(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1309.《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的下一句正是“魂兮归来哀江南”,言其与庾信《哀江南赋》之题有所对应,乃至《伤春五首》正是杜甫致意庾信《哀江南赋》之作,恐非厚诬古人。
从内容上看,则更可找到杜甫《伤春五首》与庾信《哀江南赋》的共通之处。《伤春五首》其二“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一联,同时出现“兄弟”与“别离”两个词语,庾信《哀江南赋》则有“五郡则兄弟相悲,三州则父子离别”③(北周)庾信,撰,(清)吴兆宜,笺注.《庾开府集笺注》卷二《哀江南赋》,上海图书馆藏中华民国75 年(1986 年)影印本(书号:006703),第17a-17b 页.此后引庾赋原文均据此本,不再一一出注。之语,“离别”倒换次序作“别离”,与“兄弟”连用。倪璠注此句曰:“言侯景攻城甚急,武帝诸子援兵在外,父子兄弟不相接救也。”④(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6.认为此乃庾信为梁宗室不能勤王所作的忧愤之辞。前辈学者研究认为倪注多剿袭吴兆宜的注解成果,且其差异处往往为倪氏为标新解而故发异说,不可尽信⑤朱晓海.庾信《杨柳歌》释论[J].古典文献研究,2008(00):152-187.。吴兆宜《庾开府集笺注》卷二《哀江南赋》注此句,则谓侯景之乱使“兄弟相要俱缘山岳”以避乱,千里断绝人烟。即不以倪注为是而认为此处“兄弟”确指王室手足,亦不得不联系《哀江南赋》的创作主旨:乡关之思的来源正是“哀梁亡也”。除了自伤身世乱离与痛悼王气黯然,更重要的是反省与追索梁亡根由。《哀江南赋》以极大篇幅对此予以剖析,其中宗亲不睦以致国本不固,亦为其深自措意处。其中“晋郑靡依,鲁卫不睦”之语,谓诸王相互倾轧而无讨贼之志;在行文接近尾声时再论“伯兮叔兮,同见戮于犹子”,对萧墙之祸的伤恸贯穿全篇,亦见其深知萧梁王室骨肉手足间的惨酷之事反复上演,桩桩件件均使本已飘飖的山河社稷于外患之外更摧折于内。若不断章取义而将《哀江南赋》作为整体予以关照,“兄弟相悲”“父子离别”之句在指代五郡三州的普通人家外,以隐晦方式对需承担故国覆灭之责的萧氏父子兄弟加以影射,恐为庾信作赋时另一重不可忽视的心理因素。
若进一步以其他庾信赋作为着眼点,虑及庾集系统内部存在紧密联系,即见《伤心赋》与《伤春五首》同用“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之句,一者伤心,一者伤春,文化符码实无差异。更紧要之处在于,兄弟离别的句式在《伤心赋》中再度呈现:“兄弟则五郡分张,父子则三州离散。”与《哀江南赋》所言几乎没有分别,而《伤心赋》“既伤即事,追悼前亡”,亦深怀家国之悲,以金陵丧乱的国难为自伤失子的注解。“在昔金陵,天下丧乱。王室板荡,生民涂炭”⑥《庾开府集笺注》卷一《伤心赋》,11a.正是兄弟父子离散分别的背景,此与《哀江南赋》实为哀伤之同调,唯其立意于伤己,而彼多着墨于萧梁政权耳。二者的共同之处,仍在于大我与小我的打通,这缘于庾信生平际会,无论是射策之年的风流俊赏,抑或流寓秦川后的千愁万恨,均与社稷治乱安危不可须臾或离,其身遭遇既为国家盛衰之反映,其文亦时时兼二者而共论,不得明晰区别何者为己身所作而何者为政局写照。
无论是《哀江南赋》还是《伤心赋》,目极千里而伤的春心,均为家国一体的真切反映。其中分离散乱的父子兄弟,当是既人既己,亦国亦家。而杜甫一生奉儒守官,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儒家精神不仅为他所躬行终身,亦时时交织于其作品中。前文论述已备,杜甫写作《伤春五首》之时,有庾信其人其事的影子徘徊于心,所谓“萧条异代不同时”,而国身通一的诗史精神,则与庾信见证金陵覆灭后窜身北国,歌咏赋颂以载史、以抒郁的怀抱一脉相承。杜甫世称诗史,庾信亦夫子自道“唯当一史臣“,固然如上文所论,“兄弟”一词包含家国同构的传统政治特征,而以庾解杜的成立理据,则正在于二人均有意实践以诗(赋)存史的文学精神。
此外,梁元帝在《驰檄告四方》云:“虔刘我生民,离散我兄弟。”①(唐)姚思廉,撰.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23.亦为“兄弟”与“别离”(“离别”“离散”)连用的句式。这种叙述模式会带来王室手足离散,兵乱兴起而无兄弟接救的联想,在时代间距不远的杜甫眼里,甚至可谓是一种固定的文化符码。据此,《伤春五首》其二“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一联,乃杜甫感时伤事之语,与庾信既伤即事且追咎前业一般无二,在慨叹身世飘零,不得与兄弟聚首之外,对造成骨肉分离的政治原因亦曲折隐写,宜其与庾赋相侔,对唐王室兄弟之事有所指射。
2.以杜证杜:杜集内部的对应
着眼于《伤春五首》文本内部,尚有对此联“兄弟”一词予以异解的旁证。杜甫作组诗多一气贯注,浑涵汪茫、不蔓不枝,丝丝入扣而自成系统。《伤春五首》乃为吐蕃之乱、代宗出奔的国难而作,主旨与叙写脉络均甚分明,故“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一联于其间显得颇为突兀。实则清人注杜时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杨伦言“二首感身而仍归感世”②(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87.,浦起龙称“本是忧朝廷,而兼及兄弟者”③(清)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738.,张远曰“独第二首略入兄弟”④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037.,皆以过人眼光点出若以思家阐释此联,则与全诗方枘圆凿。
这组诗作于广德二年春,此时僻居巴阆的杜甫不知代宗已还京,消息阻隔,只能凭借“近传”“闻说”了解时局。《伤春五首》其二曰:“牢落官军远。”仇兆鳌注曰:“援军不赴”;其三曰:“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吐蕃入寇之时,代宗狼狈出奔,征召诸道兵马,而将帅不和,“莫有至者”。当时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⑤(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21:7274.情况与侯景攻城之时,武帝诸子无人急难勤王相类。其五曰:“胡虏登前殿,王公出御河。”王公皆逃出京城,无人为王室效力,尤为切近“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一联所指之事。这段历史在《资治通鉴》得到保存:
射生将王献忠拥四百骑叛还长安,胁丰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仪于开远门内,子仪叱之,献忠下马,谓子仪曰:“今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在一言耳。”子仪未应。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仪责让之,以兵援送行在。⑥(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21:7270.
当时王室宗亲各怀异心,已失去庇护本根、屏藩中央的作用。丰王等十位宗亲非但不能跟随车驾、援助代宗,甚至西迎吐蕃,图谋废立。此时政局动荡不安之状,正同于侯景乱时。“友于兄弟”之义已不再起效,内忧外患齐作,面对这种情况,杜甫自然忧心忡忡,对历史经验的熟悉,以及对未来现实的洞察,使他不能不将此刻的危局与庾信所处的时代相联系。
非但《伤春五首》,作于同一时期的作品亦反映了同样的心态,如《遣忧》“纷纷乘白马”,即用《哀江南赋》“青袍如草,白马如练”典故,明以侯景之乱比拟即事。再如《有感五首》其四以青梧丹桂谓王室宗藩,“言王室不安,由于宗藩削弱也。”⑦(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95.此与自古以来枝叶本根的喻象一致,唯以颜色修润其形貌,使其愈富天家气象。然而这般高贵美好的生命却面临着风霜摧折、日夜凋伤的处境。杜甫于起句比兴后赋以直叙:“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直以“强干”一词钩连起譬喻之树与现实生活中的王权政治。层层推进的写法,有如愤懑已久的情感亟需抒泻,致君尧舜的忠谏已不吐不快,“授钺亲贤往”乃令同姓掌兵的具体措施,“终依古封建”则是殷切期许下掩抑不住的失落与忧思。杜甫对于王室宗亲的看法与各时代有识之士一脉相承,主张分封同姓,以固中央之本,敦睦兄弟,使患难之时有手足驰援护持。安史之乱时,房琯献分镇讨贼之策,曾令安禄山叹息不得天下。杜甫深许于此,多有劝谏朝廷封建宗亲之议,其《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必以亲王,委之节钺”①(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2656.即是“授钺亲贤往”的同趣异构,亦以古为证,切切申说“维城磐石之义”,使根固流长以葆社稷于万代。国家治乱在于同姓宗亲是否同心,能否有力维持中央稳固,杜甫对这一点的认识极为深刻,且身体力行以至坐房琯一党贬斥。诚然,杜甫写作《伤春五首》之时,有思念手足、自伤兄弟失落各地而不得聚首的忧家之情,而无论是结合传统政治的亲缘性质,或是关注杜甫以诗存史的特点,皆促使我们不可一叶障目,在忧家之语外更须措意其对政局动荡原因的反思,同对家国从未弃捐的忠忱与关切。
从外部系统看,杜甫写作《伤春五首》之时实为遥相呼应庾信的《哀江南赋》与《伤心赋》,连用“兄弟”与“别离”,暗蕴手足离散、政局危乱的喻义;从杜集文本内部看,杜文有谏议分封宗亲之语,且与《伤春五首》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有感五首》明确提出亲睦兄弟、以枝叶强化本干的观点。《伤春五首》其二“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这一联中的“兄弟”一词,涵义极为丰富,既是忧念手足,亦兼指李唐王室宗亲,关涉代宗时期藩王不能拱卫中央之时事,故其不仅反映着杜甫国身通一的诗史特征,更是血缘政治家国一体的诗性写照。
四、结 语
通过对历史各时期“兄弟”一词内涵的梳理,可以发现从先秦至唐代,其用法的生成与演进均与王室手足这一指涉密不可分。杜甫《伤春五首》其二“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这一联,更是以“兄弟”与“别离”连用,暗用庾信《哀江南赋》《伤心赋》等名篇,具有讽喻王室宗亲不能捍卫中央,乃至祸起萧墙的隐形笔墨。“兄弟”一词的文化含义,是本文立论的内在理路;杜甫对六朝文学的自觉师法与化用,则是此一推论得以成立的互文依据;杜集系统内部的同时作品,则为此联“兄弟”一词兼指杜甫手足与王室宗亲提供了有力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