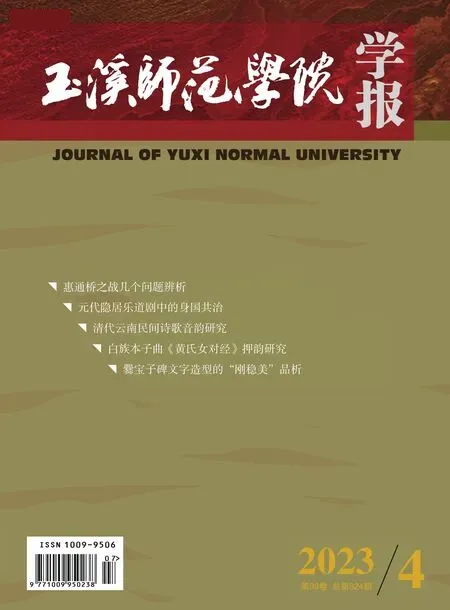论多多诗歌的现代修辞策略
宋艳珊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诗人多多从1972 年开始写诗至今,持续创作出众多成熟而厚实的诗作,但因其“流亡者”的身份,其诗歌在上世纪的中国一直遭受“冷遇”。2003 年,多多从海外归来,之后频频摘得华语传媒大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屈原诗歌奖、北京文艺网诗人奖、昌耀诗歌奖等国内外诗歌大奖。归国20 年来,多多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批评家所提及,并且越来越响亮,在诗坛上引起过不小的“多多热”,甚至于在所谓的诗坛排座次中成为遥遥领先的大师之一。然而,很可能是因为多多倾心于语言极限性试验而使得他的诗歌代表了现代汉语诗歌阅读的难度,因此目前关于多多诗歌文本的单独研究成果甚微,诗歌批评多是粗括性评论和对多多在当代诗歌中的重要性给予总体肯定,或者是对其个别诗歌的细读。
多多作为“白洋淀诗群”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是一位具有现代主义诗歌品质的诗人,他在现代诗歌技巧的运用上不断实验力求走得更远,甚至投入每首诗至少修改70 遍的热情,苛刻去经营每一首诗歌,几十年如一日地演练着现代主义诗歌技法,真可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多多现代主义诗歌技法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象征与暗示、变形与荒谬、机智的反讽三个方面。
一、象征与暗示
象征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借用具体、形象的事物,暗示特定的人物或事理,以此表达更深层次的情感和寓意,象征的形象要求去探索它背后的内在意义。这一定义规定了象征的两个必备条件:象征物与象征意义。可以这样说,象征的含义和隐喻相近,是词语的想象性含义、词语与词语之间意义的隐喻性释放,它的暗示和隐喻色彩更浓,充满着艺术魅力。象征是意象的表达手段和存在方式,因此谈象征手法离不开意象。从某一程度上说,意象其实就是象征化的结晶。象征往往不明确地表达意义,而是通过暗示把象征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取消或打断,从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己去操作完成两者之间的联系。诗歌和暗示紧密相连。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就认为如果一味直陈其事会让诗歌的乐趣消解掉四分之三,而这四分之三的乐趣就包含在读者一点一点用心去领会它的过程之中,他强调“暗示”,重视“隐语”,并觉得只有“暗示”或“隐语”才能让诗歌意象超越日常事物,给读者以幻梦,并引领读者在幻梦中振翅飞翔。在诗歌创作中,多多有意识地规避着传统手法中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和直接抒情,经常娴熟地运用象征和暗示去建构自己独特的诗歌世界,使得诗歌深层具有无穷的意蕴,从而更具感染。
多多很早就标榜他是一个象征主义诗人,并声称波德莱尔对他影响极大①多多.多多诗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269.,他尤其擅长从感觉形象中化出多义抽象,所谓“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多多诗歌中象征与暗示手法的运用已经非常纯熟,试看一例:
十一月入夜的城市/唯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突然//我家树上的桔子/在秋风中晃动//我关上窗户,也没有用/河流倒流,也没有用/那镶满珍珠的太阳,升起来了//也没有用/鸽群像铁屑散落/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显得空阔//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我的祖国//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阿姆斯特丹的河流》②多多.多多诗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158.
游子客居在远离乡土的异国城市里,入夜不眠,因此,“阿姆斯特丹的河流”不仅仅只是一条地标性的河流,它成了游子浓重乡愁的象征。“十一月”正值秋天,加之后文的“秋风”,“秋雨”,全诗笼罩着一种“已觉秋窗秋不尽,哪堪风雨助凄凉”的愁绪。“桔子”是暖色调的,犹如橘黄色灯火,暗示了一种归属,它是“我家”的、“树上的”,它的“晃动”既象征着召唤,也暗示诗人内心的震动不安。“关上窗户”象征着逃避现实,“河流倒流”象征着回忆过去,等待太阳升起,象征着寄希望于未来,可是无论逃避、回忆还是期待未来都没有用。“鸽群”是轻盈的、温暖的、灵动的,“铁屑”则是沉重的、冰冷的、生硬的,诗人在此把两个具象词语进行非常规搭配,把无形的、抽象的乡愁表现得影像一般具体和立体。诗人思念的祖国是“爬满蜗牛的屋顶”,屋顶供蜗牛栖居,而每一只蜗牛背负着专属于自己的“家”,无论屋顶还是蜗牛都有一种踏实的负重感,于是,阿姆斯特丹的河流便蕴涵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去国怀乡的忧愁与追思。
再比如,在《大宅》中,“月亮亮得像伤疤”暗示着自然所受到的伤害;在《万象·夏》中,“花仍在虚假地开放”象征着欺骗与谎言;在《年代》中,“血淋淋的篱”表现了暴力带来的恐怖,等等。多多的诗歌创作擅长突破传统语境去开掘出具有现代象征意义的意象,显现出强烈的个性特征。
二、变形与荒诞
变形和荒诞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常用的手法,多多在创作诗歌时也大量地运用变形和荒诞来增强诗歌的表现力。所谓变形,原意是“歪曲、走样”,作为写作技法使用时是指作者根据需要,对人物、情节和环境进行突破常规的艺术重组和曲折表现。而荒诞是指诗人通过非理性的极度夸张、离奇幻想、变形扭曲等等表现形式,将现实与非现实杂糅在一起,寓严肃于荒诞的艺术手法。多多的诗歌意象给人奇诡怪异的感觉,这“怪”多半源自他所采用的变形与荒诞的艺术手法。
艺术变形是艺术家们利用高超的审美智慧去再造外部世界,或把内容中事物的本质特征放大,或夸张处理形式方面的表现对象,使之艺术地呈现出“歪曲走样”的陌生感,使作品更具有表现力,因此它也是现代诗人最惯用的艺术手法之一。运用变形手法,可以悖离常规,超越读者习惯性的阅读期待视野,从而艺术地创生一种新鲜奇妙的趣味感。荒诞艺术是一种具有彻底的否定精神和强烈的批判精神的批判艺术,它不是简单肤浅地针砭时代的某些弊病或人性的劣处,而是通过表现一个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的充满悖谬的世界,来唤起人们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怀疑、否定以及反抗精神。无论是变形还是荒诞,关键在于能不能巧妙地把客观真实与作者主观感受之间的对立合理转变,使之生成一种“无理之中的有理”。
多多写诗开始于“文革”时期,那是一个非理性的年代,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语境之中,诗人们也遭遇着无比尴尬的境遇,多多与同时期的“地下”诗人一道,他在精神上与心理上被迫强行完成了一次彻底的大手术,“好像刀光一闪”(《那是我们不能攀登的大石》),从恐怖的手术台上重新站起来的诗人重新开启自己人生道路的方向,他把诗歌作为武器,用不一样的声音替一代人呐喊,同时也是为自己申诉,如同秉持锋利手术刀的医生,精准地切下被粉饰的社会所掩藏的肮脏与腐败。这时,如同觉醒之后的卡夫卡让格里高利变成一只大甲虫,非常荒诞而又非常合理地表现了社会对人的挤压、打造和改写,多多在其诗歌作品中极为熟练地采用了变形与荒诞的艺术手法去打破寻常逻辑,瓦解和重新组合被理智法则所规定的世界,以扭曲变形的意象构成一个怪异荒谬的诗歌世界,从而表现其怪异荒谬之中的内在真实。例如“醉醺醺的土地上/人民那粗糙的脸和呻吟着的手”(《无题》),“土地”成了醉醺醺的酒鬼模样,丧失理智与人性,而“呻吟着的手”显得多么的不可思议,又错乱又荒谬,同时弥漫着一种恐怖气息,而这里越是怪诞,就越是表现出那个荒谬年代里让人禁不住倒抽冷气的内在真实。再比如《妄想是真实的主人》一诗,标题本身就充满悖谬意味,是肯定之否定。简单看来,诗歌有两个中心意象即“鸟”和“人”,从诗歌内容与诗题的关系来看,“鸟”对应“妄想”,“人”对应“真实”,诗人就是通过以妄想的物形去对抗真实的人形,来传达出某一特殊时代生命的虚幻存在。“钥匙在耳朵里扭了一下/影子已经脱离我们”,“钥匙”和“耳朵”,冰冷的坚硬的金属器械与温暖的柔软的肉体部分之间形成对抗,“扭”是打开也是破坏,是“扭曲”,这种妄诞的想象在让读者感觉不近情理之外,却也在否定当中感受到了虚妄的真实,“影子”本来就是虚的,而“脱离”更让读者体会到分离,是虚的“影子”与妄想中的“鸟儿”(即“我们”)的分离,这样,“脱离”就变得神秘莫测起来了:那么,是什么脱离什么?是灵魂、精神脱离肉体?是理想脱离现实?是虚无脱离意义?诗人采用荒诞艺术扩开了诗意空间,在物形和人形的异化之中叙说出生命的虚幻,而“鸟儿已经降低为人”中,“降低”一词则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自卑,这样,从“人”到“鸟儿”再到“人”,表面看好似绕了一个圈子,实则已是物是人非,后一个人是“鸟儿一无相识的人”。那么,人到哪里去了?我想这正是多多想要引起我们深思的。
再如《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一诗,在诗人多多的眼里,苦难的中国妇女“没有脸孔却挥着手”“一个生锈的母亲没有记忆”,这近似于西方印象派的抽象变形手法,人形扭曲变成虚幻可怖的异形,从而再现了原先的恐惧感和无意义感,使“疼痛”感痛彻每一个读者的心扉;而在《噢怕,我怕》里,“……从打碎的窗子里拔出/我只有/一颗插满玻璃碴的头/还有两只可憎的手/会卡在棺盖外/而那是你的。我/不愿去想”,变形到如此怪异和恐怖,种种不和谐的异象幻化成一个足以惊醒人生的噩梦,真如同诗歌里说的“想想都怕”;此外,在诗人的眼里话语能变成苹果,“……话语在窗外散开/看它们它们就变成苹果/声音浸透了果肉”(《病人》),夕阳成了背运工——“夕阳,背着母亲走下黄铜屋顶”,马匹能像脱衣一样脱下马皮——“失去动力的马匹脱下马皮”,而“有着蜂形面孔的女人/把害怕死亡的裙子拧成了绳”(《当我爱人走进一片红雾避雨》)。多多还把感觉外化出来,改变对事物原有状态的摹写,比如“啊我记得黑夜里我记得/天是殷红殷红的/像死前炽热的吻”(《我记得》),“大地被毯子蒙住了头/世界鼓起了一个大包//斗争就是一个大墩布/看不见血/可是拼命擦”(《十五岁》),“噢,我的心情是那样好/就像顺着巨鲸光滑的脊背抚摸下去”(《冬夜的天空》)。诗歌意象的变形其实是诗人心态的体现和情绪的流露,还是诗人对世界万物的独特感受与精妙理解,多多像一个语言的巫师,拿着施过魔法的鞭子驱赶着词语不停变幻,使现实中的实际现象具有了离奇古怪、玄妙幻想的形式,以使其达到最大的表现力,对人产生最大可能的审美感染力:
十月的天空浮现在奶牛痴呆的脸上/新生的草坪俯向五月的大地哭诉/手抓泥土堵住马耳,听/黑暗的地层中有人用指甲走路!//同样地,我的五指是一株虚妄的李子树/我的腿是一只半跪在泥土中的犁/我随铁铲的声响一道/努力//把呜咽埋到很深很深的地下/把听觉埋到呜咽的近旁:/就在棺木底下/埋着我们早年见过的天空/稀薄的空气诱惑我:/一张张脸,渐渐下沉/一张张脸,从旧脸中上升/斗争,就是交换生命!//向日葵眉头皱起的天际灰云滚滚//多少被雷毁掉的手,多少割破过风的头/入睡吧,田野,听/荒草响起了镀金的铃声……
《十月的天空》①多多.多多诗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125.
整首诗歌抛开正常逻辑,打破合乎理法的寻常世界,从而模糊并消解掉色彩、音响、形象等界线,超越时间,突破空间,就像在洗过牌之后去重新建构世界的秩序,于是在诗人的主观意识支配下,重组的新世界产生变形——奶牛有痴呆的脸,草坪俯向大地哭诉,堵住马耳的是泥土,而黑暗地层中有人走路已经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更何况是用指甲走路!天空与大地都激烈变形,荒诞奇诡却又直观,穿透,让读者来不及思想便被抓入了诗歌世界当中,等待着进入诗歌那不可言说的部分,这用多多评价策兰的话来说叫做“空白”,它以异常和荒诞之下的隐喻效果展示出无尽的魅力。接着,诗人“我”如同被施了魔法,四分五裂奇形怪状变成物形,五指成了虚妄的李子树,腿成了半跪在泥土中的犁,呜咽与听觉被深埋于地下,而同时被深埋的还有“我们早年见过的天空”。之后,随着一张张脸的“下沉”和“上升”,斗争也被演绎为没有意义的事,显然,世事的迁移让诗人沉入了绝望之中,却在绝望之中苦苦挣扎,力图寻找到另一种天空和大地的秩序。因为,恰恰在荒诞变形的世界里,只有内心深处的生活才具有了意义。
三、机智的反讽
多多对诗歌技艺的有益尝试,还表现在成功地运用了“反讽”。
早在古希腊时代,“戏剧之王”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之中,就塑造了一个向自诩高明的对手说傻话的佯装无知的角色,最终他所说的那些愚蠢的话却被证明是真理,令对方猝不及防出尽洋相,这种表现手法即反讽。但最初人们对反讽的理解是狭隘的,只把它看做一种修辞。18 世纪以后,反讽内涵逐渐复杂,外延不断发生迁延,其文本形态种类种类渐渐繁多,涉及人的语言、行为,还上升为一种艺术观甚至人生观,难以被明确定义。现在所说的反讽一般指写作时用戏谑嘲讽的口吻来表达言外之意从而达到强烈的反差效果的写作技巧。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反讽通常传达出和字面意思截然不同的内涵,以达到背离内在逻辑意义的目的,从而表现出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和反叛。反讽所产生的荒谬怪诞的喜剧效果往往暗示着悲剧的内蕴。
多多机智的反讽艺术早在他写于七十年代早期的诗歌中就体现出来:
……而,我们应当有过的品格/早被剥制成干果/就和干辣椒、葱头一块儿/挂到门前的小钉上/一些把尾巴也一块儿/穿到裤子里的男人/在时时向它张望……
《鳄鱼市场》②多多.多多诗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46.
《鳄鱼市场》的残忍与丑恶都是无形的,就像我们只能在这一节诗歌里看到被挂到门前小钉上的“干辣椒”和“葱头”一样,《鳄鱼市场》的残忍与丑恶隐藏在那我们应当有过的早被剥制成干果的“品格”上面,这变成了干果的品格从视觉里的墙面上的钉子移到了知觉里,像一枚钢针那般给了心灵尖锐的一刺。能愿动词“应当”和表示曾经的“有过”联在一起,一方面传达出心之向往,另一方面表明了“品格”的“有”已成为过去,一切烟消云散遁匿无踪,空留下因记忆而起的伤痛。“应当有过的品格”成了标本,它甚至还不如标本,被剥制成干果的品格是和作为佐料的辛辣的干辣椒、葱头一起被挂在钉子上的,“挂”即是展览,当那在“童年的那架大管风琴”音响里培养起来的优良品格像备用的佐料一样被展览在众目睽睽之下,即将成为满足“一些受到惊吓的懦夫”的口腹之欲的佐料的时候,诗人几乎因激愤和悲痛而嗤嗤冷笑起来,连这些本来已经很可怜的“懦夫”也不放过,继续给予辛辣的嘲讽,把先前看起来是懦夫的“我们”歹毒地唤作“把尾巴也一块儿穿到裤子里的男人”,这是对人的异化,对丧失了早年应当有过的品格而“夹着尾巴做人”的一群不幸者的同情与愠怒,而最悲哀的是这些人在时时向它“张望”,向着“我们应当有过的品格”张望!最残忍最痛苦的莫过于这种“张望”了,这比“大树,吃母亲的树/已被做成了斧柄”(《大树》)还要残忍些,从“应当有过的品格”到“时时向它张望”的人,都同是“我们”! 诗人通过对现在的“我们”的夸张变形和丑化,依稀和童年的“我们”构成对比,由强烈反差形成反讽,从而让诗歌语言具有了更多的秘而不宣的含义,这恰恰是诗歌最有价值的所在。
多多总是敏锐地抓住诗歌中的对比因素以形成反讽,无论是显而易见的矛盾悖逆,还是最细微的差异,他都能通过反讽赋予诗歌语言更丰富的启发性和深层意蕴,额外地满足那些充满探求心的读者,引导着他们在一遍遍的文本细读中发掘出表面意义之下的幽微曲折,从而去探索诗歌间接表达的潜在思想。例如在《灌木》中,诗人通过根的纠缠和人的性爱交欢的类比,传达出爱的缺席与人性的难堪;或以滑稽模仿给予击刺,例如《吃肉》,诗人戏谑模仿被吃的肉的口吻,以绝少有的锋利和怪异去逼审吃肉之人,如同暴力之下的受害者以无形之矛刺向施暴者的软肋;或不时来一点小幽默,例如在《那是我们不能攀登的大石》中,西西弗斯的神话摇身一变,就成了中国式寓言,“我们造出它又向上攀登”,最讽刺的在于这块大石出自我们的手,我们就像西西弗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那样,永远做着徒劳无功和毫无希望的事,诗人又适时地在徒劳无功和毫无希望的人生当中幽默了一下,“还来得及得一次阑尾炎”,这句诗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却又簇眉沉思,而有“阑尾炎”就有“手术”,“十年”无疑影射“文革”,漫长的十年不过是“刀光一闪”,犹如被割掉的无用的阑尾,淡出历史记忆。尤其是那首写于1973 年并被万人称道的《手艺》更能显示出多多运用反讽技艺所能达到的高度:
我写青春沦落的诗/(写不贞的诗)/写在窄长的房间中/被诗人奸污/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我那冷漠的/再无怨恨的诗/(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我那没有人读的诗/正如一个故事的历史/我那失去骄傲/失去爱情的/(我那贵族的诗)/她,终会被农民娶走/她,就是我荒废的时日……
《手艺——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①多多.多多诗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25.
这是多多题献给俄罗斯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和诗,茨维塔耶娃所出版的诗集里就有一本名为《手艺集》,她在组诗《尘世的特征》里更是把自己定位为“我,一个匠人,懂得手艺。”②[俄]爱伦堡.人,岁月,生活[M].冯南江,秦顺新,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11.多多以茨维塔耶娃为师,他们同样高贵、敏感和敬重诗歌艺术,而从内在质地来说,多多早期的诗作的确与茨维塔耶娃那具有惊世骇俗独特品质的诗有着诸多契合之处,但也存在差异,茨维塔耶娃的诗偏于“清”气,而多多的诗歌则多了些“硬”气,这“硬”气主要得自反讽的功效。诗人通篇把自己的诗置于最低的位置,“青春沦落的”“不贞的”诗,写于“窄长的房间中”的、被“辞退”的诗,“冷漠的”“再无怨恨的”诗,“没有人读的”“失去骄傲的”“失去爱情的”诗,诗歌中仅有一个“贵族”,孤零零地置于全诗灰暗的底色中,随着贬义词汇一路沉下去,这一“贵族”也就近墨者黑般地隐含了“低下”的意味,并见证着“我荒废的时日”,于是诗歌低到极点,低到尘埃里去。此外,表面上多多把诗歌放得很低很低,甚至把它置于被动之境,比如“沦落”“没有人读”等等,这些词语隐含了公众对“我”的诗歌的批判与侮辱,显出“我”的诗歌的不合时宜,然而诗人始终把“我”放置在主动位置,整首诗以“我写……”“我那……”的句式贯穿,“我”推动全篇得以延展,并标举出自己富含主动性的诗歌态度,这样,那些处于被动地位的语词就以退为进,滋生出一种互相对峙、互相冲击的趋向,在反讽中流露出一种挑衅和叛逆:我写“青春沦落”的诗怎么啦,我写“不贞”的诗又怎么啦、我就是要写,我偏要写……总之,我的“诗”就是要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于是,尽管诗人从内心透出对现实的绝望,然而绝望之中守住了对诗歌高贵精神的追求,原先自己那低到尘埃里去的诗歌便在尘埃里开出花来,具有了诗歌本身独一无二的高度。
四、结 语
诗人多多以明晰的洞察力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性,纯熟地运用象征、暗示、变形、荒诞、反讽等现代诗歌技法,从驳杂的日常语言中萃取出诗歌语言的精华,以富于深层意味的语言去审视个体生命,直面人性的幽微与晦暗,剖析复杂社会,展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多多尤其擅长通过反讽抽丝剥茧般层层剥开人的心灵,引领读者直面真诚的人性,并思考个体生命历程中无法绕行的种种困厄,包括出生,死亡,疼痛,别离,暴力,恐惧,猜忌,冷漠,焦虑,孤独,绝望。在诗人多多眼里,诗歌被看得很高级,它代表一个民族和一种语言最能体现出尊严的那部分。在诗艺的追求上,多多宛如一个殚精竭虑炼制金丹的巫师,日日潜心锤炼与打磨,最终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诗歌,每一个字句都是在语言的炼金炉里至少炼过七十遍的。多多努力把公共词语资料锤炼成珍奇的诗句,在其中凝结出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诗意,以独一的姿态和高超的技艺努力抵达诗歌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