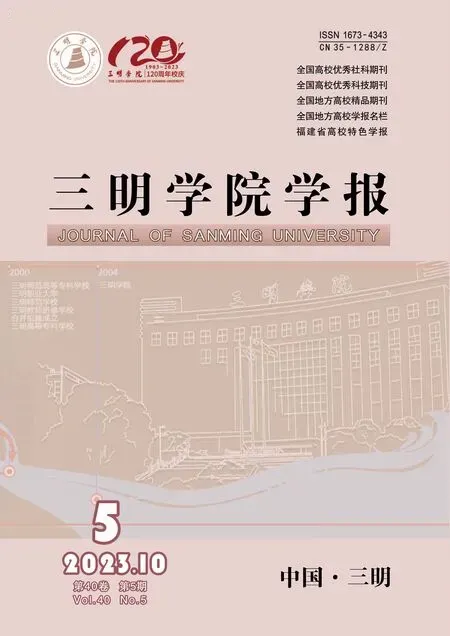“生产”与“接受”的博弈:对AI文学文本的审美解读
付青蔓,孔令辉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在如今的算法时代,人工智能正以不同的形态渗入人类生活,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并乐享其中。然而,当大量AI文学文本、AI写作软件出现后,人类之于文学的独创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这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重新审视。就其写作状态而言,人工智能写作是对现有审美经验的复制拼接和机械模仿,于是有学者认为AI文学不能称之为文学,并将AI写作视为对本雅明“灵氛”的蔑视,否认其审美解读之可能性。但不论认同与否,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开发,AI写作所生成的文本的确语言通畅、措辞优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传统美学标准,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审美解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合理看待AI文学对美学传统及审美观念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从“生产”与“接受”的裂缝中找寻作者存在之必要性,才能重新焕发“人类智能”的光芒。
一、文本生产的变迁:从“人的诗性”到“机器模识”
在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学领域内,创造主体“人”一直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探讨的重点。中国古代文论中强调“文如其人”,认为文学作品是人之感情流露:荀子在《乐论》中将音乐的产生归结为“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陆机《文赋》中认为创作是 “诗缘情而绮靡”,诗歌创作的意义是让诗人能够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作品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心即神”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的融合统一; 钟嵘在《诗品》中写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1]308,认为气决定了物的变迁进而惹起了人的感慨,由此引发文学创作。上述这些艺术构思活动的美学原则无不显示出,诗歌的本质乃是表现“人”的情感,文本生产的主体是有感而发、即事而作,具有能动性和创作性的“人”。
而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已渐渐融入了文学领域并生产出了大量的“类文本”,文本生产的主体开始出现“人机之争”。人工智能文学写作发端于1962年美国的诗歌写作软件“Auto-beatnik”,21世纪以来该项技术日趋完善,中国在此方面更是实现了新的突破。2016年,清华大学研发出了“九歌”系统,该系统可自动生成绝句、宋词、藏头诗、近体诗、现代诗等不同体裁的诗歌,并已累计为用户创作超过700万首诗词;2017年由微软小冰出版的《阳光失了玻璃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造的诗集,诗作中情感符号和诗性语言的使用极度契合人类的审美意趣。可见,现代人工智能生产的文学文本已超越字符缝合的初期阶段,发展成为集语言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数字技术、媒介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多技术的强大文本生成机器。因此,文学生产者便出现了分化,即作为人类文学生产者的作家和作为AI文学生产者的人工智能。
从本质意义上说,AI写作模式遵循着恒定的编码程序,按照“人建立文学数据库——机器进行数据分析——机器自动生成文本”[2]41-42的流程,程序制造者首先将搜集、整合来的海量数据输入程序之中,机器根据先前设定的符码转换规则,再将数据分析结果转换生成符合要求的文本。机器所使用的符码转换规则由程序制造者提前预设,通过分析大量的作家作品,总结出某作家或多个作家的表述习惯及高频词汇,进而以杂糅的形式提炼出“全新”的风格。从发生学意义上说,AI文学生成的文字组合以符号形式而存在。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强大的习得功能,从而具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和提取审美规律的归纳能力,再通过固定数据的演绎实现对语汇的整合排列。由此观之,AI所“生产”的诗歌,无论是否符合人类审美,依旧不过是机器在诗歌语料库支配下所生成的类文本,它既不是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情感冲动,也不是出自主体经验的心灵映射。
毋庸置疑,AI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学界对文学创作主体身份的重新考量。传统文学是由“人”利用想象力和主动性来书写自己的诗性意识,而AI文学则是通过“机器”来模拟、识别人类创作进而生成文学文本。虽然写作并不完全等同于生产,但仅从狭义的生产角度来说,文本生产的发展确实经历着从“人的诗性”到“机器模识”的变迁,甚至在未来会出现“人机交互”的生产模式。
二、文本接受的多重身份:读者、阐释者和拟设作者
站在文本接受的角度来看,人类之所以能够对AI文学文本产生审美共鸣,甚至出现将其误认为某知名作家作品的审美错觉,归根到底是因为接受主体将自身情感移入其中。换言之,AI文学只有在人的情感参与下才可能被审美诠释。那么,作为文学接受主体的“人”,在文本阐释活动中充当着“读者”“阐释者”“拟设作者”的三重身份。
“作者”是构成阐释活动乃至文本生发意义的关键要素,也是判断文本接受主体身份的重要标准,因此对“作者”身份的辨析成为阐释活动的重要内容。表面上看,人工智能虽是此类文本的直接作者,但实则是多位作者共融的结果,真实作者仍是“人”。以小冰的诗作《阳光失了玻璃窗》为例,其诗歌学习了胡适、北岛、顾城、汪国真等519位现代诗人,甚至在许多作品中直接挪用了著名诗人的典型意象,如这首《我寻梦失眠》明显可以看出诗人徐志摩作品的身影。
康桥
新鲜的
未经三月之蕙风已不追踪
在梦里我寻梦失眠
我是一座长桥
你可以找到我新鲜的爱情
将希望之光投射到你
也不知道是风
首先,“康桥”是徐志摩笔下的典型意象,提起康桥,人们就能自动联想起诗人徐志摩;其次,“在梦里我寻梦失眠”中的“寻梦”一词,是沿用了《再别康桥》中“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最后,“我是一座长桥……将希望之光投射到你”是对徐志摩《偶然》中“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的效仿。除此之外,小冰中的部分诗歌还对一些诗人的篇目命名进行了直接移用,如其中的《乡愁》移用了余光中的《乡愁》,《彷徨》取自鲁迅创作的近现代诗歌《彷徨》,《可爱的人啊》借鉴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由此看来,AI文学创作的本质是对于大量“真实作者”的模仿融合,它并不具备诗人在创作时所怀有的对生命的感知和对人生的思考,“审美活动中的愉快感是一种‘生命的情感’”[3],没有“生命”的人工智能文学正与康德所构建的美学体系完全相悖。作为直接作者的“AI”与隐藏在背后的真实作者“人”,二者之间依旧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但当读者未被告知AI写作身份而去阅读其生产的文学文本时,却又真实地感受到了它的“美”。这是因为AI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接受主体——“人”的审美趣味,它的算法将人类的审美习惯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故而可以呈现出符合人类审美意趣的作品。具而言之,由于人们对于现代诗人“浪漫主义”写作风格的崇拜,这些AI写作机器为迎合人类审美,逐渐完成了对抒情风格的学习,借用较多、较为典型的意象主要有眼睛、黑夜、梦、宇宙、寂寞、天空等入诗。除此之外,克洛夫斯基接受美学中的“陌生化”理论也很好地证明了AI文学的美感来源。人工智能只是类人的存在,其创作也只是类人化的创作,它自身并不具备一种清晰明了的旨意和判断,所以其诗歌大多是一些朦胧意象的重组搭配。如《乡愁》中“晚霞水在蕴藻浜的战场上/我的生命像是圣洁的/那水里一阵阵的旋风卷入暮霭/是在流水里钻出来”,通过“晚霞”“蕴藻”“生命”“暮霭”“流水”等朦胧意象的“陌生化组装”,给读者带来了既新奇又熟悉的审美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他们的共鸣甚至崇拜心理。
当隐瞒作者身份时,读者会充分发挥个体的审美经验,将主观意志置于文本之上。因此,文本意义的生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解读,此时的“读者”完成了向“阐释者”身份的转换。经过精心伪装过的AI诗歌,很容易造成阐释者“主体的幻想”,阐释者会根据自己的阐释需要、审美经验,联想起某诗人的文风、偏好等,在头脑中拟设此文本的相应“作者”,此“作者”又可称为“拟设作者”[4]。对于阐释者而言,“拟设作者”是他们进行有效阐释的论断和证明。由于每位阐释者拥有独一无二的经验阅历和思维判断,阐释者对于同一文本的“拟设作者”会有所殊异,但无论如何,“拟设作者”在他们的阐释活动中始终在场。
“人”是人工智能分析的主要对象,人工智能为迎合“读者”而向大量的“真实作者”学习,而读者又在品读其文本时成为“阐释者”,并根据主观审美经验为其文本冠以“拟设作者”。综上所述,AI文学文本的美感主要源于人工智能对文学中朦胧风格的把握和对意象的陌生化处理,归根到底是人工智能文学针对文本接受主体所做出的理解和奉迎。
三、“生产”与“接受”的角逐:作者存在之必要性
以上对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及接受主体的阐释活动进行了大致概括,从中可以发现,无论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变迁还是阐释活动的意义指向,其都是围绕“作者”展开,作者存在之必要性成为值得关注的话题。
自“文学接受”成为一种理论以来,文本接受与文本生产之间的裂隙逐渐拉大,这意味着作者不再是文学话语权的掌握者,其对作品的阐释也不再具有唯一的权威性,其在文学中的地位受到空前挑战。对作者地位的消解从柏拉图就可见发端,艾略特的“诗人的思想是个储存器”、荣格的“艺术家是艺术的工具”等对作者进一步祛魅,再到福柯的“何为作者”、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作者存在之必要性遭到了强烈质疑。发展到如今,当西方解构主义竭尽全力地解构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决定性地位时,AI文学生产及其受众的出现似乎是加速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表面上看,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以及接受主体构建的拟设作者都印证了解构主义的主张,即文学活动中不存在所谓的作者。解构主义代表罗兰·巴特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写作,是因为“一种纯粹的誊写动作所引导”[5]298,更将人之作品视为符号系统,这与AI写作的生产原理和生产成果不谋而合。但“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后起飞”[6]16,“从后思索”发现,恰恰是对作者的彻底消解才更能凸显其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如上文所述,阐释者在面对众多文学文本时,如若未被告知此文本的作者为人工智能,其针对文本进行的多种阐释都将以自身所推演、拟设、考证的相应“作者”为依据。由于不同诗人都有独特的背景经历和写作风格,因此就算是相同的“太阳”意象,海子和艾青的理解和表达就有所不同,可见作者身份之于文本解读非常重要。阐释者只有对作者有一定的知晓,才能有解读文本的抓手,所以对作者的猜想与推断成为阐释活动的重要内容。概言之,即使在缺乏作者的文本阐释活动中,接受主体所构建的“拟设作者”也始终在场,这更加印证了作者存在之必要性。
况且,以上述前人的观念来贬斥作者、追捧AI,就会发现其对作者的颠覆缺乏坚实的学理支撑。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只是现实的模仿者,他得到的不过是影像,从未抓住真理,然而AI是对诗人的又一层摹仿,是与现实的隔了再隔。“人”尚且能够把握并贮存无数种感情、意向,即使是欣赏同样的风花雪月也会引发不同的诗情,面临相似的时代境遇而各有别致的方式来表达愤慨感伤。相较而言,AI根据输入的图文写出的诗总是趋同,文本整体呈现出“虚无化的伤感”“风格化的品味”“符号化的生产”等美学特征,其创新性仅停留于意象的任意拼接。如若将其写作视为某种先锋性的美学追求,这将是人类文学和人类审美的一种悲哀。
这样一个文本阐释活动从表面看来是“生产”投合了“接受”,实则却是“生产”与“接受”之间的博弈。首先,AI文本生产之初就是围绕接受主体的审美趣味而设计,然而片面的趋承会麻痹大众的审美机能,是“生产主体”对“接受主体”的一种捧杀。其次,AI作为机器既无情感参与又缺乏创新性,故而人工智能文学“生产者”根本无法承担引领“接受者”审美向上发展的责任,作者存在之必要性再次显现出来。
四、“生产”与“接受”的正和博弈:未来文学之反思
毫无疑问,发达的人工智能正影响并形塑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向人类引以为豪的文学领域发出挑战。但在这场难舍难分的博弈中,人类与人工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只需要“生产者”和“接受者”双方共同发力,就可以实现生产与接受的共赢,推动未来文学蓬勃发展。
从“生产者”角度来看,作为人类文学生产者的作家和作为AI文学生产者的人工智能都需要正视“接受者”的审美需求。一方面,作家要摆脱对人工智能文学的偏见,积极寻求与机器协作共生的创作模式。人工智能作为社会进步的产物,其走入文学领域已成为大势所趋,作为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应该具备与时俱进的包容能力,主动接受科技提供给人类的便捷。而且,AI文学文本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读者的审美喜好,作家可以据此了解读者的阅读反馈,从而更好地实现文学的艺术表现和创作效果。另一方面,机器写作的研发者不能一味取悦大众喜好,如果任由其迎合而不能向大众供给新的养分,人类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也会在机器所打造的“舒适圈”中不断闭塞衰退。研发者除了让机器学习大量的作家作品,更应该让其能够理解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情感原理,以期为受众提供更高的审美价值。因此,无论是作家还是程序研发者都应明确的是,文学作为人类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的独特表达,人在文学活动中具有不可抹杀的主导作用。“个性化”永远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如何在人工智能挤占文学领地的现状下建构起我们的特殊属域,是生产者们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接受者”角度来看,读者要坚守住审美红线。正如布莱兹·帕斯卡尔所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苇草”[7]21-22,读者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能沉浸于短暂的审美愉悦和即时满足,时刻将审美价值放在阅读过程中的重要位置。面对机器的取悦,公众的正确做法是改变“意图相关”的评判标准[8]2,摆脱固化的审美准则,寻求随机、不确定的审美体验以打破人工智能所使用的常规鉴赏法则,促使人工智能的文艺写作和人类创作的不断调整更新。马尔库塞曾言,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强大渗透和包围作用下,文化消费者会失去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也会随之变为“单向度的社会”[9]66。这个预言并不是危言耸听,它反映了AI时代对人类审美提出的更高要求,人类必须对周围世界保持更加清晰的感知,不断发掘人类自身的独特属性,否则就会被机器的取悦束缚住思想,最终异化为机器的附庸。
但面对人工智能的文学文本,人们也不必过于忧虑和恐慌,因为单凭人工智能进行文学生产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创作”是基于人们无法复刻的个体生命体验而产生的,是人类独特精神世界的外显形式,人工智能以程序模拟代替了生命体验,以理性逻辑的运行代替了情感的酝酿与抒发,这样的思维理路从本质上只能称之为“写作”而不能称之为“创作”,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只有将正确的价值理念嵌入到人工智能的文学生产之中,以人为本,将人文与技术相结合,才能使人工智能视野下的文学发挥最大的魅力。
总而言之,“生产者”与“接受者”可以在互相弥合的过程中实现“正和博弈”。“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可以倒逼“生产者”主动调整,从而衍生出新的审美观念;“生产者”之间相互学习可以使创作更加便捷科学,从源头上提升“接受者”的审美能力。唯有选择正视技术与文学交叉引发的新现象,才能达到“读者”“作者”“AI写作”的多方共赢,促进人类未来文学的蓬勃发展。
五、结语
人工智能文学以现象级速度席卷了文学领域,人类将如何在这轮技术革命中解决身份认同危机,则不仅是文学问题,更是哲学问题。人对于AI文学的恐惧,一是来源于“弗兰肯斯坦式” 的造物惊惶,二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文学专属地位的攻占所带来的危机感。但从“生产”与“接受”的博弈中可以看出,人之为人的精神意识的独特性从未消弭。与此同时,我们理应看到AI文学在清理与革新当下的创作状态、反促和提升人类审美品味等方面的共生作用,应用一种审慎包容的姿态,合理看待AI文学等一系列新的人文现象,让它们成为重新焕发“人类智能”光芒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