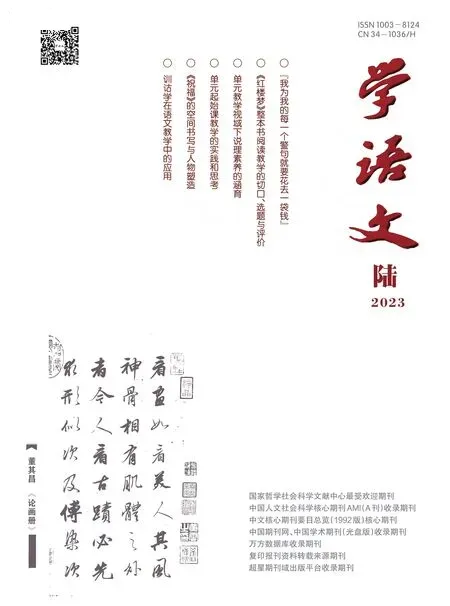打通文化视域,探求时代共性*
——《装在套子里的人》与《阿Q正传》跨单元联读
□ 刘 心 郑晓勤
在“大单元教学”“群文阅读教学”视野下,许多教师在执教统编版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的《阿Q 正传》时,往往会联读与之编排在同一课的《边城》。这种组元方式通过文本互涉,揭示两篇小说“国民性观察的不同视角和相同诉求”,有助于学生直观了解不同作品的诉说方式与表达风格。但《边城》与《阿Q正传》风格迥异,差异一望即知,二者的比较就好比一场不对变量进行控制的实验,缺乏对照的价值。
文本联读的取舍关键是:“最为可取的并非跨时代、跨文体形式、跨价值的异类组合,而是以同类文本的具体分析为基础。”[1]依循这一思路,教学的任务就应该在于找到与《阿Q正传》“无限接近却又不可取代”的同类文本,从而在文本的共通性、普遍性中观照特殊性,释放文本的特殊生命力,实现对“类性”的把握与对“篇性”的极致探求。
由此观之,《装在套子里的人》与《阿Q 正传》有着极强的可比性。两篇选文除国别、时代、单元归属、人文主题和所属学习任务群不同,就其文体、风格、主人公的典型性以及文章的思想性与时代性而言,皆有诸多重合,可谓跨越时空的交响曲。教师可打破传统的单元组元壁垒,对二者跨元整合,引导学生充分研读,在从“这一个”到“这一群”的观照中,深化对作品共通的思想性与时代性的认识,进而体察其“隐而难觉”的个性化表达与艺术魅力。
一、时代背景设置之“同”
《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898年,当时,面对汹涌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沙皇政府加强反动统治,反对任何自由的要求和革新的行为,使俄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小说中,契诃夫借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之口说:“是的,我们都是有头脑的正派人,我们读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以及巴克莱等人的著作,可是我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一再忍让……问题就在这儿。”可见当时即使是能接触到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被禁锢在压抑、隐忍的环境之中。
《阿Q 正传》创作于1921 年底,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当时,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未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广大农民仍然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如文中阿Q 的疑惑:“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可见当时封建帝制尚有残余,赵太爷等封建遗老尚存,百姓的封建思想仍旧根深蒂固。
就时代背景而言,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生活在统治者的压迫之下。如果说别里科夫是装在沙俄专制统治套子里的人,那么阿Q 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套子里的人。《装在套子里的人》选自必修下册第六单元,从属于“文学阅读与写作”学习任务群,人文主题为“观察与批判”。单元说明中提示:“要注意知人论世,在人物与社会共生、互动的关系中认识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关注作品的社会批判性。”《阿Q 正传(节选)》选自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从属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研习任务群,人文主题为“时代镜像”。单元说明中提示:“要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解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探索其中蕴含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百年来人们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变动的轨迹。”二者主题和任务群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在教法上都强调人物与时代的关联。
二、主人公形象之“同”
别里科夫与阿Q都是矛盾的结合体,是可笑、可恨又可怜、可悲的典型文学形象。
其一,他们在思想上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生活理论。比如别里科夫以“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为口头禅,体现的是他封闭守旧、胆小多疑的特质;阿Q总是在受了屈辱后,以忘却、自欺欺人等精神胜利法来缓解痛苦,体现的是他麻木健忘、自轻自贱的精神状态。
其二,他们在行动上都有背离常轨、滑稽怪诞的表现。例如,别里科夫身上有着生活和思想方面的形形色色的套子:穿着上,他“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出行时“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棚”,封闭自我,杜绝与外界的一切交往。阿Q亦有诸多荒唐行为,例如,通过挨赵太爷的打来获取人们对他的“仿佛格外尊敬”,受了“假洋鬼子”的气,就通过调戏小尼姑来发泄冲动,转移屈辱。
其三,他们都有“外强中干”的属性。别里科夫被科瓦连科推下楼,本是安然无恙,其后却因为华连卡清脆响亮的笑声而“结束了人间生活”,可见其心理防线一触即溃、不堪一击。阿Q 以“儿子打老子”赢得精神上的胜利,却在“精神胜利法”被周围人识破后,自称“虫豸”讨饶,在“假洋鬼子”拿着手杖向他走来时,“耸着肩膀等候着”,可见其逆来顺受的奴性。
其四,别里科夫与阿Q 虽然都是扁平化的典型人物,但他们身上充满矛盾。一方面,别里科夫“套己”也“套人”,“把整个中学辖制了整整十五年”“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阿Q不自觉维护着象征封建思想的辫子并对女人有着偏见和歧视。这就是鲁迅在《华盖集·杂感》中指出的:“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2],他们都是专制统治的卫道者,可笑又可憎。同时,他们也是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在社会上毫不起眼,缺乏基本的人权与尊严,甚至因之失去生命,可怜亦可悲。
三、人物社会关系之“同”
在小说中,别里科夫和阿Q都没有亲人,别里科夫性情孤僻,很少与人来往,阿Q则是无名无姓无家无业的“四无人士”,缺乏社会支持。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往往被当做取乐的对象。
别里科夫不受欢迎,被促狭鬼以漫画捉弄讽刺,被华连卡的弟弟讨厌。甚至,他决定结婚的原因,是“校长太太的尽力撮合”,是因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这时,别里科夫其实是活在他人的看法之中,对他来说,选择恋爱结婚是因为“别人认为应该”,而不是因为“想结婚”。
阿Q 周围的人也有故意拿他取笑的,小说第二章写道:“谁知道阿Q 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闲人喜欢在阿Q 的伤口上撒盐,就他的“癞疮疤”大做文章;小说第三章写阿Q 和王胡比赛捉虱子,之后阿Q“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从“照例”一词可知,阿Q 平时被打的频率很高,即使是像王胡这样的闲人,也习惯于欺负阿Q,并不将其放在眼里。
在婚恋方面,两人都对婚姻有过追求。契诃夫写别里科夫“差点结了婚”,鲁迅为《阿Q 正传》第四章起名“恋爱的悲剧”,写阿Q 向吴妈表白,吴妈发抖大哭,可见他们的婚恋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就其社会关系而言,周围的人对两位主人公死亡的反应,最能影射出当时的社会人心。别里科夫生病在家时,无人探问,对于他的死,大家只觉得“大快人心”,可见当时的人们不仅是与他关系疏离,还对他厌恶和憎恨。阿Q的死则充分揭示了周围人们的冷漠无情,小说的结局是“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阿Q的死没有唤起大家任何的同情和悲哀,只让周围人慨叹死得不够“精彩”,看客的无情显露无疑。
四、艺术特色之“同”
其一,鲁迅和契诃夫的作品都带有讽刺、幽默和夸张的意味,运用夸张的手法、漫画式的笔调勾勒人物形象。
以夸张手法的使用为例,《装在套子里的人》对人物本身的性格和人物的影响力都有所夸大,像别里科夫这样整天躲在“套子”里的人,竟然“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连“全城都受着他辖制”,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阿Q正传》中,阿Q自欺欺人、妄自尊大、欺弱怕强等性格特点,其实是周围人性格的集中体现。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如揪辫子、“照例”被碰头、咬虱子、“耸了肩膀等候着”挨打等,都经过夸张、滑稽的艺术处理,是作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夸张的典型。
然而,不同于李白“白发三千丈”“危楼高百尺”的虚构式夸张,契诃夫和鲁迅的夸张是一种“艺术性的真实”。尽管人物经过夸张处理,但读者总是能从人物身上发现现实的影子。就人物本身的形象特质而言,即使别里科夫极度孤僻,也对婚恋有过追求,即使阿Q再自欺欺人,在面对王胡和假洋鬼子的欺辱时,他也有过短暂的错乱,“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写出他被打时真实的恍惚状态,这些描写都是对真实人性的深度还原。究其区别,李白的夸张让读者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冷静看待作者描摹的神奇瑰丽的世界,契诃夫和鲁迅的夸张则让人置身其中,更易共情,更易从主人公身上观照到自己的影子。
其二,契诃夫和鲁迅的语言都简练传神。
契诃夫认为“简洁是天才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他的文学创作就是自己文学理论的实践。例如,在塑造别里科夫形象时,他对人物的长相着墨极少,只是对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加以巧妙概括,通过对他随时带着雨伞、穿着套鞋、用棉花堵住耳朵的生活习惯的描写,生动刻画了一个逃避现实生活、惧怕新生事物的保守形象。只用寥寥几笔,就把人物的神态、性格乃至社会地位都鲜明地勾勒出来。
鲁迅也擅长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提到:“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3]这一艺术追求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就是抓住人物最关键的特征,用简练省净的笔墨将其展现。比如描写阿Q被闲人们欺负时,自称“虫豸”讨饶,又写阿Q被假洋鬼子打时,不敢还手,只是“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耸肩膀等候着”,这些描写简洁传神地刻画出阿Q懦弱畏强的形象。
五、创作动机之“同”
两文作者虽国籍不同,但创作动机却非常相似。别里科夫和阿Q都是可恶、可恨之人,却又是作家抱以同情的对象。
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即使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依然无法改变民众精神的愚昧麻木,《阿Q 正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4]由此观之,鲁迅除了在作品中探索国民的劣根性外,还意图反映底层的不幸。他想批判的并非阿Q 一人,而是控诉当时封建思想对百姓精神的压制。因此,在阿Q的“怒目主义”之后,鲁迅特意描写了未庄的闲人们,承接上文对阿Q 欺弱怕强的描写,写未庄的闲人故意调侃欺凌阿Q,这就表明阿Q 并非个例,而是当时民众的典型,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创作动机是“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别里科夫扮演的是旧秩序、旧思想的卫道者,他之所以能够“辖制全城”,原因就是背后有沙皇专制政府作为后盾。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别里科夫何尝不是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牺牲者?他不敢大胆追求婚恋,是因为怕结婚会带来什么乱子,当他被科瓦连科推下楼时,他最害怕的不是身体的受损,而是担心“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的耳朵里去……”,可恶的他也和阿Q一样,可怜又可悲。契诃夫的创作动机,当然不只是批判因循守旧的别里科夫,而是以小见大,以别里科夫的悲剧揭示沙皇专制必然灭亡的结局。科瓦连科和华连卡所代表的新生力量的出现,则是作者在黑暗中洞见的光明的力量,表达了契诃夫对旧制度的鞭挞和对新生的积极力量的支持。
阿Q 和别里科夫最后都死了,但是这个群体并未消亡,在作者眼中,“精神胜利法”和“套中人”的属性都并非小说的主人公所独有。两篇作品共同的旨归都是画出一定时期的人物群像,再现时代特征,呼唤新生力量,这是中外两位作家的深刻之处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正是因为两位主人公都是可恨、可怜又可悲的矛盾结合体,他们身上都隐藏着作家对人性的探视,而成为具有超时空意义的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