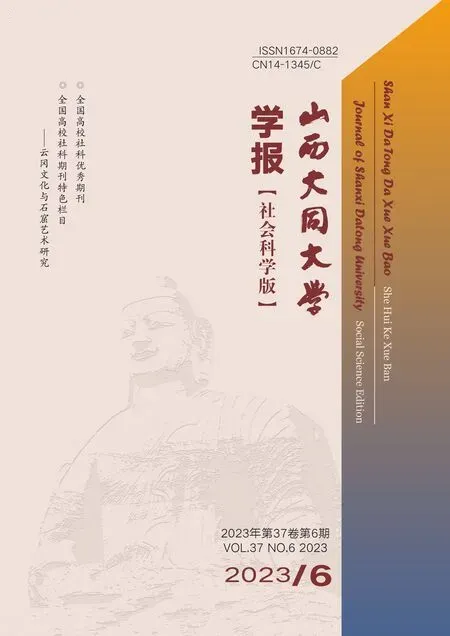对深藏于文化底层的神话的触摸
——《额尔古纳河右岸》隐秘意蕴探析
王金茹;杨 旸
(1.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吉林 四平 136000;2.航天工程大学基础部,北京 100081)
迟子建在CCTV《文化访谈录》节目中曾讲道:“人在宇宙长寿不过一百岁,是一个瞬间,可是宇宙是永恒的,青山绿水是永恒的,在一个瞬间的生命当中,我们渴望着一些温暖,这是人世间最动人的一种情感。……我写了这么多的苍凉,这么多的人生的不平等等以后,我要看到这一团火光,我要体会到这种温暖。”正是循着这种对“温暖”的珍视,她创作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下称《右岸》)。这部小说发表于2005年,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最近几年,《右岸》的读者与日俱增,《右岸》一再重印,销售量达到十分可观的程度。《右岸》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是它所表现的大大不同于我们汉民族的鄂温克族的狩猎生活,还是它浓郁的大大迥异于今天现代性的原始文明?是它呈现的“野人”神乎其神的萨满仪式,还是它与大森林、日月星辰和动物为伴的恬淡生活?是它浓郁的忧伤、苍凉和凄美的叙述风格,还是它美不胜收的“金句”?是对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遥远家园的殷切回望,还是族群式微引起人们对现代生活的深深反思?是对一个少数民族族群历史的文化人类学解读,还是对一种逝去文明的拳拳眷恋?这些都可能是构成《右岸》与日俱增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但是,它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它的决定性因素是隐藏在这部小说中的神话意蕴。这部小说蕴含着一个火神神话,由火神神话指引的鄂温克族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体现在萨满仪式中的火神原型象征,表现了鄂温克人思想性格中的火神精神,呈现在鄂温克族创造的文明中,这些深层意涵与读者心底的集体无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共振。
一、老祖母的岩画:鄂温克族神话原型的象征
《右岸》这部小说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为第一人称,讲述他们氏族的历史故事,在她的口中,鄂温克族的历史悠长而又丰富,动人心魄、荡气回肠而又令人落寞、忧伤和悲凉。仿佛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在激动人心,而那种东西的消失又使人落寞和悲伤。老祖母的故事中究竟隐藏着什么?
在老祖母的晚年,她曾深情地在河畔的岩石上画过几幅岩画,老祖母的外孙女伊莲娜也画了一幅油画。老祖母讲述了他们氏族的故事,也可以看作是讲述了他们氏族的历史,但是,老祖母为什么又讲述了她画的岩画和她外孙女画的油画呢?岩画、油画和讲述故事及历史的不同之处是,故事或历史故事是以具体事件(故事情节)来体现的,而绘画是以意象来表现的。前者的表现方式是叙事,后者的表现方式是意象;叙事是写实性表现,而意象则是象征性表现。这样看来,老祖母是以岩画和油画的意象作为她讲述故事的一种象征。准确地说,是作家迟子建在通过岩画和油画的意象对她讲述故事的一种象征。在故事之上有岩画和油画的意象象征,是迟子建《右岸》的一大特点。意象象征通常是对具体故事的一种整体性、核心性象征,因而可以看作是一种原型性象征。作家是在通过老祖母的岩画和老祖母外孙女的油画对她所叙述故事进行一种原型性象征。
在老祖母讲述的故事中所隐藏的重要内容就蕴含在她那几幅岩画和她外孙女的油画之中。那几幅岩画隐藏着鄂温克族故事的原型,也可以看作是隐藏着鄂温克族文明和文化的原型,包括鄂温克人的性格和精神,包括鄂温克族的心灵史和民族史,当然也包含着他们面对文化变迁和现代文明所产生的哀伤、愁怨和苍凉的心绪。可以说,老祖母的岩画和她外孙女的油画,就是破解《右岸》艺术魅力之谜的密钥。
在老祖母讲述的故事中,讲到了她画的将近10处岩画。老祖母始终居住在森林里,既没有学过绘画,也从来没有看过三百年前额尔古纳河的阿娘尼岩画,当然更没有看过他们祖先“雅库特”人几千年以前留在贝加尔湖畔的岩画。但是,她就是画出了与三百年前初来额尔古纳河鄂温克先人相似的岩画,更神奇的是,这些岩画与几千年前“雅库特”先祖留在贝加尔湖畔的岩画也十分相似。老祖母说:“我画岩画的时候,还没有被发现,虽然它早在我之前就存在了。”那么,老祖母是根据什么画她的岩画呢?老祖母曾说过:“它帮我说出了那么多心中的思念和梦想。”[1](P127)老祖母“心中的思念和梦想”,并不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整个鄂温克族的,这也体现在老祖母说的另一段话中:“你们现在都知道贝尔茨河支流的阿娘尼河畔的岩石画,在河畔已经风化了的岩石上,呈现的是一片血色的岩画。我们的祖先利用那里深红的泥土,在岩石上描画了驯鹿、堪达罕、狩猎的人、猎犬和神鼓的形象”。[1](P127)阿娘尼河畔岩画,也是鄂温克先民根据他们“心中的思念和梦想”画出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把故乡贝加尔湖畔的岩画形式带到了额尔古纳河畔。贝加尔湖畔的岩画也可以看作是那个民族最早的“心中的思念和梦想”。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中,“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原型是我们继承于自己祖先的心理遗产,因而具有遗传和普遍的性质。”[2](P13)由此可以推断,这最早的“心中的思念和梦想”就是鄂温克族的集体无意识原型。也就是说,老祖母是根据鄂温克族心理原型来创作她的岩画的,老祖母的岩画便是鄂温克族心理原型的象征。
老祖母前前后后画了近10 处岩画,最典型的是那幅由他们氏族失去的三个男人组合而成的岩画,它是鄂温克族“天神”原型变形的岩画。老祖母是这样描述那幅岩画的:“我画的第一个图形,就是一个男人的身姿。他的头像林克,胳膊和腿像泥都萨满,而他那宽厚的胸脯,无疑就是拉吉达的了。这三个离开我的亲人,在那个瞬间组合在一起,向我呈现了一个完美的男人的风貌。接着,我又在这个男人周围画了八只驯鹿,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各一只,其次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各一只,它们就像八颗星星一样,环绕着中间的那个男人。”[1](P128)
这幅岩画是鄂温克族天神神话的一个象征性变形。鄂温克族崇拜天神,其实也是创世神,“把客观存在的天空人格化为‘天父’,赋予它人性,从而在神话中把这种精神信仰表现出来”,如雅鲁河流域鄂温克族神话:“天是父亲,太阳月亮当做天父的眼睛,天上的人高大,善良,心眼好”。[3](P108)天神神话在阿娘尼岩画中有非常形象的表现。阿娘尼为鄂温克语,意为“岩石如画”,岩画就在贝尔茨河的支流阿娘尼小河岸的岩石上,那上面画着高大的男人和雄壮鹿类动物,是天神创造宇宙万物神话的岩画表达。这种岩画在鄂温克族的故乡贝加尔湖畔有着更为丰富的表达。这种岩画是作为祭祀天神的仪式而创作的。老祖母的岩画是这种“天父”岩画原型的变形,她以三个男人不同部位重新综合为一个男人象征着“天父”形象,而以周围四面八方的驯鹿形象象征着天父对世界万物的创造。那三个男人分别是由她父亲林克的头、尼都萨满的胳膊、腿和她第一任丈夫达吉拉宽厚的胸脯合成的。由三个男人合成的形象象征着天父伟大的形象和创造精神。父亲林克是氏族生活的创造者,他为寻找走失的驯鹿所做的努力,等于为他们氏族保留了“火种”,自己却被雷电击中身亡。尼都萨满是氏族光明的守护者,他能够给失去光明的人治好眼病,也能够为了抗击入侵者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老祖母的岩画使鄂温克远古神话、岩画和鄂温克人现实英雄故事连接在一起,使远古天神崇拜的神话原型成为现实具体故事,在现实故事中折射着远古天神神话原型。
老祖母另一幅典型岩画,是火神神话原型、萨满神话原型和北斗七星神话原型的综合变形。老祖母是这样讲述的:“在贝尔茨河极小的一条支流旁,找到一处白色的岩石,画了一面印有火样纹的神鼓和环绕着神鼓的七只驯鹿仔。我把神鼓当做了月亮,而那七只鹿仔就是环绕着它的北斗七星。那条河是没有名字的,自从我在那里留下画后,我就在心底叫它温都翁河。温都翁,就是神鼓的意思。……我一直画到太阳落山。当夕阳把白色的岩石和流水镀上一层金光的时候,我已经为即将来临的黑夜升起了一轮圆月和七颗星辰。”[1](P164)这里面的“火样纹”是象征火神的;月亮和七颗星辰发出光明,它们也成了火神(光明)的变形象征,因为神鼓是萨满仪式最重要的神器,因而是萨满神话的象征。在鄂温克族的神话里,火神和七颗北斗星都是创世神,萨满因能通神而进行死而复生的创造活动。表现火神、北斗七星和萨满的岩画,以及表现神鹿的岩画,在额尔古纳河的阿娘尼,特别是在贝加尔湖畔的岩画中都有丰富的表现。作家通过老祖母画岩画的方式,把鄂温克族当下的生活与古老文化传统相衔接,无形之中,也触摸到了隐藏在其中的神话原型。“实质上,《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关于神灵和‘最后的萨满’的史诗,神性已成为她乐于书写的对象。‘通神’在迟子建的小说文本里,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有意味的文化存在”。[4]
老祖母教外孙女伊莲娜画岩画,是《右岸》中颇有意味的一个情节:“我交给了她一枝画棒,她在岩石上先是画了一只驯鹿,接着就画了一颗太阳。我没有想到,伊莲娜画的岩画是那么生动。我画的驯鹿是安静的,而她画的则是调皮的……我说,你画的驯鹿我怎么没见过?伊莲娜说,这是神鹿,只有岩石才能长出这样的鹿来”。[1](P231)这个祖孙学画情节体现了鄂温克族文化的传承,同时在伊莲娜画的七杈角神鹿这个意象中,也折射出集体无意识的传承。老祖母没有在现实中看到过七杈角的鹿,但是,在远古岩画中,七杈角的神鹿屡见不鲜。伊莲娜在老祖母画的鹿、花朵和小鸟基础上,又画上了一颗太阳和七杈角神鹿,生动地印证了神话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被神秘地传承。
伊莲娜后来成了画家,她的皮毛镶嵌画比老祖母的岩画更具有原型意味。皮毛画“画的上部通常是天空和云朵,下部是起伏的山峦或者弯曲的河流,中间呢,永远是千姿百态的驯鹿”。[1](P238)这幅图像中虽然没有描绘天神和萨满,但是,通过那千姿百态的驯鹿和宁静和谐的生活样态,勾勒出神话光辉照耀下的和谐生活。另一幅油画“很有气魄,上部是翻卷着浓云的天空和被烟雾笼罩着的黛绿的青山,中部是跳神的泥浩和环绕着她的驯鹿群。泥浩的脸是模糊的,但她所穿的神衣和神裙却是那么逼真,好像风儿轻轻一吹,那些闪光的金属片就会发出响声。画的底部,是苍凉的额尔古纳河和垂立在岸边祈雨的人们”。[1](P241)这是对尼浩萨满跳神祈雨情景的描绘,翻卷着的浓云和被烟雾笼罩的黛绿青山,是山林遭遇大火的劫难;跳神的泥浩和环绕着她的驯鹿群,是泥浩萨满跳神获得的结果;泥浩萨满之所以是模糊的,那是对尼浩萨满进入通神情境的象征性描绘,苍凉的额尔古纳河和垂立在岸边祈雨的人们,是萨满祈雨仪式的一部分,那是人们对萨满通神的膜拜。如果说老祖母的岩画倾向于反映鄂温克族原始神话原型的话,那么她的外孙女伊莲娜的画则更倾向于展示鄂温克人当下现实生活的形态。无一例外的是,她们的画里都内蕴着鄂温克族的神话原型。
遗憾的是,伊莲娜跳河死了,她告别了她的油画,当然也告别了她外祖母的岩画。如果她的油画和外祖母的岩画我们可以看作是鄂温克族神话的原型象征,或者是鄂温克族文明的象征,那么她的离去似乎也暗示了鄂温克族神话和文明的式微。伊莲娜的死,是《右岸》中最发人深思的一个情节,它以伊莲娜的自尽,表现了一个族群的迷失,一种文明形态的远去,一种神话指引生命形式的消失。
老祖母最后一幅岩画,是在伊莲娜被捞上岸的地方,小说写道:“找到一块白色的岩石,为她画了一盏灯。我希望她在没有月亮的黑夜漂游的时候,它会为她照亮。我知道,那是我一生画的最后一幅岩画了。画完它,我把脸贴在岩石上,哭了,我的泪水沁在岩石的灯上,就好像为它注入了灯油。”[1](P242)这不仅是为伊莲娜而哭泣,也是为鄂温克人而哭泣。
二、萨满与酋长:神性的现世担当
《右岸》以老祖母讲述的方式,呈现了三百年前从贝加尔湖迁徙至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族由盛而衰的部族历史。他们以驯鹿为伴,以萨满为精神依托,他们虽然不断地搬迁,但大森林始终是他们栖居的家园,他们虽然居住在希楞柱里,但是他们能够看到天上的星辰,他们的生活虽然充满着艰苦和危险,但是这样的生活是和谐、安宁、喜悦甚至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精神信仰,有自己的神话,有自己的萨满仪式,有自己的舞蹈和歌唱,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性格,等等,这一切构成了鄂温克人的文明。然而,这样一个在大森林里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生活的“野人”或者说是“原住民”,在日本人的侵略和所谓现代文明(以现代性开发为名对森林的乱砍乱伐、“野人”移居“文明化”)多重冲击下,整个氏族逐渐走向式微。
与老祖母岩画相呼应的是,在鄂温克族生存与生活中,他们是以神话为指引的。在老祖母的讲述中,穿插着泥都萨满讲述的火神故事,其实就是对鄂温克族崇拜火神的交代。那是一个火女神的神话,讲的是一个猎人在森林里奔波了一整天,一个动物也没打到,晚上回到家后他升起火来,听着柴火燃烧噼噼啪啪的,感觉似在嘲笑他,于是他很生气,扬起手中的刀把燃烧的火刺灭了。第二天他再也点不着火了,出去打猎也空手而归。第三天,他还要出去打猎,正当他四处寻找猎物之时,忽然听到一阵哭声,走过去一看,是一个老女人,正掩面而泣。猎人便上前询问缘由,老女人说自己的脸前天被人刺伤了。猎人立刻明白是自己冒犯了天神,马上跪下来低头乞求老女人宽宥。当他抬起头看向老女人时,却发现人不见了,只见一只山鸡蹲在树杈上,于是成为他当天的收获。更让猎人惊奇的是,他回家后发现,灶里的火竟然自己燃起来了。这则神话是对鄂温克族神话的一种改造,在原来神话中,是那个猎人生不着火冻死了。作家迟子建是具有文化人类学和神话学知识背景的,她用这个火女神神话表现了鄂温克人对火神崇拜的历史。火对生活在大森林里的人极端重要,因为它带来了光明和温暖,也就带来了生命。鄂温克人营地的火从来不熄灭过,搬迁的时候,是用驯鹿驮着火种的。老祖母说:“我们把火种放到埋着厚灰的桦皮桶里,不管走在多么艰难的路上,光明和温暖都伴随着我们。”[1](P29)
崇拜火神就是崇拜光明,在鄂温克人看来,是火神、太阳神带给了他们光明。因而,鄂温克人的生活是笼罩在火神和太阳神的光辉之中的。老祖母有一段话,表达得很好,她说:“我始终不能相信从书本上能学来一个光明的世界、幸福的世界。”“我觉得光明就在河流旁的岩石画上,在那一棵连着一棵的树木上,在花朵的露珠上,在希楞柱尖顶的星光上,在驯鹿的犄角上。如果这样的光明世界不是光明,什么又会是光明呢?”[1](P184)
《右岸》虽以岩画的形式象征性地描写了鄂温克族的神话,在故事的叙述中也交代了鄂温克族的神话,但是,表现鄂温克族神话并非《右岸》的重点。相对神话表现而言,作家所描写的重点是体现神话是如何转化为鄂温克人自己的内在精神。这是《右岸》最突出的特点。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萨满角色的尼都和泥浩牺牲自己,而给鄂温克部族带来光明的思想行为,另一方面是作为鄂温克酋长的林克、达吉拉和瓦罗加等为部族利益牺牲自己的故事。作家通过这些人牺牲自己给部族带来光明的描写,将鄂温克神话与鄂温克人的文化性格连在一起。从而表现了鄂温克神话不只是一种讲述的神祇故事,不只是一种神圣崇拜,不只是萨满跳神仪式,也是在讲述神的神圣性如何转化到一个族群性格之中,使之成为神的神圣精神的体现者。
我们在老祖母叙述尼浩成为萨满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鄂温克人对神圣精神的自觉选择。当前一任萨满尼都为了使日本人战马死去而即将牺牲自己的时候,他离开人们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扔掉了鼓槌、神鼓、神衣、神裙,“而尼浩慢慢地跟在他身后捡拾着。尼都萨满扔一件,她就捡拾起一件”。[1](P102)终于在一个大雪天,尼浩光着脚跑了出去,她的丈夫鲁尼是氏族中跑得最快的人了,但是却怎么也撵不上尼浩,而光着脚的尼浩一点也没伤着,人们问尼浩,你刚才去哪里了,尼浩说我就在这里喂孩子呀。这种特异行为是一般人成为萨满的神奇表现。但是,在作家的描写中,妮浩是先有了为部族光明生活而选择做萨满的思想,然后才有成为萨满的转变仪式。尼浩捡拾尼都萨满扔掉的神鼓和神衣等,对她来说是一种先在的仪式,她通过捡拾尼都萨满神鼓神衣方式在接过萨满的神圣职责。因而,与其说是上天选择了妮浩为萨满,不如说是妮浩自选了萨满。是她自己选择了要用自己的生命去给整个部族带来光明和幸福的神圣职责。妮浩是先有了神话的神圣精神然后才获得了萨满的神秘力量。在成为萨满的正式仪式上,尼浩表示“她成为萨满后,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和神赋予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氏族,让我们的氏族人口兴旺、驯鹿成群,狩猎年年丰收”。[1](P119)
尼浩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她明明知道要救活别人的孩子,就要牺牲掉自己的一个孩子,但她还是要去,她为此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尼浩是为祈雨熄灭森林大火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一段叙述很生动,特别凸显了尼浩作为萨满用自己的生命为部族换取光明生活的神圣精神,整个森林得救了,整个驯鹿群得救了,整个氏族得救了,但妮浩却永远地告别了她的大森林,告别了她所爱的鲁尼,告别了她所拯救的氏族。
萨满研究专家伊利亚德曾指出,“雅库特”人有鹰化萨满神话,老鹰有一个至上神的名字,即“光明的创造者”。[5](P104)萨满是光明的使者,是萨满把太阳和火的光明带到寒冷的人间。作家描写妮浩萨满和尼都萨满,并非为了写萨满而写萨满,而是为了体现神话和萨满精神已内化为鄂温克人的思想性格。作家通过对萨满仪式的描写,使遥远的神话与当下鄂温克人的思想精神紧密相连,从而表现了独属于鄂温克族的文明。
三、土著没日:神话家园的遗失
鄂温克的文明瓦解了,它瓦解于现代社会对一个古老部族的搬迁:在持续的开发和某些不负责任的乱砍滥伐中,大森林树木稀少了,动物稀少了;他们和他们相依为命的驯鹿都被迁移到山外的定居点去居住,从此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古老家园。家园在这里有双重意旨,一是指人们日常生活起居所处的场所范围,二是指人们在情感思想方面的精神寄托之处。一个古老民族文明的衰落不仅给人带来震撼,更发人深思。在这个苍凉故事的背后,也蕴含着作者深邃的思考。
作家在小说行文中铺设了多处情节,来隐喻象征鄂温克族文明的衰落、瓦解及其带给人的忧戚与绝望。老祖母的外孙女——伊莲娜的死,便具有极强的符号性意义。伊莲娜怎么也不习惯定居点的生活方式,但是,她回不去她美丽的森林家园了。伊莲娜只能把那个古老家园连同古老的萨满神话留在她的油画中,而她自己却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她的死象征了鄂温克民族失去“家园”的绝望,他们心中的“家园”,不仅仅是大森林和希楞柱,还有“玛鲁王”和那安静恬淡乐天知命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有了新的居处,但那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走失”了,他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人。
老祖母说:“以往我们搬迁的时候,总要带着火种。达吉亚娜他们这次下山,却把火种丢在这里了。没有火的日子,是寒冷和黑暗的,我真为他们难过和担心。”[1](P5)在鄂温克民族那里,火种不仅仅是火种,而是神的象征、光明的象征、精神信仰的象征,因而它们才有了火神神话、天神神话、萨满神话等。鄂温克人被迁移到森林之外的定居点,他们不再需要原来的火,就是不再需要火神神话、天神神话、萨满神话。他们离开了大森林家园,离开了在大森林中产生的神话,离开了由神话产生的独特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鄂温克人从此也就与这些原始神话信仰越来越远,因为在现代性价值取向里,不需要也便不会再联系。小说中,被搬迁到森林之外定居点的人们没有带走火种,这也是他们失去神话精神家园的象征。
这部小说的结尾,写到老祖母的幻觉,意味深长,含义隽永。可以看作是一种美好的期待与憧憬,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绝望与告别。部族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了“我”和安草儿,“我”和安草儿一起看向那条通往山外的路:“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分不清天上人间了。”[1](P249)这段描写,有点魔幻现实主义,这分明是幻觉,或者也可称之为“白日梦”。幻觉和“白日梦”是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后想象性满足。达吉亚娜他们沿着那条道路走向了山外,却永远无法再沿着那条道路回到山里了。幻觉中驯鹿的归来正是“我”对鄂温克族重回森林家园的渴望。这一情节既揭示出“我”对鄂温克族被迫迁出森林家园的绝望,也暗含了作者内心之中那份怅然与忧伤。
迟子建不止一次表达过自己的心声。她在她的短文《土著的落日》中写道:“当我在达尔文的街头俯下身来观看土著人在画布上描画他们崇拜的鱼、蛇、蜥蜴和大河的时候,看着那已失去灵动感的画笔蘸着油彩熟练却是空洞地游走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了一团猩红滴血的落日,正沉沦在苍茫而繁华的海面上!”[6](P255)在一次关于《右岸》的访谈中,她也提到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表达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7]但从整体故事和象征的角度看,迟子建所表现的除了“尴尬、悲哀和无奈”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绝望。
这个绝望当然有现代文明不能保留那种独特的狩猎文明的绝望,但是,在迟子建小说的结构内部和意象象征中还包含着另一种更深刻的主题:现代文明对土著民族居住地“毁灭”的同时,也“毁灭”了他们的神话——他们赖以生存的神圣的精神家园。正是这个内容和主题的表现,使迟子建的《右岸》具有了超越描写少数民族生活故事而具有了世界性的现代意义。小说表现永恒回归的神话,是贯穿20 世纪一直到21 世纪初人类文学一个普遍重大的主题。这类文学所表现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失去了神话的精神家园,而陷入人性异化、追逐欲望和精神迷茫的痛苦之中。著名神话学家阿姆斯特朗曾在对艾略特《荒原》的评论中指出这种回归神话创造的意义。她指出:“《荒原》通过中世纪的‘圣杯’神话隐喻现代西方的生存状况,人们在‘荒原’过着不真实的生活,盲目追随社会规范,却没有来自内心深思熟虑的坚定信念。在这遍布着现代性之‘乱石’的荒原中,人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深藏于文化底层的神话的触摸,又如何能在此扎下创造之根?他们只有‘一堆破碎形象’,而无法深入到传统文化的内部核心。诗人艾略特细致而悲伤地引述着过往的神话……在他的《荒原》里,现代性之颓废暴露无遗:异化、倦态、虚无、迷信、自负和绝望……《荒原》薮集了大量已逝的神话无疑,神话的洞察力将成为拯救我们的一种力量。”[8](P148)《右岸》虽然是描写鄂温克少数民族衰落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的内核却是天神神话、火神神话和萨满神话,以及神话精神如何转化为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而那个民族的衰落也即那些神话的没落和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衰微。迟子建以鄂温克族衰落的故事触摸到了远古神话,并以那种神话的光辉烛照了现实。
《右岸》只是描写了“野人”对“山外”居住点的不适应,没有描写现代文明的诸多弊端,但是,这些没有描写的内容却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被填充被丰富被再创造了。读者是带着对现代文明诸多弊端甚至批判意识的“前理解”来阅读《右岸》故事的,因而他们才被那来自古老民族的神话信仰和文明模式所深深吸引。读者带着对现代文明的疲惫感和生活体验,去理解和感受《右岸》中所描绘的神话及神话构成的独特文明生活,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结构。读者欣赏那种居住在大森林中单纯、光明而快乐的生活,并不是在现代化的今天要真的回到大森林中去——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现代化生活回到原始生活样态中去了,而是在现代文明紧张局促而又忙乱不堪的生活中,把鄂温克族的大森林原始生活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把鄂温克族对神话的信仰看作是一种对光明生活的憧憬,把那种神话式生活方式的失去看作是他们生活的一种寓言。这应该是《右岸》被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一种心理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