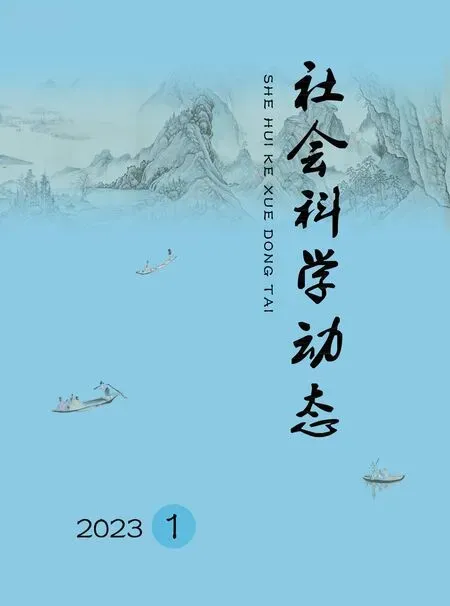《贝拉罗莎暗道》中的记忆书写与伦理选择
胡星怡 刘兮颖
《贝拉罗莎暗道》(The Bellarosa Connection,1989)是美国犹太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晚期创作的一部关涉犹太民族大屠杀记忆的中篇小说,此前学界对其研究较少,且多聚焦于创伤批评、叙事理论及犹太性等方面①。本文拟从记忆理论角度出发,结合空间批评及文学伦理学批评,对隐含在主人公回忆叙述背后的记忆危机进行发掘,进而探寻文本背后潜藏的对犹太民族苦难记忆消亡以及对犹太族裔身份缺乏认同的隐忧。小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通过 “我” 与他人的谈话展现了一场犹太民族记忆面临消亡的危机。家宅空间的流变昭示着大屠杀幸存者的不断逝去,代际更迭加速了犹太民族记忆的消亡。同为第一代犹太移民的 “我” 的父亲和娱乐业大亨比利·罗斯,曾试图以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两种外在方式来挽救记忆危机,但均以失败告终,历史与现实间的巨大鸿沟始终无法弥合。最后一代大屠杀幸存者方斯坦夫妇的意外死亡唤起了 “我” 的回忆义务,并促使 “我” 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伦理身份。在被美国社会同化抑或是坚守犹太民族记忆两者之间的选择弥补了先前伦理意识的缺失,使 “我” 对犹太族裔这一伦理身份的重新产生认同,并自觉肩负起传承犹太民族记忆的重任。
一、空间流变与记忆遗忘的危机
在小说文本中,回忆与现实交互穿插,在 “我” 所身处的当下完成了对过去的回溯。而无论是 “我” 的回忆抑或是我所身处的现实,始终发生在一系列的家宅空间中。换言之,是这一系列家宅空间承载着 “我” 对过去的记忆,也接纳着 “我” 对现实的思考。从湖林镇的房子到费城豪宅,再到仅留下一位守门人的方斯坦夫妇的空宅,三处家宅空间的流变潜藏着几代犹太移民的生活轨迹,也暗示着美国犹太移民的代际更迭。纵观文中三处家宅空间的流变,不仅展现了犹太移民及其后裔的生活轨迹,也契合犹太民族代际更迭这一过程。但代际的更迭并未使大屠杀记忆自然地在犹太移民之间传递下去,以哈里·方斯坦为代表的犹太移民们所承载着的大屠杀记忆,也将随着其肉身的消亡而逐渐消亡,一场记忆遗忘的危机随着空间流变而缓缓展开。文化认同首先是建立在对个体族群身份的记忆上,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中家宅空间的流变史也即犹太民族大屠杀记忆的消亡史。
湖林镇的旧房子、费城豪宅、方斯坦夫妇的空房子,三处家宅空间相继出现,对应着美国犹太移民的代际更迭。湖林镇的旧房子是 “我” 出生的家宅,也是第一代美国犹太移民主要活动的场所。 “我们的身体永远不会忘却这座不能忘却的家宅”②,更遑论发生在家宅空间中的记忆。由于父亲对难民故事的痴迷,在这座旧房子中 “我” 和父亲数次听闻了哈里·方斯坦对大屠杀的回忆叙述。而作为大屠杀的见证者与讲述者,哈里·方斯坦与在场所有人共享了犹太民族的苦难记忆,大屠杀记忆也由此得以延续与传递。因此,湖林镇的旧房子成为承载着第一代美国犹太移民关于大屠杀记忆的 “容器” 。
随着时间流转, “我” 搬进了费城豪宅,顺利地踏入美国上流社会。父亲的溘然长逝与继母的离去,使旧房子被空置。其后妻子的逝去与儿子的独立,使 “我” 孤身一人居住在荒凉的豪宅中。当初旧房子中大屠杀记忆的见证者转眼只剩下 “我” 和方斯坦夫妇,二者间也早已中断联系,只剩下身为第二代犹太移民的 “我” 试图回忆曾经见证过的苦难。但此时的 “我” 早已被美国上流社会同化,不仅极力淡忘出生地新泽西,甚至潜意识里已将费城当作 “我” 的归属地。即便是在大屠杀记忆的回忆叙述中, “我” 也只不过把这种怀旧式的记忆以及由此带来的伤感当作是一种讨厌的东西——大屠杀记忆在 “我” 看来,似乎并没有留存与延续的必要。从湖林镇旧房子到费城豪宅的时空流转,隐喻着第一代及第二代犹太移民的代际更迭。 “我” 作为第二代犹太移民对大屠杀记忆的漠然无谓,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屠杀记忆面临消逝的现实危机。
第三处家宅空间是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方斯坦夫妇意外死亡后留下的空宅。守门人带来方斯坦夫妇意外死亡的噩耗及其子辈吉尔伯特也从数学天才沦为赌徒的消息。如果说,第一代犹太移民还能有意识地坚守大屠杀记忆并极力延续与传承它,那么第二代犹太移民对大屠杀记忆的冷淡态度则昭示着它将走向消亡的前景,而第三代犹太移民——方斯坦夫妇的儿子吉尔伯特,从被方斯坦夫妇寄予厚望的数学天才,到成为沉迷赌博以致间接害死自己父母的罪人。吉尔伯特无意成为犹太大屠杀记忆的见证者或承载者,甚至逐渐丧失其身为犹太移民后代的认同感,并被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美国社会同化——大屠杀带来的民族惨痛已被他全部遗忘。 “ (家宅)原初的特性,也就是认同感产生的地方。”③方斯坦夫妇的家宅如今已人去楼空,这一定程度上隐喻着吉尔伯特对与其父母的犹太民族记忆认同感的丧失。换言之,吉尔伯特的记忆已经深受美国社会影响已被其重新改写,完全遗忘了犹太民族曾经历过的一切苦难。至此,除 “我” 以外的犹太大屠杀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全都逝去了。方斯坦夫妇留下的空宅无疑象征着大屠杀记忆承载者生命的终结与肉身的消亡。 “终极的遗忘指的是痕迹的消失,我们感受到它是一种威胁。”④大屠杀记忆承载者留下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空间流变象征着的代际更迭背后,正是一种终极的遗忘。
正如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所说: “在这场危机中,由于再一次的代际更迭,本世纪最大的灾难——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见证者一个个逝去。”⑤潜藏在文本中由空间流变表征的代际更迭背后,是犹太民族有关大屠杀的苦难记忆面临被终极遗忘的现实危机。如何使这种沉痛的历史记忆在犹太移民后代之间传递下去,使这场记忆危机得到消解并挽救因遗忘记忆而带来的身份危机,便成为美国犹太移民亟需关注和思考的现实问题。
二、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的代际传递
代际的更迭使犹太民族的大屠杀记忆面临消亡危机,而身为第一代美国犹太移民的 “我” 的父亲和犹太同胞的拯救者比利·罗斯则意识到了这种危机,于是他们试图通过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这两种外在方式,使大屠杀记忆在代际间传承与固化。 “在受到规定性文本支撑的跨时代的文化记忆,和通常联系三代人、由口头流传的记忆组成的交际记忆(交往记忆)之间,存在着平行关系。”⑥“我” 的父亲试图通过交往记忆使大屠杀记忆在代际之间传递;而比利·罗斯则选择以文化记忆手段,即着手建造具有特殊意义的雕塑园以及纪念碑式的建筑来固化大屠杀记忆。不幸的是,这两种手段都无法真正实现群体记忆的延续,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挽救大屠杀记忆的遗忘危机。
在小说文本中,交往记忆表现为大屠杀幸存者哈里·方斯坦在湖林镇旧房子中对 “我” 和 “我” 的父亲的回忆讲述,以及 “我” 在与方斯坦夫妇交往过程中所能见证的大屠杀记忆。哈罗德·维泽尔在《交往记忆》一文中指出,交往记忆 “是一种互动的实践,位于个体和群体对过去的回忆的张力之间”⑦。但由于 “我” 并未亲历过大屠杀事件,也就不能真正对方斯坦等人的回忆感同身受,大屠杀记忆并未真正在 “我” 与方斯坦夫妇的交往过程中得到有效传承——它仍旧处于断裂和脱节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交往记忆是 “我” 的父亲以半强迫式地要求 “我” 去记住的,或者说,见证方斯坦本人的大屠杀记忆并非 “我” 的主观意愿。 “我父亲对难民故事很着迷,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我。他以为如果我听了人们在欧洲、在现实世界如何受尽苦难,我就会循规蹈矩。”⑧由此可见, “我” 的父亲或许是意识到了关于大屠杀的苦难记忆不能被忘却,因而对哈里·方斯坦的故事意外着迷,甚至试图影响 “我” ,希望 “我” 能够在与哈里·方斯坦的谈话中获得一点受益。但 “我” 的态度无疑是令父亲失望的,尽管已经多次听过这个故事, “我” 却只将它当作一部好莱坞每周播出的惊险片而已,不仅未意识到哈里·方斯坦受难史的苦痛意义,只是单纯地将其看作是一部惊险史,甚至认为关注像屠宰场、焚尸炉这种直接对犹太民族造成伤害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浪费精力。究其原因,在于当时 “我” 的自我身份认同是一个年纪轻轻、我行我素的美国犹太人。 “我” 这种令人失望的态度恰恰来源于自身对大屠杀的苦难缺乏认同,既未亲身经历过大屠杀,也对哈里·方斯坦的讲述缺乏兴致,故而无法严肃对待他这些口头流传中承载的交往记忆。 “我” 既不能理解哈里·方斯坦充满苦难的过去,也无法赋予这一特定历史过往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意义, “我” 注定无法和父辈达成对大屠杀记忆的一致认同。
更为不幸的是,交往记忆只存在于交往过程中,它 “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的短期记忆,注定存在于活着的记忆承载者身上,存在于交往对象的体验当中,涵盖了三至四代人”⑨。这种记忆是短期的、不长久的,一旦记忆承载者如方斯坦夫妇或是 “我” 的父亲逝去,它们就会宣告消亡。同时, “交往记忆随世代改变而改变”⑩, “我” 无法对大屠杀记忆产生认同,它也就无法在 “我” 这一代中传承下去。因此,父亲试图以交往记忆这一外在手段使 “我” 成为犹太民族苦难记忆的承载者这一做法,结果只能使大屠杀记忆处于一种对话的断裂状态,这也说明了 “我” 对过去民族记忆的脱节。
与父亲相比,比利·罗斯更早意识到了这种危机,也意识到了将记忆固化下来的重要性。于是在以色列建国初期,他通过在耶路撒冷出资修建一座带有纪念意义的雕塑公园以及纪念碑式的建筑,试图将大屠杀记忆固化在耶路撒冷这片土地上。文化记忆 “由一些固定的要点支撑,这些要点不会随着当下而变动,相反,它们被视为命定的、有意义的,并通过文本、仪式、纪念碑和纪念活动得到标记”⑪。在这种意义上,比利·罗斯试图建造的建筑,属于 “文化记忆” 的范畴。
通过贝拉罗莎暗道,比利·罗斯将一个又一个大屠杀幸存者从纳粹手下拯救出来。出于 “对犹太同胞的感情” 和 “父辈们的上帝” ,比利身上具有的犹太民族性在这场拯救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这其中也寓含着一种反讽:作为拯救者的比利·罗斯可以拯救犹太民族同胞的生命,但人的自然生命终会结束,而那些逐渐丢失渐至消亡的记忆又要靠谁来拯救呢?于是他选择以色列建国初期在此兴建一座 “文化记忆” 建筑,试图花费几千万美元通过物化载体将其 “固化” 在耶路撒冷这片作为犹太民族历史核心的土地上。犹太民族在比利·罗斯心中仍旧占有一席之地,但肆意挥洒金钱这种做法又是极其 “美国式” 的。这种美国和东方混合的古怪而宏伟的姿态,昭示着比利·罗斯始终在美国化与犹太性之间来回摇摆,犹太民族的影响最终占了上风,由此,有了这样的文化记忆在犹太教圣地耶里撒冷留存下来。 “文化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形态,它为许多人所共享,向这些人传递着一种集体的(即文化的)认同。”⑫比利·罗斯想通过使所有可见到这座纪念碑式建筑的人,获得对大屠杀记忆及犹太族裔身份的集体认同,耶路撒冷也由此成为一处 “记忆之地” 。但这处 “记忆之地” 是否能够真正影响到美国犹太移民后代呢?对于犹太移民来说,耶路撒冷不过是他们旅游途经的一个地方景观而已, “这次旅行对于他们在哪方面有纪念意义?这个问题不禁令我想起了自己,于是我以犹太人的方式以另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有什么值得记忆的呢?”⑬显而易见, “记忆之地” 虽然能够使记忆得到一种持久的延续,但这种持久的延续却依然不能影响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美国犹太移民身上。 “一旦被写下来的东西,也就可以被推翻或被消除”⑭,被外置的文化记忆同样面临着被遗忘的风险。
无论是交往记忆还是文化记忆,都是试图使大屠杀记忆得以延续或固化的外在手段。 “我” 既不能从与方斯坦夫妇的谈话中获得对大屠杀记忆的认同,也不能单凭在记忆之地的一次游历而重新意识到自己身为犹太人需要将记忆传承下去的义务——这意味着:两种拯救手段最后只能走向失败。
三、伦理选择与身份的背离及回归
作为外在手段的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并不能使 “我” 意识到将记忆传承下去的重要性,最终是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使 “我” 意识到需要承担起延续大屠杀记忆的义务。正是由于第一代犹太移民哈里·方斯坦以及 “我的” 父亲等人对犹太民族记忆的固守,以及努力将记忆在代际之间传递下去的坚持精神,促使 “我” 在被美国社会同化抑或是坚守犹太民族记忆这一困境中做出伦理选择。在完成这一艰难选择的过程中, “我” 也经历了自身对犹太族裔这一伦理身份的背离与回归。
整个故事中,在被美国社会同化或是坚守犹太民族记忆选项中, “我” 经历了从摇摆到坚定的心路历程。作为犹太民族后裔,青年时期的 “我” 对这一伦理身份存在明显抵触心理,潜意识中渴望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真正的美国公民。 “我” 无视不能与异教徒通婚的规定,娶了一位清教徒家庭的白人富家小姐,背离了犹太民族后裔的身份。这个阶段, “我” 更倾向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就连 “我” 对自己的剖白,也时常显示出对美国身份更加趋于认同,认为与犹太教相比美国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也更加适合 “我” 的发展。但当 “我” 年事已高,逐渐意识到犹太民族性不断受到美国经验的考验。随着回忆的铺开, “我” 意识到这种失落来源于自身对犹太民族记忆的淡忘。这一阶段, “我” 逐渐意识到坚守民族记忆的重要性。直到 “我” 做了一场梦,在梦里, “我” 在洞里不断挣扎,直至筋疲力竭也无法爬出。当 “我” 从这场带有隐喻性的梦中醒来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 “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犹太人”⑮,而非美国人了。 “我” 的内心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即选择坚守民族记忆,回归自己犹太族裔的身份。
方斯坦夫妇意外死亡的消息,进一步使 “我” 觉醒,更加坚定内心想法,进而做出最终的伦理选择: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犹太族裔,牢记犹太民族关于大屠杀的记忆。 “在私人记忆里,一个共同记忆的毁灭使回忆有了一种强烈的内在强制力。这种力量唤起了每个人的回忆义务,同时由于对归属的渴望,就产生了身份的神秘。”⑯方斯坦夫妇的死亡预示犹太民族苦难记忆的消亡,这种消亡或毁灭催生了 “我” 对坚守记忆的强烈渴求,也使 “我” 意识到需要对年轻人有所影响,要让下一代犹太移民也能坚守住有关犹太民族记忆。
人类的伦理选择是 “人的本质的选择”⑰,在被美国社会同化抑或是坚守犹太民族记忆之间, “我” 最终选择了后者,回到 “我” 作为犹太族裔这一伦理身份的本质。 “身份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如血缘所决定的血亲的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取的,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⑱在 “我” 所做出的伦理选择背后,实质是对 “我” 与生俱来的身份——犹太民族后裔以及后天获取的身份——美国公民这两个伦理身份之间的选择。对于犹太民族后裔这个身份来说, “我” 的选择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其背离与回归的过程。从开始对美国公民这一身份的认同与追求,到最后自觉肩负起传承犹太民族记忆的重任,以及将影响后来的年轻人作为己任—— “我” 由此也完成了对犹太民族后裔这一身份的精神回归。而身份的回归,昭示着 “我” 对犹太民族大屠杀的记忆也完成了觉醒、回忆和回归的过程。
与 “我”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斯坦夫妇的儿子吉尔伯特。他在被美国社会同化抑或是坚守犹太民族记忆这一困境中,最终选择了完全被美国社会同化,彻底背离了犹太民族后裔的身份。作为数学天才,他从小就被方斯坦夫妇寄予厚望,但成年后却迷失在美国社会的纸醉金迷中,甚至是沉迷于赌博,最后还间接害死了自己的父母。可见,吉尔伯特是逐渐背离自己犹太民族后裔这一身份,并在这条被美国社会同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 虽然完成了伦理身份的回归,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说,犹太民族记忆的前路又在何方? “我” 曾经也像 “我” 的父亲一样,试图和 “我” 的儿子讨论有关犹太民族记忆的问题,但 “我” 的儿子并不能理解,因为他认为自己只适合做商人或是走上仕途; “我” 也试图向和吉尔伯特一样年轻的守门人讨论此类问题,但他只是在取笑 “我” 的犹太情感,对 “我” 所讲述的有关犹太民族的故事完全无动于衷。
小说中, “我” 虽然完成了对犹太民族后裔这一伦理身份的回归,但索尔·贝娄却在小说结尾处塑造了像守门人这样代表着遗忘了犹太民族记忆的年轻移民后代——这体现了作家本人对犹太民族记忆传承及其身份建构的隐忧。
四、结语
索尔·贝娄在《贝拉罗莎暗道》中以 “我” 的回忆展开叙述,通过三处承载着记忆的家宅空间的流变,展现了一场犹太民族记忆将被丢失与遗忘的记忆危机,进而揭示了犹太民族现实与历史的脱节。这种脱节不仅表现在交往记忆的断裂上,也表现在被搁置在记忆之地的文化记忆无法在美国犹太移民身上固化下来。过往的记忆不断被覆盖清除,外在的手段无法拯救这一危机。或许,在被美国同化或是坚守犹太民族记忆——只有通过内在伦理意识的觉醒才能做出伦理选择,重新使伦理身份归位,将民族过往的记忆内化为个人记忆的一部分。暗藏在小说字里行间的是作家对这一记忆危机不容乐观的态度。《贝拉罗莎暗道》作为索尔·贝娄晚期的代表作品,沿袭了其在文学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即主人公如何面对犹太性与美国化的双重难题,在背离原有的犹太族裔的伦理身份后又选择复归。实际上,在索尔·贝娄其他作品如《洪堡的礼物》《萨姆勒先生的行星》中,都展现了作家对犹太族裔身份建构这一主题的关注。可以说,《贝拉罗莎暗道》通过回忆叙述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对大屠杀记忆的书写,也是对犹太民族后裔这一伦理身份重新认同和建构的过程。
注释:
① 如:宁宝剑在《〈贝拉罗莎暗道〉:创伤的传播及其反思》一文中,从创伤批评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索尔·贝娄对种族创伤书写的遗忘与反思,通过描写创伤记忆的抑制和播散,辩证地思考了创伤的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尤广杰在《论〈贝拉罗莎暗道〉的叙事技巧》一文中从叙事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叙事视角、人称转换、视角越界对小说文本中犹太民族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凸显作用;木下喜美在《ユダヤ系アメリカ人の苦悩: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をめぐって》一文中,探讨了文中主人公美国身份与犹太性之间的冲突问题。
②③ [法]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④ [法] 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72页。
⑤⑥⑭ [德]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4、298页。
⑦⑨⑪⑫ [德] 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5、353、285、139 页。
⑧⑬⑮ [美] 索尔·贝娄:《索尔·贝娄全集》第12卷,段惟本、王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241、248页。
⑩ [德] 扬·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黄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9页。
⑯ [德] 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页。
⑰⑱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