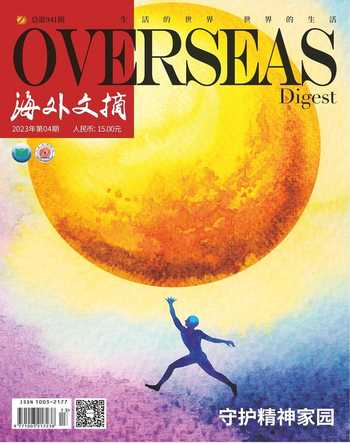非洲精神健康危机实录
埃莉斯·巴尔泰

“因抑郁症而自杀,这根本就不是非洲人会做的事。这种疾病大概只有白人或中产阶级才能有幸患上。”2014年,美国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自杀身亡,肯尼亚讽刺作家、《世界报》专栏作者泰德·马兰达有感而发,写下了这段话。
这段充满刻板印象的话语引发了舆论热潮,这正是马兰达的目的:聚焦非洲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撕破精神疾病的神秘面纱,让这个话题在非洲不再是难以涉足的禁忌领域。“肯尼亚和整个非洲的情况差不多,人们对抑郁症及其他心理疾病充满了误解。这类疾病遭到污名化,在家里也是禁止讨论的。”马兰达说,“虽然目前,非洲媒体对自杀行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会抱着同情与理解进行报道,但总的来说,非洲在精神健康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相当薄弱。”
在这一方面,马兰达所处的肯尼亚远不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精神卫生报告显示,2020年,人口为5300万的肯尼亚拥有超过8000名精神健康专业人员。而与此同时,人口约为肯尼亚一半的马里仅有46名精神健康专业人员。总体而言,在非洲,一名精神科医生平均要为50万名居民提供服务,而国际组织建议的比例为1比5000。
非洲人对精神健康服务有着巨大的需求,然而非洲的公共卫生政策却长期忽视这一领域。喀麦隆人类学家帕尔费·阿卡纳说:“在街头游荡的精神病人是非洲城市里永恒不变的元素。小的时候,我就经常看见有人在大街上赤身裸体,在垃圾堆里找吃的,在路边随地排泄,在泥浆里打滚。我听说有男人会侮辱疯女人,还有人会拿精神病患者作为祭品,献祭给神灵。这些病人从未受到重视。只有在高喊‘提高卫生健康水平’的口号时,人们才会关注他们,并盘算着该如何将他们除掉。”
| 自杀率全球最高 |
世界卫生组织称,非洲国家在精神健康方面的投入,人均仅有0.46美元,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为低收入国家建议的人均投入标准(2美元)。经济金融以及众多其他危机使得非洲成为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大洲。2022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曾呼吁应给予非洲的精神健康危机更多关注。
70岁以上人群的精神健康问题尤为严重。“但这只是冰山一角罢了。”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司的地区顾问弗洛朗丝·巴因加纳说。她主张政府大力增加对精神疾病预防项目的投入。然而,预算是有限的。非洲大部分资源都被用于防治致命性极强的传染病,包括疟疾、艾滋病、结核病、麻疹、埃博拉出血热以及新冠病毒。而且,也极少有国际援助组织能够拿出资金专门解决精神健康问题。
不过好消息是,部分非洲国家近年来已将“加强精神健康服务建设”提上了日程。2021年,肯尼亚及乌干达通过了精神健康方面的五年计划。加纳和津巴布韦也与世界卫生组织达成合作,为国民提供相关服务。

| 塞内加尔的精神病中心 |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他接受过哪些治疗?”主治医师阿达玛·孔度向正在翻阅默罕默德病历资料的护士询问道。默罕默德在三天前被送入了埃米莉–巴迪亚纳精神病中心。该中心位于塞内加尔西南部城市济金绍尔的郊区,掩映在繁茂的芒果树、柠檬树及香蕉树下。院内排布着18间小房子,用以容纳前来治疗的病人及其家属。
家人可以陪同治疗,是埃米莉–巴迪亚纳精神病中心的特色之一。“家属是共同治疗师。”孔度说。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12年。中心里的18名患者都有家属或朋友陪伴,他们会被安排住在同一间小房子里。“我和我妈妈一起来的。她每天帮我做饭、洗澡。有她在,我很安心。”31岁的患者帕普·布瓦耶说。他在这里已经待了一个月,即将出院。除了照顾患者的日常起居外,陪护者还负责与其他家属保持联系,充当患者与外界之间的桥梁,避免患者感到孤独。
长期以来,塞内加尔一直是非洲精神健康领域的领先国家。上世纪60至70年代,达喀尔的范恩大学附属医院开创了两个“精神疾病村”,这也是埃米莉–巴迪亚纳精神病中心的源起。精神科医生亨利·科隆及穆萨·迪率是这个项目的牵头人,认为精神治疗不应忽略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提倡使用非洲本土的传统药物。患者可以在家属的陪同下入住“精神疾病村”接受治疗。“这么做是为了让治疗过程更具有人情味。”孔度解释道,“只有护士长常驻村中,为病人发放药物。科隆每个月都会到村中探望病人。”
馬穆尔·法尔曾是“精神疾病村”(即如今的埃米莉–巴迪亚纳精神病中心)中的一名患者,于1975年入住。现在,他病情已然稳定,在中心担任运营负责人,时常会与患者分享自己的故事。他说:“以前这里没有警卫,是开放式的村庄。我们可以随意出入,附近的居民还能来找我们喝茶聊天。”
上世纪90年代末,当年的护士长退休后,一直没能找到新的人选,精神疾病村便也渐渐没落了。2002年,从塞内加尔济金绍尔返回首都达喀尔的“乔拉”号轮船倾覆,导致1800余人丧生大海,其中971名遇难者来自济金绍尔。四年后,荒废的精神疾病村被改造为了如今的精神疾病中心,让幸存者及遇难者的家属能够在这里接受心理治疗。
自1974年以来,该中心接治了将近6.3万名病患,主要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急性妄想症患者及癫痫患者。家属陪护在治疗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个星期,患者家属会聚在中心的一棵大树下,与医护人员讨论他们在陪护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 来自邻国的患者 |
埃米莉–巴迪亚纳精神病中心的常规问诊费为0.32美元,每日住院费4美元,精神疾病咨询费6.4美元,脑电图检查费16美元。如此低廉的价格吸引了许多邻国患者前来看病。57岁的塞内布·马内就是其中之一,她带着女儿从几内亚比绍来到塞内加尔。“她有多语症,会和脑海里的声音对话,而且很焦躁。”孔度医生说,“这其实是一种急性妄想症,患者会逐渐和现实脱离联系。”孔度给她开了旧版的安定药,虽然有副作用,但价格便宜。“新一代的药品全国都断货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她说。
这一天,孔度接待了27岁的萨内女士。她来自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她是丈夫的第一个妻子,孩子八个月大。近日,萨内的父母接连去世。除了要承受失去双亲的痛苦,她还需应对与另一个妻子源源不断的矛盾。她低声向医生述说道:“最近我根本睡不着,脑子很乱,很容易感到疲惫。”孔度诊断她为产后抑郁症,给她开了抗抑郁药物。

将药物递给萨内之前,孔度询问她是否在服用非洲传统药物。“出于谨慎考虑,我会让病人不要将传统药物及现代药物混合服用。不过,他们可以继续进行传统的仪式疗法,比如泡泥浆浴。有信仰,有家人的支持,病能好得更快。”孔度说。
资金短缺是埃米莉–巴迪亚纳精神病中心面临的一大问题,国家补助仅占该中心预算的13%。塞内加尔卫生部在2019年的一项报告中揭露:精神健康领域的人力、资金及药物均极其短缺。该国共有13家精神疾病机构,配备38名精神科医生及363张病床。超过半数的精神疾病机构都位于首都达喀尔。埃米莉–巴迪亚纳精神病中心的医护人员也并不充裕:两名精神科医生每周到访中心四次,为新入住的病人及情况严重的患者会诊;还有六名护士负责跟踪病情稳定的患者的情况,他们都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
| 精神科医生匮乏的南苏丹 |
因为停电,天花板上的吊扇纹丝不动。阵阵微风从窗户吹入,让这间有着淡绿色墙壁的小诊室稍稍凉快了一些。阿顿·阿尤艾尔医生的办公桌上放着一袋从街头买来的炸糕,她还没来得及吃早饭。这名南苏丹的精神科医生毫不掩饰她的疲倦。在两次问诊的间隙,她用双手撑着头,闭上眼睛稍作休息。

这是去年10月的一个周五,阿尤艾尔医生忙碌的一周已经接近尾声。她40岁,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自2014年起担任朱巴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南苏丹卫生部精神卫生司司长。阿尤艾尔医生致力于从不同层面推动该国精神健康事业的发展。作为精神卫生司司长,阿尤艾尔制定了一项“战略规划”:五年内,让80%的南苏丹乡村居民享受到精神健康方面的基础医疗服务,预估费用为1800万美元。
南苏丹内战多年不休,人民心理受到重创。然而,该国却没能为国民提供最基础的精神健康医疗服务。2009年的一項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首都朱巴,约36%的居民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50%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世界卫生组织称,2019年,南苏丹的自杀率排在非洲国家第四位(全球排名第13)。这个国家同样面临资金匮乏的问题。此外,南苏丹当局也缺少必要的数据,难以精确衡量精神健康情况的严重性。直到2021年,该国才开始在五个州(全国共十个州)内系统性地收集国民精神健康数据。
南苏丹拥有1200万人口,全国却仅有三名精神科医生,阿尤艾尔就是其中之一,她也是唯一一名在公立医院行医的精神科医生。“需求太大了!”阿尤艾尔不顾家人及朋友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进入了这个行业。“在医学院上学时,我是全年级第二名。当时大家都说,我做精神科医生实在是太可惜了。”她说。她原来的志向是儿科。在西加扎勒河州的一家医院实习时,她改变了想法。她说:“面对患有精神障碍的病人,我感到很无力。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把他们关进监狱。我感觉我的专业知识毫无用处。于是,我想,为什么不做一名精神科医生呢?”后来,阿尤艾尔完成了苏丹医疗专业委员会的研究生培养项目,毕业后成为了朱巴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的负责人。
“那时的精神科十分混乱,没有病历,也没有合格的心理专家,每天只开诊几个小时。”阿尤艾尔回忆道。经过多年发展,精神科团队已扩大至八人,包括多名心理专家及医护,能够为市民提供不间断的接诊服务,并与多个非政府组织达成了合作。精神病患者、抑郁症患者及情感性障碍患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相应治疗。
“我们收治的大多数患者都是因为物质滥用——比如酗酒或吸食大麻——而患上了精神障碍。”阿尤艾尔说,她坐在大大的办公桌后面,桌上摆放着几份病历。“患者有心理创伤,想试着自我修复,滥用物质是他们的常用手段。”


阿尤艾尔所在的精神科被称为“11号病房”,位于朱巴大学附属医院的边缘地带,和医院不共用一个出入口。精神科共有12张病床及一间用于问诊的小诊室。诊室内光线昏暗,褪色的墙壁和铁窗让氛围显得更为阴森。走廊上睡着一个男人,脚踝上拴着铁链。阿尤艾尔解释道:“我们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正考虑把他送入朱巴中央监狱。我们没有能力处理有暴力行为的患者。”由于医院缺乏相应资源,南苏丹首都的中央监狱设有专门区域,用于关押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患者。
虽然精神健康领域的医疗服务水平有所提升,但困难依旧存在。“我们科室的资金是全院最少的,没有钱翻新病房。科室里的医护人员工资都很低,缺乏工作动力。”阿尤艾尔说。作为精神科的负责人,她的月薪仅为十美元。“工资低就算了,还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她接着说。阿尤艾尔除了在公立医院接诊外,还有一家私人诊所,这是她的主要收入来源。依靠私人诊所的收入,她才得以抚养三个孩子,同时——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建设南苏丹”。
南苏丹的少数民族多达60余个,与他们沟通并不容易。“我学会了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很少出错。为少数民族患者服务,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话语来解释精神疾病及症状。很多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某些症状是精神病的表现。”阿尤艾尔说。

她还说起了她在瓦拉卜州的经历。2016年,她在当地遇见了一名被称为“疗愈者”的传统医师。这名传统医师在远离人烟的村庄“医治”着13名精神障碍患者,多年来一直用铁链把这些患者拴在大树上,惨叫声不绝于耳。阿尤艾尔以自己的名声担保,才说服了疗愈者释放病人,把他们送入医院。对此,她至今仍记忆犹新。想起当时的情景,她不禁长舒一口气,说:“从那以后,村庄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编译自法国《世界报》]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