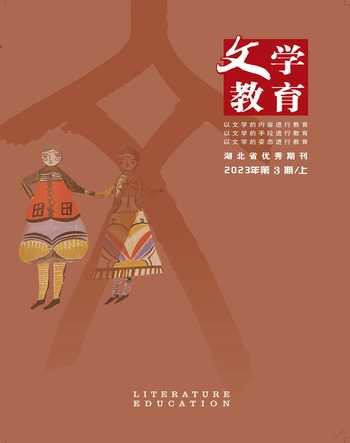海涅《巴赫拉赫的拉比》的互文性解读
应彬琛
内容摘要:《巴赫拉赫的拉比》是德国浪漫派晚期改宗犹太作家海因里希·海涅的断片之一。本文借助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对文本与历史进行互文性解读:一方面追寻文本的历史线索,明确故事发生时间及背景,从而进一步揭示因缺乏史实记载而被历史掩盖的部分西班牙马兰诺人的心声;另一方面,探寻15世纪末的西班牙犹太人与19世纪的德国犹太人的相似之处,由此窥见包括海涅在内的19世纪犹太知识分子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巴赫拉赫的拉比》 海涅 互文性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是19世紀上半叶德国著名诗人及作家,凭借其杰出的诗歌、游记和文艺评论文章,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继歌德之后的又一颗璀璨明珠。但因其特殊的改宗犹太人身份与敏感的政治倾向,海涅始终不为当时的德国知识学界正视,甚至不断被边缘化、污名化,其本人后半生也一直流亡法国巴黎,并最终客死他乡。当时只有少数德意志知识分子愿意与他交好并欣赏其文学才华,如首次在《美学征讨》中提出“青年德意志”流派的“三月革命前时期”作家维恩巴格、女诗人霍恩豪森、犹太女作家拉赫尔·法恩哈根的丈夫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后者更是与海涅终生保持紧密的书信往来。
海涅于1824年夏天着手小说《巴赫拉赫的拉比》的创作,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在他1826年完成第三章的一部分之后便无疾而终。《巴赫拉赫的拉比》可以说是海涅由浪漫派晚期作家转型为当时官方认定的“青年德意志”派作家[1]的过渡时期作品,虽然这份断片只有短短三章,但海涅却在书中详细描绘了15世纪末期德意志地区犹太人的真实生活,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欧洲(主要是德国和西班牙)犹太文化的文本素材。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研究视角分析文本。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概念由美国文学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莱特提出,首次出现在《文类》的专刊导言。新历史主义是聚合历史、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核心表述,挑战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实现文学的“历史转向”:一方面,历史事实通过经权力挑选和抹除而保存下来的“文本”得以表述,使得文学文本有可能成为反映历史镜像的特殊载体,“所有的文本实际上都是社会文献,它们反映着且更重要的是回应着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2];另一方面,文本并非是一个超历史的审美课题,而是特定时代的历史、阶级、权力以及文化等语境的产物。因此,只有将两者结合比较,通过分析文本的历史性尽可能还原最真实的历史,通过分析历史的文本性找到历史中被虚构或被抹除的成分,才能更大程度上贴近真相,文学文本对于历史的反映价值也得以体现。本文旨在对文本与历史进行互文性解读,再现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初期的德意志地区犹太人与西班牙犹太人的生存状况,重视19世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焦虑问题,并探究海涅对于德国犹太人义无反顾走上同化道路而发出的隐晦预警信号。
一.文本的历史性:中世纪末期的德意志地区与西班牙
海涅并未在文中直接交代《巴赫拉赫的拉比》故事发生的时间及历史背景,但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不难看出小说描绘的是一幅中世纪末期德意志地区犹太人的生活图景。
首先,小说开头两段主要按照时间顺序,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巴赫拉赫的建城史,以及中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大规模迫害犹太人运动。莱茵河边的巴赫拉赫城位于德国西南部,毗邻美因茨和法兰克福。小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4世纪末罗马帝国衰落后,巴赫拉赫“经历了风云变幻的诸多朝代”(461)[3],最终由霍恩施陶芬家族接管,1254年之后又成为了威特斯巴赫家族的统治领域。从古罗马时期开始便有犹太人居住在此,但因宗教、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占统治地位的贵族、神职人员等团体对犹太民族的迫害从未停止,不止针对巴赫拉赫的犹太人,在法兰克福、在德意志其他地区、甚至在整个欧洲地区,犹太人都经常面临莫须有的指责。十字军东征时期(1096-1291),天主教徒打着收复圣地的旗号首次大规模迫害犹太人;14世纪中叶前后,犹太人又为鼠疫的蔓延肆虐承担罪责;“另外一种对他们的指责,从过去很早的时代就开始,经整个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初”(462),即发生在1287年的圣维尔纳的故事,“但是自那以后的两个世纪里,他们(犹太人)就幸免于这种来自平民愤怒的袭击,尽管他们期间仍然受到各种敌视和威吓”(463)。因此前文提到的“上世纪初”便指向海涅所处时代的上世纪,即18世纪初,而“自那以后”更是可以将故事背景缩小到1487年前后。
其次,文中个别词汇具有浓重的中世纪色彩,或是暗含了人物的身份指向。第三章出现了“Frauenhaus”[4]一词,其现代含义确实为女子收容所或妇女之家[5],在此处却不尽然,译为“妓院”更为妥当。文中以色列餐馆的老板娘施纳帕-艾勒提起她那次在阿姆斯特丹的倒霉遭遇,就用“无耻的”来形容被“老奸巨猾的车夫”骗往的“Frauenhaus(妓院)”。阿姆斯特丹一直以来都是一座水陆四通八达的海港城市,中世纪晚期城市的发展及转型又必然伴随着商业卖淫的兴起[6],因此施纳帕-艾勒才会“吓得差点晕了过去”,她在那里“哪怕只有一小会儿敢于闭上眼睛,就真的会晕倒”(501),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历史污点,风评差劲却极力想自证清白的施纳帕-艾勒,才会在与他人交流时无数次强调她的道德原则[7]。此外,断片第二章还提到了“马克西米利安国王”(477),德国历史上共有两位马克西米利安国王,即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27-1576)。考虑到文本语境中丰富的中世纪元素,以及文艺复兴之风、宗教改革之风尚未吹进普通民众内心的事实(如神职人员仍旧在暗中控制人们的精神思想[8]),并参考其他译者给出的注释[9],可得知文中的“马克西米利安国王”指的就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而德语中的“国王”和“皇帝”具有不同的人物身份象征,马克西米利于1486年4月9日在亚琛大教堂加冕为德意志国王,直到1508年2月4日,经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批准,他才在意大利特伦托大教堂被授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由此可进一步缩小故事发生时间,即马克西利安一世作为德意志人民的国王之时(1486-1508)。
最后,西班牙是整篇小说的重要底色,比如海涅在描写主人公亚伯拉罕时,提到了这位拉比年轻时赴西班牙求学的经历,他与“那些当时有着极高修养的西班牙犹太人”(464,下同)一起学习了七年。福柯指出:“它(作品)可以在本文中辨读本文所要掩饰同时又要表现的某种东西的记录……(话语单位的)不连续性不仅仅是所有构成历史地质上断层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存在于陈述的简单事实中。”[10]因此,无论是从主人公去西班牙求学的选择上看,还是从巴赫拉赫的犹太人对西班牙犹太人的固有认知中看,西班牙在文本语境中无疑具有话语场中心地位,这种深入日常话语中的对西班牙的提及,甚至不为巴赫拉赫犹太人所意识。由此可知,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发展明显落后于西班牙,当巴赫拉赫犹太人仍旧保持中世纪的习惯、对犹太教心怀虔诚时,“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已深入西班牙犹太人的头脑中,而另一方面,巴赫拉赫的犹太人又对“模仿基督教习俗”、甚至改宗的西班牙犹太人感到鄙夷和不耻,这恰好印证了15世纪末的德意志地区和西班牙的历史。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德意志地区虽然社会经济较前已有很大进步,但封建生产方式仍占其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西班牙却早已萌发资本主义萌芽、接受哲学思辨之风、点亮启蒙理性之火,并利用地理优势逐渐成为海上殖民霸主,最终通过扩张、联姻等途径,一跃成为16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因其地理环境,西班牙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先后经历了蛮族统治、阿拉伯人统治和基督徒—穆斯林共治的时代,“伊比利亚半岛是整个拉丁基督世界对抗穆斯林的前沿战场”[11],直到12世纪,北方基督教王国和南方穆斯林统治依旧是西班牙的矛盾中心。而处于矛盾中心之外的少数族群——西班牙犹太人因此得利:无论是罗马帝国时期还是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统治者都对犹太人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8世纪的西班牙南部犹太人甚至可以做到宫廷级别的官吏以及军事统帅;10世纪至11世纪,北非穆斯林定都塞维利亚,强力推行宗教统一政策,但北方基督教王国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向犹太人抛出橄榄枝,犹太人就此北迁,犹太精英族群成为基督徒的国务活动家、顾问和医生。相比于夹缝中生存的其他国家犹太人,西班牙犹太人似乎备受上帝恩宠,但这份恩宠从13世纪末开始逐渐被收回。此时的基督教王国已站稳脚跟,不再需要犹太人的支持,在宗教统一的方向上,犹太人更是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因此他们对犹太人的宽容政策逐渐收紧,尽管很多犹太限令并未彻底落实。1391年,在西班牙发生了犹太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改宗现象;1492年,西班牙彻底驱逐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包括改宗犹太人)为了生存而选择离开西班牙。
诱发这两大历史事件的因素复杂且多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像巴赫拉赫犹太人,“来自外部的仇恨越是威逼他们……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和敬畏也越加深沉,越加根深蒂固”(463),西班牙猶太人经历过的磨难相对较少,对上帝的信仰远不如德意志地区的犹太人忠诚,一旦面临生存危机就有极大可能接受洗礼,尽管这一选择很大程度上出于被迫,尽管他们只是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暗地里仍信仰犹太教。这类改宗犹太人被称为马兰诺,如断片中的西班牙改宗犹太人伊萨克就符合马兰诺人的部分特质,本文也将在第二节中详细分析这一重要人物。根据伊萨克在故事中的表现,文本背景符合15世纪末西班牙历史现状,且更有可能发生在1492年针对所有犹太人的驱逐事件之前。
二.历史的文本性:超脱时代的人物——伊萨克
断片第三章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西班牙骑士唐·伊萨克,他可以说是西班牙历史经过沉淀后的鲜活缩影,并与“符合上帝要求的生活方式的典范”(464,下同)——主人公亚伯拉罕形成了鲜明对照。巴赫拉赫的犹太人因他们的拉比亚伯拉罕赴西班牙求学七年而隐约听闻过一些不敬上帝的传言,但拉比从西班牙回来后“哪怕最细小最不起眼的犹太教教规习俗”也兢兢业业地身体力行,谣言不攻而破;与此相反,唐·伊萨克不仅视基督教礼仪习俗为无物,也有意与犹太教划清界限,他甚至算不上是一个西班牙马兰诺人,更像是一个无信仰者,他通过味觉和嗅觉唤起血脉中与犹太教之间割不断的联系,犹太美食是他扎在以色列土壤上的根,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抹去身上的犹太印记。
然而,伊萨克的行为举止就其所处时代而言未免过于大胆放肆。伊萨克在法兰克福犹太区的集市上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异教徒,[12]这很可能令其引火上身,因为他的异端思想在当时为犹太教所不容,也为基督教所不容。历史上,15世纪的犹太知识学界将14世纪末犹太人大规模改宗的原因归咎为哲学,犹太哲学家们面对刀剑顺势而为,选择了受洗而非殉教,从而引导了大量普通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西班牙在1492年彻底驱逐犹太人之后,大量犹太人逃离西班牙或是接受基督教洗礼。可以确信的是,在马兰诺中存在一些持有异端思想的哲学家,但至今并未发现存有相关著作,因为这些异端思想一旦泄露,他们将失去过安稳日子的机会,改宗也就失去了意义。[13]因此,伊萨克的言行与当时的社会规则产生强烈冲突,这一文学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引人注意的矛盾感又恰好反映了那段被掩藏却真实存在的历史,借伊萨克之口揭示了部分西班牙马兰诺人的真实心声:即使受礼,也依旧扎根于犹太教的土壤。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由于每个文本都有一个实际的作者,他(她)的行为与观念就既反映了作者本人也反映了作者所在社会的关切,并构成文本本身的必要元素”[14],因此“超前”的伊萨克可以说带有海涅本人的影子,而海涅却没有他笔下的虚构人物那么洒脱。《巴赫拉赫的拉比》开始创作于1824年,且1822年至1824年是海涅集中创作犹太题材作品时期,直到1825年迫于现实压力而改宗后,他才逐渐放弃这一题材。显然,海涅对犹太教的情感并不淡薄,他试图通过文学手段记录犹太民族的处境、表达犹太民族的诉求;同时,他皈依基督教更多也是基于现实利益考虑而非信仰,尽管他想借此做一名律师的目的最终并没有达成,且对改宗一事深感后悔,他就像是一个既想坚定犹太教信仰并从中找到归属感,又因现实处境而不得不公开割断犹太情结的矛盾体。
但海涅面临的身份认同焦虑并非代表个人,而是十九世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掩藏在两个重要人物——亚伯拉罕和伊萨克身上的这段时期的历史以文学形式被书写下来,此过程甚至不为海涅本人所意识。与十五世纪西班牙相似的是,启蒙思想终于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广泛传播,将德意志民族从落后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但德国同时面临社会转型,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称帝等多重影响下,危机显得更为复杂尖锐。十九世纪,德国民族与种族思想逐渐觉醒,犹太知识分子融入德国社会的传统方式(即改宗)日渐失效,而倾慕启蒙思想的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又不愿遵循正统犹太教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犹太教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一样,是被理性排除出社会发展过程的事物。与此同时,生长在德国的部分犹太知识分子坚定认同自己是德国社会的一份子,并渴望在政治文化舞台上发挥才能,但德国社会上的种族主义歧视愈演愈烈,拿破仑击溃普鲁士后又对犹太民族采取宽容政策,从中获益的德国犹太人遭到德意志民族的嫉恨。面对这些社会现象及矛盾,大多数犹太知识分子为保障和实现自身诉求而选择了逃避,然而无论怎样同化、皈依,往往都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德意志民族建立共同的信仰与民族精神并不能通过简单的皈依来实现。[15]处于社会思潮变化中的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理应具有更敏锐地洞察能力,但对此的错误判断和选择使他们并未发挥适当的预警作用,这也为近现代史上德国犹太人的惨剧埋下祸根。
站在十九世纪历史洪流中的海涅不会不知道1492年的西班牙究竟发生何事,也不会不知道当时的改宗犹太人最终还是面临流离失所的命运,也许他在二十年代仍心存侥幸,但伊萨克这一超脱时代背景的小说人物已在时刻提醒着他犹太人将会面临的灾难,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在德国。也许海涅抹去故事时间及背景的做法,正是想向所有义无反顾走上同化道路的德国犹太人发出隐晦的警示信号,只是这一信号确实过于微弱,甚至没有人能够注意到。
1826年后,海涅再未动笔续写《巴赫拉赫的拉比》,或许是因为流亡生活令他无暇顾及小说创作,或许是因为他迫于现实利益皈依基督教的做法使他再也无法面对笔下虔诚的主人公拉比,或许是浪漫派作家写断片的偏好使然,又或许是因为小说的献予者劳伯的“背叛”[16]。但无论如何,《巴赫拉赫的拉比》给予后人足够大的阐释空间。正如本文借助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分析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一方面拨开故事背景之迷雾,明确了故事发生时间为15世纪末,并借助文本载体挖掘出了一些未被记载下来的历史痕迹;另一方面又通过作者海涅与笔下人物的隐匿对话,发现了处于不同时空却有着相似命运的犹太人群体,由此窥见十九世纪犹太知识分子面临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源之一,即犹太知识分子的“失格”。
由此可见,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确实存在着互动和张力,文学文本不可避免地被历史语境形塑,与此同时,历史画卷也因文学文本而变得更加清晰。
注 释
[1]“……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于1835年12月10日通过决议,全面禁止(包括海涅在内的5位)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作品……虽然联邦议会禁止青年德意志作家的决议中把海涅的名字列在第一位,但是,按照传统惯例,“青年德意志”却不包括被視为青年德意志之父的海涅和伯尔纳。”摘自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2007):德国文学史(第3卷)。北京:译林出版社,第322页+第326页。
[2]查理斯·E·布莱斯勒,赵勇、李莎、培杰等译(2014):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37页。
[3]本文引用《巴赫拉赫的拉比》均出自:《海涅合集(第一卷)》(Heinrich Heine: Der Rabbi von Bacherach. In Klaus Briegleb (Hg.):Heinrich Heine Smtliche Schriften,Band 1. München 1975.)
[4]DWDS就“Frauenhaus”一词列举出三种词义。(https://www.dwds.de/wb/Frauenhaus,2021年9月27日访问。)
[5]赵译为“女子寄宿所”,并给出注释:“为收容遭到家庭暴力伤害的女人而设的女子庇护所”。参见海因里希·海涅,赵蓉恒译(2015):佛罗伦萨之夜:巴赫拉赫的拉比。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61页。
[6]参见Christian Zarend: Bordelle.Frauenhaus und Prostitution im spten 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06.S.2.
[7]参见Heine,S.500-501.引文如下:“美德比美貌更有价值(Tugend ist mehr wert als Schnheit)”,“为了我的美德(Meiner Tugend wegen)”等。
[8]参见Heine,S.461.引文如下:“神职人员在暗处控制人们的精神思想(Die Geistlichkeit herrschte im Dunkeln durch die Verdunkelung des Geistes)。”
[9]潘译文中注释如下:“马克西米连(1459-1519),德国国王,自1493年起被选为德国皇帝。”参见海因里希·海涅,潘子立译(2003):巴赫拉赫的拉比。载于:海涅全集(第7卷·散文作品),章国锋、胡其鼎编,潘子立、赵蓉恒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49页。
[10]米歇尔·福柯,谢强、马月译(2003):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第24页+第29页。
[11]王玖玖:中世纪盛期西班牙犹太人与基督徒的族群融合。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8期。第93页。
[12]参见Heine,S.498.引文如下:“是的,我是一个异教徒…(Ja,Ich bin ein Heide…)”
[13]参见王彦:论哲学与14世纪末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关系。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27页。
[14]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第五版)。第240页-第241页。
[15]王雪:19世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问题研究。载于:《北方论丛》2013年。第109页-第110页。
[16]“表现得最没有骨气的大概要算劳伯……海涅曾戏称他为‘只能死在竞技场上的斗剑士……(但到)1836年初,他(劳伯)又写道,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觉得文学不再是政治愿望的表现了。他要对目前的文学(青年德意志派的文学)进行斗争。”摘自任卫东等,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323页。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