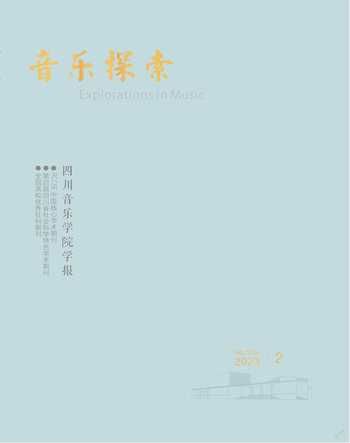谈二胡经典作品中的中国音乐审美观The Chinese Aesthetics of Music in Erhu Classic Works
摘 要 :文学与艺术本该是表达生命内涵的重要方式,是生命中爱与美的呈现。但在一些音乐学习者和从业者中却出现了日益功能化、技术化和功利化的倾向,舞台上夸张而超越内心的外化形体动作、对速度和竞技技术超过音乐人文情感本体的过度追求,千人一面的标准化艺术评判标准等,让具有生命温度的音乐艺术逐渐减少。尝试从生命中爱与美的本源出发,还原艺术的本质,以二胡经典作品为例,探究中国音乐的审美思维,以及中国音乐文化所具有的本真属性。
关键词:中国音乐审美;中国音乐文化;二胡经典作品
中图分类号:J63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23)02-0102-07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3.02.012
内在和外在,内涵与形式是音乐审美的两个方面。外在包括如音乐表演的音色、韵律、情感表达、技术完成,作品的和声、旋律、结构等。内在则包含生命与爱的内在信息传递,音乐所传递出来关于生命和哲学思考的共鸣等。生与死、爱与恨、美与丑、浪漫惬意与质朴自然都是音乐表达的内在主题。这种内外相互作用的音乐审美,便形成了中国音乐的演化逻辑。
一、审美的维度和内涵
审美是对美的一种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审美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以不同角度的局限入手,会陷入单一化,形成审美盲点。例如,作曲家习惯从作品创作角度看音乐;演奏家习惯从演奏好坏的不同标准角度看音乐;而爱好者则习惯从氛围和自身喜好角度看音乐。因此,同一个人演奏的音乐,这三种人听后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结果。如果从宏观(整体)把握,跨越专业的局限性,着眼于多种局部和多元微观,则容易形成较为完整全面,跨越通道的审美思维。
宏观审美能够产生一种气象(气势、气韵所构成的意象),它以整体感觉的形式来呈现。如曹操《观沧海》中,“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①诗句中所描绘出的种种感觉都可以称之为气象。宏观审美中所产生的气象之美是较为容易感知到的,不需要经历过多细细的品味、丰富的经历或系统的训练,只要有片刻的专注即可感知。那种扑面而来的宏观气象给人以强烈的审美冲击。①
局部审美则指一般情况下人们所普遍能够观察到的相对细节。局部审美是对人或事物的内在规律到达某种深度的了解,越过了第一印象的感知,但又没有进入精深的阶段。在这一层面,已经需要去细细地品味和解读才能发现其中的意味了。
微观审美是审美的高级阶段。进入审美微观境界需要深厚的相关专业素养和通达的思维境界,实现透过事物表面体察本质的审美层次。②在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当代,人们在不断获得物质的反复中极易产生一种审美的疲劳和麻木。觉知上的专注和耐心也会因为得到过多而减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③人的感知系统变得更加麻木和难以满足。培养对平淡事物的觉知力,回归自然和简单的断舍离等潮流理念,正是人们试图找回觉知和专注的探索。
二、二胡经典作品中的中国审美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乐器,承载的是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美学思想表达。但当代二胡演奏及作品的解读多注重于外在,如演奏技术完成的标准、外在审美的音色,而从力度和情绪、作品强弱规律、气息及乐段乐句的连接等相关问题的分析较少,缺少了对内在中国历史文化审美的解读。本文所举二胡经典作品中的音乐意象,意图从中国文化历史观的角度还原中国音乐的内在审美,通过音乐意象来带动作品的形神和演奏的技艺,而非用技艺来表现音乐内涵。
审美是生活追求的升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美已经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但审美远远不是好看与否这么单一的含义,而应是多元化的理解,是不同民族、地域、时代文化精神的标志。中国音乐的审美观是由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文化土壤培育起来的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当代国人思想中传递而成的音乐文化审美思维,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和历史传承性。用二胡经典作品解读的视角,是对中国文化内涵的一种再认知。
本文选取八首二胡经典作品是以中国音乐为载体,用写意和具象等手法对中国文化思想进行凝练。中国古代音乐多为文人和贵族所用,贵族用乐彰显地位。礼乐制度让音乐有了等级产生的审美观;而文人用音乐,或寄情山水,表达爱意,或抒发理想抱负。修、齐、治、平,儒、道、墨、法,百家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历代的中国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多是以“音乐意向”来表达思想和美感。而意向,是类似于中国绘画中用写意的手法对情景含蓄却又让人心领神会充满期待与想象的勾勒。这种中国音乐独特的文化现象,给人提供了具有中国浪漫主义情怀的期待和想象空间。④
三、中国音乐审美八意象
音乐的审美是多元的,每个人都可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⑤意思是说音乐的本初,是由人内心的感动而产生的,人内心的感动,是源于外物的触发。每个人所感不同,对音乐的理解也就本该是多角度的。那么该如何理解、欣赏及把握中国音乐文化审美观中的这种思维呢?笔者用清、坚、逸、健、莽、凄、浑、采八个字分别引出八首二胡经典音乐作品中的音乐意象①,借此引导读者去感受中国民族音乐中的审美趣味和人文情怀。
(一)中国音乐八意象之“清”——《月夜》
“清”是雅的根本,是音乐的精神。环境的清幽,一把好琴所带来的清透,琴弦的爽利,都是音乐能否通透的所在。心如果不静则不清,气息如果不顺畅则不清,手指按音和运弓如果犹疑不定、迟重浑浊,音乐就更不能清。
清雅是音乐中心灵的沉静。不追求情绪的大起大落,不被焦急所催促,清新淡雅、安稳自然。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的一切美好都需要在过程中细细地品味。凝神静气,化神为意,形神气韵合于一弓,一颦一笑、一扬一落、一招一式,顺着乐句的气韵,将每一处虚、实、浓、淡都泰然处之,不将就、不刻意。轻松恬淡,则能真正到达外明音而内精神,通透却静谧的清雅意向。如果草率出弓发声,神未聚,气尚散,那声音中就只剩下外在浑浊的力量躯壳,而失去了音乐文明的厚度与神韵。只有进入疏密有度,张弛相应的无我、沉静、通达、清明状态,才能够体悟到音乐中的清雅意趣。
《月夜》这是民国时期国乐大师刘天华先生十首二胡独奏曲之一,也是十大二胡名曲中梦幻和富于诗意的一首。乐曲创作于1918年的夏天,那时,年轻的刘天华先生正在家乡江苏江阴居住。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月夜》。在欣赏或演奏这首乐曲之前,可以想象一下这位23岁内心细腻的年轻人在面对皓月当空的景象时,内心所泛起的波澜。
乐曲第一段,触发了一种从容淡雅的意境之美。月兔东升,皎洁如雪,在这种氛围之下,人的思绪沉醉在美景之中,仿佛是置身于天地间,同自然融为一体。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才子佳人,都被这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同一轮明月牵动过心弦,人生中那美好的瞬间也定格在了这一轮明月映照下的夜晚。王国潼先生曾谈到二胡音乐中的三种意韵——清、淡、雅,而此曲第一乐段所蕴含和表现出来的乐思,也正是这样清雅之感。乐曲第二段,似乎有一种内心的流露,有彷徨、有留恋,也有向往。这一乐段仿佛是心灵在诉说,感怀生活与自然中美丽的花草树木,亦感怀某一个夜晚,那轮明月下的时光。作品第三段中,音乐开始流动起来,一种向上的动力流淌而出,好似对人生的憧憬和追寻,让人内心沉浸。
(二)中国音乐八意象之“坚”——《二泉映月》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二泉映月》是描写瞎子阿炳(华彦钧)悲惨人生的悲情作品,演奏时应着力刻画阿炳波折坎坷的情感内涵。其实,作为二胡传世经典,《二泉映月》有着巨大的内涵容量,可以承载悲、欢、坚、朴、得、失、愤、舍等无数个解读视角。以悲为意不是唯一,只是对《二泉映月》的一种解读方式。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都有所不同,此曲的内涵也同样应该是包容而非局限于悲情基调上的。
坚,有坚守、坚定、坚毅、坚韧等含意。坚可以是一种品格,也可以是一种信念。艺术中更有一种坚的境界,就是用眼泪来表现喜悦,而用微笑和豁达来表现悲伤。坚的演奏在音量与力量上的控制尤为重要。体现坚韧时,运指以压代按,先按而后压,压揉结合,力度强而音量先弱后强,之后再加力而减音量,形成声音意向的不屈不挠感。在表现坚定时,可通过先以幅度小而快,压力重而紧的压揉起势,运弓形成锋利音头与强结构感,形成外果决而内扎实的稳定性。随之左手持续不断而立刻松右臂,转而为右掌指运弓,再造层层递进,形成坚定的声音意向。老子曾说,“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白与黑之间的反衬和交错,更凸显出演奏内在表达的深层力量。
华彦钧自幼随父在道观中学习音乐,并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宗教人士的社会地位较高,阿炳算得上是思想文化和艺术水准兼而有之,同时衣食无忧,一帆风顺的幸运青年了。但世事不可预料,在走入人生的后半段时,阿炳由于双眼失明和父亲的离世而跌入了人生的谷底。被赶出道观后,开始了异常艰辛的生活。哀莫大于心死,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前后人生境遇的强烈反差,恰恰成了让内心成长和坚韧的契机。
用坚的品格来品读《二泉映月》可能会有人疑惑琴声中缺少阿炳的悲凉和痛苦。然而这正是坚的性格,用坚强、坚韧来面对苦难;用波澜不惊,甚至平淡的笔触去书写人生的跌宕。
(三)中国音乐八意象之“逸” ——《椰岛风情》
“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非有逸致者,则不能也。”①逸致是人天赋中蕴含的能力,这种天赋让灵魂能更自由地去表达,进入没有挂碍的舒适状态中从而迸发出独具魅力的美感。逸是浩然之气充盈后绽放的光彩,是天地赋予人天性精华的显现,这样的天性之美还蕴含着恬淡虚无间的一股洒脱,透出了本性具足的雍容和自信。
《椰岛风情》是二胡演奏家陈军先生根据海南西沙音调创作的乐曲,描绘了一幅风情独具的梦幻“逸”境。乐曲引子部分以自由的散板开始,仿佛从现实进入了梦乡,又在梦境中苏醒,一股朦胧和慵懒的气息弥漫开来。乐曲的上板段落,旋律的开始是以前调的结束音为起点,呈现出一派新鲜的海南风情之中。
乐曲运用“连滑揉”的演奏技法,结合长线条气息自然起伏的运弓,给人慵懒而略带异域风情之感。左手动中有静,而右手静中带动,两手配合丝滑严密,形成奇异、飘逸的意向之境。此时应十分小心仔细对地每一寸运弓进行工笔描绘,随境而转入一个个不同景象,景象丰富层次递进,但风景不同心境不同。接下来过渡性的乐句,以前段的结束音为开始进入B调的散板。这段尽情陶醉的华彩虽然短小,却大胆表达出了内心自由而充满愉悦的深情独白。随着欢乐小快板的铺垫,音乐逐渐进入激情的高潮段落,从声音中透露出内心如火一般热烈的张扬。尽情挥洒中,一根引线的长音将音乐慢慢地拉回到乐曲的再现场景,让音乐在朦胧梦幻中逐渐远去。
这蕴含着逸之美的音乐感觉,令人心驰神往。明代徐上瀛先生曾说:“临缓则将舒缓而多韵,处急则犹运急而不乖。”意思是在演奏缓慢的乐句时,需要做到恰到好处又充满神韵;演奏快速的乐句时,又要操作迅捷而又不毛躁、不慌乱。这种得心应手,也造就了演奏这首作品时动中有静的演奏乐趣。
(四)中国音乐八意象之“健” ——《赛马》
健是天的品德。天在运行时,是刚毅坚卓,发愤图强且永不停息的。君子也应当效法天地的德行,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以健为题来引出《赛马》这首黄海怀先生的经典之作,正是因为此曲中蕴含着健之意象的诸多内涵。
《赛马》是一首极富奥妙的传奇之作。说它极富奥妙,是因为《赛马》的演奏技巧并不复杂艰深,甚至可以说是简单的,但其音乐效果却给人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乐曲帶给人热血沸腾,眼花缭乱之感,用寥寥几笔凡尘之音,便可激荡风云,足见此曲的奥妙精深。作品不仅好似一匹黑马在全国大赛中脱颖而出,被评为优秀新作品演奏奖后,更是很快风靡全国。
如果说《赛马》的奥妙和传奇是它雄健姿态的两个体现,那它乐曲内容所展现出的底蕴就更显示出此曲“天行健”的品德。声音远近(强弱)造成的距离对比感形成了赛马场上大轮廓下的你追我赶,乐曲演奏中用粗犷的音头带动整个弓段,展现出骏马不畏惧、不退缩的雄健风姿。两个相同乐句用一强一弱来呼应竞赛的场面,四个相同的句型则以由弱到强、起承转合来表现竞赛的激烈豪迈以及路途的扬尘与激荡。时而穿插着一大段悠扬的旋律衬托出晴空万里之下在无尽大草原上奔驰的痛快,描写了蒙古游牧民族驰骋、奔腾的赛马场面,在听觉起伏的追赶中呈现出近大远小的视觉联想效果。其中不仅有争夺追赶的激烈,更揉入了潇洒张扬的欢乐,在民歌的旋律之中,骑手们仿佛忘却了比赛,沉浸在一片信马由缰,尽情放歌的欢乐之中。马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代表,中国成语中就有龙马精神,龙马是炎黄子孙的化身,代表了中华民族进取向上的精神。
这首作品使用中国民族五声调式与蒙古族民间音调,运用了二胡与蒙古族音乐风格的音乐语言,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展现了中国音乐中雄健意向的民族精神。
(五)中国音乐八意象中的“莽” ——《宁夏川好地方》
二胡音乐八意象之中的“莽”字是广博、辽阔的意思。音乐中有了莽的意境,便平添了一种胸怀。人心中有了莽的信念,便融入了一份担当。
《宁夏川好地方》是二胡演奏家周维先生2014年以宁夏民歌音调花儿为基调创作的一首二胡曲。乐曲描绘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阔秀丽,传唱出了当代华夏儿女的积极向上,朝气蓬勃之心。
乐曲开场的引子,就像是一位朴实无华的西北汉子高唱山歌号子,来赞颂自由自在的山里生活。同时,这好听的大山之声也仿佛展开了一幅西北风土人情的画卷。乐曲第一段旋律平稳而舒缓,大段憨厚朴实的旋律中其实包裹着一颗炽热而细腻的心,用偶尔点缀对比的手法来衬托乐曲憨厚纯粹的性格。主线条以饱满的运弓来完成,在衔接处不经意间透出弱起音和几起几落带出长音的委婉和羞涩。乐曲第二段是欢乐的生活场景,描绘了人们干劲十足的状态,充满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此时的音乐在粗线条中加入抹压滑音与短吟揉弦的结合,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场景中,恰到好处地点缀出西北人的性格,用生动活泼的音乐形象描绘出中国西北的山川大地、风土人情和家长里短。乐曲的末段在经过了几个乐段后,回到再现部分,升华出莽莽若山之巍峨的大写意情景之中,此时的每一弓,每个音符都更加开阔。用时间放大手法,将运弓气息拉宽,呈现出历经沧海桑田,再回首已能容纳万千的莽莽意向。
(六)中国音乐八意象中的“凄” ——《江河水》
凄美,是从悲情之中绽放出来的美。欢乐的作品能让人获得轻松愉快,但要让作品内涵更加深刻,则多数都需要具有悲情的元素。跟开心相比,悲情色彩更能激发人去深刻地思考生命中的问题。《江河水》就是这样满是凄情的乐曲,这首曲子是二胡演奏家、作曲家黄海怀先生移植创作的一首二胡传世经典。
乐曲讲述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恩爱夫妻,新婚不久,丈夫就被官府抓去外地做劳役。妻子不舍,江边相送,一对新人洒泪分别。不曾想这一别竟成了诀别,很快便传来了丈夫在劳役中客死他乡的消息,一对伉俪从此阴阳两隔,再无相见。妻子闻讯悲痛欲绝,跌坐在那条曾经数里相送,同丈夫分别的江水边失声痛哭。
乐曲《江河水》开头便是低声的抽泣和叹息,在凌厉的音头后,乐句呈现出一种无力和有力相映的起伏,就像女主人公的内心一样,难以平静。在一阵哭泣之中,她疲倦了,音乐的旋律里仿佛是女主人公在睡梦中回忆起了两人当初的日子。心中满是甜蜜的小两口,夫唱妇随充满幸福。朦胧中妻子从睡梦中醒来,她惊醒后想起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一切美好只是一场梦中的记忆罢了。如此残酷的现实让妻子陷入了惊恐之中。她呼喊着、奔跑着、尖叫着、痛哭着,这一乐段在一片惊恐中回荡,最后她终于用尽了力气,音乐在微弱的旋律中结束。但这个柔弱女子今后的命运该怎样呢?留下对主人公命运的担忧。
情到凄处,已经没有语言能够再去表达什么了,只剩那种滋味回荡空中。艺术中的凄其实是一种美,艺术中的丑也是一种美。就好比法国文学家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作者将生活中外表丑陋、地位低下的敲钟人,转化为艺术上的一种美。这种艺术化对美丑的表达是人类共通的审美语言。①
(七)中国音乐八意象中的“浑”—— 《秦风》
浑之美是一种敦厚质朴之美。浑是天地的起源。《幼学琼林》中写道:“浑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②这里的“混”“浑”互为通假字。
《秦风》是二胡演奏家、作曲家金伟先生创作的二胡曲,也是众多秦派二胡曲之中的上乘佳作之一。乐曲中音乐具有浓郁的陕西民间音乐风格,反映了秦地人们的音乐审美和性格,同时展现了当代陕西地方的音乐韵致,也是先秦时代中国民风乐律的文化艺术传承。乐曲在二胡标准音的定弦基础上降低了大二度定音,使音色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变得更加浑厚沉稳。在演奏技法上,根据陕西民族音调的风格,也进行了压滑揉以及反向滑音等技术处理,在陕西方言同民间音调、戏曲等充分融合的基础上,表现出秦地音乐的鲜明性格。
(八)中国音乐八意象中的“采”—— 《空山鸟语》
二胡音乐意象中的“采”,是富有活力、神采飞扬的意思,是天地精华外化出来生命的神韵和光华。
《空山鸟语》是国乐大师刘天华先生所创作十大二胡名曲之一。乐曲的创作初稿源于1918年。但直到1928年,才真正定稿完成,并公开出版发表。《空山鸟语》的曲名来源于唐代诗人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③诗中大自然秀丽风采的意境让刘天华先生心生灵感,想到何不反其意将诗中“人语”二字换为“鸟语”,将“响”字换为“声”字,并以《空山鸟语》作为乐曲的标题。
《空山鸟语》一曲中点出了两个主要的音乐形象,其一是空山,其二是鸟語。从空山幽谷,鸟语交映的灵秀山光中表现出一幅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的诗情画意之景。空山的声响是回声空荡的效果,在演奏中运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来表现山谷的远近浓淡,让声响在山谷中呼应,实音饱满洪亮,回音则微弱悠远。鸟语则二胡的用点、按、压、滑等手法,来表现鸟之间跳、跃、飞、落、荡、鸣、啄、扇的各种自然形态。
这首曲子中还有一些十分别致有趣的技法,如同音指的运用,就是以无名指、中指和食指三个手指在交替中快速依次滑按出同一个音位,从而产生类似琵琶轮指技巧的点状效果。再加上轻重缓急的力度变化,在音乐形象上给人以珠落玉盘,鸟鸣不绝回响的感觉。
笔者记得年少时初见《空山鸟语》曲谱,觉得满纸都是技术和音符,又难学又不中听。到大学再演奏此曲时,感觉简单,但却肤浅而无趣。随着人生的积累,慢慢地开始对艺术有了一些理解,如今再见《空山鸟语》,可感受到神游在川谷飞鸟之间,进入那种忘我的空山无人之境,雅趣灵韵、神采无限。
结 语
音乐作为直达灵魂的听觉艺术,是一种高级的智慧。能够感知听觉审美的人,要具有更加敏锐和清明的感知力,它超越了知识的层面,进入思想和智慧的意境。中国音乐审美观是在审美的角度上与中国哲学思想的一种深刻融合,而文人音乐思维也推动形成了中国音乐审美观的主要形态。通过二胡经典音乐作品提炼出清、坚、逸、健、莽、凄、浑、采八种具有中国音乐写意文化思维的意向,以含蓄而古典的音乐方式来抒发对这八种意向美的认知,希望通过这一视角传递出人生苦辣酸甜承载的爱与美。音乐艺术是感知宇宙万物和人生大爱、大美的绝佳路径,音乐可以直达大脑皮层,更能触碰心灵。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和谐的基础是完美的数的比例,音乐与宇宙天体存在类似。音乐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宇宙运行的规律。” ①站在中国文化来看,音乐、美术抑或是文学、历史和哲学都是人灵魂、思想和情感外化连接天地时空的文化表达,体现出作为每个个体以及不同文化生命群体对哲学精神的诠释。用觉知力去观察和感受生命,去爱和聆听,是完成从肉体到灵魂;从外在向内在的文化升华。中国音乐以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视角诠释出了具有东方魅力的独特音乐审美观,将中国民族音乐艺术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在深入传承的基础上进行挖掘、思考和梳理。
以二胡经典作品中的审美意为基础进行研究,对中国音乐审美观的阐述,不仅仅是针对二胡音乐文化的美学逻辑,更是对整个中国音乐文化的一次思考。
本篇责任编辑 李姝
收稿日期:2023-01-04
基金项目:2021—2023年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基于OBE理念与PDCA方法的音乐表演专业特色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JG2021-1181)。
作者简介:张国亮(1979— ),男,硕士,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讲师(四川成都 610021)。
- 音乐探索的其它文章
- 川南合江汉画像石乐舞图像考A STYDY ON THE STONE CARVINGS OF MUSICAL DANCE OF THE HAN DYNASTY IN SOUTHERN SICHUAN HEJIANG COUNTY
- 论清代湖北礼俗音乐文化的社会属性The Social Attribute of the Musical Culture of Etiquette and Custom in Hubei in the Qing Dynasty
- 北朝时期贵族阶层的乐舞生产与消费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USICAL DANCE AMONG ARISTOCRAT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 游于城:宋代成都城市音乐略考THE CITY MUSIC OF CHENGDU IN THE SONG DYNASTY
- 文献记载与现实关照Documentation and Reality: The Stories of Performance in Ancient Chinese Music Documents
- 铜磬考述A STUDY ON BRONZE CH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