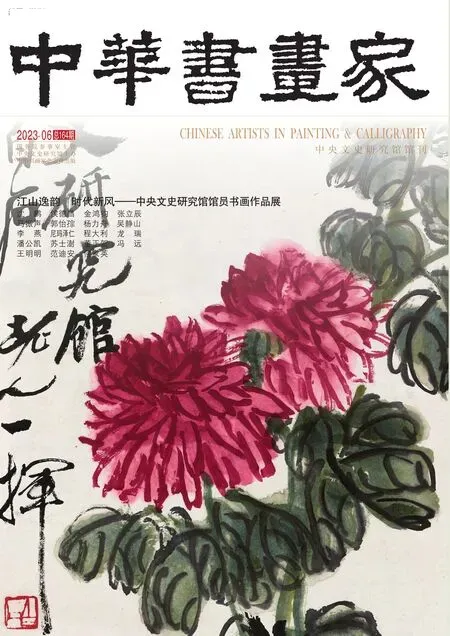书法,在比较中索解(节选)
□ 沈 鹏
我国传统艺术崇尚“言有尽而意无穷”。傅毅《舞赋》:“歌以咏言,舞以尽意。”舞比歌相对而言是“尽意”了。可是再往下看:“修仪操以显志兮,驰思乎杳冥。”显然“尽意”又是相对的,“驰思乎杳冥”才是高境界。舞蹈与别的艺术一样,仍以“不尽意”为上乘。

沈鹏连续六届担任“国家图书奖”评委、副主委,图为沈鹏(前坐者)在评审现场

2002年9月,沈鹏在“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颁奖大会”上讲话

2005年,沈鹏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谈中国书法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006年4月,沈鹏(前排站立者)出席“沈鹏先生诗词研讨会”

沈鹏诗稿
以言志为特长的诗,重在抒情,抒情又贵乎“言有尽而意无穷”。“意”重于“言”,形象大于思维,是普遍规律。诗词的虚写比实写更可贵,“虚”不脱离“实”,但“实”如果没有了“虚”,诗词便不能超越较少字数的局限以扩大境界。人们熟知的像“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李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无不在实中求虚,以虚带实,以有限之言抒写无尽之意。
书法也十分讲究虚实相生。虚比实更可贵。蒋和谓:“大抵实处之妙,皆因虚处而生。”笪重光谓“匡廓之白,手布均齐;散乱之白,眼布匀称”,认为“眼”重于“手”,“散乱”高于“匡廓”,美学境界不在同一个起点上。在书法作品中,虚实境界与黑白分布有密切关系。书法少不了黑白,问题在善于分布,而黑白的分布不以“均齐”为美,“均齐”只能产生“状如算子”的效果。至于“匀称”,按笪重光的意思,当与“散乱”相称,“散乱”非一团乱麻,是统一中的变化。如此,各类书体中最有条件体现虚实相生者莫过于草字了。但虚实黑白的基本规律,在篆、隶、楷各体中也同样体现。王献之楷书《洛神赋十三行》,妙在空间布白的风神萧散,疏远淡泊,我们未尝不可以当草书看。而草书中之劣者,被讥为春蚓秋蛇,连绵游丝,收放无度,疏密失体……看来,对草书的批评正如对草书的赞扬一样多于其他各种书体。
虚实、黑白分布,由逐字逐行到整篇,整篇效果是最重要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在书法则为“字有尽而意无穷”,以有限的空间给人无穷的联想,超出了作品的局限性。书法的联想还可以扩大到时间,读者设身处地想见书写者挥毫之际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空间分布与时间运行同步进行。有两句经典的名言:“诗言志”(《尚书》),“书,心画也”(《扬子法言》),古人用最精练的语言指明了诗与书的本质。扬雄在“书,心画也”前面有一段话:“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昏昏,传千里之态态者,莫如书。”此处的“书”显然指文字,后来者乐于将它包括书法,或者索性认定“书,心画也”的“书”即指书法,原因大概不但因为文字的工具作用一开始就与书法同时存在,所以“书”涵盖了书法;而以“心画”概括书法艺术,实在太精粹、太准确不过了。诗与书,一个言“志”,一个“心”画,在表达思想、意志、情感的根本点上,达到了一致。在诗为虚实者,在书法出于黑白分布。虚实不能没有黑白,但并非所有的黑白都能达到虚实相生的效果,虚实是一种美学境界,进入美学境界的黑白才是真正的黑白。

沈鹏 题林散之致高二适诗卷 纸本 2015年释文:适我之所适,之吾所欲之。二老砺文艺,双峰一扶持。得意洛下纸,问道山阴诗。识见人天合,肝胆义理齐。高山与流水,伯牙共子期。西窗秉烛夜,夜雨涨秋池。哲人其未远,斯文永在斯。吴为山君珍藏林散之致高二适诗十八首,事涉今古,情系八方,洋洋纚纚,目不暇给。二位前贤雅谊之真切今世尤稀。爰得五言七韵以志敬仰。乙未立夏,后学沈鹏于介居。钤印:沈鹏(白)介居主(朱)金铁烟云(朱)

沈鹏 《九一》诗 纸本 2022年释文:九九归于一,生年终有极。日月巡地天,万事周期率。功利弃敝屣,贪婪愧造物。宇宙囊心胸,良知脱胎骨。壬寅秋作《九一》诗。沈鹏。钤印:沈鹏(白)介居主(朱)春华秋实(朱)

沈鹏 忆秦娥·二零一五年九月三日纪念大典 纸本 2015年释文:忆秦娥·二零一五年九月三日纪念大典。长风激,碧天如洗雄鹰击。雄鹰击,彩虹飞画,啸呼鸣镝。河山重建光阴急,长龙方阵东方立。东方立,高翔白鸽,梦圆和璧。乙未,沈鹏词并书。钤印:沈鹏(白)春华秋实(朱)
再从诗、书深层寻找两者共同点,就该提到“节奏”了。诗的语句,以节奏为结构,在节奏中运动。常见的五字句、七字句,分为二/三、四/三,吟诵的时候按平仄、诗韵,发出和缓、急促的语音,五字句为二/二/一,七字句为二/二/二/一。朱光潜先生以“的当、嗤当、嗤当、晃”徽调中的锣,说明节奏与韵(见《诗论》第一章)。节奏是至关重要的,有了节奏,诗的形式才有生命。节奏的重要性不亚于平仄、音韵。有写得好的新诗,不讲平仄,不押韵,依靠节奏注入生气。
节奏之于自然界,于人本身,无所不在。节奏与和谐几乎是合而为一的美学概念。节奏营造和谐,和谐依靠节奏,但都不是单调一律。优美的节奏与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所谓“和而不同”,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由变化达到统一。书法艺术的美,也深藏在节奏之中。“一波”为什么要“三折”?“三折”就含有变化着的节奏。“波”说的是捺笔,其实书法的各种笔法包括一点、一画,都内含“三折”,“三”是常数,也无妨是变数,书法的一笔中可以有数不清的“折”。
书法作品由一笔开始就有节奏,由一笔到一字、一行、一篇,节奏在展开、丰富。长卷如怀素《自叙帖》,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像时间中行进的交响乐,浩荡跌宕,前后呼应,高潮迭起,有极丰富的变化。书法家完全按照自己的美学观念,以书法自身的规律运行无阻。
书法与诗,最深层的美虽可以归到节奏,但书法家写诗却不与诗的节奏同步。这一点说起来有点儿“煞风景”,然而理论与实践证明为必然。我们从黄庭坚的《李白忆旧游诗》《花气熏人诗》《经伏波神祠诗》的书法艺术中不但不能找到与诗的内容的“一致性”,并且也不可能找到诗书节奏的“一致性”。诗的节奏与书法的节奏独立存在,各自发挥特有的美则合为完璧。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回忆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吟诵诗文,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微笑着”“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都是对诗的激赏,是对节奏感的体验。然而书法家对诗的激赏,并不直接将诗的节奏融进书法,书法节奏因书法自身特点形成。
照这么说,书法家多读点儿诗,或自己作诗,是不是有益于书法呢?好的书法肯定与诗意相通。海德格尔说过一切艺术品都具有诗的特点。一个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未必是诗人,但作品会含有诗意——诗的深邃的意境,丰富的情感,简练的语言,有韵律的节奏……一句话,诗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说某个不写诗的作家堪称诗人。对书法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书法家笔下的线条,一任自然,流露出来的情感、意境、黑白、节律,都与诗相通,与诗共鸣。我们不能要求书法家读了点儿诗便立即有益于书法创作,但是当书法家的阅读出以真诚的而不是漠然的,深情的而不是肤浅的,并且较好地理解诗的本质特征,那就肯定会对书法创作产生有益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越是无意于“直接”从诗里受益,越能获得更多的益处。因为诗的感人在于“言志”,诗的节奏、韵律从深层影响书法家的素质,所谓“潜移默化”。像“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我们从中体悟人生,游乐人生,却不能获得知识。为了理解诗的背景,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贺知章、程颐的经历以及他们写诗的时代。而要理解杜甫的“三吏三别”、《秋兴八首》,更要懂得历史,也不能不懂得诗里的典故。读诗不能不依仗知识,但归根结底诗给人的还是言志。叙事诗虽然要叙事,却仍旧是诗。
书法艺术同样不能给人知识。书法纯粹抛开知识内容。汉斯立克在《论音乐的美》一书中的著名论点“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用来解释书法非常恰当。“乐音”作为音乐最基本的元素,在书法以“线”的形式出现,都从生活中提炼出来,规范化、美化。在音乐为乐音的运动,在书法则为线的运动。还是汉斯立克说的:“这些乐音的行列和形式除了它们本身之外别无其他内容。”
书法就这样以自身的特殊性进入艺术行列。书法是不是一种文化?当然是。但重要的是界定它在文化中的坐标,研究它以何等“身份”如何进入文化范畴。书法之所以成为文化现象,不是因为文字传达的内容。甲骨文的卜辞,使我们了解大量殷商历史;石鼓文,提供秦国君游猎的情况;每件魏晋墓碑,都诉说一段故实……人类文明的历史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字作为工具的作用是书法不可比拟的。但当我们研究书法的时候,必得把文字作为工具的功能放在一边,把书法当作一门独立的艺术,不然无法深入到本质。书法的历史,就其本质来说,应是书法风格的发展史,是由书法艺术纯粹性所决定的。
笼统地说书法属于文化,是容易的。书法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只因它是艺术,不然便失去了书法自身的存在。肯定这一点,对于我们确立书法发展、提高的方向,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把书法艺术在文化中定位,肯定它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不因其特殊性而超越一般性,也不因强调其重要性而违反科学性。有一种说法值得商榷,即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我疑心这个命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出自对书法的挚爱乃至偏爱。欣赏艺术不排除偏爱,各门艺术有特殊的爱好者。艺术的偏爱甚至促进艺术的多元与繁荣。然而我们不能在情感因素与科学论证之间画上等号。我重新阅读熊秉明先生的《书法和中国文化》,论证的出发点是“一个文化的核心是哲学”,然而“中国传统哲学家的终极目的不在于建造一个庞大精严的思想系统,而在于思维的省悟贯通之后,返回到实践生活之中”。熊先生把中西哲学的思维方式作了一个对比,从艺术与哲学的双向思考,说出通过书法可以“研究个人心理,了解个人的心灵”,“通过书法研究集体心理,了解民族性和文化精神”。熊先生有不少颖悟给人启发。使人不解的是,熊先生突然(恕我看来如此)超越许多中间环节,并且没有考虑到各门艺术都以其特殊性跻入广大的艺术之林,便提出了:
抽象思维落实到具体生活的第一境乃是书。如果哲学是“高处不胜寒”的峰顶,则书法是可以游憩流连的园地,所以可以说是文化核心的核心。
既然哲学是文化的“前提”,书法又是“文化核心的核心”,那么书法必然又推向了哲学的“核心”?要说书法内含哲学思想,哲学思想启示书法,当然不错,正如各门艺术都可以上推到哲学。在众多的艺术门类(特别是造型艺术)中,书法以它的抽象性,甚至可以给其他艺术更多的启发,林语堂在《中国人·艺术生活》中曾说过:“在我看来,书法代表了韵律和构造最为抽象的原则,它与绘画的关系,恰如纯数学与工程学或天文学的关系。欣赏中国书法,是全然不顾其字面含义的,人们仅仅欣赏它的线条和构造。”依我看,书法说到底是一门艺术,它并不因其特殊性而高于其他艺术或凌驾于其他艺术之上。在这一点上可能同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类似。
书法依赖文字,文字为传播文明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中,文字的书写与书法的传播从现象上看几乎是二而一的事情,会不会因为如此难分难解,我们产生错觉,把书法在文化中的位置夸张到不适当的地位呢?会不会因为我们情感上偏爱书法而忽略了理性思考呢?好在熊先生自己也曾怀疑他是否有“故作夸张”,我们的目的在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探讨问题,使认识接近真理。

沈鹏 兔毫国事七言联 纸本 2023年释文:兔毫落墨三江水;国事开春八阵图。兔农历癸卯,公元二零二三年,沈鹏撰并书。钤印:沈鹏(白)介居主(朱)春华秋实(朱)

沈鹏 景山古槐 纸本 2015年释文:古槐毁去易新槐,随处移来随意栽。苦嘱后人常记取,乔装陈迹隐疑猜。欲云真假真痴绝,不识存亡存劫灰。今日新枝苍翠滴,槐花应记几回开!景山古槐三首之三。沈鹏。钤印:沈鹏(白)春华秋实(朱)馀(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