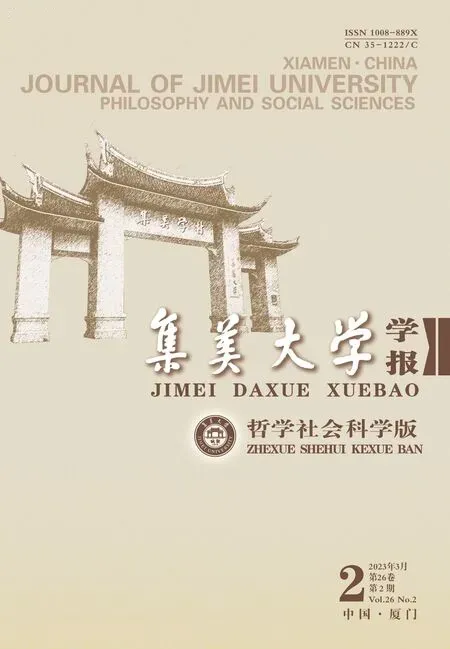琴、士之和
——高罗佩琴学研究的文化认知观
蔡锦芳,葛桂录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字笑忘,号芝台,荷兰职业外交官。他“一生任外交官,一生著作”[1]55,以研究中国书法、篆刻、琴学、绘画、收藏、佛学、性文化等多个领域为中国学者熟知。他践行着中国传统文人雅士诗酒风流、琴棋书画的生活方式:其所调任之处,皆为书室起雅名,并刻章记之;他在厅内设几席,上置“无名”古琴一张。斑驳的漆面暗示着琴随它的外交官主人,几经调任,几经易所。高罗佩闲时操缦,同步开展深入的琴学研究,所著《琴道:论琴学思想》(TheLoreoftheChineseLute:AnEssayontheIdeologyoftheCh’in,以下简称《琴道》),旁征博引,对中国古代琴学典籍加以翻译整理,随附中文原文。因之,这部代表性的英文学术研究著作,可视作他对中国古琴及士人阶层的体认。1943年,高罗佩调任战时重庆。彼时山城学术大家、社会名流荟萃,高罗佩与之相往来,一同成立天风琴社,诗酒唱和,践行士人生活方式及精神理念。在以《琴道》为代表的古琴研究、纠合同道结天风琴社于渝都等古琴艺术实践中,高罗佩逐渐形成自身的审美意趣。他将古琴视为中国传统书斋必不可少之器,古琴逐渐从其音乐属性中脱离出来,成为文人生活的象征。
《琴道》的写作及天风琴社的成立,凝结了高罗佩对以古琴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认知,成为探究高罗佩士人精神追寻的线索。
一、明制“无名”琴与《琴道》创作:以古琴为士人身份的象征
1936年9月,高罗佩在任荷兰驻日本公使馆助理翻译期间,出差前往北京。这次旅行使他真正接触到中国古琴,从京师琴家叶诗梦习琴1月。待返东京,高罗佩“买了一支定音笛,请人制作一张专用古琴台,练习弹奏他新买的漂亮旧古琴,并且也开始在东京找中国古琴大师学习”[2]53。这张“新买的漂亮旧古琴”为明代琴,正是他北京之旅购得。据高罗佩《琴道》所附关于此琴正、反面的两幅黑白插图可知:该琴为仲尼式,用于系弦的雁足或为木制。琴池上方刻“无名”二字琴名,池下方刻细边粗笔方印,隶书“集义斋记”四字。“集义斋”正是高罗佩在东京就任期间为自己的书房起的名字[2]68。结合《琴道·后序》以及所钤印章名,可以判断高罗佩收藏的这张明制琴,底板上原无任何铭刻印记。
操缦之余,高罗佩留心琴学古籍,于故纸堆里遍寻原典材料,所得资料除了中国典籍(自商代始),也不乏日本、法国相关的中国古琴著述。在对这些资料进行英译整理后,高罗佩写就《琴道》一书,于1940年交付日本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琴道》共7卷,前附英文、文言序文各一篇,亦高罗佩自书。全书围绕古琴乐器所包融的思想体系展开,首先表现在高罗佩对于关键词“琴”的英译上。作者以“lute”译“琴”,在其“自序”中,将英译过程中的取舍、与其他学者的讨论一并示之读者。他认为,外部形态(the outer form)及文化指涉(cultural reference)的对等是英译“琴”时首先要考虑的标准。鉴于古琴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的独特地位,对后者的观照尤为关键。“lute”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自古就与富于艺术气息(artistic)、雅致(refined)、为诗人所歌颂(sung by poets)的事物联系在一起[3]viii,因此选用该词。然而,高罗佩这个观点曾引起争议。美籍德国音乐家萨克斯(Curt Sachs)致信高罗佩,指出这种译法的不当(incorrect)之处在于容易造成西方读者对古琴外形的误解[3]ix。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同样对“lute”一词在西方语境中唤起的图式能否代表中国古琴存疑[4]302-303。古琴的外部形态的确有别于西方的鲁特琴(lute)——鲁特琴是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欧洲使用的古乐器总称,却是曲颈拨弦乐器。而古琴形制的规定由来已久,如《五知斋琴谱·上古琴论》曰:“琴制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年岁之三百六十五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有上下,象天地之气相呼吸也。”(1)转引自:王建欣:《五知斋琴谱》四曲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2:5.这一论说足见古琴外观之精致,形制之考究。且不论高罗佩综合诸说而自有识断,坚持用“lute”一词,是否有失偏颇,其重文化指涉,轻外形构造,实为向西方读者着力推介古琴这一代表士人身份、包融中国文化意蕴的乐器。
高罗佩对古琴文化指涉的倚重同时体现在《琴道》文言序文上。文中借《礼记·乐论》“乐由中出”,论证古琴音乐符合老子“去彼取此”言,认为作为“众乐之首”的古琴,是“古之君子”向内心回溯以反观自身、用器物体认生命本真的方式。高罗佩对古琴“尊生外物养其内”的论述,大有明代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文人雅士玩物尊生的主张意味。高濂论琴,多是对琴器形制的品赏[5]12;而高罗佩论琴,除了技术材料、指法曲谱的基本介绍,更多的是对古琴所包融的琴学思想的探讨,即以古琴为媒介而指向中国传统士人理想人格、精神特质的构建。
高罗佩首先界定了中国“文人”(the literatus)的范畴,称该群体为官员(official)、诗人(poet)、画家(painter)和哲学家(philosopher)的结合体[3]vii。“literatus”大意是“知识分子”,与高罗佩的定义不尽相同,显然,他还将“官员”身份囊括在内。不难发现,高罗佩所刻画古琴象征的身份群体与中国的“士人”阶层相近。许慎《说文解字》对“士”的界定为:
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段玉裁注曰:
《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推十合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惟以求其至是也。若一以贯之。则圣人之极致矣[6]20。
以上对“士”有两个层面的界定:(1)以“事”训“士”,但对于所做具体之事,没有进一步框定。则“事”可以关乎一切之事。仅从事仍不足以称之为“士”。对于所做之事,还应化繁为简,由博返约,综万理于一源,形成事物的普遍规律。(2)提出了对“士”的人格素养要求,即:勤思考、辨是非、格物致知、力学求进。余英时认为,东汉中叶以后,多数士大夫个人生活之优闲,又使彼等能逐渐减淡其对政治之兴趣与大群体之意识,转求自我内在人生之享受、文学之独立、音乐之修养、自然之欣赏,与书法之美化遂得平流并进,成为寄托性情之所在[7]349。此论断表明:历史形塑之下的士大夫群体,仍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社会舆论的制造者。同时,他们以文学、音乐、自然、书法等为理想士人人格表征,寄情于物,以物修身。高罗佩正是以“传统的中国式学者型官员”为理想,“但他意识到自己还缺乏这种官员的本质特征,弹奏中国的七弦古琴是这些特征之一”[2]51。高罗佩以古琴为士人身份的象征,则习琴、从事琴学相关研究,自然成为他追寻士人生命状态的重要步骤。
为建立古琴音乐与士人崇高精神追求的直接联系,高罗佩旁征博引,称“在中国传统中”独奏古琴乃“圣王之器”(Instrument of the Holy Kings),其音乐为“太古遗音”(Tones bequeathed by High Antiquity)。另外,他借法国传教士钱德明观点论证道:“圣人(sages)方可抚琴。常人屏息凝神,以至高的敬意凝视着古琴,便是莫大的满足。”[3]3(2)高罗佩《琴道》中,高氏中文自译部分为直接引用。此外,本研究对高罗佩著作和其他英文著作引文的中译均出自笔者。引文中,“Special”“Privileged”“sages”等词无一不彰显着古琴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此段论据是高罗佩对古琴所持的态度,虽然对于“圣人”没有给出进一步阐释,但对琴人人格、道德层面的苛求可见一斑。
可见,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由宗法关系生发出的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秩位的划分(士人阶层),以及对文化雅俗有别的判断(琴乐为雅乐),高罗佩是深切认同且极力维护的。二者结合,共同塑造了高罗佩对古琴(雅文化)是文人阶层(等级秩序)特殊乐器的认知。
二、天风琴社成立:士人生活理念的践行
1941年,太平洋战起,高罗佩匆促离开了日本。在东非短暂任职后,高罗佩被荷兰外交部任命为驻重庆大使馆一等秘书。他在日记中记录道:“在1943年3月15日,我登上了飞机,它将越过喜马拉雅山把我送回中国。”[2]981937年的重庆机关团体荟萃,文艺界、美术界、音乐界相继成立抗敌协会,发扬国粹,复兴民族,以期国家巩固。至20世纪40年代,高罗佩入渝时,山城已然充满了艺术的空气。
此时文学、绘画、音乐作品喷涌,学术大家及社会名流齐聚山城,高罗佩更是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之中,古琴自然是高罗佩中国艺术实践的主要代表。1943年8月9日,高罗佩、张宗和等人一同到琴人查阜西家做客,“人到的差不多了,于是查阜西先介绍一阵高博士,然后大家表演古琴,先是高洋人《梅花三弄》”[8]161。“抗战在重庆……三日后还是演了《游园惊梦》,善芗的春香,项馨吾的柳梦梅,我的杜丽娘,开场是荷兰高罗佩的古琴独奏”[9]365。高罗佩的自传稿也多有与中国文人切磋琴艺的记录,“1945年2月9日:与杨少五和石绍夫老先生一起弹奏古琴和琵琶。吃了晚餐,聊天,弹奏音乐”。“2月23日:在康先生家里与中国艺人跳舞,弹奏古琴”[2]116。对在渝这段琴乐唱和的岁月,高罗佩总结道:
在重庆度过的岁月,对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具有了不可估量的价值:来自中国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优秀学者和艺术家都聚集在这里……我加入了几个文学协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天风琴社”,在那儿我遇到了很多于右任那样的知名学者和像“信仰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那样的很有趣的人物。我们与四川本地的“富裕阶层”保持了密切联系,在没有日本飞机来袭击时,我们在那些富人的郊外别墅里度过美好的周末。我现在首次完全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2]98-99。
论及这时期加入的诸多文学协会,高罗佩特意指出天风琴社。此琴社组织为高罗佩在渝操缦、交谈,开展古琴雅集、以琴会友提供了契机。
随着大批著名琴家自北京、上海等地相继进入川蜀一带,如查阜西、胡盈堂、管平湖、徐元白、杨荫浏、梁在平、徐文镜、徐之荪、黄鞠生等[10]114,“一时重庆琴艺活跃,推动了琴艺的发展,这时琴人达三十多人,是近几十年来最多的了”[10]127。各方琴家的广泛交流将重庆古琴文化氛围推向高潮。至此,天风琴社这样一个以琴会友、联合在渝琴家共同推广古琴文化的琴社组织应运而生。“四川本地的‘富裕阶层’”指的是杨氏家族,重庆富商、古琴家杨少五。他继承家学,经商之余,痴迷古琴。“富人的郊外别墅”是位于重庆江北杨家花园(今龙湖花园小区一带)的杨少五住宅。除杨氏家族,高罗佩提及的其他琴社成员包括:于右任、冯玉祥。结社成员身份除琴家外,不乏当时政界、军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此成员组合,与高罗佩心向往之的士人群体相伴唱和的生活场景相契合。
“天风”一名的由来,现存多种说法,大致归结为两类:一类称其名沿用自杨少五家宅产业原有的名称,包括“天顺祥”钱庄、“清白家风”宅、“天风”书斋[11]31-32;另一说谓或出自《周易》六十四卦之姤卦。《易传》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据此,这个名称包含了烽火岁月,在渝琴家们对和平正义与祖国繁荣强大的期望。同时,“天风”又可以形容空灵、悠远、清扬的天外风声,带有一丝丝神秘肃穆[12]19-20。彼时,防空洞外战火轰鸣,院落里琴音激越高亢。这或是对烽火岁月里,这一批因战争离乡入渝,援琴而歌,将琴代语,以琴音抗争日本侵略者的琴家、官员的浪漫解读。
中国学者、外交家陈之迈曾与高罗佩共事,论交颇笃。陈氏所作的3篇中英文长文:《荷兰高罗佩》、《杰出的汉学家》(SinologueExtraordinaire)、《忆高罗佩》(RobertHansvanGulik:InMemoriam),被视作记录高罗佩生平最为详尽的资料。陈之迈回忆道:“在战时重庆,高罗佩博士曾多次在观众满席的演奏厅弹琴筹赈。这是他为中国抗战所做的贡献。就这点而言,(古琴)音乐成了他外交活动的一部分。”[1]32在当时的形势下,报刊杂志振臂高呼:“全民族艺术的笔要一致为这被残酷侵略的现实生活而描绘。”[13]14余英时认为中国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性格类似,他们不仅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更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7]2。高罗佩与在渝琴家、官员几度会琴。弦音与炮火齐鸣,轻重缓急,交替绰注间,除了引为同道知音的相惜,亦有弦歌不辍一致向敌的决心。
天风琴社的结社雅集大致就是高罗佩心中理想生活的描摹,对集官员、学者于一身的士人的定义是他在重庆接触到的琴家的概括。
三、文化认知观:以士人精神的追求为古琴音乐活动的旨归
高罗佩对士人群体形象最初的认知,或许直接来源于以其古琴蒙师叶诗梦为代表的琴人。他曾称叶诗梦是保留中国旧时文人最崇高传统的典范。以古琴为人生趣尚,以恩师的人格高致为琴人的精神气质要求,高罗佩的琴士形象逐渐生成。
(一)作为文玩清赏的古琴——士人玩物尊生的审美意趣
中国文人雅士自古就有搜集书法画帖、窑玉骨玩的习惯。这些文玩器物不仅有怡养心神的功用,还言说着主人的审美意趣。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古琴也常被视为文玩清赏,或悬于壁上,或置于几案间。陶渊明有“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语,高濂称“清音居士谈古,若无古琴,新琴亦须壁悬一床。无论能操,总不善操,亦当有琴”[14]630,都论说了古人于器物间发现乐趣,将生命之灵气映照世间之物的生活情趣。高罗佩在日本任职期间便践行了士人这种收藏器物以供闲时把玩的生活方式。他以书画古董布置书斋及厅堂,将北京购得的明制琴陈设在厅内,“油漆已剥落不堪,但仍可奏出高山流水之音,置诸几席,古色古香。他收有许多名瓷的碎片,仍不失为粉定龙泉。北平故宫的琉璃瓦,曲阜孔庙的砖石,都是骨董,正堪赏玩”[1]41-42。
《琴道》中多处对书斋的描写,也体现了高罗佩对这种审美意趣的着意渲染。比如,高罗佩详细刻画了中国传统文人书斋的固定范式,“历史上,对于书斋的固定传统已经形成,它细致入微地描摹了文人应时刻置于手边的物品:桌案上应该有一方砚台,一只毛笔(置于特制的笔架上),一只花瓶(瓶内的花一定是精心挑选插好的)……一张小案几上应置一个棋盘,另一张设香炉。书房四个角落必是书架,空白的墙上,悬有书画卷轴。在一个干爽、远离窗户且无阳光直射的角落,则要放置至少一张或几张古琴”[3]17。当古琴成了士人书斋文玩清赏之物[3]18,它也就逐渐从其音乐属性中脱离出来,成为文人生活的象征。
将这种生活方式内化为个人的观物态度,由器及道,高罗佩发出如下感叹:
茅斋萧然、值清风拂幌、朗月临轩、更深人静、万籁希声、浏览黄卷、闲鼓绿绮、写山水于寸心、敛宇宙于容膝、恬然忘百虑、岂必虞山目耕、云林清閟、荫长松、对白鹤、乃为自适哉、藏琴非必佳、弹曲非必多、手应乎心、斯为贵矣[3]xiii。
这段文言序言体现了高罗佩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寥寥数语刻画出士人身居茅斋陋室,犹以琴书自遣的高洁品性,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虽在穷阎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语义相通。此段中,高罗佩对文人雅士书室的描摹,与上段关于书斋固定传统的刻画明显不同。此处为“茅斋”,带有一点野趣,与上段摆放考究的书斋相比,更闲散自由,富有生气,表现了生活的自在闲适。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茅斋二首》中有“时开玉怀卷,或弹珠柱琴”一句,与高罗佩的“浏览黄卷,闲鼓绿绮”意境极为相似。清风明月为伴,胸纳天地万象,高罗佩此处着意表现的已不仅是士人雅致的生活方式,更是精神气度的宣发。高罗佩“弹琴尊生”的思想主张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雅士对清赏文玩所持的思想观念:以物修心,物中生意,乃达物我交感[5]7之境。
(二)古琴恩师叶诗梦——士人人格高致的映照
高罗佩对士人群体形象最初的认知,或许直接来源于以其古琴蒙师叶诗梦为代表的琴人。叶诗梦,字鹤伏,号诗梦居士,自小跟随刘蓉斋、祝桐君等著名琴家习琴,为清末民初北京琴坛耆宿。高罗佩对恩师的推崇景仰溢于言表,尊其为保留中国旧式文人最崇高传统的典范[3]211。
高氏仅从叶诗梦习琴短短1月,叶先生去世后,高罗佩忆之不已。1940年,即叶诗梦去世后3年,高罗佩将初版英文《琴道》题献叶诗梦,称其乃天才之音乐家,伟大之君子,孟子所谓之大丈夫[3]209。入渝后,高罗佩延请叶诗梦弟子汪孟舒、宋绮堂,以及关仲航、查阜西、徐元白、徐文镜等18位琴士题《叶诗梦抚琴遗像》(高罗佩据汪孟舒赠《讣闻》所附诗梦遗照,参考《琴学入门》之抚琴图式自绘)[15]45。其中,汪孟舒所作长跋也表现了高罗佩对恩师的无限景仰与追忆:“芝台学长手写叶诗梦先师遗像,悬诸案右,时望弗替。”(3)高罗佩绘:《叶诗梦抚琴遗像》,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藏。转引自:杨元铮.琴家叶诗梦年谱[J].中国音乐学,2015(2):45-46.
高罗佩《诗梦先生的书法》一文收录了叶诗梦留赠旧诗。诗中“聊将散曲弹流水,敢把长歌和大风”[15]46一句,是这位一生历尽顺逆的琴家风格气度的自我书写。高罗佩尊其师为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一类,想必高氏向往的士人精神,正印证以叶诗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琴人的人格高致。结识叶诗梦后,高罗佩对士人这一群体精神世界的认知或许也有了新的整合与定位。后在重庆与汇聚山城的琴人、学者、书画家、官员、外交家往来,一定程度上丰富、加强了高罗佩对士人理想人格的刻画。天风琴社的成立可谓烽火年代的历史偶然,却是战时重庆的历史必然。“然众乐琴为之首,古之君子,无间隐显,未尝一日废琴,所以尊生外物养其内也”[3]xiii,高罗佩的这个观点,竟遥遥应和了几年以后天风琴社成员的生命状态。生命隐显有常,琴凝结的并非士人对“外物”的流连,而是以琴为媒介,向内观之,以修“其内”的自我探寻。
(三)高罗佩琴士形象生成
1943年至1946年,高罗佩在战时重庆工作,正式融入中国文人圈子,其中国文学艺术成就在与友人的诗书往还中得到彰显。2011年,高罗佩的后人决定将其生前的部分书画藏品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批收藏是这份中荷情缘的历史见证。其中,从几幅中国官员、学者书赠高罗佩的楹联可见,琴在高罗佩形象的文学生成过程中,常被作为重要意象,纳入其中。1943年,王芃生钟贤英夫妇贺高罗佩水世芳婚礼七言联为:“华国芳荷被怀琰,高山流水鼓鸣琴。”王芃生任职东京期间高罗佩曾为其抚奏琴曲《高山流水》,并谓:“贵国琴理渊静,欲抚此操,必心有高山流水,方悟得妙趣”。[8]118江南丝竹大师甘涛亦以楹联相赠,庆贺高罗佩水世芳缔结良缘:“凤凰于飞梧叶秋风喜顾曲,琴瑟协律高山流水缔知音。”两对楹联以“高山流水”“凤凰于飞”“梧叶秋风”等自然意象入诗,同时应和了表现觅得知音之意的古琴名曲(《高山流水》《凤求凰》《梧叶舞秋风》)。除了对新人良缘永结、琴瑟和谐的美好祝愿,高罗佩以琴自遣的形象也得到了深化。
陈其采楷书七言联完整呈现了琴人(高罗佩)左琴右书的形象:“枕边书卷有余味,徽外琴声妙入神。”此联是1945年高罗佩请托陈其采为其书写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的联句,与高罗佩《琴道》序言中“浏览黄卷,闲鼓绿绮”的生命状态相应和。“君子之座,必左琴而右书”,琴的意象反复出现,勾勒出琴人高罗佩琴书论道、相乐终日的诗意生活。
与浙派古琴名家徐文镜渝都一别后,高罗佩曾以一首七律相赠。其中“巴渝旧事君应忆,潭水深情我未忘”[1]41道出两人在渝期间的深厚交情。高罗佩故去,徐文镜在亲斫的“松风寒”(此琴铭自高罗佩)古琴后附诗以记之:“海波澜,天风翻。鹤西还,松风寒。一弹指,千秋看。人间天上,流水高山。”[8]182诗中“天风翻”一句,影射的是结社于烽火年代的天风琴社,“翻”字哀乐低回,“弹指”间,物是人非,表现的是对天风故人的无限追忆;“流水高山”则是琴人之间引为知音同道的经典表达,是对知己的希求和渴慕。忆往昔以琴会友,援琴而聚,如今只有借琴抒怀。古琴缀连起高罗佩与友人诗书往来的始终,成为高罗佩形象的标志性存在。君子之交形诸文字,高罗佩的琴士形象得以传录。
四、结 语
高罗佩的古琴学术著作《琴道》,被视作西方对中国音乐介绍的最佳成果[4]302。高氏梳理古琴在中国历朝发展阶段时,不满于西方写作者将明代士人群体的高雅志趣匆匆带过、对明朝璀璨的文化艺术甚惜笔墨,试图以己之力印证“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璀璨的时期之一”[3]165。且不论这些论断的事实依据,其推动中国音乐文化域外传播的决心之坚一望而知。他的琴学研究是对琴、诗、书、画等中国文化志趣的自然流露,亦是对后起学人以此为起点,重拾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研究的企盼。
高罗佩的写作目的是将研究东方的学者的目光,吸引到一个鲜有人问津的领域上。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认为:高罗佩对包括古琴外译用词取舍的讨论,仅仅是为了抛砖引玉,以便后人从《琴道》出发,深化对中国古琴相关课题的研究。种种文献援引、翻译选词,甚至文化认识上的执着(4)施晔列出三处高罗佩《琴道》的欠缺:一是“琴之英译名”;二是“琴并非高氏所认为的士人专属乐器”;三是“资料搜集的局限性及由此引发的判断失误”。可参阅施晔.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指向高罗佩意欲传递的不仅是“琴声”,更是“琴意”(5)原句为“琴声虽可状,琴意谁可听”,出自欧阳修《江上弹琴》诗。《琴道》前言中,高罗佩所作英文前言引用此句。Van Gulik,Robert Hans,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An essay on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M].Tokyo:Sophia Universtiy,1969:Preface.,即,古琴指向的中国士人阶层的精神风貌。施晔道出高罗佩琴学译事所体现出的脾气禀性,认为他“意欲展现古琴阴阳合意、悠然千古、造化一心的精神品质的坚持浪漫而又固执,实与古代琴士清介孤高、不媚时议的气质暗合”[16]16。士人之审美、精神已内化成为高罗佩个人之识物、决断。高罗佩一生服膺中国文化,以士人的生活理念、审美意趣、人格修养为其人生目标,并将其贯之于现实生活,追求一种“浏览黄卷,闲鼓绿绮,写山水于寸心,敛宇宙于容膝”的闲适超逸境界,而“闲鼓绿绮”[4]则成为达成这一人生境界的重要手段。高罗佩古琴著述中的表达是其琴士形象生成的基础和依据,其中建立起的琴人形象,是高罗佩自我的表达和化身、生命理念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