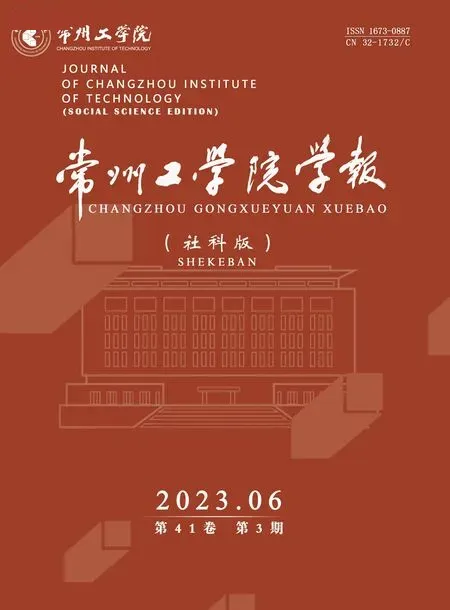洪亮吉西域遣戍诗的边地书写
王高潮,孙文杰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
洪亮吉(1747—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别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清代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今江苏常州市)人,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毗陵七子之一。洪亮吉自幼聪敏好学,4岁即能识七八百字,随后勤奋学习《礼记》《大学》《中庸》《论语》等经典,13岁学作诗,读经史。他虽自幼勤奋读书,但由于种种原因,数十年后才中进士。洪亮吉好直言,“嘉庆三年,大考翰詹,试征邪教疏,亮吉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落职‘免死戍伊犁’”[1],到戍百日左右被赦还。嘉庆帝本来的旨意是斩立决,张珪为其求情才改死刑为流放伊犁。流放期间,他创作了《万里荷戈集》《百日赐环集》等诗集。
一、对天山的书写
洪亮吉弱冠时就曾梦到天山,后来因言获罪,亲赴西域,如此巧合,大大激发了洪亮吉的诗兴,《万里荷戈集》中有诗句“万余里外寻乡郡,三十年前梦玉关”[2]1200(《抵玉门关》),“卅年前记梦中过”[2]1215(《行抵伊犁追忆道中闻见率赋六首》)。洪亮吉在进疆时,经过哈密、巴里坤,在翻越天山时创作了长篇歌行《天山歌》:
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穷冬棱棱朔风裂,雪复包山没山骨。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鸿蒙万年雪。天山之石绿如玉,雪与石光皆染绿。半空石堕冰忽开,对面居然落飞瀑。青松冈头鼠陆梁,一一竞欲餐天光。沿林弱雉飞不起,经月饱啖松花香。……南条北条等闲尔,太乙太室输此奇。君不见奇钟塞外天奚取,风力吹人猛飞举。一峰缺处补一云,人欲出山云不许。[2]1202
洪亮吉此前很少见到雄伟如天山一般的峻岭,天山带给他的震撼无可比拟。这首诗运用了许多宏大的意象,如“日月”“飞瀑”“瀚海”“黄河”“九州”“五岳”等,描绘天山的壮观景象。在艺术手法方面,此诗用了夸张手法,如首句“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写天山山体宽广。日月挂在青松之顶,展现了天山之高。“鸿蒙万年雪”,展现了积雪存在的时间久远,高山之巅的积雪从未融化。天山的绿石似玉,色彩白绿交相辉映,给人一种纯净之感。接着,诗人又写了天山中的动物、气候,松鼠欲餐天光、弱雉饱食松花的香味,想象独特,意象清新别致。山腰充满春季的气息,诗人感慨天山气候的独特。诗人用不需筑造长城来衬托天山之险,由此等雄壮的自然景象联想到古代的仁人志士——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汉代西域都护班超,借此抒发豪情壮志,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诗人把天山与南条荆山、北条荆山、太乙太室等中原的山作对比,凸显了天山的雄奇壮伟。天山风大云厚,“风力吹人”写风势之大,“人欲出山云不许”用拟人的手法展现了云厚重的特点。“末二句确有神韵,的为佳句。洪亮吉感受到了天山的脉搏,天山也给他的诗作增添了豪迈瑰丽的气韵。”[3]322
《下天山口大雪》书写了壮美的雪景、连绵的高峰和吹人的疾风。“鞭梢拂处险接天,风势吹人欲离地。千峰万峰迷所向,意外公然欲相抗。云头直下马亦惊,白玉阑干八千丈。”[2]1202山峰高耸入云,挥动马鞭仿佛要触碰到天穹,狂风几乎要把人吹起来。在云雾缭绕和白雪覆盖中,山峰连绵,稍有不慎人便会迷失方向。云雾也变化莫测,骏马惊起,“白玉阑干八千丈”所展现的景象非常壮阔,丝毫不显得夸张。
七言古诗《松树塘万松歌》写的是东部天山奇景,诗句摘录如下:
千峰万峰同一峰,峰尽削立无蒙茸。千松万松同一松,干悉直上无回容。一峰云青一峰白,青尚笼烟白凝雪。一松梢红一松墨,墨欲成霖赤迎日。无峰无松松必奇,无松无云云必飞。……[2]1203
此诗在用词上最大的特点是数词反复使用,“千、万、一”等数词既切合诗题“万松歌”,又写出松树塘的山峰、松树之奇。“作者对天山青松描摹之生动,想象之阔大,比喻之新奇,语言之流畅,无不臻于佳妙。”[3]322回环往复的手法又在节奏上形成协调、有余韵的诗味,尤其是“无峰无松”一句,写“松、峰、云”相互映衬、互相影响成为奇景,又颇有哲理。景物描写方面,诗人多采用白描手法,如“一峰云青一峰白,青尚笼烟白凝雪”一句写青白色彩交汇在高峰之间。色彩描写方面,诗人使用了红、墨、赤、白、青等色彩词,充满想象力和浪漫色彩,给人一种千峰万松扑面而来之感。洪亮吉认为“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2]2257,认为“格”不能成为艺术表现力的禁锢,因此对“格”颇有负评。他反对死守格律的作诗方法,主张灵活用韵、换韵。此诗灵活换韵,体现了他的作诗主张,他所倡导的五字要素也由此可见。
洪亮吉在归途中,仍对天山有所书写。如其《凉州城南与天山别放歌》:
天山送我出关去,直至瀚海道尽黄河流。今年赐敕回,发自天山尾。天山送我复入关,却驻姑臧城南白云里。……兹来天山楼,欲与天山别。天山黯黯色亦愁,六月犹飞古时雪。古时雪着今杨柳,雪色迷人滞杯酒。明朝北山之北望南山,我欲客梦飞去仍飞还。[2]1239
百日放还之后,将与家人团聚的激动和脱离苦海的愉悦感让洪亮吉诗意大发,在途经甘肃武威时,他大声放歌,对雪饮酒。“天山送我出关去”一句,透露出诗人的惬意与激动。“天山火”“天山楼”“天山别”等是诗人对西域生活的回忆。纵然遣戍的生活艰苦,离别时,洪亮吉对天山的壮丽景色依旧心怀不舍。诗人自知此生恐难再历西域,因此发出“我欲客梦飞去仍飞还”的感慨,希望在梦中重游天山。
“天山”一词在洪亮吉遣戍诗中频繁出现,体现了他对雄伟天山的眷恋。如“东西南北尽天山”[2]1200(《出关作》)写天山的广阔,“万古飞难尽,天山雪与沙”[2]1200(《安西道中》)写西域严酷的气候,“天山南北口,百里积冰雪”[2]1203(《菩萨沟道中》)写一望无际令人惊叹的雪海,再如《发大石头汎》中对天山高耸、夕阳红霞映雪美景的书写,《牛触冰行》中“天山十丈冰棱大”[2]120对寒冰的描写,《行至头台雪甚益》中对雪花大如席的夸张描写,等等。
二、对西域风情与物产的书写
乾嘉时期,许多遣戍文人汇聚伊犁,留下了大量书写西域风物的诗作,如卢见曾《出塞集》、庄肇奎《胥园诗钞》、王大枢《西征录》等皆有关于西域的描写。“伊犁诗坛的创作主体是由以伊犁将军为首的驻镇官员和遣戍废员组成。这两大群体一显一隐,互为表里,共同推动了伊犁诗坛的发展与繁盛。”[4]许多来自江南的遣戍文人,如陈庭学、史善长等到达风景奇异的西域之后,会把见闻记录于诗文中。洪亮吉也不例外,他在伊犁戍中不过百余日,其往返经历对他的创作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洪亮吉的一些作品展示了边疆人民的朴实和尚礼,如《人日白山道中》中“居人能尚义,犹馈束脩羊”,诗下自注:“逆旅主人子将受经,属余为分句读。”[2]1206诗人帮助客舍主人的儿子划分经典的句读,这位主人以羊作为束脩,由此可见当地人民淳朴好礼。
西北大多地区土地贫瘠,少数民族多依靠放牧和打猎为生,如“羊群居前牛在后,鹰忽飞来攫羝走。……云中健儿弓已拓,一箭穿云觉云薄”[2]1207(《鹰攫羝行》)描写健壮的汉子射鹰护羝的生动场面,展示了边疆牧民能牧善射的高超技艺,表达了诗人对其射艺的敬佩之情。《百日赐环集》中的《四十里井汛》也描写了边地人们的劳作生活:“四十里井间,只有十家住。十家汲井过,并向麦畦注。麦肥如野菽,饱食耐征戍。耕余了无事,间或插桑苎。遂令半里间,夹屋无杂树。”[2]1232在土地肥沃的地方,人口并不稠密,西域地区普遍缺水,当地的人民汲井灌溉小麦,并在耕作之余,种植桑树与苎麻。“夹屋无杂树”写了当地居民高效利用土地,房屋周围多种植桑树与苎麻。《自三堡至头堡一路见刈麦者不绝多回部所种》亦有农事场面的描写:“三堡至头堡,亩亩麦新刈。咸携菠笨车,往返数难记。缠头何辛勤,风雨所不避。”[2]1236诗歌记录了哈密维吾尔族人民收麦忙碌的情景,“笨车”“数难记”表明农用运输工具落后,人们只能拉着木车一趟趟地运输新麦,非常辛苦。《将至滋泥泉泛雨》中也写到“沿村拾新麦,打鼓杂俚唱”[2]1231的收获场面,相对于前首诗歌,内容显得更加轻松欢快,描写了丰收时人们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
除了放牧和收麦等劳动场面,洪亮吉还描写了边地人民的生活图景。如《廿八抵巴里坤》先写巴里坤一带的地形特点,然后写年底飘落大雪,雪非常厚,甚至掩没车轴。岁底冷风更暴烈,行人裹着厚厚的帐幕抵御严寒。“灯火集一城,宵惊烛光绿”[2]1204,巴里坤城内虽有灯火,但仍然透露着萧凉的气息。
再如《未至吉木萨二里见赛神者络绎不绝时刘二尹之芳亦出城相迓因作此以赠》:“彩旗彩胜从空堕,满屋春人赛神坐。赛神已毕跨马忙,十里红袖沿春塘。城东出城愁不及,争上城楼向西立。钟鱼声中角声响,马上人皆避官长。”[2]1232诗中未详写赛神仪式的细节,而是写了彩旗飘飘、赛神人员众多的热闹场面,跨马等动态场景描写得非常生动。这种赛神活动也是当地居民互相交流的一种方式。“由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汉族人民在保留了特有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之外,也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如赛神活动就是一种融合四方性的移民文化活动。”[5]
西域地区贸易往来频繁,这在洪亮吉诗歌中也有体现。如《伊犁纪事诗四十二首》之六:“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2]1211此诗描绘了布鲁特人到伊犁互市的盛况:十万牛羊拥挤在路上,道路三日都不通畅。这也反映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洪亮吉在此组诗中,多赞颂伊犁当地物产,如“苹果花开雀舌香”写春天花开之香,“携具方家说饼来”“铜盘炙得花猪好”写食品之精致,“杏子乍青桑葚紫,家家树上有黄童”“山沟六月晓霞蒸,百果皆从筵上开。买得塔园瓜五色,温都斯坦玉盘承”写瓜果之美,一夜雨水过后,“十万鱼皆拥甲来”写水产丰美。对西域风物的具体书写使洪亮吉的西域书写具有了现实色彩。
三、对遣戍路途艰难的书写
洪亮吉遣戍途中路途艰辛且危机四伏。《三台阻雪》一诗云:“北风吹雪入鬼门,风定雪已埋全村。”诗人行至三台,北风怒号,鹅毛大雪纷飞,仿佛要把人吹入鬼门关。风止时,大雪已经覆盖了整个村落。诗中,“征人欲行马瑟缩,冰大如船复当谷”[2]1210一句,用比喻和对比的手法写路途艰难,气候酷寒,道出诗人雪中前行的艰辛。冰雪中行路容易迷失方向,道路被掩,极易发生意外。再如《覆车行》:“车厢压马马压人,马足只向人头伸。身经窜逐死非枉,只惜同行仆无妄。”[2]1205诗人详细描述这一意外,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危险情境,画面感极强。其他描写路途艰辛的诗歌还有《牛触冰行》《肋巴泉夜起冒雪行》《至蝎子泉雨骤大》等。另外,诗人在从天山到噶顺途中,“狗亦不吠鸡不鸣”“车厢缩项冻欲死”[2]1206,驻扎休憩时遇到野兽,“狼驯似马凭鞭策,鹊大于鸡共树栖,穴鼠岸然欺客睡,野猿时复难儿啼”[2]1208,诗人既担心风雪太大,又畏惧野兽袭击,其危险与艰苦可想而知。西行越远,天气越寒冷,甚至有人冻掉了手指,“路人伤坠指,迁客屡摧颜。倘有攀跻处,思排虎豹关”[2]1208。极度寒冷的气候、随处出没的野兽等境遇,在清代许多遣戍文人诗文中均有体现。
四、洪亮吉遣戍诗的艺术特色
洪亮吉在其遣戌诗中既真实地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和行路的艰辛,又运用了想象的艺术手法,诗中既有对沿途景色的想象,又有自我情感的想象。洪亮吉在《万里荷戈集》中关于梦的描写可以视为其潜意识的想象。“三十年前梦玉关”表达了他对多年前梦至西域如今成真的感慨,待亲入西域后,所见之景与梦中景象无异,更使他觉得奇妙。“世缘应已尽,梦亦不还家”[2]1204(《除夕夜坐》),除夕日诗人没有梦到回家,诗句表达了诗人觉得没有机会返回故土的悲凉心境。结合其他诗句如“今来迁客梦,仍阻乱山旁”[2]1206,以及“征人”“异乡人”等自称可知,他在艰苦的行路环境中如履薄冰,暂时忘却了思乡。“万松怪底都相识,曾向童年入梦来”,童年关于西域的梦境与现实所见一致,这是想象与现实的契合。“云边一笛惊残梦,天外三山伴此身”[2]1207(《古城逢立春》)写被打断的梦境,表达了诗人的孤独感。汉代的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均在西域建立了丰功伟绩,《天山歌》中“控弦纵逊骠骑霍,投笔或似扶风班”一句借典故表达了诗人想要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这也是诗人的想象构成。
洪亮吉所描写的边地风光以及习俗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如上文提及的布鲁特人互市、麦忙、赛神等,再如《自三堡至头堡一路见刈麦者不绝》中写到“秦陇多流民”,洪亮吉在自注中提到当时邪教滋扰秦陇一带,所以当地有很多流民,这些都体现出很强的纪实性。
五、结语
作为清代乾嘉时期遣戍西域的废员之一,洪亮吉的人生是不幸的,但这段西域之行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严迪昌在《清诗史》中评价洪亮吉在诗歌史上的贡献时说到:“洪氏诗早年即奇思独造,五古歌行尤气盛,中年后经荷戈塞外,奇景奇情,纷然笔下。他的天山景物诗为清代山水诗史添上丰富的一页,较之纪昀之作更精彩。”[6]写西北边塞的诗歌,自汉唐已有之,汉唐边塞诗的主题有着明显的尚武、苦寒和征戍制度下的乡恋特征。“清代西域诗人则更追求西域与内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相似性。汉唐诗人笔下的龙沙万里、狂风暴雪的西域印象逐步被淡化。”[7]洪亮吉的遣戍西域诗作,既沿袭了唐代西域诗歌雄浑的美学风格,又细腻地描写了西域的风情、物产和奇山异水,拓展了他的诗歌题材。他的遣戍诗也受到孙星衍、赵翼、赵怀玉等人称赞,其遣戍诗作促进了清代边塞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