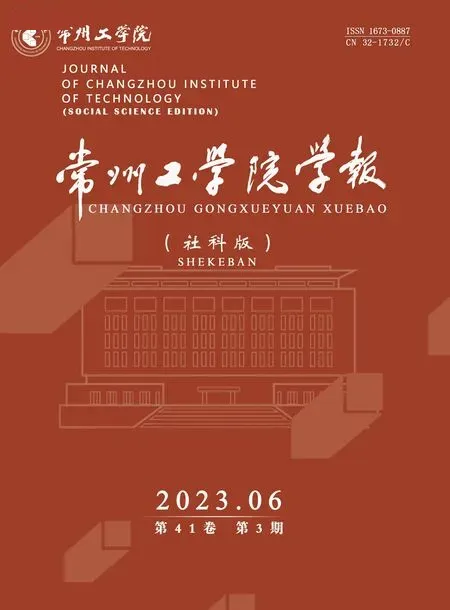颜师古《诗经》学探析
——以《汉书注》为中心
杨楠,吴从祥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受官方统一思想的影响,唐代研究《诗经》的学者和著作较汉魏六朝时明显减少,目前仅有孔颖达《毛诗正义》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其实在此之前,唐代还有许多研究《诗经》的学者,但他们多因著作缺失或亡佚而未引起学界重视,颜师古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颜师古《五经定本》现已亡佚,其所注《毛诗定本》的原貌已不可考究,要想进一步了解颜师古对《诗经》的看法,《汉书注》的研究价值极大。颜师古《汉书注》共引《诗经》372条,根据注释来源的不同,可分为两类:《汉书》引《诗》颜师古作注,共182条;颜师古注释引《诗》,共190条。后者在数量上多于前者,且是颜师古本人的一种自觉行为,体现出他独特的《诗》学观,因而成为本文论述的对象。
一、《汉书注》引《诗》方式
颜师古注释《汉书》讲究考据,“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1]2,在注释中援引经典,为自己的注解提供强有力的论证,注释引《诗》便是典型之一。颜师古注释引《诗》分为两种方式。
(一)仅提《诗》名或《诗序》
颜师古注释了一些语句简短、内容概括的引《诗》条目。其一是只提篇名并简单概括《诗》旨,无具体《诗》句的说明,共27条。如《汉书·外戚传下》:“《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颜师古注:“《绿衣》,《诗·邶风》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华》,《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1]2933又如《汉书·冯奉世传》:“《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颜师古注:“《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傅作焉,刺幽王信谗,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1]2467《汉书》原文中提及《绿衣》《白华》《小牟》3个篇名,颜师古注释时进一步点明3篇的类别并阐释《诗》旨。
其二是不引《诗》篇,也无《诗》句,只引《诗序》,共16条。《诗序》是对《诗》篇主要内容的概括总结,有“大序”“小序”之分,“《大序》者,论全诗之义也,《小序》者,论一诗之义也”[2]。颜师古注释所引,有论说全文的“大序”,其中以论说风、雅、颂者最多。如《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风,教也。《诗序》曰:‘上以风化下。’”[1]122又如《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颂谓《诗》颂,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言发其志而为歌颂也。”[1]2628颜师古注释中也有引用独立各篇的“小序”,其目的是借《诗序》来解释字词意思。如《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劳来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小雅·鸿雁》之诗序曰:‘劳来还定安集之。’”[1]174又如《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颜师古注:“考,成也,成其礼也。《诗·小雅·斯干》之诗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1]2376无论是引“大序”,还是“小序”,颜师古对《诗序》的认识多以《毛诗序》为主。
(二)直接引《诗》篇和《诗》句
除上文引《诗》方式外,颜师古注释中也有一些较为复杂的条目,即在文中既引《诗》篇又引《诗》句,共114条。根据其引《诗》目的的不同,又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根据原文,指出其化用的《诗》篇和《诗》句,并对诗句大意和具体字词进行阐释,这一类共64条。如《汉书·薛宣朱博传》“不吐刚茹柔”,颜师古注:“《大雅·烝民》之诗云‘惟仲山甫,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1]2524颜师古根据原文,指出其化用的是《大雅·烝民》中的句子,并参考《毛传》《郑笺》的注释解析《诗》句、字义。虽参考《毛传》《郑笺》的学说,颜师古也会遵从文理,使注解贴合原文,如《汉书·扬雄传上》颜师古注:“《周颂·清庙》之诗云‘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昊天有成命》之诗曰‘于缉熙’,言汉德之盛,皆过之也。”[1]2628《毛诗序》:“《周颂·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3]451-455《毛传》《郑笺》都将这两句《诗》解释为祭祀,赞美周王的功德。颜师古解释其与帝王功业有关,但又将这两句放入《汉书》文本中,解释其为“汉德”,认为这两句《诗》是说汉王朝的功德已超过了周王朝,称赞汉朝的强大。
第二类是在解释字词意思后引《诗》句为证,共50条。如《汉书·韩彭英卢吴传》颜师古注:“樵,取薪也。苏,取草也。《小雅·白华》之诗曰:‘樵彼桑薪。’樵音在消反。”[1]1460颜师古在注解“樵”字后,又引《小雅·白华》中带有相同字的句子作证。这种情况在注解一些不常见的古字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汉书·地理志》:“浩亹,浩亹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颜师古注:“亹者,水流峡山,岸深若门也。《诗·大雅》曰‘凫在亹’,亦其义也。”[1]1290《汉书·地理志》“川曰泾、汭”,颜师古注:“汭在豳地。《诗·大雅·公刘》之篇曰:‘汭鞠之即。’”[1]1243颜师古引《大雅·凫》《大雅·公刘》中的句子注解当时人们不太熟悉的古字“亹”和“汭”,增加了注解的真实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个别《诗》句进行注解时,颜师古也会对其进行评点,由古及今,流露出对当时政治的担忧。如《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注:“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之诗曰:‘肃肃王命,仲山父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父明之。’将,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诰命,则仲山父行之;邦国有不善之事,则仲山父明之。故引以为美,伤今不能然也。”[1]934颜师古感慨于仲山父的正直,在行文的最后流露出对国家缺少这种贤才的痛惜。又《汉书·杨胡朱梅云传》颜师古注:“《大雅·荡》之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虽无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时’,言殷视夏桀之亡,可为戒也。赞引此者,谓梅福请封孔子后,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视秦灭二周,夷六国,不为立后,自取丧亡,可为戒也。”[1]2206颜师古在注解最后告诫今人要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以仁义立国。颜师古注释中采用的这两种引《诗》方式,使其注释有繁有简,详略得当。
二、《汉书注》释《诗》特征
颜师古在注释引《诗》时,也会对所引之《诗》进行解析。颜师古释《诗》不同于前人,表现出鲜明的特征。
(一)融古文经、今文经于一体
汉代《诗经》研究有“四家”——齐、鲁、韩、毛,前三家专明大义微言,属于今文学派,毛《诗》多详章句训诂,属于古文学派,两者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同归。至东汉郑玄《毛诗传笺》,以《毛诗》为主,兼采三家诗说,使今古文经走向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融合趋势也在不断发展,颜师古祖父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就曾兼引今古文《诗》,其《书证》篇云:“《诗》云:‘将其来施施。’《毛传》云:‘施施,难进之意。’《郑笺》云:‘施施,舒行貌也。’《韩诗》亦重为施施。”[3]240戴维在《诗经研究史》中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研究已摒除了今古文之争[4]。颜师古受家学和时势的影响,在注释中融今古文《诗》为一体,以《毛传》《郑笺》为主,兼引今文三家诗。
颜师古对《毛传》的遵从,主要表现在字词的解释上,如《汉书·李广苏建传》颜师古注:“王国风《菟爰》之诗云‘有菟爰爰’,爰爰,缓意也。”[1]1864《毛传》注:“爰爰,缓意。”[5]101颜师古的注解与《毛传》相同。而对《郑笺》的遵从,则主要表现在《诗》意的阐发上,如《汉书·王莽传》颜师古注:“《商颂·殷武》之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言商邑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1]3003颜师古择善而从,直接套用《郑笺》之释,融合了今古文经。
颜师古兼引三家诗,其中以《韩诗》引用最多,有10条,如《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韩诗传》云:‘三月桃华水。’反壤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壤反还也。羡音弋缮反。淤音于庶反。”[1]1343颜师古引《韩诗传》来解释《汉书》原文中的词。除上述单引今文《诗》外,有的注释中今古文《诗》还会同时出现,如《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诗·小雅·雨无正》之篇曰:‘若此无罪,沦胥以铺。’胥,相也。铺,遍也。言无罪之人,遇于乱政,横相牵率,遍得罪也。《韩诗》沦字作薰。薰者,谓相薰蒸,亦渐及之义耳。”[1]3123前文注解与《郑笺》基本相同,后文又引《韩诗》指出与《郑笺》所用字词的不同,注解多种说法。
(二)注音与释义合一
《汉书》因其文辞晦涩,历来不乏为其作注之人。从东汉末年起,就有服虔、应劭等为其作注,颜师古《汉书叙例》中记载的较为著名的作注者有23人。但前人注本大多以音义为主,偏重字词读音,颜师古《汉书叙例》云:“《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1]1之后注家也多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总结,“意浮功浅,不加隐括,属辑乖舛,错乱实多”[1]1。颜师古吸取前人经验教训,所注《汉书》既重字词音韵,又重意义解说,对《诗经》的注解也是如此。
颜师古解《诗》集前代注《诗》体例之大成,遵循由字词解释到诗意解说再到反切注音的基本范式,如《汉书·匡张孔马传》颜师古注:“《诗·郑风·太叔于田》之篇曰:‘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汝。’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郑庄公也。将,请也。叔,庄公之弟太叔也。狃,忕也。汝亦太叔也。言以庄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献之。国人爱叔,故请之曰勿忕为之,恐伤汝也。襢音袒,裼音锡,字并从衣。将音千羊反。狃音女九反。”[1]2486颜师古解《诗》先注字词,再解诗句,最后使用反切法注音,这是其注解中较为全面的解《诗》体例。但许多时候这三者可能不会同时出现,如《汉书·哀帝纪》颜师古注:“《大雅·假乐》之诗曰:‘干禄百福,子孙千亿。’言成王宜众宜人,天所保佑,求得福禄,故子孙众多也。十万曰亿。”[1]234注者只对《诗》意、字词进行解释。又《汉书·谷永杜邺传》颜师古注:“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交》诗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刺厉王淫于色,故皇父之属因嬖宠而为官也。远音于万反。父读曰甫。”[1]2561注者只注解了《诗》意和读音。不论是字词读音还是意义解说,颜师古在小学和经学上的造诣之深,从其解《诗》体例可见一斑。
(三)引史证《诗》,增强说服力
颜师古《汉书注》引《诗》多以《诗》句为主,为了使自己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颜师古在遵从《毛传》《郑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具体字词和句子出处的考辨,尤喜引证史书中的例子,增加其注释的可靠性。
《左传》是颜师古解《诗》时引证最多的一部史书,共有8条注释。颜师古引《左传》中的内容以证明《诗经》中某些地名存在的真实性或交代《诗》句所发生的故事背景。如《汉书·地理志》原文:“汶阳,莽曰汶亭。”[1]1307颜师古先引应劭对“汶”字的注解:“《诗》曰‘汶水汤汤’。”[1]1308随后注释:“汶音问。即《左传》所云‘公赐季友汶阳之田’者也。”[1]1308此句所涉《诗》句虽是出自应劭的注释,但颜师古并没有批判他注解的错误,反而紧跟其后进行注释,可见颜师古是认同应劭所注《诗》句的。颜师古注此句“汶音问”,与《郑笺》相同,但《郑笺》注释仅限于此,注释简单,故颜师古又引《左传·僖公上》中的语句,进一步证明“汶水”是真实存在的,且就在今泰安县西南楼上村东北[6]279。又如《汉书·楚元王传》颜师古注:“《春秋·公羊经》隐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传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也。曷为贬?讥继卿。继卿,非礼也。’又《诗·小雅·节南山》云:‘尹氏太师,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刺之也。”[1]1506《郑笺》注释此句时只说:“责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为也。”[6]261对于“不平”的原因交代得并不是很清楚,故颜师古在注释前引《左传·隐公三年》为我们交代清楚了尹氏为政不平的原因是尹氏曾世代为公卿,而当氏族所掌握的权力过于集中时,则往往会造成贤才之路的堵塞以及君主权威的削弱,十分不利于国家的发展,故《汉书》原文称尹氏“世卿而专恣”,颜师古引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诗》句。
(四)崇尚简洁,语言质朴
班固《汉书·儒林传》中言汉代经学“一经说至百于万言,大师众至千于人”[1]2684,点明汉代经学发展到极盛时的盛状,但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学者不可以不察。”[7]汉及后代解经“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1]1365,表现出“烦妄”的特征,注解经学逐渐脱离了其本身的意义。
针对前代解经烦琐的弊端,颜师古吸收南北学术文化之长,在注解《诗》时表现出简洁、质朴的语言特征。无论是注解《诗》意还是阐释《诗》旨,相比于《毛诗》《郑笺》,尤其是后来的《毛诗正义》来说,都显得更加简洁平实。如《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诗·小雅·节南山》之篇曰‘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言师尹之任,位尊职重,下所瞻望,而乃为不善乎,深责之也。”[1]3127《郑笺》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视女之所为,皆忧心如火灼烂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戏而言语。”[5]261《毛诗正义》曰:“以兴赫赫然显盛者,彼太师之尹氏也。尹氏为太师既显盛,处位尊贵,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8]698对比《郑笺》《毛诗正义》,颜师古的注释更为简洁。又如《汉书·叙传下》引《小雅·节南山》篇“尹氏太师,惟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颜师古注:“言大臣之职,辅佐天子者也。”[1]3125相比《郑笺》“言尹氏作大师之官,为周之桎辖,持国政之平,维制四方,上辅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无迷惑之忧”[5]262,以及《毛诗正义》“言汝职维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当使下民无迷惑之忧,何为专行虚政,以胁下也?”[8]701颜师古仅用11个字就准确地表明了诗句的意思,表情达意上不输《郑笺》《毛诗正义》,反而更显明白晓畅。
三、《汉书注》中的《诗》学观
颜师古《汉书注》引《诗》时条目众多,内容丰富,释《诗》时旁征博引,涉及广泛,从中可以窥探颜师古独特的《诗》学观。
(一)采怨刺诗说
《诗经》来源,有“采诗”“献诗”“删诗”3种说法。其中关于“采诗说”的史料常见于汉代诸家,如《礼记·王制》载:“岁二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9]363班固《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1]947诸家虽都指出有采诗之事,“然而采诗之人不同,如轩车使者、遒人使者、采诗之官、老而无子者、国史、孔子等等,……采诗方式也各异,有的说天子巡守时命太师陈风,有的说是徇于路以采诗,有的说太师正其音律以闻于天子等等”[10]。对于“采诗说”具体的内容一直没有定论。
考察《汉书注》中颜师古的看法,其在《汉书·食货志》《汉书·礼乐志》中分别注释:“行人,遒人也,主号令之官。……徇,巡也。采诗,采取怨刺之诗也。”[1]947“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1]894颜师古解释“行人”为遒人,认为古代“采诗”之人为遒人,即帝王派出去专门了解民情的使臣。颜师古解释“徇”为“巡”,认为“采诗”的方式是使者到各地巡视采风所得,其目的是知政教得失。颜师古的这些说法大抵不出前人的理解,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在注释中首次对“采诗”的范围进行了限定,颜师古认为所谓“采诗”,特指采怨刺之诗,这是前人所没有涉及的方面。怨刺诗的产生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汉书·礼乐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1]891,怨刺诗直指现实政治生活,是对时政、国事的讽谏,能够帮助帝王知晓政治的兴衰,因此对《诗经》中的怨刺诗,如“二雅”中的《节南山》《十月之交》,《国风》中的《相鼠》《伐檀》等,颜师古在注释中大量引用,并在注解时以“刺”解《诗》,如《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皇甫,周卿士之字也。用后嬖宠,而处职位,诗人刺之。事见《小雅·十月之交》篇。”[1]1196又《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颜师古注:“《伐檀》,《诗》篇名,刺不用贤也,在魏国风也。”[1]2298颜师古从儒家政教伦理出发,认为“采诗”特指采怨刺诗,带有明显的讽谏意味,符合其儒者的身份。其说法有可取之处,但由于不能囊括《诗经》全部,终是一家之言。
(二)新十五国风说
对于“十五国风”,历代学者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其次序的排列上。《左传》所列次序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毛诗》所列次序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郑玄《诗谱》所列次序为:周南、召南、邶、鄘、卫、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左传》《毛诗》《诗谱》关于“十五国风”,名称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次序。关于十五国风的次序,孔颖达认为无论根据时代早晚、国地大小或采得先后,都缺乏可信的依据,以致这最终成了一个难以论定的悬案[11]。
颜师古不同于前人,他在《汉书注》中提出了有关“十五国风”在称谓上的不同说法。《汉书·王莽传》:“《诗》国十五,抪遍九州。”颜师古注:“谓周南、召南、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鲁、商,凡十五国也。一曰,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是为十五国。”[1]3031颜师古在注释中提出了有关“十五国风”的新说法,将邶、鄘、卫合归于卫,又后加鲁、商二地。颜师古的这种新说法很明显是为了解释《汉书》原文“抪遍九州”,力图将“十五国风”与当时的九州地域强行联系起来,因邶、鄘、卫3国的诗实际上都是卫诗,在同一地域,故将三者归于卫,而后又将《颂》中的两个诸侯国鲁和商添入其中,使其能够囊括九州,但由于九州地域复杂,他的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合理。而颜师古注释保留后一种说法,显然是受《毛传》的影响,《毛传》所列“十五国风”的次序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这反映出颜师古对《毛传》的遵从,以及颜师古注《汉书》中“具而存之”[1]2的注释原则。以上两方面是颜师古在《汉书注》中所表现出的不同于前人的《诗》学观,体现出他本人对《诗经》的独到理解。
四、结语
综上所述,颜师古《汉书注》中所表现出的繁简有序、详略得当的引《诗》方式以及融今古文经于一体、注音与释义合一、引史证《诗》、简洁质朴的释《诗》特征,反映出颜师古本人在经学、小学和史学上的造诣之深。而其在注释中提出的不同于前人的两大新《诗》学观——“采怨刺诗说”和“新十五国风说”,不仅表现出他本人对《诗经》的某些独到见解,同时也丰富了唐代《诗经》研究的成果。颜师古《诗经》学弥补了唐代《诗经》研究的一些空白,是唐代《诗经》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