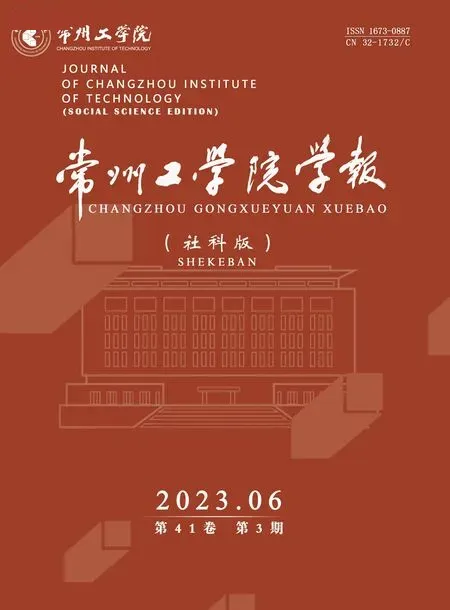顾恺之绘画中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
方毅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引言
文学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建立于汉代以来文人越来越多的两方面的参与:一方面,作家观画写出诗词歌赋;另一方面,画家根据歌诗词赋绘制画作[1]。文字的出现使得记忆可以被保存下来,文字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成为保存记忆的物质载体。而图像早于文字出现,与文字相比,前者是一种具体的形式,后者则是一种抽象的形式[2]。
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认为:“伟大的民族以三种手稿撰写自己的传记:行为之书、言词之书和艺术之书……但是,在这三部书中,唯一值得信赖的便是最后一部书。”[3]其原因在于,艺术叙述能唤起人们的历史想象与情感,增强了人类的鉴赏能力,同时也使人类的审美意识达到了较高的境界。所以,历史的艺术叙事是一种多感官、多媒介融合的叙事。如顾恺之的作品可以从笔法、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等角度进行多维度的分析,手法技巧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但缺少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角度的研究。文章以东晋画家顾恺之的绘画作品《洛神赋图》《女史箴图》为考察对象,探究其绘画作品所呈现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
一、顾恺之与《洛神赋图》《女史箴图》
顾恺之(约334—405),字长康,江苏无锡人,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画家。东晋的谢安评价他是“自生人以来未有也”[4]。顾恺之出生于士族家庭,有“三绝”(画绝、痴绝和才绝)之称。他在总结汉、魏两代绘画经验后,将传统绘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现今流传的摹本有《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和《烈女仁智图》。
(一)《洛神赋图》的时代背景与内容
屈原的《离骚》和《天问》中首先出现了“洛神”这个角色,但是“洛神”一直到魏晋时期才引起文学、绘画、书法等领域人们的注意。
尽管学界对洛神的原型还存在一些争论,但人们普遍认为,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曹植的《洛神赋》。曹植笔下的洛神是文昭甄皇后甄洛。甄氏是上蔡令甄逸的女儿、汉末军阀袁绍之子袁熙的妻子。官渡之役,袁绍战败而亡,曹操出兵平冀州,甄氏等人也被抓了起来。曹丕见她容貌出众,便求曹操将甄氏许配给他。曹植比甄氏年纪小,对她的美貌和才华也极为欣赏。曹丕登基后,册封甄氏为文昭皇后。因为后宫中文德郭皇后、李贵人和阴贵人得到宠幸,甄氏心存不满,对此颇有微词,曹丕便派人将她处死。之后,曹植觐谒魏文帝曹丕,与甄氏的儿子共进晚餐,想到已故的甄皇后,心中悲恸万分。曹植临行前,曹丕将甄皇后的遗物送给了曹植。曹植在回自己封地的路上睡了一觉,梦到甄妃乘风而来,两人情投意合,回到自己的封地后感慨万千,写下了《洛神赋》。
目前故宫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洛神赋图》藏本(下称故宫本、辽宁本)具有代表性。二者最大的区别是辽宁本图文并茂,故宫本有图无文。该画描绘的是曹植和洛神在洛水畔相会的场景。整幅作品可以分成3段:第一部分描写了曹植和洛神在日落时相遇的情景。他向仆人问道:“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画中,曹植见到洛神极为惊喜。第二部分描绘了洛神窈窕的身材和华丽的衣着。第三部分描述了人神殊途,洛神已经走了,曹植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能再见到她,于是坐船去找她。
顾恺之画中的洛神,身材柔美,服饰华贵,他用线条为洛神增添了飘逸的气质。这幅画突出了仙道的朦胧美,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含蓄美、朦胧美相吻合[5]。
(二)《女史箴图》的时代背景与内容
《女史箴图》以张华《女史箴》为蓝本。张氏《女史箴》是一部讽刺晋惠帝贾皇后的文学作品。晋武帝司马炎于290年去世,其子司马衷登基,即晋惠帝。司马衷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朝政大权全由西晋太宰贾充之女——皇后贾南风一个人掌握,朝中大臣极为不满。所以大臣张华创作了《女史箴》,一方面,倡导儒家的礼教,告诫后宫女子要恪守妇道,另一方面,从侧面抨击了皇后贾南风荒淫、专制、祸国殃民的行为。
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最具有代表性。《女史箴图》分为12段,现存9段。依次为:冯媛挡熊、班姬辞辇、世事盛荣、修容饰性、同衾以疑、微言荣辱、专宠渎欢、靖恭自思、女史司箴[6]110。
顾恺之“游丝画法”“传神写照”等绘画理论在这一长卷中得以表现。画面中环境优雅,人物形象端庄,多身着宽松的白色长裙,长裙上系着五颜六色的彩带,飘逸出尘。人物的构图都是用细细的线条勾勒,只在头发、裙边等部位涂以浓重的颜色,稍加点缀。画面优雅恬静,却不失灵动明快。
二、 《洛神赋图》与历史记忆
皮埃尔·诺拉《在历史和记忆之间》中提到:“为什么会有很多人说起回忆,是因为回忆已经消失。”[7]绘画作品中也有回忆的场景,有的是以画面旁边的题跋来提醒观众,有的则是通过画面中人物的动作来表达,甚至一些由文学作品而作的图画作品也有对记忆的描写。顾恺之的作品《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都对记忆有所描绘。这两幅作品都是根据文学作品转化为图画,可以视为一种“出位之思”,“即表示某些文艺作品及其构成媒介超越其自身特有的天性或局限,去追求他种文艺作品在形式方面的特性”[8]99。叙事性图像的核心元素是图像,以文学作品为基础,而图像作为一种空间媒介,并不擅长表现具有时间进程的事物,如果需要表现时间,则需要对故事的时间进行大量压缩,以一个画面或瞬间来进行描绘[8]99。《洛神赋》从曹植对宋玉和楚王的描述写起,之后写对洛神的思念。张华的《女史箴》由4个典故写起,最后通过女史官将道德标准传达给他人。如何将这种带有时间性质的文字描述表达到绘画中?顾恺之在绘画创作中运用了“出位之思”。
曹植的《洛神赋》运用文字再现想象中的世界,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则是通过绘画的语言来实现基于文本的再创造。《洛神赋》描述了黄初三年(222),曹植前往京城洛阳,途经洛水与洛神相恋的故事[9]181。曹植在赋的前言中谈到了创作原因:“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曹植回封地的途中回想到古人所言神女宓妃,以为神女宓妃就是甄氏,同时也想到宋玉对楚王所说的那位“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之所见也,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通过曹植和侍从的对话可知,侍从是无法看见洛神的,需要通过曹植的描述想象洛神的样貌。
图像学家米歇尔认为:画面与它所体现的意义在感官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作用于视觉的作品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听觉、嗅觉和触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各种门类艺术的互通性。人类的感官虽然各司其职,但视觉本质上是一种理智的、客观的、距离性感官,与理智连结在一起。换句话说,视觉是精神和理性的眼睛,它是“最能接近真理的感官”[10]。与视觉的“理性”相比,“听觉”更加具有情感色彩,它更注重“参与”与“共享”。那么,纯视觉艺术如何体现视听的“互动”呢?诗人在此将“视”和“听”进行转化,只有曹植能看到洛神,他需要将自己所看到的视觉形象转化为语言,身边的随从则需要将语言转化为视觉形象。这也意味着当我们随着故事继续观看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画面是曹植眼中的景象。在《洛神赋》中,曹植问仆从“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其中,“艳”字形容洛神的美丽,他运用与视觉相关的词语来进行文学表达,并实现了视觉和听觉的转换。
史学上的想象是指对过去与将来的想象,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已有的,一类是没有的,在叙述中,想象以历史记忆为基础。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却不会受到历史记忆的制约[11]。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是根据宋玉对楚王的论述想象的,在宋玉所创作的《神女赋》中,“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楚襄王与宋玉在云梦泽边游览,他要宋玉为他讲述先王梦遇高唐神女的故事。楚襄王将梦中遇到女神的事情告诉了宋玉,宋玉也和曹植身边的仆从一样,问道:“其梦若何?”“状何如也?”楚王心中的神女与曹植描写的洛神都是在梦境中或想象中出现的。可以认为,曹植的《洛神赋》是建立在宋玉或楚王想象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想象与记忆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叙述者与倾听者、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中,叙述者的回忆就会转化为倾听者的想象,而倾听者的想象则会被后人所记住[9]128。因此曹植的历史记忆也就转换为顾恺之的历史记忆了。
在对仆从形容完洛神后,曹植在赋中再次谈及记忆的问题。“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曹植钟情于洛神的美貌,希望有人给他说媒,而正当两人开始交换信物的时候,神女却不见了。那么,画中如何表现曹植既迫不及待又深思熟虑呢?在辽宁本顾恺之描绘的这个场景中,曹植的身体前倾,仿佛迫不及待地要将手中的信物交给洛神,主从之间的距离比之前曹植描述洛神样貌时的距离更大,并且与之前的图像不同,在这幅画面中,曹植从双手需要仆从搀扶转变为只需要仆从搀扶一只手,体现出曹植希望爱情可以成真的迫不及待。而“深思熟虑”则是一种对记忆的重建,它可以将真实的记忆展现出来,也可以根据现实的利益,对历史的真实性进行人工的拟制[12]15。画面中,曹植身边的仆从共有3位,曹植的目光向前,看着洛神,他左手边的仆从微低着头,目光向下,右手边的第一位仆从头微低,朝洛神的方向看去。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瞬间在叙事中的意义。洛神从一开始出现到这一幕,一直处于江水上,而在这一时刻,洛神首次登上陆地,这也象征着她进入了凡人的领地。并且,曹植和洛神也交换了位置,此前,洛神一直处在曹植的左方,是他注视的对象,但是此时她出现在曹植的右边。手卷一般都是从右至左慢慢展开,洛神位置的变动也使她从“焦点”转变为“聚焦点”。从洛神的身姿和动作可以看出,洛神也是迫不及待地接受曹植的信物。这一画面准确地抓住了《洛神赋》文学叙事中的关键转折点,诗人将自己描绘为因犹豫而错失良机的失败恋人,这也引出了赋中第三处对回忆的描写。
曹植与洛神交换信物时,回想到郑交甫曾遇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犹豫迟疑,导致信物未能交换成功,洛神悲伤离去。洛神离去后,曹植在赋中写道:“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洛神被众神接走后,曹植思念洛神,夜不能寐。而众神接走洛神后,洛神的云车即将飞跃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夹在两岸岩石中间,切开了水平展开的画面,竖立在洛神云车前的是一个类似山峰的物体。画卷开始处,从陆地到水域的转移象征曹植与洛神相会幻觉的开始。当洛神离开后,画家以一条河流和一座山峰来象征“界框”的意义,宣告梦幻的终结。
临近画面结束,当搭载曹植的马车开始疾驰时,车中的曹植回头观望。而在这之前,画中的人物,尤其是曹植,他的目光是聚焦的。在这一片段中,曹植的目光不再聚焦,而是带着一种忧伤、遗憾和惆怅。
三、《女史箴图》与身份认同
在社会学领域,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对自身身份和角色的正确性、对身份和角色的一致性、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身份认同的本质是一种精神归属,它强调了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心理认同感。
顾恺之《女史箴图》以《女史箴》为基础。“箴”是一种在魏晋时期广泛使用的劝诫语。《女史箴》《女史箴图》的创作目的是让当时的女性建立一种身份认同,它们通过叙述和描绘历史中品德高尚的妇女,树立女性的榜样,由此引发女性的身份认同。
张华在《女史箴》开篇谈到:“茫茫造化,两仪既分;散气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牺,肇经天人;爱始夫妇,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伦。妇德尚柔,含章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结褵,虔恭中馈;肃慎尔仪,式瞻清懿。”[13]张华将宇宙的秩序映射到现实生活中,以统治秩序与伦理秩序引出天人合一以及家庭秩序,从文学的角度形成一种身份认同。文学是承载与传递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可以展示个人记忆,而且可以塑造一个人的个性或身份地位[14]。张华在《女史箴》中,讲完伏羲、君臣以及家道等秩序后,讲述了5个有德行的妃妾的故事。个体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对过往的片段进行了转换、加工和重组,从而形成了一种更为完整的、与当下阐释角度一致的个体记忆。这种个人记忆通过文学作品被固定下来[12]20。并且,个人在文学创作中也会逐步形成和加强自身的身份认同。
莱辛认为:“绘画要选取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刻。”[15]简单来说,就是指将一段带有时间特征的故事凝练成一个最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的“点”,接受者可以根据这一点展开联想,进行绘画创作。在大英本的《女史箴图》中,顾恺之忽略了樊姬和卫女等人的故事,直接描绘“最富有孕育性”的“冯媛挡熊”的故事。冯媛是西汉时期光禄勋冯奉世的长女,汉元帝刘奭的宠妃,汉平帝刘衎的祖母。“玄熊攀槛,冯媛趋进。”黑熊爬过栏杆扑向冯媛丈夫时,冯媛勇敢地上前挡住。张华通过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事件规劝当时的女性。
在《女史箴图》中,顾恺之为了突出对女性的道德要求,采用了两个反面的例子来强调妇德乃至身份认同。“出其言善,千里应之。苟违斯义,则同衾以疑。”这是在教导妻子和丈夫说话时言辞要得体。画中的女性身着红衣,右手搭在屏风上,充满自信。而与她对视的男性既可能在穿鞋离开,也可能是在脱鞋准备上床。巫鸿认为,画面中的女性是以反面的形象来进行描绘的,她直视丈夫的目光显示出这是属于她的“领地”[6]114。
在接下来的画面中,画家再次以反面的人物进行强调。“欢不可以黩,宠不可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雠。”被宠爱的时候女性不可以无礼。画面中,男性的身体前倾,左手向后面的女性做拒绝的动作,他似乎想要赶紧逃离这个地方。这符合诗中所描述的“冶容求好,君子所雠”。
此外,顾恺之在画面中增加了两位人物来凸显这幅作品的回忆部分。画面的卷首和卷尾都有两位女性正在回首并相互交谈。画家通过卷首回头看的形式来表达对这一“故事”或者“连环画”的回忆,通过卷尾向前走的形式来表达故事的进行,正好与文章末尾所说的“女史司箴,敢告庶姬”相契合。
四、结语
顾恺之的绘画作品不仅涉及历史记忆,同时也涉及身份认同。这两者看似是相互孤立的,其中却有着联系。在《洛神赋图》中,顾恺之阅读曹植的诗赋后,将曹植的记忆转化为自己的,根据诗赋中所论述的两个“感”与历史记忆相联系,并通过绘画的形式来表现。以历史记忆来唤起对女性身份地位的认识则是记忆的另一个功能,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根据张华的文学作品而作,唤醒了女性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