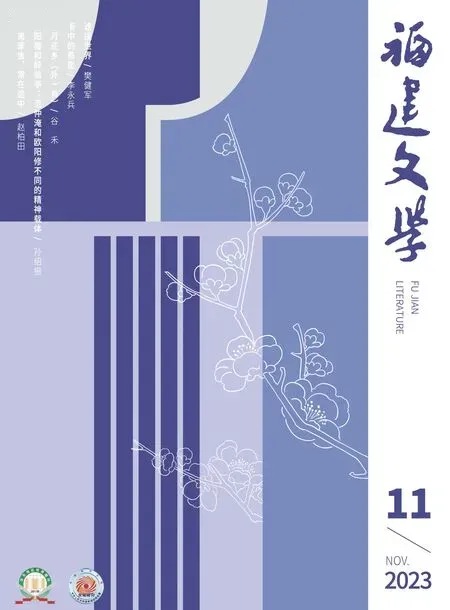泥土芬芳
绿 萍
侄子出生那年,母亲到弟弟工作的城市帮忙照看。从那时起,父亲开始开辟菜园,算来也有好几年了。
父亲的菜园在自建房的顶楼。这个六层的空中平台在老城区算是高层了——向下俯瞰,能看到周边低处错落的人家,往东边的远处眺望,尽头是茫茫的天际,和不远的海平线交汇在一起,茫茫地连为一片。
开辟菜园,首先要有土。土不能直接置于地面,父亲先是寻找盛土的容器。他陆陆续续从附近的农贸市场寻来十几只白色的泡沫箱——这种箱子轻便,透气,不失为盛土的好容器。接下来是大量囤土。早期的楼房没有电梯,土只能一袋袋地由脚力运送——蚂蚁搬家、燕子衔泥,说的就是这般原始却实实在在的搬运方式。从少到多,积微成著,很快地,楼顶便堆满了土。这些来自郊区不同之处的土,颜色深浅各异,得益于主人的勤劳相聚于同一处,彼此也算是有缘之土了。
有了土,就有发芽的希望。每天上午,父亲的身影便出现在这个空中菜园里:撒种,浇水,松土,捉虫……亲近菜园,显然让父亲感受到了泥土中藏着的快乐。家里的微信群开始时常看到他拍的照片——有菜园长势良好的全景图,也有各种果蔬的特写镜头:青翠闪亮的白菜、芥菜、葱蒜苗,竹架上挂着瓠瓜、丝瓜,线条浑圆优美,茄子披着一身深沉的紫色,那些只把“发丝”露出地面的萝卜,茎块状的果实深埋于土中。按时浇水,定期除虫、修剪,尽量使用低比例调配的杀虫剂,这是父亲一以贯之的原则。父亲使用的手机像素并不高,照片都是原图拍摄,在无滤镜的自然光下,清晰真实。空闲的时候我点开图片,放大细细观赏,偶尔会发现一两只青色的虫子正在叶片上蠕动,还有一些小小的虫眼出现在青色的叶片边缘。秋葵已经到了可以采摘的时期,颜色仍然青嫩,西红柿常见的嫣红偏于橘黄,显得没那么喜庆。至于茄子,粗细和长度都远远超出我之前购买的经验——细长而不规则地弯曲着,让人疑心它这一生是否任性得有些过头了。
于是,父亲的朋友圈发布的内容几乎成了种菜系列笔记:
“昨天跟邻居要了鸽子粪来施肥。”
“今天阴,看起来不会下雨。准备喷第一轮波尔多液。”
“前段时间台风残留的烂叶子,今天要清理干净。”
……
年近七旬的父亲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在家休养,不必这么劳累的。自小数学天赋极高的父亲在少年时期遭遇了动荡的年代,和大多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在漫长的看不到前头光亮的时光里,早早成家。待到学习的机会再次到来,父亲即将为人父了。生不逢时,徒唤奈何。命运的齿轮总是由时代这只不可逆转的巨手,联结着个人的种种背景和缘由,共同推动运转着——彼时,一个男人肩负的养家的责任远胜于对学业的热爱。所幸的是,这个以无数的传统工匠著称的建筑之乡,给予这个勤劳奋进的年轻人新的梦想。父亲的大半生从此都在与泥水打交道中走过。他对数字的敏感天分在这个专业上得到了良好的发挥,超强的速算和数字统计的能力,以及严谨细致的思维方式都得以充分地运用。从师徒传承,到成立一支不小的团队,南征北战的父亲有如统帅般挥斥方遒,一座座优秀的建筑拔地而起。大地上飞扬的泥土,被水泥和混凝土浇筑的建筑封闭,从此不见了天日。
时光轮回——现在,在这个并不宏大的天台上,父亲仿佛回归到大地之上,每日兴致勃勃地与泥土交流着。天边的晚霞绚烂地燃烧着,远处的海浪发出的声音似乎阵阵地袭入耳畔,他全然顾不上停下来抬头看它们一眼——还是脚下的这些泥土更有乐趣些。
父亲开垦的这片空中菜园所在的位置,三四十年前曾经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一条从县城西边的山麓奔涌而下的溪流,在穿过半个县城后分为几股支流,流经至此处,河床清浅,潺湲不息,四季水汽丰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在历史上成为连接着县城与郊外的古驿道的重要歇息地,各路的商贩、小农户都要途经此处,舟楫相会,鼎盛一时。
以当时我们家的条件,吃上粮食的温饱已不成问题,这块不大的土地本可以放弃耕种的实用意义。母亲还是坚持要开垦它,侍弄着许多她自小在乡村里熟悉的作物。她尝试着播种各种豆子,黄豆、豌豆、芸豆、黑豆、绿豆……当然,还有闽南土地上最常见的花生和番薯。这块不大的田地成了我和弟弟们的乐园,我们看见了不同豆子开出的花朵。三四月阳春天气一到,早熟的青豆、豌豆就开花了。豌豆的花最漂亮,紫色的花瓣轻盈别致,随风飘摇,犹如蝴蝶上下翻飞,香气在风里远送,馥郁芬芳。晚熟的豆子,如黄豆、绿豆则在盛夏的早晨开花。暑假的时候如果赶上八九点跟母亲到菜地里去,能看到它们徐徐绽放的过程,持续两三个小时。黑豆的花期最晚,总是要到秋分前后,别的豆子开始陆陆续续结果子了,它才慢腾腾地开起花来。黑豆的果实看起来不怎么养眼,开的花纯净洁白,很是清雅。豆子们开的花不会齐聚于顶端,大多三三两两地闪现于绿叶和茎秆之中,花朵颜色素淡,香气也淡淡的。它们开放的能力远远强盛于家里院子里的月季和三角梅,往往能持续一两个月。
7 月是高粱成熟的季节,细长的秸秆已经撑不住冠顶的重量,饱满的穗粒喝醉了酒般红着脸,低垂着头,跟小人书上画的关公似的。春季播下的花生种子在地下已沉睡了小半年,芒种过后刨开土地,像是打开一个又一个的盲盒,挖出深埋于地下的果实的惊喜,远远超越一个孩子认知世界里所有的想象。
番薯的故乡在南美洲,从明朝的时候传入我国。这种作物算起来在国内也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番薯来到中国后遍植南北,据说在南方尤其是闽南一带,繁殖得最为旺盛——这里少水、干旱的盐碱土壤,还有温润的南亚热带海洋上吹拂来的海风,竟然意外地适宜番薯的生长。父亲说,红薯曾经救活了上亿人,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据说在当时饥不果腹的年代,人们就是靠它来填饱肚子,度过了饥荒的年代。番薯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的番薯是作为杂粮来吃,不少人常会把它当早餐,或者烤熟了当零食来吃。七八月间,番薯开花了。薯蔓的顶端状如喇叭的花朵,直径有三到四厘米,白色的花边轻柔地围成一个椭圆形,花心是一小圈淡淡的紫色。离花近一点时,闻到红薯花淡淡的清香味。番薯的叶子匍匐在地面,花朵在叶片间星星点点地闪动,如果俯下身子贴近地面去看,往往能看到藏在薯叶下的三两朵薯花,羞涩地依偎着,如同家乡土地上所有矜持平凡的女子。这片宋元以来才开垦出的土地上,女子和男儿一样,刚毅、坚忍,她们从不高调地示人,却以千年来自带的蕙质兰心,轻易地征服了世界。
农产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检测技术是对有机磷农药残留进行定性定量分析。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农残分析由单一种类农残分析向农药多残留分析发展,快速、高灵敏度的分析方法逐渐受到追捧。目前,有机磷农药残留分析使用的检测方法主要有色谱法、色谱质谱联用法、酶抑制法、免疫法等。Arjmandi等人利用薄层色谱法检测稻田的有机磷农药残留[7]。近年来,毛细管柱有分离性能、灵敏度和分析速度等方面的优点,使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成为多种类型或同一类型农药多残留分析的最得力工具,广泛应用于挥发性农药的残留测定。
当然,泥土里也有意外的惊悚出现。有一年,我们坐在田垄边等待劳作的母亲,一条小蛇突然蜿蜒着向我们爬来,母亲正好回头看到,抡了棍子向它的头部打去,一下击中它的要害处。蛇瞬间昏死过去。母亲脸上却从从容容的,扔掉棍子继续忙活。不一会儿,苏醒的小蛇歪歪斜斜地爬远了,母亲也不去追它。在她关于唯物主义的朴素认知里,这厮与生俱来是泥土的一部分,只要不伤及人便放它生路,自不必取它性命。
母亲乐此不疲地与泥土亲密接触着。她每天早早地到地里去,傍晚又像看望老朋友一般再去地里走走。这片我们看起来不动声色的土地,在母亲的眼里每天都有细微的变化在进行着,她在饭桌上喜滋滋地向我们讲述。从地里归来的母亲,裤脚常常沾满泥土。她把换下的衣服放在水盆里浸泡,黄色的泥水浸染开一大片。有一回弟弟看到,说了句,好脏。母亲却说,土是最干净的。说完这话,她拎起几处的衣角,在水中晃荡了几下,再倒去泥水,反反复复几次后,水盆一如既往地洁净。
从我记事起,天气稍有转变,母亲的偏头痛就会犯,父亲带她上医院做过好几项检查,都找不到缘由,吃了各种药和偏方也无济于事。从这点上看,也许母亲天生就不适合稼穑之事,命运才安排她告别土地来到县城。即便如此,只要头痛稍稍好转,她就迫不及待地起身,到田地里转转看看,呼吸呼吸那里的空气。回来的时候,她就像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安泰一样,脚一沾地,身上如同安上了一个小马达,瞬间充满了活力。
留存在我7 岁之前有关家乡的记忆里,家家户户都是清一色的土坯房。晴好的日子里,父亲用一个砖块形状的木模具,放入和好的泥巴,做成一个个土坯,然后放在阳光下晾晒。晒干后,自下而上砌起四围的墙。墙砌好后,便是择吉日上房梁,搭瓦片。瓦片是从山里的窑洞里运来的,一片片红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院子的一角,像极了一排排罗列有序的锦鲤的鳞片。瓦片的材料取自山里的泥土,烧制后拱桥般的身躯上,略显粗糙的纹理里还残留着匠人手上掌纹的痕迹。还有灶台、房前屋后的猪圈、鸡舍,也都是用土坯垒起来的。此时的泥土不只位于低处,为人的脚力踩踏,它们有如神明,高高在上地于头顶、四周,庇佑着我们的身躯。尤其赶上狂风骤雨的天气,在外的归人进入其中,身体立刻被温暖和干爽包裹住。家人围坐,灯火可亲,手捧着粗瓷大碗,就一口清甜简单的番薯汤下肚,任外头风萧萧兮雨潇潇,内心安然无惧。
小时候,我最喜欢大雨滂沱时泥土散发出的味道,清新中夹杂着淡淡的青草味儿,恐怕世上的顶级香水师也无法调配出这种气味。尤其是盛夏,雨下得越急,雨点儿越大,这种味道层次感就越强烈。刚开始,雨珠迫不及待地想要与泥土相拥在一起,颗颗圆润饱满,坚实有力地敲打在炙热的土地上。泥土也不甘示弱,紧紧拥抱住最先落下的雨珠。这时,泥土颗粒所蕴藏的精华散发出来了,犹如刚打开包装的巧克力,颗颗清香甜美。这时,我干脆脱去鞋袜,光脚踩在泥土上,挥舞起竹编的大扫把去追赶低飞的蜻蜓。它们像天空中的小精灵,在屋檐下翩翩起舞。
霎时间,天地之间弥漫着浓郁的泥土的气息。
雨雾中,家家房顶的烟囱里,炊烟照常按时地升起,锅与勺相碰发出聒噪又曼妙的鸣奏。一锅的饭菜还未揭开盖,香气已经在屋前屋后氤氲飘散。雨停了,大人孩子都端着一个个瓷碗,站在门口或路边,吃得津津有味。那时的食物里,没有过多的油盐和调味剂,白水青菜也吃得啧啧有味,唇齿生香。那些来自大地腹中的蔬菜瓜果,挟着泥土的气息落入口腹,让平淡无奇的一日三餐,都有滋有味活色生香起来。
喜好清净的祖母固执地认为,天下最好的职业是做一名像祖父那样的教师——绝对没有之一。一根粉笔,两袖清风,指缝自然不会嵌入洗不掉的泥土,脚下穿着的鞋子永远沾不到丝毫的泥土。还有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走到哪里都清清爽爽,很精神。一辈子只穿斜襟大裾衫的祖母,反反复复地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将与泥土隔绝的想法嵌入儿孙们的脑海。我们似乎也很认同这样的想法,信誓旦旦地想跳出泥土,跳入流光溢彩的城市里。我们家族这一支的第三代——我,我的兄弟,我的堂亲们,林林总总二三十人,外出求学后无一例外不再回到故乡。就如我,16 岁那年外出求学后便继续留在了这个城市,如今我在这里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我曾经在家乡生活的时间,早已把他乡认作了故乡。
“泥土”二字,俨然与我们生疏太久了。
现在的城市里,和土有关联的就是农贸市场,如果要感受泥土气味就要早早去那里走动,去迟了,可能就打扫干净,是另一种味道了,只好等明天早上再来。
周末西街的清晨,一定是最先被肃清门广场一带市场的喧闹声唤醒的。从入口的两侧开始,塑料筐、泡沫箱里摆满各种产品,满目的青绿橙黄。再往前进入,一字摆开的摊位上各类物品就更为丰富了。走到第一个通道,再右转到达第二排的摊位。这个摊主的菜是我女儿指定的。这里的包菜叶片浑圆肥大,马铃薯裹着地里带来的泥土的颗粒,块头却偏于小家碧玉。萝卜也不如别家的肥硕,尤其是零零散散堆在角落的红萝卜,身躯中部的结节处常常附着大坨湿润的泥块,显然是一早拔出来后便直接扔入麻袋,然后抵达这里,到了摊位上又被主人从麻袋里一骨碌地倒出来,不再去管它了。
女摊主似乎几十年间都是一身不变的装扮——高筒的水靴,裤脚高高地挽起,腰间的一条围裙永远是一片湿漉漉的。和其他摊位上从菜贩子手中批发来的大棚种植的蔬菜不同,她的菜都是十几里外的洛江老家种的,家里人手本就不多,每天的收获也有限,如果不赶早,稍迟一步菜便被抢光。
有时候,摊位上会偶尔立着一两把刚刚割下的米蕉,因为连着秆子,直立着明显高于台面上果蔬的高度,很是显眼。尚未成熟的秆子和果实表皮,都带着鲜嫩的青翠,田园的气息扑面而来。有人经过看到,觉得成熟的时间尚久,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也可以把它作为家里的装饰,到成熟了再一颗一颗掰下来品尝,真是两全其美,何乐不为,便抡起扛在肩上,带走。
十年前,我从老城区换到了现在居住的地方。这里道路开阔,交通便利,尤其周围矗立着好几家大型的超市,让人从视觉上一眼就感受到新区的气象。超市里24 小时灯火通明,敞亮洁净,货架上的物品排列有序。尤其是夏日里冷气不间断开放,让每个进入的人身心舒畅,购物也如同旅行般轻松自在。食材区域分工明确,包装细致——哪怕是一根葱,在附上透明的薄膜或装入袋子之前,也都要经过细细的净化,去除掉泥屑,每一支根须都洁白如玉。
吃过一段去超市采购来的食物,倒也没有觉出异样。有一天,女儿突然在餐桌上指着一盘萝卜说:这个萝卜没有萝卜味。天下的萝卜与萝卜之间,还有不同的味道吗?这个8 岁的小女生一脸认真地说,有,就是泥土的味道。我哑然失笑。我和先生细细咀嚼着,似乎也觉得味觉中少了点什么。少的究竟是什么呢?大约就是女儿说的泥土味儿吧。必须承认,越来越精细的食物和过分的调料、添加剂钝化了人类原本敏锐的嗅觉和味觉,在这点上,孩童单纯的味蕾的确比大人的更敏锐可靠。
从那以后,每到周末,我还是起早去往老城区的菜市场,穿梭于熙熙攘攘之中。还是一如既往,没有客套话,看准了,就指指不同的箩筐说,这个来两斤,那个要五颗。不用费口舌讨价还价,不用看秤头的星点刻度,摊主便麻利地称好了递到面前,报出价格,然后我付好钱拎了走人。一切进行得迅速明快。
天光从老菜市场上方高大的透明顶棚投射下来,明亮又有些模糊,如同许多朴素粗糙的旧时光里,许多乡间独有的泥土的气息渐渐升腾,弥散开去。
假期里,7 岁的侄子随母亲回到老家。他最乐此不疲的事情,就是跟着父亲到顶楼的菜园里拔萝卜,或者拿着一把小铁锹,帮忙翻搅泡沫箱里的泥土。他似乎对泥土有天生的亲近感,一点儿不嫌弃衣服会沾染到泥土变脏。
我问他:泥土是什么味道?
他捧到鼻子前闻了闻,说:苹果的香味。
芬芳的泥土里,一切都欣欣然的样子。
年复一年的光阴中,人终究要活得像草木那般,落地生根,站立在泥土里,神采飞扬,当风有声,最后,零落成泥尘,轻轻融入大地深处,唯有香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