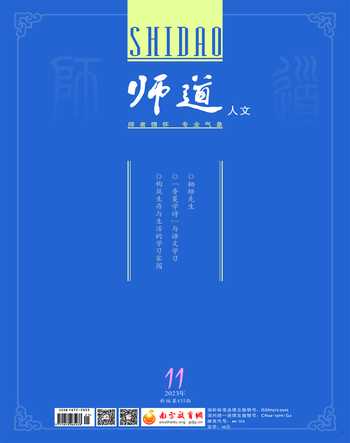刊林撷思
人文学归根结底是认识人的学问。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认为,认识物与认识人需要作为两个极端来对照。物是纯粹死的东西,它只有外表,只为他人而存在,能够被这个他人以单方面的行动完全彻底揭示出来。而认识人的极致则是在上帝面前思考上帝,是对话、提问、祈祷。人文学因此需要对话的方法论,而一个特色随之产生,那就是在人文学的研习中,不只认知主体会去理解认知客体,认知客体也会回报以能动性,去影响改造认知主体。文学教育作为人文学教育的一个种类,受教育者也是在和文学文本、文学作家、文学传统对话,一个人阅读了文本这一精神产品,精神产品上蕴含的作家心智也会参与对读者精神的形塑。这种对话以及由此成立的心灵改造,其实就是人文学的事功。
人文学心灵建设的方法有多种,陈平原谈及语文教育时则认为,过于直接的道德说教,过于强烈的伦理诉求,易引起学生反感,效果并不好。如传统中国虽强调文学与教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诗言志”与“文以载道”就大不相同。套用到语文教学,更让人欣赏的则是风流蕴藉的“诗教”。我想提出“诗教”作为语文教育的一个推荐方法是十分可取的。诗教,其实也就是用文学来进行教育,但这个词更多地包含了古典的渊源。在春秋时期,孔子被记载下来的言论就屡次提到“诗教”的意义,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比如谈论诗之“兴观群怨”的功能。在上古时期,“诗教”的起源其实是一种外交辞令和政治素养,是贵族教养的一种体现。在之后的岁月里,它逐渐有了更多用文章进行人格修持的内涵。古代“诗教”借助于文学而使人“温柔敦厚”,“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它是一种合群的教养,纵使有所“怨”,也是怨而不怒的态度,因而在古代社会里不着一字地规范了人际、人伦的种种隐曲,而共同体也是这样得以凝聚的。至于现代诗教,我赞同学者姜涛的归纳:“现代‘诗教强调‘内面自由,而二十世纪的革命‘诗教、集体主义‘诗教,则提倡‘爱憎分明,用‘大我来克服‘小我,在奔跑的历史中校正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手势。”(姜涛:《今夜,我们又该如何关心人类》)如果我们认为现代诗教的传统可以溯源至波德莱尔的诗歌生命,那么这是一个从世界中醒觉而追求自由的、个体与世界充满张力的诗歌自我,中国“五四”的觉醒者、铁屋中的呐喊者们,也在这种类似的情感与境遇中借着舶来的文艺和思想而掀起了社会的更新运动。革命的诗教也在这条延长线上,只是轻重方面有所转移,以加入一个大的洪流。借助欧西资源而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对自我的肯定,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反叛性起点,我们因此也可以说,现代诗教有自我肯定的、自爱的传统。现代诗教最终流向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因而这也是一种发展出了共同体维系方法的、合群的诗学。自爱与群的联合,看似两端,实则是现代诗教的一体两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传统。
但在当下的语境里,自爱的、合群的精神状态或许并不是那么普遍。那么当下的气质更可能是什么呢?陈平原有一个观察,那就是当代的一些文艺更倾向于回到内心生活,而这可能是一种社会中主体普遍的无力感所致。这是一个文学史上屡次出现的现象,在无力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刻,人们就向内收缩,回到了内心。内心的深渊或富矿的挖掘,带来了某种繁华到颓废的先锋美学,而内心的沉溺也在加剧人际联结的衰弱,如果是这样一个涣散的、无力的,但是同时又极度焦虑和恐惧失败的年代,我们可能确实需要对自爱合群的诗教做一些召唤。但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应该用更详细的谈论说明一些中国社会精神上的当代特色。
(中略)诗教也不一定只要温柔敦厚,它有时是神奇的本质直观,让人在当头一棒后理解了世界上多一些深一些的事情,这未尝不让人明智、被疗愈。确如陈平原所言,真的研习人文学得从人生忧患上用功,是不能太富贵、太精英、太顺畅的。如能深入体察和理解当代某些症候性的普遍感受的因由和层次,一种解救的希望、心灵的建设,是可以期待的。世界是那样正负面经验的参差,如果直面困顿且知道自爱的重要,把自爱的源泉开掘在对世界复杂性、悖论性乃至残酷处的了悟上,这将可能是一种深厚的理解之爱,它背后是更高级的心灵的健全。
——摘自康宇辰《当代“诗教”的可能性》,《读书》2022年第1期
儿童的文化品性主要体现为游戏精神的追寻及人文价值的求索。在数字技术与现代儿童的结合中,资本裹挟着技术,技术追逐着资本,儿童的文化价值遭遇技术资本冲击。当儿童文化品性代表的精神人文价值与技术资本代表的物质价值在儿童文化领域碰撞时,便不可避免的滋生现实冲突,二者的价值冲突,主要体现在儿童、技术、资本、游戏、教育等的交互性矛盾。
(一)儿童的可塑性为技术影响提供文化空间
(中略)儿童的可塑性使技术对儿童的发展呈现正负双向影响。符合儿童人文品性的技术,促进儿童的正向发展。文明历史的进化中,儿童作为人类一道,因技術进步对人的身体解放得到精神智慧发展,内化精神世界的文明与进步。技术发展过程中其附带的具身祛除、精神消耗等衍生效应,致使儿童负向发展。儿童因其未成熟性而缺乏理性判断和自我控制能力,尤其是在音色、画面等视听觉方面都极具精神控制的网络游戏面前,缺乏价值判断。传统游戏的具身认知及体验功能,现代游戏的文化衍伸功能,需要教育调和以呈现和谐游戏生态。
(二)亲资本的技术行为破坏儿童游戏生态
童年是一个社会历史文化概念,其核心特征在于社会性建构。集自然生物性、社会文化性、个体差异性于一身的儿童,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时空中建构童年成为人类文化的特殊存在。儿童依据个体的发展需求及社会发展需求进行着社会文化建构,在技术与文化共生中实现着儿童文化的时代演进。儿童网络游戏的盛行,既是数字化技术与现代文化共生的产物,又是儿童内在精神驱动的产物。技术环境的新异性诱导着儿童对世界的惊奇,无限的网络世界吸引着儿童前往探索的动力。
然而商业技术亲资本的文化本质,以资本驱动的魅惑吸引着好奇又好动的儿童,侵蚀着儿童的文化生活及成长空间,潜移默化中改变儿童文化品性,导致儿童自我的缺失、身体的忽视及精神弥散。商业文化背景下的童年建构,缺乏儿童成长的自然、人文的环境背景,缺少儿童的具身认知及经验体会,儿童跟随他者安排,失去了儿童文化的自我主动建构机会。儿童在文化“已成”的状态下,“享受”被设计和被预期的文化,在目的性引导下失去了文化的创造力之源,失去生命探源的自然动力。需重新定位儿童的生态文化视角,建构童年文化,回溯童年游戏品性。
(三)精致化商技模式无视儿童人文特征
(中略)商业文化活动以精致的包装褪去儿童的人文本质,使儿童游历于商业文化带来的精神幻象:幻想艺术的想象狂欢弥补了儿童无法清晰表述的内心需求,且以游戏性呈现。这种以儿童为参与对象、专为儿童打造的幻象游戏文化,从根本上说并非儿童文化。回归儿童本质,关注儿童成长的文化环境且为儿童创造的主位性文化,才凸显儿童文化的人文性。因此,需要祛除商业文化对儿童的侵扰,祛技术之魅,正视儿童的文化品性的变迁:重新发现儿童的身体,平衡物质与精神的游戏生态,减少精神幻象刺激,寻求自然的游戏生态,在优秀文化引领下还儿童文化环境以自然及科学品性,成就儿童的健康成长。
(四)迟缓的教育应对忽略边缘化的儿童技术
(中略)技术的儿童文化性,需要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核心价值引领。“媒体或文化权利不应该孤立于有关儿童社会及政治地位这些牵涉较广的问题来看待……对于文化权利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政治权利的要求”。这种政治权利即政策、法律法规所规定儿童文化自主的基本权利,数字技术虚幻和封闭了现实中儿童的基本权利。我们已经无法避免地面对儿童的权利保护,必须主动祛除无视儿童、轻视儿童及歪曲儿童的传统文化理念,在支持儿童技术与儿童文化的发展中找到平衡点,保障儿童的基本技术权利和文化权利。教育依据技术媒体服务儿童发展的取向,思考减少儿童的人机虚拟互动和符号创作,回归儿童的现实主体性,回归真实的自然、游戏及文化。
——摘自贾琳琳、张姝玥《技术文化共生中儿童游戏品性嬗变与教育应对》,《中国电化教育》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