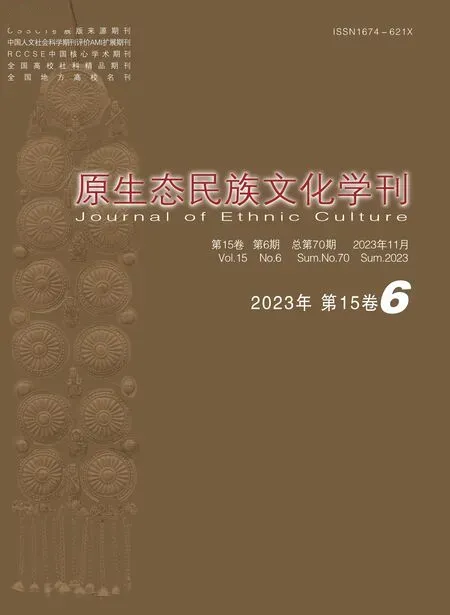清前期西南矿区“夷民”的生存策略与边疆秩序
——以东川府为中心
李培娟
一、问题的提出
清代中国的矿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各类矿种的产量均有大幅增长,在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矿业在当时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上升,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二千年”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在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中,云南铜矿的成绩尤为突出,当时各省报开的铜矿中,“云南铜矿尤甲各行省……秦、鄂、蜀、桂、黔、赣皆产铜,而滇最饶”②赵尔巽:《清史稿》卷124《食货·矿政》,中华书局,1977年,第36666页。,甚至有学者认为当时滇铜铸出的钱约占全国铸钱额的80%~90%③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第23-24页。。从云南省内来看,东川府又是滇铜最为重要的产区④全汉昇:《清代云南铜矿工业》,《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卷第1期,1974年12月,第155-156页、第178页。,在产铜最盛的清中叶,东川府铜产量占云南铜产量的70%以上⑤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第31页。。
然则,矿业兴盛的背后,是整个矿区社会陵谷沧桑的巨变。在清康雍年间矿业兴起之前,以东川府为代表的西南矿区原本多为“夷人”①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文本的准确性,本文中的“夷人”“夷民”“夷窟”等词均采用明清史料中原本的记载,而绝非代表笔者对少数民族具有歧视性。在本文关注的东川府地区,“夷人”主要是彝族先民、苗族先民等,明清史料中把这些非汉的族群统称为“夷人”。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其地林深箐密、夷多汉少,有一套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在汉文献的话语体系中,常常称之为“夷窟”。随着清初矿业的发展,来自外省、旁郡的移民迅速汇聚于此,一时间“夷区”五方杂处、熙熙攘攘,“夷民”、移民、清政府、土目等各方势力在其间活络互动,这一时期矿区各种力量的互动对边疆社会秩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实际上,以往对清代西南矿业开发的研究可谓发蒙较早、硕果迭出,其中针对云南铜矿业的专门研究尤为丰硕,从20 世纪40 年代严中平对云南铜矿业的整体情况进行高屋建瓴的论述,到近年来马琦从国家资源的层面去理解清代滇铜的开发问题,对云南铜矿业的研究一直赓续不断②相关研究参见严中平:《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彭雨新:《清代前期云南铜矿业及其生产性质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陈征平:《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的制度演化及“官治铜政”的特征》,《思想战线》2003年第5 期;邱澎生:《十八世纪滇铜市场中的官商关系与利益观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4 年,第72 本第1 分;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 年第3 期;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因篇幅所限,兹不赘列。。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多侧重于矿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矿业政策、矿产量、矿运路线、矿税征收等角度,而较少涉及矿区的社会史,“人的历史”常常隐没在“矿的历史”之下。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矿区的“人”及矿区社会的变迁,如杨煜达在考察不同时期铜产量的基础上,分析了清中期铜矿业发展对滇东北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③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温春来剖释了“夷制”瓦解之后,伴随着矿业开发和移民涌入,西南矿区商业市镇兴起的历程,还分析了矿区的两类市镇(交通要道市镇和矿区市镇)不同的发展命运④温春来:《矿业、移民与商业:清前期云南东川府社会变迁》,《区域史研究》第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1月,第129-132页。;马晓粉则关注与铜矿开发相关的内地移民对矿区社会经济的贡献⑤马晓粉:《清代云南矿业中的内地移民及其作用——以铜矿为中心的考察》,《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总体来说,这些研究聚焦于矿区环境变迁、市镇兴起、商人的活动等方面,比较注重“移民”及其活动,但矿区的另一个重要群体——“夷民”,他们作为矿区的原住民,曾经“蔓延山谷,种类各殊”⑥雍正《东川府志》卷一《户口》,《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789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97页。,拥有非常可观的数量,是地方社会曾经的历史主角,但在以矿业和移民为视角的研究中,他们在时代剧变下所作出的生存抉择随其微弱声音常常被遮蔽掉。
近年来,随着一些彝文毕摩经文献的整理出版以及《东川湖广会馆传书》等清代会馆资料的利用,加之田野中收集的碑铭、族谱、村志等民间文献,使我们得以窥见矿业开发背景下清政府、地方土目、外来移民、原住“夷民”等各方势力之间的活络关系,重新审视“夷民”在清初社会变动下的生计抉择以及矿业开发背景下“夷疆”基层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比起以往的研究,本文更加重视“夷民”在此过程中的能动性及其生存策略。
二、“夷窟”及“夷民”的采矿传统
东川府地处滇东北,东与贵州大定府相接,西与四川宁远府相连,境内峰峦起伏,金沙江、牛栏江分别从其西境、北境穿过,是传统时期的彝族聚居区。在宋以前,此地因跋扈而“靡得而统焉”,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沐英开滇,东川土酋禄鲁祖望风归附,明王朝授其东川土知府,东川府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中,先隶云南,后又改隶四川①乾隆《东川府志》卷三《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10》,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但整个明代东川皆叛服不常,中央王朝常常无法对其进行实质性的统治,这片位于滇黔蜀三省交界区的广阔土地在明代的里甲赋役系统中仅“编户一里”,甚至在云南巡抚鄂尔泰的上奏中,直接称东川“明季并未归版图”②《云南巡抚鄂尔泰奏陈东川事宜折》(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页。,可见清以前中央王朝对此地控制的薄弱。
甚至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东川改土归流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这里仍然“夷多汉少”③《清世宗实录》卷六十一,雍正五年丁未九月庚辰。,留给外来官员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夷窟”。在雍正《东川府志》中,东川府知府崔乃镛称:“夫东,夷窟也,政教、风俗、人物、事实荒略不备。”④雍正《东川府志·序》,《国家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789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6页。在乾隆《东川府志》中,东川府会泽县知县许肇坤亦称,东川“号夷窟,叛服靡常,隶蜀时为土酋禄氏据,羁縻而已”⑤乾隆《东川府志》卷二十《艺文·新建魏公祠碑记》,第153页。。不难看出,在地方官员眼中,当时的东川常常跟“夷窟”这一标签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跳出府县城,到高山深谷间“夷民”自身的社会中,会发现被称为“夷窟”的东川绝非一盘散沙。温春来结合汉、彝文献中的历史叙述,发现宋至清西南的局势非常复杂,并非只有一个大理国与中央王朝相对峙,实际上在崇山峻岭间还有罗殿、自杞、阿者等政权纷错于大理国与宋王朝之间,形成多“国”林立的西南社会⑥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33-45页。,而东川府所在地即为这些众多政权之一,被称为“阿芋陡部”。在明清时期的官私文献中,东川府的土著民族被称为“倮罗”“夷民”等,其最高首领为彝族禄氏土司,汉文献称之为“土酋”“夷酋”。在这套独特的政治架构中,禄氏土府之下又有营长、头目⑦“头目”在史料中也常常被称为伙目、夷目等。,乾隆《东川府志》亦称东川有“六营长九伙目”,营长、头目的身份比较复杂,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土酋的兄弟、子侄,也有些营长、土目可能并非禄氏家族中人,而是地方实力派。原则上,土酋“辖有营目,表帅雄师”⑧乾隆《东川府志》卷十四《秩官·附六营长九头目考》,第115页。,营目是效忠于土酋的,但土酋对营目的控制力也很有限,营目发生叛乱而倾危土府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营目有时还与东川外部的势力相结合。
在“土司——营目”的政治架构之下,是人数众多的“夷民”。据乾隆《东川府志》,东川府“夷民”有六类:黑倮罗、白倮罗、干倮罗、苗子、鲁机、孟达后人。其中,黑倮罗等级最高,营长、伙目家即为黑倮罗,其家中“多用缎帛”,且“有夷书,字如虫蚓”。越往后则种族的混融性越强,如“鲁机”为明时流寓于此的赵、杨、李三姓之子孙,从明至清初东川府彝族的姓氏特点来看,赵、杨、李三姓很可能为汉人,而“孟达后人”在史料中则明确被称为“久变为夷”之汉人①乾隆《东川府志》卷八《户口·种人附》,第71页。。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清初以前“夷多汉少”时期的东川,只有极少数汉人。至于这些汉人的来历,可能是主动迁入,也有可能是被掳掠进入,但在一个“夷人”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他们的力量极其微弱,以致其结果往往是被“夷化”。
上述六类人群之外,还有大量被汉文献称为“荒夷”“野夷”的人群,他们的归化程度更低,几乎在国家的赋役系统之外。清初,云南总督庆复在奏折中言及东川的“野夷”时,称“云南、四川俱未收管”,甚至“从古不入版图”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68-276页。。从地理位置来看,“野夷”多生活在金沙江、牛栏江流域的险要地带,又常被称为“江外野夷”,他们一方面流动性极强,“暖则登山,寒则就水,迁徙不常……沿江西岸驰骤往来,为鬼为蜮,出没不常,其巢穴岩蹊盘谷,取路必纡,登临必曲,转折必危,攀缘必隐”。另一方面,这些人群数量众多,在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的一次追剿中,见“野夷如蚁,沿坉而上,对山可见”;雍正八年(1730年),“野夷”跨过金沙江之蜈蚣滩,“入乌蒙抢掳男妇数千”③乾隆《东川府志》卷四《疆域·边要附》,第42页。,拥有如此实力,可想见其人数之众、势力之盛。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地区的“夷民”一直有采冶铜矿的传统。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书中就有记载:“铜有赤铜、白铜、青铜。赤铜出川、广、云、贵诸处山中,土人穴山采矿錬取之,白铜出云南,青铜出南番。”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赤铜》,刘衡如,刘山永校注,华夏出版社,第330页。明末曾亲履西南的徐霞客,在其广为人知的游记中,还曾记载了在滇东北看到东川驼铜的道路,称“自寻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径多错,乃今日东川驼铜之骑所出”,⑤徐霞客:《徐霞客游记》,朱惠荣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第429-430页。彼时东川驼铜的马匹已经走出了专门的道路,可知明代东川铜运量已有一定规模。有理由相信,明代东川“夷民”对铜矿开采具有一定的规模,且有相当数量的东川铜外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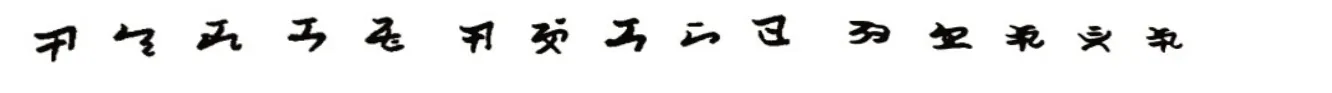
汉语意译:有铜匠银师,铜饰做出了,罗人来使用①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三十五卷《滇彝古史》,师有福、满丽萍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97页。。
不仅如此,根据彝文的记载,“夷人”铸造铜锣、铜雁、银鹤、铜虎、金虎等器物用于祭祀,且其工艺颇为精湛,制作出来的器物往往栩栩如生,“银鹤似真物,铜虎映日光”②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三十五卷《滇彝古史》,师有福、满丽萍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可见,“夷区”不仅有采炼铜矿的传统,还有一定的铜器制作水平。但据彝文毕摩经书,这些技艺似乎只是掌握在特定人员手中,且这些物品主要是用来献给彝族毕摩和君王,彝文称:“铜器来祭天,铜器嵌鸟头,铜王做出了,铜鸟更逼真,铜饰献自非”③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三十五卷《滇彝古史》,师有福、满丽萍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98~199页。,其中的“自非”即毕摩“自屋”和君王“非审”。
综上可知,清初以前作为西南矿区典型代表的东川府是一个中央王朝统治力量极为薄弱的“腹地边疆”,在“土酋——营目”的政治架构之下,有众多不同等级的“夷民”,还有部分很难被管控的“野夷”。这些夷民有采冶矿产的传统,但采炼矿产的技艺似乎只是掌握在“铜匠银师”等特定人员手中,且矿产品主要是用于祭祀以及献给毕摩和君王。
三、从“夷目”到里长、甲首
“土司——营目”政治体系的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央王朝对西南矿区的深入管理。虽然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东川已经改流,但是直到雍正四年(1726 年)三月,云南巡抚鄂尔泰上奏时,依旧对东川的状况深表忧虑:“四川东川一府,原系土酋禄氏世守地方……川民不肯赴远力耕,滇民亦不敢就近播垦,故自改土以来,历今三十余载,风俗仍旧,贡赋不增。”④《云南巡抚鄂尔泰奏陈东川事宜折》(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页。《清史稿》亦云:“东川虽已改流,尚为土目盘据,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⑤赵尔巽:《清史稿》卷288《列传七十五·鄂尔泰》,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30页。可见改流之后,由于营目势力的根深蒂固,清政府依旧无法对东川实行有效的田赋征收,“夷疆”社会的管理呈现出力有不逮之势。
东川这样的情况在西南地区并非特例,同一时期的黔西北威宁府、黔西南南笼府等地亦与此相似。《清实录》载:“云南东川府会理州,贵州威宁府属之阿底盐仓等处,永宁之各夷屯,归流已久,其土目各治其民,流官向土目收粮。”⑥《清世宗实录》卷60,雍正五年丁未八月乙未,中华书局,1985年,第916页。黔西南《南笼府志》亦载,当地原住民“心忠直恋主,虽改土归流数十年来,犹听土目之子孙约束……苗民耕种粮田输纳,而外出谷一二斗于土目,是主佃之名犹存也”⑦乾隆《南笼府志》卷二《地理》,乾隆二十九年刻本,第19b页。。不难看出,即便在改流之后,清政府对地方税粮的征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原有的一套政治秩序来完成的,即土目向夷苗佃户收粮,流官又向土目收粮,“夷苗”佃户心中的“主”是土目,而非清政府指派的流官,真正向朝廷纳税的,只有土司和营长、土目等。
对于上述现象,清政府从主佃观念出发,解读为“夷民”受土目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代官私文献中多次表现出这样的意思,连鄂尔泰也对土目深恶痛绝,控诉东川“归流之后仍属六营盘踞,诸目逞凶,岁遇秋收辄行抢割”①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五《请添设东川府流官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在与东川相邻的乌蒙地区,清政府亦力陈“夷民”生活的惨状,其辞诸如“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娶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不见天日”②赵尔巽:《清史稿》卷288《列传七十五·鄂尔泰》,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30页。,把土司描绘为罪大恶极、贪婪无度的形象,而土民成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群。
实际上,如果回到区域社会的具体情境中,“夷民”向土目交粮只是地方社会因袭多年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彝族土司岭光电的回忆录中,改土归流后他到外地求学,彝民每年都会派人去看望他,“他们一见我就痛哭流涕,要求我回去当土司”③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页。。这些情况跟官方描述的“夷民受压迫说”显然是相悖的。为何会发生这种悖情呢?笔者以为,“彝民受压迫说”一方面是清政府为破除土目问题而造势,为打击营目力量提供合理性;另一方面,“夷民”也在利用官府的话语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借官府的力量来摆脱营目的控制。温春来在黔西北的研究中也发现,原住民并非“憨而恋主”“暴虐不怨”,实际上他们懂得利用制度争取自身的利益,甚至能利用国家的力量对抗主奴之争、主佃之争④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57-274页。,“夷民”并非单纯被压迫的角色。
为了达到破除营长、土目势力的目的,清政府试图“将土目迁往腹地,其催粮之里长、甲首令内地轮流充当,其土民悉令剃发,男妇俱照内地服饰”⑤《清世宗实录》卷60,雍正五年丁未八月乙未,中华局,1985年,第916页。。这些将土目迁移、令“夷民”剃发易服的政策无疑打压了营目的势力,挑战了东川原有的社会秩序,雍正八年(1730 年)的东川营目叛乱即与此相关⑥乾隆《东川府志》卷三《建置》,第26页。,当时东川营目发生叛乱,清政府通过武力直接镇压,甚至斩杀了一部分营目。
但需注意的是,上文中“催粮之里长、甲首令内地轮流担当”的措施并未得到彻底执行。囿于史料的阙如,我们无法确知担任里长、甲首、乡约、保长的是何人,但从后来村史中留存的一些集体记忆来看,里长、甲首等并不一定都是由内地汉人担任,东川矿区拖落村村史《乾圆山下》显示,曾有一些彝族人担任乡约、保长,比如东川阿旺镇拖落村清代的朱乡约、马乡约均为彝族,朱乡约“性善喜施,常帮助困境中人”,马乡约则“性幽默机智,善与官差周旋”⑦王永军、张金权:《乾圆山下:拖落村村史》,晨光出版社,2016年,第120页。。由此可知,东川的里长、甲首与原先彝族社会的掌权阶层是有所重叠的。试想,内地移民来到夷区之后连语言都不通,一向桀骜的“夷人”又岂会轻易服从汉人的管理,规规矩矩纳赋应役?贵州南笼府的苗人就因“语言不通,名姓难辨”导致征粮不便,改流之后官府“惟有土目以统辖之寨把以分管之”,①乾隆《南笼府志》卷之二《地理》,乾隆二十九年刻本,第20b页。由外来移民担任征粮之里长等应该只是在官方力量控制力较强的府城附近而已。
这种现象在西南地区绝非东川所独有。在黔西南,张楠林的研究亦发现田赋的具体征收过程中,官府不得不依赖地方原有的土判官、营长等统治阶层②张楠林:《明清时期黔西南的“土流并治”与赋役征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第75页。。在滇东北彝族精英后代的口述史中,安恩溥后人也明确说道:“土司取消后,土目并没有消除。”③吴喜编著:《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家族口述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有理由相信,即使在国家力量深入之后,彝族的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并未突然消失,虽然“营长、伙目改立乡约、保长”,但是部分“夷目”随形势而巧妙地“改头换面”,依旧在地方上延续其影响力。
在基层行政建置上,雍正六年(1728年),东川“改六营长九伙目地,置四乡八里”④乾隆《东川府志》卷三《建置》,第26页。,但这四乡八里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之前六营长、九伙目的设置,很多乡、里对应的地区其实就是之前六营长、九伙目分别管控的地区,只是名字改变为“归治”“忠顺”“向化”等士大夫们喜欢的风格而已,其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清前期东川府“六营长九伙目地”改“四乡八里”情况⑤根据乾隆《东川府志》之《秩官》《户口》部分整理而来。
当然,原先彝族的“六营长九伙目地”与后来编立保甲之后的四乡八里并不是严格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四乡八里编立保甲,分属巧家经历、者海典史、待补、则补两巡检司”⑥乾隆《东川府志》卷之十四《秩官·附六营长九头目考》,第115页。。换言之,四乡八里其实还在之前的“六营长九伙目地”的脉络之下,特别是之前的六营因其地处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依旧是东川基层社会治理的骨架。不难看出,清政府的里甲赋役体系利用了原先“六营长九伙目”的政治架构,对西南矿区的基层社会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因其旧制的,这些变化实际上对于基层社会并没有伤筋动骨,进一步可推知,彝人的力量并没有在国家权力深入之后彻底消失。
综上,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东川府改流之后,“土司——营目”政治体制的存在制约着国家统治的深入以及矿业的发展,清政府为破除土目的势力塑造出“夷民受压迫说”,“夷民”也顺势借助中央王朝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将土目迁往腹地,其催粮之里长、甲首令内地轮流充当”的政策并未在基层社会得到彻底落实,部分夷目摇身变为里长、甲首,依旧在地方上延续其力量。种种迹象表明,清代西南地区的基层制度,在脱胎换骨的表象下,也不乏很多因其旧俗的延续。
四、移民的涌入与厂矿劫掠、土地纠纷
康雍以降,随着清政府对富饶铜矿的东川府的控制逐步深入,加之官府向厂民放贷的“放本收铜”政策的实施,使得开矿资本更加充足,这一时期可谓“资本、劳力、技术与丰富的优质矿藏结合”①温春来、李贝贝:《清初云南铜矿业的兴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17页。,铜矿业进一步发展乃至日臻鼎盛,包括东川府在内的西南矿区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大量移民涌入东川。“放本收铜”政策实施之后,形成了“铜厂大旺,鼓铸新添,各省其旁郡民聚二三万人,其娶妻生子,凿井耕田”的局面②乾隆《东川府志》卷八《户口·种人附》,第72页。。在官方的记载中,乾隆《东川府志》的编纂者称:“东川一带地方银铜铅锡各厂共计二十余处,一应炉户、砂丁及佣工、贸易之人聚集者,不下数十万人。”③乾隆《东川府志》卷十三《鼓铸》,第95页。在民间留存的清代会馆碑刻中,从江西迁入东川的人也不禁感叹道:“溯前之始游兹土者,寥寥数人耳……今群萃同处,往来络绎,名成利就者几何辈!”④乾隆二十七年《万寿宫重修碑记》,现存于云南省会泽县江西会馆旧址。笔者要感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温春来教授于2012年田野调查时抄录碑文,并无私地分享给笔者使用。可见矿业兴盛之后东川人口的骤增、社会环境的巨变。
另一方面,矿业的开发还促进了原住民的入籍。前文提及之“野夷”“荒夷”,便是在矿业开发的大潮中进入国家的统治秩序的。为了满足滇铜京运的水路需要,清政府于乾隆五年(1740 年)动工开修金沙江河道,在勘探时发现金沙江“沿河千余里,凡属荒旷之区,夷徭之境”,这些地区几乎在版图之外,历任文武官员不仅无法管束,甚至在征税时“畏滋夷衅,从未催征,相循垫解”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直到云南总督庆复查勘金沙江河道时才发现。对于这些游离在统治之外的人群,清政府准备好银牌、红绸、布匹等,“晓谕各头人,俟霜降瘴消之后,尅期投出,永为良民”⑥《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第271页。。当时投出之夷民“计共黑白夷猓九百六户”,涉及21个村寨。⑦《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第272页。清政府将这些川滇二省皆无法管束的民众“造具户口”⑧《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第273页。,正式纳入国家的统治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矿区不仅人口数量大幅增长,人口来源也日趋复杂,从现今东川府遗存的清代会馆遗址来看,仅府城就有湖广、江西、江南、四川、陕西、贵州、福建等省级会馆,还有宝庆、衡州、临江等府县级会馆。在矿业运输的交通路线上,也兴起了一些商业市镇。矿区人员流动性较强,往往厂兴则聚、厂衰则散,呈现出“各厂人户去往不常”的特点,原住“夷民”又“好劫掠”,往往“伺行旅过,潜出其后,缚之”,甚至把虏获的汉人在川滇之间转卖,“狡则转卖于蜀,掠自蜀者又卖于滇”⑨乾隆《东川府志》卷八《户口》,第72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移民与原住民在同一个空间中生存,又要共享土地、矿产等资源,势必产生诸多冲突。
首先是矿厂方面的冲突。清前期曾有不少关于“夷民”与移民厂矿争端的事件被记载而流传下来,比如雍正八年(1730 年)八月,“土目张宿率贼兵劫汤丹厂,厂硐民万余一时惊散,课铜、银两抢掳一空,贼阻隘路,四方文书不通”①雍正《东川府志》卷一《建制沿革·平东川记》,第288页。。或许正是因为夷民“好劫掠”的个性深入人心,在乾隆年间朝中大臣议论是否开凿金沙江铜运水道时,反对派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沿途夷人的劫掠之患,他们担心金沙江“经历蛮境、深入夷穴……如阿都、阿驴等皆有名土族,僻处深山,一旦于人迹罕至之区载铜过往,不独乘间邀劫,为将来之隐忧”②《清高宗实录》卷127,乾隆五年庚申九月丁酉,中华书局,1985年,第866页。。在当时官员的眼中,东川“夷人”的抢劫和滋扰是矿厂经营的一大障碍,“米粮坝、蒙姑、汤丹、大碌两厂,处处均关险要,稍一疏防,即滋骚扰,案牍繁多矣”③乾隆《东川府志》卷四《疆域·边要附》,第42-43页。。清代四川冕宁县彝族档案中,也记载了大量“夷民”与移民之间在矿厂方面的争端案件,比如雍正年间当地“番蛮”见汉人进入附近区域挖矿,于是进行武力驱赶,“共去一百多人,杀有十多个汉人……还绑了五个来,别的也有走了,也有落在河里淹死了”④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四川省编辑组编写:《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56页。。
除此之外,土地方面的纠纷也很突出。在政府招垦措施的鼓励下,许多移民进入西南矿区承垦,还有一些失业矿工也进入附近原住民的村寨谋生,所谓“硐老山空,逃蛮寨为谋”⑤乾隆《东川府志》卷八《户口·种人附》,第72页。,这些外来移民不断侵占原住民的土地,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雍正八年(1730 年)东川府的“庚戌之变”,当时招垦新田,旁郡之人纷纷涌入,“占夺蛮产,厚放重利”,而清政府又没有及时处理土客矛盾,导致了原住民心中积怨甚多,以致“蛮饮恨刺骨,遂酿成庚戌八年之祸”⑥乾隆《东川府志》卷八《户口·种人附》,第72页。。土地纠纷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土地诉讼案的增加。
康雍以降,移民与“夷民”之间的土地诉讼案常见于官方史册,比较典型的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东川府境内因为土地租佃而产生的“拖罗土地争讼案”。拖罗位于东川府敦仁乡,距府城二十里,系楚省邓三英捐入湖广会馆,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报垦升科时,这片土地共有中田五十六亩五分八厘,一直租给“猓佃”分耕,但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湖广客民与“猓佃”围绕此地发生了长达两年的争讼,“控告两载,由县至院,呈词累牍,不可胜纪”⑦佚名:《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二《拖罗田地》,乾隆四十九年刻本,会泽县图书馆藏,第16a页。,个中缘由,双方各执一词。从外来移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借助官府的垦政取得“垦照”,获得官方认可的土地垦种权;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视土地为“祖业”,却突然被告知这些土地不属于自己,且对方手中还握有官府颁发的垦照作为凭据,原住民认为自己的产业被侵夺,于是关于土地的纠纷不断发生,甚至酿成武力冲突。
在处理矿厂争夺和土地纠纷时,官府的态度往往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发展。而在清代的西南地区,地方官府更倾向于站在外来移民一边。这种官府偏袒垦户的行为在当时应该比较普遍,清代曾以幕僚身份亲履云南、见闻颇广的倪蜕有云:“东川久为流府,汉、夷相安。自招垦之法行,而知府黄士杰颇袒垦户侵占熟田,夷民怨甚。”①倪蜕:《滇云历年传》,李埏校点,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86页。官府对移民的偏袒影响到移民与“夷民”之间的关系,刘正刚在研究清代移民与少数民族相互接触的问题时,也注意到“官方的政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②刘正刚:《清代移民开发边疆与少数民族关系——以台湾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第111页。。其实,地方政府对于垦户的袒护并不难理解,因为清政府垦政措施的制定,其意旨不外乎增加税收和巩固新辟疆土,因此官府才会想尽办法招民开垦,移民到来之后官府自然优先维护他们在土地方面的利益,当然,官府的这类做法显然是不利于地方社会的稳定的。
综上,康雍以降,矿业的开发和招垦措施一方面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进入西南矿区,从事与矿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工作;另一方面,以矿业的开发、运输路线的疏浚等为契机,大量游离在国家统治之外的人群“入籍夷乡”,进入版图。但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夷民”的入籍使得西南矿区的人群日趋复杂,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也在增加,在分享资源的过程中,“夷民”与移民曾产生诸多冲突,主要表现在厂矿劫掠和土地纠纷上。
五、“夷民”与移民的合作与交融
前引彝文毕摩经文献分析得知,“夷民”虽然早有开矿的传统,且具有一定的冶铜、制器技艺,但从事与铜矿采冶相关工作的主要是“铜匠银师”等特定人员,铜器制作出来也主要是献给君王和毕摩,大部分的“夷民”对于矿产的冶炼并不熟悉,那么,在清代西南矿业开发的大背景下,众多的“夷人”又是如何参与到矿业的开发中的呢?
虽然目前很难找到更多关于“夷民”开矿具体情况的材料,但他们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矿业采冶、运输等环节,并为矿区人员提供食用等,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连云贵总督张允随也注意到这些现象,其奏云:
夷人不谙架罩煎炼,唯能烧炭及种植菜蔬、豢养牲畜,乐与厂民交易,以享其利。其打嶆开矿者,多系汉人……现在滇省银、铜各厂,聚集攻采者,通计何止数十万人③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42页。。
张允随的奏言高度概括了“夷人”在清代矿业发展中的作用,虽然他们对于矿产开采和冶炼的事情并不熟悉,但他们在矿区物资供应、矿产品运输等方面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矿厂人数众多,且多为青壮年,张允随有云:“滇省银、铜各厂,聚集攻采者,通计何止数十万人。”④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第642页。这些众多的青壮年体力劳动者日常生活需要消耗大量的粮、油、菜蔬、肉类等,而矿山又多位于自然条件恶劣的高山或深谷中,正所谓“凡厂,皆在山林旷邈之地,距村墟、市镇极远”⑤王菘:《矿厂采炼篇》,吴其濬纂:《<滇南矿厂图略>校注》,马晓粉校注,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7页。,矿厂很难就近种植粮食及蔬菜,而“夷人”“种植菜蔬、豢养牲畜”,又“乐与厂民交易”,正好可以为矿区提供生活物资。在云南南部的缅甸、安南等地,情况也与此类似,据《圣武记》载:“滇边外有缅属之大山厂、粤西边外有安南之宋星厂,银矿皆极旺,而夷人不习烹炼。”因此,江西人、湖广人、广东人等前去开采,“大山厂多江西湖广人,宋星厂多广东人”,而当地的原住民也加入这场矿产采冶的活动中,“镇安土民肩挑针线、鞋布诸物往,辙倍获而归,其所得银皆制镯贯于手,以便携带,故镇郡多镯银”①魏源:《圣武记》卷14《附录·军储第二篇补注》,韩锡铎,孙文良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566页。。可见当地的“土民”在矿业开采中很快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从中获利。
这些情况,在现今矿区村民的集体记忆中也得到些许证实。在位于东川矿区的拖落村,据彝、汉村民世代口耳相传,清代外地人云集附近矿山时,矿区附近形成了街市,“七天赶一街,卖的都是矿工们所需之物”,甚至在人多的时候“每天要食用三石左右黄豆做的豆腐,打牙祭时,一次食用牛十二头”②王永军、张金权:《乾圆山下:拖落村村史》,晨光出版社,2016年,第8页。。矿工们流动性较强、来去无定,工作的地方亦多在矿硐内,显然不可能种植需要一定生长周期的黄豆并制作豆腐、养牛羊等,这些物资自然会依赖附近的“夷寨”供应。甚至,还有清代彝族档案显示,原住民还为开矿的汉人提供赊账,比如雍正年间湖广长沙府人唐思贤到四川冕宁开矿,一个名为丫巴鸟济容的原住民赊油米给他做工本,后来厂矿倒闭了,唐思贤无力偿还油米账,于是“被蛮子拉住作当,不得出来,替蛮子家砍柴背粪”③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四川省编辑组编写:《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55页。。这些迹象表明,原住民在矿业开发中并非处于被动的角色。
“夷民”还为冶炼铜矿提供必不可少的木材及燃料。矿业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木料,采矿时硐内需要镶木,用以支撑矿硐,炼铜时更是需要大量的柴薪、木炭等燃料。有学者认为,在开矿所耗需之油、铁、盐等物中,最主要的便是炭的消耗,“每炼铜百斤,依矿石的品位高低和提炼的难易程度,需炭数百斤至千五六百斤不等”④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62页。,可想而知矿区对燃料的需求之盛。而作为原住民的“夷民”世代生活在山区及林间,处于半农半牧的生活状态,他们对当地山林资源的特性及分布更为了解,自然更便于提供燃料。甚至有些“夷人”还专门到有矿的地方,从事与烧炭相关的工作以维生,比如云南的“红彝”听说与东川隔金沙江相望的四川会理州办铁厂,而铁厂“需人烧松炭”,于是“蔡、王、普、陈等四姓相约逃来会理”⑤方国瑜:《凉山彝族的来源、分布与迁徙》,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编:《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页。。可见在矿业发展的大潮中,“夷民”也顺应时势加入产业链中。
在铜矿的运输环节中,“夷人”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矿区往往山路崎岖、险峻异常,但是对运输的需求却很旺盛,不管是米粮、油、盐、菜蔬等生活资料的运输,还是生产工具、原材料、矿产品的运输,都至关重要。在传统时期,牲畜是矿区各类运输的主力,因此牛、马等显得异常重要,而“夷人”又“豢养牲畜”,势必对矿区的运输有利。清人王太岳在《铜政议上》亦言:“运户多出夷猓,或山行野宿,中道被窃;或马牛病毙,弃铜而走;或奸民盗卖,无可追偿;又硐民皆五方无业之人。”①王太岳:《铜政议上》,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52《户政二十七》,中华书局,1992年,第1285页。
雍正元年(1723 年)十二月,云贵总督高其倬、云南巡抚杨名时在给雍正皇帝奏报云南铜务时,亦讲到当时矿运人员的具体情况:“脚户多系彝猓,自赶牛马领运铜斤,多就山谷有草之处住宿牧放,不住店房,图省草料。”②《云贵总督高其倬等奏遵查铜斤利弊情形折》(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3页。
无论如何,矿区“夷民”参与到矿业运输中,应该是无异议的。
夷汉关系也绝非尽是紧张的局面,也有部分移民进入了原住民的村寨,甚至娶“夷女”为妻,娶妻生子之后便在“夷寨”繁衍生息,他们的生活渐渐与原住民交融在一起。乾隆《东川府志》载:“雍正间冶坑大开,炉户、砂丁蚁附,硐老山空,逃蛮寨为谋主,蛮妻以女,生子,并化为蛮。”③乾隆《东川府志》卷八《户口·种人附》,第72页。可见在清代,进入西南“夷区”的汉人有不少娶“夷女”为妻,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更有意思的是,据一些村志中保存的集体记忆显示,清中期,一些殷实的夷家就把孩子送到附近办学校的地方上学,东川府的“夷寨”中“有的还考起乡试到曲靖入学”,在“夷民”的印象中,“但凡读过书的人大多数都知书达理,说话不粗野,有板有眼的”,而且他们认识到识文断字对于买卖活动中写契约、打官司时写诉状等方面也大有裨益,甚至后来还有读书后的“夷人”帮汉人家写春联、写家信的情况④王永军,张金权:《乾圆山下:拖落村村史》,第166页。,这与我们平时对“夷民”的刻板印象甚至是相悖的。几代人同村共寨之后,语言的相互交流也成为可能,“彝族男女老少都会讲汉语,汉族一部分人会讲彝语”⑤王永军,张金权:《乾圆山下:拖落村村史》,第16页。。还有一些矿区“夷民”在与客民接触之后,原先的名字也发生了变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乾隆年间东川府的“夷民”戈着,其儿子取名为长命,孙子则直接取名为苏文明;“夷民”戈即,其儿子名为阿三,孙子则取名为包廷相⑥这些人物关系乃笔者从拖罗土地争讼案中的多篇供词中整理而来。详见《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二《拖罗田地》,乾隆四十九年刻本,会泽县图书馆藏,第11a—30a页。。这些名字变化的背后,是“夷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顺应时势所作出的改变。
综上,在清代西南矿业的开发中,虽然“夷民”“不谙架罩煎炼”,在采冶矿产方面没有太多经验,但他们“乐与厂民交易”,利用自身优势,巧妙地参与到矿业的开采、冶炼、运输等环节,在燃料、生活物资提供等方面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且他们在矿业中扬长避短,规避风险,在矿业开发的产业链中获利。在日常生活中,“夷民”也通过通婚、上学、改汉名等方式,顺势把自己融入了新的变化中。
六、结语
明至清初,作为西南“新辟夷疆”典型代表的东川府原本是“夷多汉少”之地,被外界称为“夷窟”,这里曾是彝族九大君长国之一所在地,有一套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中央王朝对其控制极为薄弱,在里甲赋役系统中仅“编户一里”,实际控制这里的是彝族土司、营目等,“夷民”虽有采矿传统,且在明代就有一定规模的东川铜外运,但采冶铜矿的技艺主要掌握在“铜匠银师”等特定人群手中,生产的铜器也主要是用于祭祀以及献给君王、毕摩。从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这一时期的矿业其实是掌握在土司、土目手中的,“夷民”生活在王朝国家和土司、土目的夹缝中,但更依赖于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司、土目,留给外来官员“憨而恋主”的感性认识。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东川府改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东川府的地方权力依旧掌握在土司、营目的手中,土地开垦和矿业开发都难以推行,为了破除土司、营目的力量,清政府利用“夷民受压迫说”来为自己造势,以便在当地打击土目势力的行为显得顺理成章,“夷民”也通过对官方权威的认可和归附,借助官方力量来摆脱土司、土目的控制。之后,伴随着东川铜矿业的兴盛以及大量移民的涌入,东川府从边徼“夷窟”,成为商贾辐辏、会馆云集之地,从一个远在天边的小城,成为支撑大清铸币的重镇,以矿业运输路线的疏浚等为契机,另一部分原本游离在统治之外的“野夷”也趁机进入版图,获得清政府的优抚,并在归附中得到官府的奖励。
在移民纷纷涌入的大背景下,“夷民”与移民在分享资源的过程中曾产生诸多冲突,主要表现在厂矿劫掠和土地纠纷上,但是“夷民”虽然“不谙架罩煎炼”,却并非被动地被改变,而是发挥自身优势,“乐与厂民交易”,有效规避矿业开采的风险,在燃料提供、矿业运输、物资补给等方面参与到矿业开发的整个产业链中来,体现出其因势而变的生存智慧。几乎在矿业开发中的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在中央王朝和土司、土目的夹缝中生存,抑或利用中央王朝的权威解决地方问题,还是顺势参与到矿业开发的大潮中,“夷民”的选择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与官府及土司、营目之间活络互动,其中莫不体现出独到的生存策略。
清前期“夷区”社会结构的演变固然有王朝国家及外来移民的推动,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夷民”一直在发挥其能动性,成为边疆秩序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边远社会自身的活跃力量并非东川府所独有,当我们尝试站在不同人群的立场,从他们自身的社会入手,关注他们的生活欲求和生存抉择时,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跳出既有观念的桎梏,从更多元的视角认识更加完整的边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