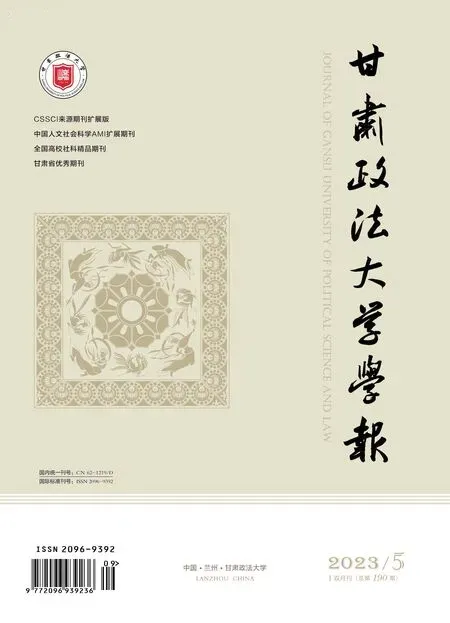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合理应用的证成逻辑与制度调适
王丽洁
2018年,南方科技大学研究人员贺建奎通过“修正患病风险”的非必要基因编辑行为,宣称“制造”出具备先天艾滋病免疫能力的“健康”双胞胎。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极大担忧。(1)See Cyanoski D,Genome-edited baby claim provokes international outcry,29 Nature 607,607-608 (2018).在倡言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以下简称“生殖系基因编辑”)治理模式的声浪中,部分学者认为潜在者具有未来健康权与开放性未来权利,应当允许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恢复健康但应禁止基因修复。(2)参见朱振:《反对完美——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道德与法律哲学思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2期。多数学者基于风险防范目的,提倡应当坚决禁止应用该技术。(3)参见贺梨萍:《百名科学家联名发声: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人体胚胎基因编辑》,载澎湃新闻2018年11月2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2612。然而,技术本身不能脱离技术所赋予的效用,生命科技进步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应不断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4)参见易继明:《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自由——科学法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41页。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不应为了防范风险而“因噎废食”,反之,应在确立合理法律边界基础上对其应用制度进行完善,从而释放技术利好,提升人类福祉。
一、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禁止制度实施效果反思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罕见病治疗方面显现出巨大潜力,但是目前我国立法规范明确禁止这一技术应用。禁止规范的直接目的是让所禁止的行为不再发生,间接目的是改变人们实施该行为的社会环境。(5)参见颜厥安:《鼠肝与虫臂的管制——法理学与生命伦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67页。即使在刑法层面禁止该技术的应用,也依然无法浇灭罕见病患者借助该技术进行治疗的最后希望。
(一)禁止制度实施致使罕见病患者医疗救助受阻
罕见病,又称“孤儿病”,是指由基因突变造成、发病率极低的遗传病。(6)See Boycott K M,Rare-disease genetics in the era of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discovery to translation,14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681,684-685 (2013).罕见病患者人数众多,且群体人数持续增高,目前已确认的罕见病已超过7000种,占人类全部疾病的10%。(7)See Cooper D N,Genes,mutations,and human inherited disease at the dawn of the age of personalized genomics,31 Human Mutation 631,635 (2010).我国罕见病的患病总人数约为1680万。(8)参见《中国罕见病患者,被遗忘的1680万人》,载新浪新闻,2019年6月11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6-11/doc-ihvhiqay4923944.shtml。虽然,对于部分罕见病的防治,可以借助孕前基因诊断技术(对受精前的卵子、体外培养胚胎进行染色体或基因检测)对健康胚胎进行识别、筛选;产后则可借助于体细胞基因治疗修正自身基因突变。(9)See César P G,Heritable human genome editing,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20,p.105.但是,这些手段存在筛选技术失灵、可供筛选的健康胚胎较少、体细胞基因编辑技术风险与治疗成本较高等各种不足。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有相同纯合突变的父母结婚生子而产生的罕见病的类型通过前述手段根本无法治愈。
按照技术应用目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可分为“增强或优生”与“预防或治疗”目的。前者按照人类预想改造原有基因,使后代身体的某些特征按照人类需要进行改变。后者通过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编辑,纠正基因组突变,进行疾病治疗或遗传缺陷修复,避免致病突变携带者将其致病突变遗传给后代,从而彻底治疗罕见病。(10)See Turocy J,Heritable human genome editing:Research progress,ethical considerations,and hurdles to clinical practice,184 Cell 1561,1570 (2021).具体来讲,该技术通过对人类精子、卵子等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改变胚胎性状,并遗传给后代。目前,最常应用的基因治疗法是CRISPR/Cas9(规律成簇的间隔短回文重复)系统。(11)See Vassena R,Genome engineering through CRISPR/Cas9 technology in the human germline and pluripotent stem cells,22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411,414 (2016).其实施原理为:用一段具有定位功能的RNA(核糖核酸)去识别细胞中的特定DNA(脱氧核糖核酸),接着用具有切割功能的 Cas9 蛋白酶剪断缺陷DNA,最后在该缺陷基因的位置插入已被编辑的 DNA 序列。举例来讲,就像在文档中对于已有的正文文本进行替换、修改、删除、增加一样,该技术可对已有人类基因进行替换、修改、删除、增加,并将这些改变遗传给后代。
2018年贺建奎事件后,为消除该事件对我国科研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保障和促进生物科学技术更好发展,我国从刑事立法层面禁止该技术在人体中的科研与医学应用。(12)参见许永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年版,第357页。《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增加了第336条之一“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该罪规定:“将基因编辑、克隆的人类胚胎植入人体或者动物体内,或者将基因编辑、克隆的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情节严重的,处……。”“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行为对象是具有特殊性的“基因编辑的人类胚胎”,当然包括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胚胎,其核心结构是谓语“植入胚胎”+宾语“人体或动物体内”,也就是说,该罪名禁止的不是基因编辑行为,而是禁止将经过基因编辑的胚胎“植入人体”的行为。(13)参见赵秉志、袁彬:《刑法修正案(十一)》罪名问题研究》,载《法治研究》2021 年第2期。这一规定使我国像德国、日本、法国等少数国家,成为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绝对禁止的国家。(14)参见叶良芳:《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基于生命伦理的视角》,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7期。伴随这一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禁止制度的确立,我国罕见病患者无法通过该技术应用进行遗传病治愈。
(二)禁止制度文本疏漏使其规范目的实质落空
目前,胚胎的立法定义本身还未明确,司法实践中对胚胎的认定存在困难,且容易产生司法认定不一。《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36条之一“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 罪名行为对象是“基因编辑、克隆的人类胚胎”。这一规范适用中,其认定前提是确定何为胚胎,但是我国法律并无准确的胚胎的立法定义。司法实践中,多发于民事领域的胚胎纠纷,主要集中在冷冻胚胎返还纠纷和要求医疗机构对其已经冻存的胚胎实施移植手术纠纷两类。这些司法案例中所涉及的胚胎形成时间各不一致,主要取决于胚胎的利用目的、冷冻胚胎医疗机构的技术条件与内部规定。医学领域中,胚胎概念并无权威界定。医学辞典中,对于胚胎的界定较为混乱。例如,胚胎是从受精后第4天到第8周、从受精到第7周、从受精后第4周到第8周发育中的有机体等。胚胎概念的认定不一,致使基因编辑的胚胎认定不一,不但背离法的安定性原则,更增加技术应用者的刑事责任风险。例如,相同时期的胚胎,不同适用者基于自身对胚胎的不同理解,认定便不同;不同时期的有机体,由于适用者不同又可能产生相同认定结果。如此一来,既不利于司法适用的统一性,更背离平等保护原则。此外,基因编辑的胚胎认定的不确定性,致使技术应用的科研工作者和医务工作人员无法确定受精卵形成多久后可视为胚胎,无法预见入罪的可能性,增加其执业的刑事责任风险。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将罪名的行为对象设定为“基因编辑的胚胎”,致使制度规范目的实质落空。罪名的行为对象为“基因编辑的胚胎”,罪名的行为是通过对其进行基因编辑行为实现基因编辑目的,但是实践中对于“胚胎”实施基因编辑技术的情况发生概率较低。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中,绝大多数操作发生在单细胞受精卵中,甚至少数直接对卵子进行操作,再将编辑后的卵子与精子结合发育成胚胎。较之精子、卵子(以下简称“生殖细胞”)与受精卵等单细胞,多细胞的胚胎具有更复杂的生物结构。具体技术应用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基因编辑技术会直接应用于胚胎,产生罪名中规定的基因编辑的胚胎。现有技术主要应用于生殖细胞或受精卵,再将基因编辑过的生殖细胞或受精卵形成胚胎。例如,最常用的小鼠动物模型中,基因编辑技术实施时间大多发生在1细胞期(受精后1天之内),既在Zygote中进行编辑。中文中,Zygote意指合子,是单细胞的受精卵,单细胞的Zygote需要经过不断的发育才能成为多细胞的胚胎(embryo)。在人类卵子和受精卵中,2017年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课题组对MYBPC3(肌球蛋白结合蛋白C3)基因进行了编辑;(15)See Ma H,Correction of a pathogenic gene mutation in human embryos,548 Nature 413,416 (2017).2021年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在合子中对POU5F1(POU 5 类同源框 1)基因进行了编辑。(16)See Fogarty N M,Genome editing reveals a role for OCT4 in human embryogenesis,550 Nature 67,70-71 (2017).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若将罪名的行为对象确定为“基因编辑的胚胎”,会出现技术应用者通过先行编辑生殖细胞、受精卵,再等待其发育成为胚胎后实施植入行为。如此一来,研究者可以实施或增强或治疗的任意基因编辑行为,并可规避罪名的适用。
(三)禁止制度制裁正当性缺失使其实效性不足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制裁规范并无改善禁止行为发生的社会环境。刑事惩罚将使行为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和预防犯罪作为两个最终目的,是应对损害和损害威胁最可行的措施。(17)参见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梁根林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35页。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刑事制裁规范的正当性在于,既能预防又能遏制滥用基因科技行为,并通过设置妥当的制裁方式与制裁程度实现科技发展对于少数人的福祉。那么,到底何种方式与程度的制裁可以被认为是妥当的?何种技术应用应该处以刑罚制裁?毋庸置疑,技术风险高、无治疗必要性、损害平等、引发歧视的增强或优生型基因编辑进行刑事处罚是正当的。但是,应用于罕见病治疗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则具有正当性。罕见病患者有权要求国家尊重、保护和帮助实现其生存与健康,且不受刑事处罚。例如,常见的罕见病亨廷顿舞蹈症,若亲本之一是纯和突变型,会导致极高的疾病发生率,所有的胚胎都会携带导致儿童发病的显性致病等位基因,患者只能依靠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进行治疗。刑法禁止技术应用导致罕见病患者必须拒绝医治机会,或者接受医治则面临刑事制裁的尴尬局面,制裁规范的正当性就很低。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正当性缺失的制裁规范,无法打消罕见病患者通过技术应用治愈疾病的渴望,改变禁止行为发生的社会环境。
法律禁止制度的设立,应该预设对于适用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医学、科研人员具有一定的检测能力。也就是说,公诉机关可以找到这些潜在的犯罪嫌疑人(技术适用者),并通过对其实行刑事制裁,改变其意欲使用技术的动机。如果很难甄别或确定这些犯罪实施者,刑事制裁规范的实施效率就很低。生殖系基因编辑应用涉及生物分子层面的操作,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加之涉及受试者基因信息这一深度个人隐私,技术应用很难被人发现,管制较为困难。例如,贺建奎事件中如若不是其主动公开,监管者一般很难知晓其所实施的基因编辑的行为与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不断更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使技术实施者无需依托“植入”行为即可实现增强或治疗的编辑目的。例如,随着卵子体外激活和移植技术的发展,基因编辑目的达成无需实施“植入”行为。技术更新后的做法是,研究者先将卵子从女性体内取出,对其进行基因编辑,再将编辑后的卵子植入女性体内,等待其自然受孕。如此一来,整个技术操作既能实现包括增强或优生型基因编辑在内的不同类型编辑目的,又能避免实施“植入”行为而引发的刑事风险。这些瞬息万变的生物科技,连本领域的专家都很难及时实现知识更新,作为法学专业背景为主的技术监管者实施管制更是难上加难。
二、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禁止制度的立法理由检视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具有高风险性、不确定性、长期效应性特点,贸然放开的确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但是,是否所有的技术应用都会引发这些风险?是否一旦有风险就应遭到禁止?是否通过禁止应用就可以防范技术滥用的滑坡效应?是否基于风险防范就一定要以牺牲罕见病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为代价?因此,有必要对技术禁止应用的立法理由进行分析与检视。
(一)技术自身安全风险检视
基因编辑技术自身具有高风险性,且产生的伤害不可逆转(18)参见姜涛:《基因编辑之刑法规制及其限度》,载《东方法学》2021 年第2期。,而且会与其他社会成员、生物体之间产生长期效应,故予以禁止,这已是共识。(19)参见陈信安:《基因科技风险之立法与基本权利质之保障——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为中心》,载《东吴法律学报》2014 年第7期。目前最常用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走向应用最大的障碍是其可能产生的脱靶效应。该技术有时会作用于非目标基因,造成非目标基因不必要的改变。
但是,伴随突飞猛进的生命科学技术发展,距离我国2015年首次使用CRISPR/Cas9编辑人类胚胎基因,该技术的稳定性已经获得了显著的发展。首先,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脱靶效应是可以控制的。脱靶效应来源于Cas9在非靶定区域(off-target sites)进行基因编辑,靶定区域是能够与gRNA(向导RNA)配对且具有PAM(候选识别位点的毗邻基序)序列的位置,而非靶定区域通常具有与靶定区域相似或相同的序列。脱靶效应的几率取决于gRNA的设计。有的gRNA可能在DNA上具有很多相似的配对序列,有的则只有很少的或者唯一的配对序列(即正确位点),而合理的设计可以避免许多相似配对序列,甚至达到在DNA上只有唯一的靶定位点,从而将脱靶效应降到最低。(20)See Lea R A,Human germline genome editing,21 Nature Cell Biology 1479,1485 (2019).其次,脱靶效应的技术可控性已相对稳定,并已经获得了临床的初步成功。例如,2019年中国科学院杨辉团队在Science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表明,Cas9的脱靶效应可以降低到自发突变的水平。(21)See Zuo E,Cytosine base editor generates substantial off-target single-nucleotide variants in mouse embryos,364 Science 289,290-291 (2019).2021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了利用CRISPR-Cas9编辑体细胞基因组以治疗镰状细胞病与β地中海贫血的研究报告,并无发现脱靶编辑效应。(22)See Frangoul H,CRISPR-Cas9 gene editing for sickle cell disease and β-thalassemia,384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52,252-253 (2021).同年8月,NEJM杂志发表了首个支持体内CRISPR基因编辑安全性和效果的临床数据,该数据证明人体内CRISPR-Cas9基因编辑治疗 I 期临床试验结果,疗法安全有效。(23)See Gillmore J D,CRISPR-Cas9 in vivo gene editing for transthyretin amyloidosis,385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493,495 (2021).再次,脱靶检测技术在不断发展,加之技术应用前还要进行大量的动物实验与临床前研究。最后,新型基因编辑方法朝着精准和安全性方向发展,脱靶检测技术亦与时俱进,脱靶效应技术风险也不断降低,实质损害概率极低。
(二)技术应用伦理风险检视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所改变的生物性状可以遗传给下一代,涉及人类及其后代生命与健康,具有极大的预测不确定性。(24)参见魏汉涛:《人类基因编辑行为的刑法规制》,载《法商研究》2021年第5期。若该技术应用于人类非治疗性基因修饰“定制婴儿”,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和尊严价值开始动摇和消弭,技术会对人性尊严产生实质影响。基于自主道德能力的康德式尊严理论,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医疗应用使得人可以通过技术加以支配,危机人的本质。(25)参见王康:《人类基因编辑实验的法律规制——兼论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的法律议题》,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1期。
不可否认,贸然大幅度应用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确实可能背离保护受试者人格利益以及背离伦常。但是,是否所有的技术应用都会产生人类尊严贬损?是否所有的技术应用都会侵害“未来世代”的利益?人性尊严保护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可以自主、自为、自决。(26)参见汪进元:《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但是,人性尊严不是绝对的价值,并非只要涉及碰触到人性尊严的问题就属禁忌。(27)参见陈仲妮:《从人性尊严面向思考之胚胎保护——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几件涉及人性尊严之裁判谈起》,载《兴大法学》2019年第23期。不同的生殖系技术应用目的,产生不同的贬损人性尊严后果。“增强或优生”目的的基因编辑按照自己的意念设计后代,使其能够进一步在综合素质上超越上一代人类,违背人类的自然本性,不利于社会个体差异性的培养,使人类失去人的特性,丧失人之为人的基础。但是,合理应用“预防或治疗”目的的生殖系基因编辑并不贬损人性尊严。一般来讲,此种技术应用涉及受试者、未来后代、社会群体等三类主体的人性尊严。从受试者角度来看,技术涉及对其生殖细胞、胚胎进行基因组编辑并不侵害其人性尊严。生殖细胞、胚胎在与受试者人体分离之前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一旦与身体分离就成为受试者所有之物,对于受试者所有物的处理,甚至性状的改变,并不产生贬损受试者人性尊严的问题。(28)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从未来后代角度来看,对于生殖细胞、胚胎基因编辑涉及未来潜在人格的利益,是对出生后罹患罕见病患者“绝处逢生”的生命救济。通过操作未来后代早期的遗传物质来干预其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进程,替代或纠正其自身基因结构或功能上的错乱,来保障其身体完整、身体健康、生命权法益是对其人性尊严的捍卫而非贬损。或许,这一立论会面临未来后代的潜在人格还不存在,更妄论对其法益保护的质疑。但是,未来潜在人格不存在,并不妨碍我国立法赋予此项权利,对此我国法律早有先例。例如,《民法典》第16条规定:“……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第1155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 立法者对于未来人潜在利益,既包括胎儿纯获利益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又涉及其财产利益保护。“预防或治疗”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应用属于使未来后代纯获利益。依据“举轻明重”原则,既然立法对其财产利益都进行保护,那么健康权益的保障亦是立法者的应有之意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社会群体的人性尊严来看,“预防或治疗”生殖系基因编辑应用有利于保护少数社群人性尊严,更有利于人类共同福祉。罕见病直接影响着全球约5%-7%的人口的生存(29)See Kofler N,Treatment of heritable diseases using CRISPR:Hopes,fears,and reality,42 Seminars in perinatology 515,516-517 (2018).,他们希望通过技术治愈自身罕见病或者希望孕育无罕见病的健康后代,是一种有助于生命健康的善举。从规范层面来看,《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罕见病患者虽仅是少数群体,但其自身以及后代的人权保障都应在这一基本权利保障范围之内。从医疗实践层面来看,我国允许通过筛选的生殖细胞进行人工体外受精,更允许胚胎着床前的基因诊断。从这些合法行为可以看出,国家并不期待罕见病患者生下带有先天疾病的子女。“预防或治疗”生殖系基因组编辑可以彻底预防、治疗甚至消除罕见病,且确保这些突变基因不再遗传给后代,是诸多罕见病患者和家庭可选择的能够有尊严生活的唯一出路。从人类尊严保护角度来看,基因库中有缺陷基因的增加会对后代产生严重后果(30)参见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0页。,“预防或治疗”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可以修正异常基因,修复后缺陷基因不断减少,未来世代中致病异常基因变少从而减少罕见病患病人数,减少了人类痛苦和遗传学危害,降低社会因罕见病治疗而产生的经济负担,保护社会资源。对于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医疗需求是保障人类尊严的必要,允许合理应用技术是一项道德义务(31)See Gyngell C,Moral reasons to edit the human genome:picking up from the Nuffield report,45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514,514-515 (2019).,将有助于“减轻人类生存的负担”。(32)See Harris J,Germline modification and the burden of human existence,25 Cambridge Quarterly of Healthcare Ethics 6,8-10 (2016).
(三)技术滥用滑坡效应检视
一旦允许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可能会产生技术的滥用与背离人性尊严不被忠诚的执行,技术利用会脱离公众可接受的范围,污染人类基因池。(33)参见崔丽:《基因权利的法理基础与规制进路——由“基因编辑婴儿”引发的思考》,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3期。人类基因库具有遗传多样性。按照预想的规划干预后代,按照自己的意念设计后代,使其能够进一步在综合素质上超越上一代人类,这种凭主观意志的人工干预导致人类遗传多样性的“趋同化”,基因多样性的特征将不复存在。但是,因为技术滥用而限制技术应用,难免有“因噎废食”的嫌疑。换言之,任何技术都有滥用的风险,技术滥用滑坡效应的防范应当通过正确、合理使用技术来实现,而非通过全面禁止技术。因为担心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风险,而禁止可以治愈遗传性基因罕见病患者的医疗技术,既不能杜绝技术滥用风险的产生,也无法实现患者生命健康权保障。事实上,防范滑坡效应,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根据不同的基因编辑目的确立不同的规制手段。“增强或优生”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滥用的风险,应该采取最为严格的禁止应用与刑事惩罚。“预防或治疗”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则应视具体风险情况予以灵活规制。“一刀切”禁止技术应用,不但无法遏制技术滥用产生的风险,还堵死罕见病患者唯一的救助希望。此外,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基因池污染问题的担忧,实则大可不必。随着时间推移,所有物种基因都在变化,这也是物种演化的原动力。基因本身不存在好与不好的区别。只有是否符合现有的生存需求与是否增加了主体的繁衍优势这种评价标准。(34)See Kimura M,Evolutionary rate at the molecular level,217 Nature 624,627 (1968).退一步讲,若对于人类基因库中有缺陷的致病基因、突变基因进行的更改、删除都属于对基因池的污染,那么放弃胚胎的堕胎行为是否系更为彻底的丧失基因多样性行为呢?(35)参见李震山:《胚胎基因工程之法律涵意——以生命权保障为例》,载《台大法学论丛》2001 年第3期。
(四)技术应用对于生物安全的检视
为了保障和促进生物科研领域更好的发展,避免我国因法律缺失或刚性不足而成为其他国家试验和转嫁风险的土壤(36)参见许永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年版,第357页。,立法机关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生物安全目的,防范生物威胁,与生物安全法衔接,增加规定了“非法从事人体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的犯罪”。(37)参见李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说明》,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12/f16fedb673644b35936580d25287a564.shtml,2022年10月9日访问。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生物有关的各种因素会对社会、经济、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产生危害或潜在风险。(38)参见李垚:《医学实验动物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8页。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会将人民生命健康置于风险之中,引发生物安全进而危及国家安全。但是,是否所有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都会出现这些问题?如果这样,《民法典》第1009条为何又规定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只要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危害人体健康等都是可以进行的。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技术应用都会侵害国家安全与生物安全。至少,经过合理、审慎、严格技术审查后应用的“预防或治疗”生殖系基因编辑不在此情形。此外,即使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仅为了防范不确定风险,从刑事层面禁止技术应用限制罕见病患者生命健康权也是欠妥的。在并无对风险进行精细化、类型化区分的情况下,仅基于安全因素考量这一理由,无法成为忽视罕见病患者这一弱势群体利益的正当理由。换言之,即使在国家安全与罕见病患者生命健康权两种价值之间进行衡量,也并非某一种价值的全有或全无,更不能将国家安全作为绝对保护的价值而牺牲罕见病患者最为基础的生命健康权。
对人民基本权的限制,只有在维护公益所不能欠缺的前提下,才具有正当性。(39)参见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 2004 年版,第162页。基于未然技术道德风险以及安全损害可能性的目的,采取切实限制主体基本权利的手段,致使罕见病患者及其后代唯一救助可能性丧失,背离比例原则。一方是罕见病患者自身基因权及其后代潜在的生命健康权。另一方则是风险防范和国家生物安全的国家保护义务。两者冲突时,立法者应该合理、妥当的平衡双方利益与价值冲突,不应仅将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作为唯一优位价值进行考量。风险不一定产生危险,危险出现不一定产生损害,即使发生损害其损害结果的程度也具有不确定性。“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禁止并未结合技术应用目的、风险发生概率、损害后果严重程度等因素进行区分管制。相反,将风险与损害后果更严重、对于国家安全影响更大的“增强或优生”生殖系基因编辑,与风险与损害后果更低的 “预防或治疗”生殖系基因编辑采取相同的限制程度。
三、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合理应用的证成逻辑
在类似CRISPR/Cas9等高效率基因编辑技术并不发达的时代,技术对于亟需基因治疗罕见病患者的急迫诉求爱莫能助。但是,在CRISPR/Cas9技术安全性显著提高的今天,不应该阻断这些弱势群体唯一的救助机会。
(一)技术理性发展的本质规律要求技术从禁止应用转向合理应用
事物本质产生的思维是类型式思维,立法者的任务是描述各种类型,立法以及法律发现的成功或失败,依赖能否正确地掌握类型。(40)参见阿图尔·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年版,第43页。现有立法对于基因编辑技术规制的类型化管制,主要以基因编辑对象(体细胞与生殖细胞)为标准,允许体细胞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禁止生殖系细胞技术应用。这种类型化管制模式,预设了体细胞基因编辑的风险一定低于可以遗传于下一代的生殖系细胞。实际上,体细胞的临床应用并非一定不会引发风险与损害,如,体细胞基因治疗的主流载体腺相关病毒(AAV)也有一定概率插入到人体DNA中带来安全隐患,如近期发现该技术可能会增加肝癌风险的基因组变化。(41)See Venditi C P,Safety questions for AAV gene therapy,39 Nature Biotechnology 24,25 (2021).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并非一定会产生风险,如通过科学论证和审慎复核风险较低的罕见病基因治疗。
立法目的无法完全被类型概念化,需要在具体的法律发现中一再地回溯到制定法所意涵的类型,回溯到作为制定法基础的模范观念。(42)参见阿图尔·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年版,第43页。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禁止的目的在于防范人的物化和工具化,科学、合理的类型化规制应回溯到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目的。换言之,应当以技术应用的“增强或优生”与“预防或治疗”为划分标准,进行分类管制。确立“增强或优生”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绝对禁止,再基于技术的安全系数与必要性程度,继续划分 “预防或治疗”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匹配不同的类型化管制手段,适应复杂多样的现实。
(二)基因正义价值的实现要求技术从禁止应用转向合理应用
个人的自由包括免除心理的压制、身体的攻击和个人完整性的自由。(43)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47页。在规范体系中,个人自由的维护主要通过权利来实现,国家对于个人自由所关涉的各项权利需制定细则,保障其能真正得以实现。我国《宪法》第37、38条和《民法典》第109条均规定自然人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那么,既然我国法律积极保护非罕见病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对于遗传天赋不均的罕见病患者理应得到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保障。换言之,罕见病患者基于自身享有的基本人格权,可以将身体作为一种人格的基础加以保护,依照其对身体自主决定权的意思表示,维护或实现身体的功能。(44)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104页。对罕见病患者而言,立法不应当设置刑事惩罚,阻碍其利用基因治疗实现人格权。合理的做法应该在积极防范技术风险的前提下,妥当履行国家保护义务;通过多种制度设计与配套保障措施,修订严格的技术适用规范标准,降低罕见病患者基因治疗的风险,切实维护罕见病患者的人格尊严。
社会基本结构应当允许某些不平等,只要他们改善每个人的状况,包括最不利者的状况。(45)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117页。正义的制度,其实施不但不能使他人状况变坏,更应该能够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作为公共社会规则的法律,为了追求社会整体和谐与安定,实现社会公共利益,面对劣势者能力受阻,应当将救助弱势者作为立法最基本的法律目的与价值。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公民具有获得救济的权利,当然包括处于劣势的罕见病患者。他们多基于遗传物质的结构改变或调控异常处于劣势,而并非由于自身原因所致。通过药物无法治愈的,只能任由病程慢性、进行性、耗竭性地发展,进而造成残疾或危及生命。若允许其应用基因编辑技术进行治愈,不但不会伤害到他人利益,还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劣势走出困境,从而更好地保障弱势者利益,实现正义目的与价值。
(三)罕见病患者及其后代基本权利保障要求技术从禁止应用转向合理应用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是部分罕见病患者实现生育的唯一手段,允许技术合理应用可以保障其生育权。生育繁衍后代是人类最基本的诉求与自由,依据传统自然法思想,生育权是公民固有权。我国《宪法》虽然并无列明,但其内置于婚姻权中,其核心是排除国家权力干涉的自由内容。(46)参见秦奥蕾:《生育权、“计划生育”的宪法规定与合宪性转型》,载《政法论坛》2016 年第5期。生育自由包括国家尊重、保障公民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权利。国家可以为公民生育期待提供医学生殖协助,以化解其不孕的痛苦。(47)参见王丽洁、汪进元:《单身女性卵子冻存与利用的分段控制及其法律边界》,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6期。例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近期报道了一个zp2基因发生点突变而导致卵子无法正常发育的病例,由于患者单基因突变,导致其生殖细胞发育缺陷,类似基因突变的发生只有通过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进行修复,才可以帮助其实现生育。(48)See Shen Y,Identification of a heterozygous variant of ZP2 as a novel cause of empty follicle syndrome in humans and mice,37 Human Reproduction 859,866 (2022).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是部分罕见病患者后代实现其生命健康权的唯一手段,允许技术合理应用可以保障其生命健康权。生殖系基因编辑主要是从生物分子层面对于人类生殖细胞、受精卵、胚胎进行基因干预,这些对象无法构成法律规范中的胎儿,无法享有《民法典》赋予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这些生殖细胞与胚胎具有生命的潜能,是人类生命的开始,它们可以发育成为完整的独立个人,并有成为权利主体的可能性,对它们应该拟制地赋予其生命最佳可能权。(49)参见颜厥安:《鼠肝与虫臂的管制——法理学与生命伦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25页。例如,家族黑蒙性白痴症(Tay-Sachs)和早发性溶酶体贮积病是由于继承了两个拷贝的隐形突变基因而导致,如若不能从基因手段导入正常的外源基因,患者会在出生后的数日或一周岁后出现迟钝、淡漠、不灵活,严重的时候呈现智力低下。类似罕见病,胚胎基因检测无法进行有效筛选,更缺乏可以治疗的药物,基因编辑提前干预是唯一的治疗手段。针对罕见病患者的生殖细胞、胚胎等基因编辑,不仅涉及罕见病患者本身利益,还涉及这些潜在发育成生命群体的生命健康权益,虽然其无法行使但是国家依然可以通过法律赋予其权利主体地位。权利主体原本就是法律制度的抽象建构,是一种承载权利义务关系的形式地位,原本并无脸庞。(50)参见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 页。对于这些“没有脸庞的权利主体”的承认与保护,应是法律对于生命伦理以及生命法学的未来取向。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禁止或应用,应立基于合理的类型化区分基础上,必要且紧迫的 “预防或治疗”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合理应用,符合基因正义制度与弱势群体扶助,更能实现罕见病患者及其后代的基本权利保护。
四、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合理应用的制度调适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法律控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既能防范技术应用的潜在风险,又能确保其在人类健康与科学研究中尽其所长。良好的治理和实践,会助力患者获得安全有效的治疗,尊重个体自主性并维护后代的最佳利益,使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真正为人类和人道服务。(51)参见雷瑞鹏、翟晓梅、朱伟、邱仁宗:《人类基因组编辑科学、伦理学和治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348页。
(一)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合理应用的原则
1.技术合理应用的例外允许原则
现有基因编辑禁止制度欠缺利用目的的类型化、风险程度、必要性的区分,忽视后代利益,制定之时就存在法律漏洞。通过确立生殖系基因编辑应用的原则,合理利用这一普遍适用的允许原则,可弥补法律的空白与漏洞,缓和现有规范产生的不公平。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应从全面禁止转向例外允许。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虽然日趋成熟,但是技术的稳定性、风险性还需要不断重复验证才可确定。所以,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原则上应该坚持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禁止应用。但是,考虑到罕见病患者的治疗诉求,可以通过例外允许技术应用来适度调整,以此调和全面禁止管制的程度。如果一种利益提高了最底层人们的期望,它也就提高了其间所有各层次人们的期望。(52)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62页。例外允许原则的正当性在于,其实质目的是在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防范与罕见病患者生存利益保障之间形成平衡,进而实现弱势方利益保障。事实上,国际层面已经确立了生殖系基因编辑应用的例外允许。例如,欧洲理事会《生物伦理公约》第13条规定,处于预防、诊断或治疗,允许实施旨在改变人类基因组的干预行为。(53)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医疗刑法导论》,王芳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49页。
那么,到底哪些罕见病属于应当例外允许的情形呢?首先,例外允许的技术应用应当具备科学的正面意义,是为了治疗、预防严重的生理缺陷疾病。其次,父母均具有严重遗传性疾病。并非所有的罕见病都会遗传给下一代,若父母双方均为纯合突变,他们的后代必定是罕见病患者,但是父母双方若非携带纯合突变,则不会遗传给下一代。较之前者,后者不属于应当例外允许技术应用的情况。再次,技术应用应当同时符合其他法律原则。通过例外允许“预防或治疗”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既可以促进新型基因治疗技术的发展,又可以保护罕见病患者及其后代的生命健康权益。
2.技术合理应用的必要性原则
《纽伦堡公约》第2条规定:“人体实验应该收到对社会有利的富有成效的结果,用其他研究方法或手段是无法达到的,在性质上不是轻率和不必要的。”必要性原则确定的实质目的是进一步缩小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适用范围,降低技术应用的风险。通过有限开放、有序开放,实现技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平衡。在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应用中,必要性原则是指前期动物实验已经有明确证据确定致病基因,罕见病患者自身或者其后代具有重大疾病或重大缺陷的发病风险,没有其他的可替代治疗方案,技术应用是唯一且最后的手段。目前,已有国家通过限定技术应用的必要性来对罕见病患者进行救济。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NASEM)发布的联合报告《人类基因组编辑:科学、伦理和治理》中认为,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有限开放应该符合最后合理方案。(54)See Alta Charo R,Human Genome Editing:Science,Ethics,and Governance,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17,p.7.
必要性既强调治疗目的的必要性,又强调治疗手段的必要性。从治疗目的的必要性来看,必须以急迫的罕见病治愈,保障其生命为主要目的,对于不涉及生命的技术应用则应该确保是不会给其他人带来风险。从治疗手段的必要性来看,虽然罕见病患者自身或者其后代具有重大疾病或缺陷的发病风险,但是可以借助基因诊断技术,实现孕、产前阻断,或通过排查有患病风险的胚胎选择性地避免将基因突变遗传给下一代,否则不满足治疗手段的必要性。除此之外,即使具有重大疾病、缺陷的发病风险的患者,若日后可以通过体细胞治疗修正自身基因突变、线粒体治疗手段进行治愈或者服用已开发的药物实现治愈,也不属于治疗手段具有必要性的范畴。
3.技术合理应用的风险评估原则
《纽伦堡公约》第2条规定:“实验的危险性,不能超过实验所解决问题的人道主义的重要性”。在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应用中,风险评估原则是指由专门机构,结合个案中技术、伦理风险进行评估、分级,进而确定技术应用的风险受益比。通过风险评估原则的适用,可以再次确定是否继续实施技术。首先,风险评估原则应借助专门评估机构的审慎评估。《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8条规定:“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应当通过学术审查和伦理审查,转化应用应当通过技术评估和伦理审查。”基于此,风险评估机构应该分为对技术应用的安全性与风险性评估及伦理道德性评估两种。其次,对于个案中所评估的风险,应该结合可能受损的法益类型、风险与损害发生概率进行分级与分层评估。技术应用牵涉生物安全、家族、个人生命健康等多重法益,评估者应结合个案,甄别技术应用对法益可能造成损害的概率以及严重程度。最后,评估技术应用后的风险收益比。技术应用产生的收益应该是大于其可能产生的损害,如此才能进一步确保技术应用的正当性。例如,贺建奎案被诟病的最大问题,除了技术应用不具备必要性之外,还存在技术应用的未知损害明显大于患儿可能获得的收益,其所编辑的ccr5基因不仅是艾滋病进入细胞内的表面受体,还有其他免疫功能,该基因被敲除可能使婴儿更容易感染流感、登革热等病毒。
4.技术合理应用的后世代利益持续保护原则
生殖系基因编辑产生的遗传变化会传递给后代,技术应用应对未来后世代利益进行持续保护。后世代利益持续保护原则的实施是对未来世代人利益保障不可推卸的基本义务,其实质目的是确保代际正义。具体来讲,应当包括事前风险防范与事后持续跟踪两部分,通过随时监控、防范其风险,保障罕见病患者及其后代权益。一方面,基于后世代利益的充分考虑,应设置专门机关代为行使未来潜在人格生命最佳可能状态权,确保技术应用会产生最低的基因性状或对疾病易感性的改变,保障其潜在人格的发育是为了实现更好的生命状态,而非为了科学或经济目的。(55)参见颜厥安:《鼠肝与虫臂的管制——法理学与生命伦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26页。另一方面,对于自愿接受技术应用的罕见病患者,应该进行长期、多代跟踪、监控其遗传变异及身体状况的变化。具体来讲,实施方应当在患者隐私权保护的前提下,建立技术实施患者档案,详细记录受试者个人情况、技术实施细节,并设置固定回访时间。这一回访时间应该持续到患者及其后三代至五代,确保受试者后代所承受风险能降至最低。此外,长期追踪回访不应仅仅关注患者及后代的健康细节,还需密切关注因技术应用受到影响的第三人、族群及对社会产生的综合效应等多个方面。
(二)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合理应用的规则构建
原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指导方针,而不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约束。(56)参见亚历山大·M.比克尔:《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67页。规则是原则的落实和具体化形态,生殖系基因编辑应用规则应从实体、形式、程序等层面进行构建,通过这些规则设定具体义务从而实现原则的目的。
1.建立技术合理应用的分类规制规则
在“增强或优生”基因编辑的绝对禁止这一前提之下,依照“预防或治疗”基因编辑的风险概率,结合技术实施的必要性,匹配不同的安全措施和法律效果。以治愈迫切疾病、保障生存权为标准,将 “预防或治疗”基因编辑继续划分为:紧迫且必要的、非紧迫但必要、非必要的治疗性基因编辑行为。首先,对于“增强或优生”、与非必要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匹配最严格的刑事法律效果。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36条之一的“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对于技术应用进行刑事惩罚。其次,对于紧迫且必要的治疗型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不将其认定为《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36条之一定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并予以出罪。最后,对于非紧迫但必要的治疗性基因编辑,基于《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第6条、《民法典》第1009条的规定,结合技术实施的具体危害性和风险性,进行行政处罚或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通过类型化技术应用后,匹配松紧不一的规制手段,从紧迫且必要的治疗性基因编辑技术应用有序开放。这既能发挥技术利好治愈疾病、保障罕见病患者生命健康,又能将技术应用产生的风险降至最低。
2.建立技术合理应用严格准入规则
《纽伦堡公约》第7条规定:“实验必须基于动物实验的结果,以及对疾病自然发展的知识,或是预期的结果将可证明实验的合理性”。《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11条规定:“未经临床前动物实验研究证明安全性、有效性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不得开展临床研究。”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具有高风险性,对其应采取更为严格的准入规则。首先,在临床研究前,需要进行严苛的临床前研究。对于动物实验的样本、流程、数量、时间长短、试验结果较之其他技术应达到更严苛的标准。尤其是应该设置严苛的动物实验(其中包括小鼠实验与设计成本更高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其次,实验应由适格的医疗机构与人员进行。技术实施机构应当具备实验的基本硬件条件,如研究设施、仪器设备、临床设施等;应当具备实验的基本软件条件,如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与临床人员共同组成的技术人员团队;应当具备实验的基本机构条件,如已经具有长期从事体外受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胚胎基因诊断技术、体细胞治疗的三甲级以上医院。最后,临床试验实施应该由多方参与。除了医疗机构与人员,还应该包括科研人员与实验监管者,确保实验中对于胚胎可能造成的伤害或失能可以提供妥当的保护,或为了保障潜在人格利益与尊严及时叫停实验。
3.建立技术合理应用审慎监管规则
首先,基于受试者医疗自主同意权,技术应用不但应该得到罕见病父母的知情同意,更应该得到代表未来潜在人格利益机构的知情同意。技术实施前,实施者应当向其提供咨询,真实告知技术的安全性、必要性、风险性、风险受益比和可能产生的最差后果,确保其基于自愿、并无强制、不正当利诱作出同意。为了监督知情同意原则的有效实现,避免因技术知识背景产生的不平衡、加剧受试者弱势地位,应建立医生在场报告制度。通过作为第三方的专业医生持续监督,确保试验前受试者及代表能够准确理解专业知识,试验后向受试者及其后代提供持续咨询。其次,个案技术实施前应该通过技术委员会的逐级审查。由省级、国务院两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成立由临床医生和科学家构成的技术风险评估两级委员会。省级技术审查委员会首先审查个案中医疗机构条件是否符合所设定的准入条件、实施人员是否具备应用能力水平,再对个案技术应用的合法性、科学性、有效性、可行性、风险性、必要性等问题进行审查。通过省级技术审查委员审核后,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成立的技术审查委员会对个案技术应用进行特别审查与技术应用的综合效应进行审查,其中包括基因组编辑具有特异性的证据、有效的证据、无脱靶或很少脱靶的证据、预期变化将产生预期临床结果的证据,以及技术应用中可能存在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及防控问题。最后,技术实施前应该通过伦理委员会的逐级审查。由省级、国务院两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成立由伦理学家、法律专家构成的伦理风险评估两级委员会。省级伦理风险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个案中技术操作是否符合伦理规范、技术方案是否符合伦理要求。通过省级伦理风险审查委员会审核后,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成立的伦理风险审查委员会对个案技术应用中的方式和目的是否符合未来潜在的人格利益以及后世代利益再次进行审查。
结 语
面对不断推陈出新的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相应的技术规制制度也需不断进行根本性重塑。无论技术如何变化,其理性发展都应与人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连。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不应受贺建奎“修正患病风险”的非必要基因编辑行为的负面影响而停滞不前。相反,制度调适应建立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和弱势群体扶助的正义价值基础之上,需不断探索其合理应用的边界和更为妥适的法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