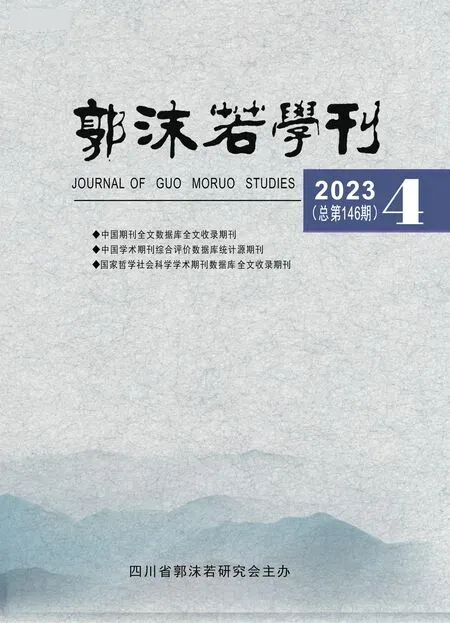负向性的海洋
——郭沫若五四新诗中海洋书写的另一向度
赵刘昆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7)
目前对郭沫若五四新诗中的海洋书写问题虽有相关研究,但目前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是从“自由”“启蒙”“创造”“新生”等视角介入,研究其“海洋精神”“海洋景观”在诗歌中的表现和作用。彭冠龙在其《郭沫若海洋体验与〈女神〉中“海的精神”》一文中,以《女神》为研究样本,剖析了郭沫若“自由”与“渴望祖国独立强盛”这两种不同的海洋体验,并具体阐释了这两种海洋体验是如何进入郭沫若的《女神》中,并产生重要作用的①彭冠龙:《郭沫若海洋体验与〈女神〉中“海的精神”》,《郭沫若学刊》2014 年第1 期。。作者的分析具体而独到,对郭沫若海洋体验进入其诗歌文本的机制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是研究郭沫若早期新诗中海洋书写的重要文献。张放的《论郭沫若早期诗歌海洋特色书写中的文化地景关系》则是从四川的地方特色与海洋文明的关系论述郭沫若早期新诗中海洋因素对其诗歌中创造与新生精神的构建起到的重要作用②张放:《论郭沫若早期诗歌海洋特色书写中的文化地景关系》,《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 年第1 期。。彭松的《略论“五四”文学中的海洋书写》亦是如此,主要关注了郭沫若新诗中海洋在新世界的象征意义③彭松:《略论“五四”文学中的海洋书写》,《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3 期。。这些研究不乏历时的对照,却缺乏横向的比较,主要关注“海洋”在其诗歌中的积极性与正向性,对其新诗中海洋书写鲜明的负向性特征的认识不够充分。因而通过文本细读,结合理论,挖掘郭沫若五四新诗中海洋书写的多元面相,理清其在郭沫若五四新诗中的呈现及其形成的原因,无疑对丰富其海洋书写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静”的属性:孤寂的海洋
与郭沫若五四新诗中常被提及的“动”的海洋精神相比,郭沫若五四新诗中的海洋还具有一种“静”的属性。这种“静”常表现为一种安静平和的状态。在《夜步十里松原》中,安眠后的海洋沉沉睡去,波澜不惊:“海已安眠了。/远望去,只看见白茫茫一片幽光,/听不出丝毫的涛声波语。”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98 页、第193 页、第193 页、第150-151页、第202 页。没有波涛的海洋没有情绪的起伏,完全是一副安静的模样,带给人平和的感受。但“静”并不意味着情绪的摒除,这种“静”还表现为一种空旷的平静,它寄寓着诗人内心的孤寂。如《雨后》:
雨后的宇宙,/好象泪洗过的良心,/寂然幽静。//海上泛着银波,/天空还晕着烟云,/松原的青森!//平平的岸上,/渔舟一列地骈陈,/无人踪印。//有两三灯火,在远远的岛上闪明——/初出的明星?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98 页、第193 页、第193 页、第150-151页、第202 页。
这里的幽静是在喧杂的雨后获得的,因而存在着隐含的动静结合。巨大的喧嚣之后往往引来巨大的寂静,带给人一种空旷幽寂的感受。在经历了悲伤的高潮之后,人的情绪得到宣泄,情感开始恢复到平静状态。此时诗人由内视角转向外视角,外在的客观之物成为诗人情绪恢复后的延伸,他所看到的海洋也就呈现为一种平和的状态。而读者也不难发现在情绪宣泄后所产生的一种空寂之感:“无人踪印。”③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98 页、第193 页、第193 页、第150-151页、第202 页。没有人的参与,而只有一串客观物的自然排列,海洋似乎成为无人之域,褪去人的印记,然而诗人正是通过对主观情感的解除达到表现自身孤寂情感的目的,孤寂在解除中得到标记,并显示出其在场性。
在《岸上(其一)》一诗中,诗人对海洋“静”的描述已有所突破,由“静”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开始得到显现,一种栖身于沉默中的悲伤在诗歌中渐次展开:
岸上的微风/早已这么清和!/远远的海天之交,/只剩着晚红一线。/海水渊青,/沈默着断绝声哗。/青青的郊原中,/慢慢地移着步儿,/只惊得草里/虾蟆四窜。/渔家处处,/吐放着朵朵有凉意的圆光。/一轮皓月儿/早在那天心孤照。/我吹着支小小的哈牟尼笳,/坐在这海岸边的破船板上。/一种寥寂的幽音/好象要充满那莹洁的寰空。/我的身心/好象是——融化着在。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98 页、第193 页、第193 页、第150-151页、第202 页。
诗歌开篇依旧在写海洋的平静及其带给人的清和之感,海洋的空阔也再次得到表现。不过,诗人在《岸上(其一)》中突出了海天之交的一线,这毫无疑问把对海洋空阔的书写转移到对其随着白昼的消散而逐渐缩小、逼仄的表现上,诗人的情感也在这一转移中发生了转换。沉默不再完全意味着安静,而可能潜藏着一种断绝声音的危险。同时,因为绝对的“静”,“静”不再是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转而成为一种令人心悸的幽魔,稍有动静,就会造成惊吓和恐惧。而那些富有诗意的渔家、月光,也因为情绪的转换而不再是一种让人心静神怡的审美对象,反而成为一种映照在内心中的孤独、寂寥情绪的投射。尤其是当哈牟尼笳奏响,破船板成为诗人短暂的归宿时,一种孤寂的情绪顿然涌上心头,而一副忧郁、孤独的海洋形象也跃然纸上。
郭沫若五四诗歌中的“静”还进一步表达了一种因孤独而造成的迷茫和彷徨。在《夜别》中,诗人感受到一种无依无靠的孤独:“轮船停泊在风雨之中,/你我醉意醺浓,/在暗淡的黄浦滩头浮动。/凄寂的呀,/我两个飘蓬!//你我都是去得匆匆,/终个是免不了的别离,/我们辗转相送。/凄寂的呀,/我两个飘蓬!”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98 页、第193 页、第193 页、第150-151页、第202 页。。“飘蓬”这一意象在古诗中较为常见,其最早出自南朝梁·刘孝绰《答何记室》中“游子倦飘蓬,瞻途杳未穷”⑥(清)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873 页。一句,用来指代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郭沫若在使用“飘蓬”表达自身的漂泊感时,突出了一种孤独的性质:同为“飘蓬”,本应能够互相理解,但终究还是在别离中无法达成,这比刘孝绰《答何记室》中游子的境遇更为凄惨,因而其漂泊感也更为强烈。而这种孤独的漂泊感导致了一种迷茫,不知该向何处去,亦不知未来的路该怎么走的情绪。
在表现海洋的“静”时,郭沫若善于借用传统的诗歌资源,首当其冲的并非我们所熟知的李白的诗歌,而更像是婉约的宋词,带有一种清丽的性质。比如《霁月》:
淡淡地,幽光/浸洗着海上的森林。/森林中寥寂深深,/还滴着黄昏时分的新雨。//云母面就了般的白杨行道/坦坦地在我面前导引,/引我向沈默的海边徐行。/一阵阵的暗香和我亲吻。//我身上觉着轻寒,/你偏那样地云衣重裹,/你团围无缺的明月哟,/请借件缟素的衣裳给我。//我眼中莫有睡眠,/你偏那样地雾帷深锁。/你渊默无声的银海哟,/请提起幽渺的波音和我。⑨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203-204 页,第206 页,第147 页。
诗中使用了一些叠词:“淡淡”“深深”“坦坦”,它们的音节较轻,同时韵律上的重复具有一种绵延的性质,这无疑增强了“哀愁”的声音表现效果。而且这些叠词的选择与婉约的宋词是极为类似的,它唤醒了读者脑海里曲径通幽的记忆,召唤出一种共同的体验结构。而“幽光”“海上的森林”“黄昏时分的新雨”“暗香”“明月”这一类主体意象的选择,在继承传统诗歌资源的基础上又生成了一些新质,那种绵密、延伸的质感,幽静的触觉体验,都为诗歌增加了一种婉约的效果。“轻寒”“重裹”“缟素”“雾帷深锁”这类古典式的表达,更加显露出诗歌的价值取向。诗人无论是在意境的营造、词汇和句式的选择,体验的表达上,都与婉约的宋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郭沫若的借用,不是一种不假思索的照搬,而是一种通境的融化,它也显示出郭沫若“五四”诗学的另一种取向。
二、“动”的属性:死亡的海洋
郭沫若“五四”新诗中的海洋书写也有“动”的属性,但这里所说的“动”不同于已被多次论述的具有一种积极力量的“动”,而是指一种与其建设性相反,呈现为一种破坏性的“动”,它给人带来不适、灾难甚至死亡。这与杨振声小说中的海洋书写不同,杨振声小说中海洋的“破坏性”完全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破坏⑩赵刘昆:《古典、日常与异域想象——杨振声小说中的海洋书写》,《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22 年第3 期。,而郭沫若“五四”诗歌中海洋虽然也有这一作用,但与此同时还具有一种消极的、负向的、毁灭性的破坏。相反,郭沫若“五四”诗歌中海洋却与庐隐小说中的海洋有诸多相似之处,那种迷茫、孤独与毁灭性死亡的海洋体验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现。与杨振声和庐隐小说中海洋书写的“同”与“不同”,也正显示出“五四”作家对待海洋不同的态度。杨振声更多的看到了海洋正向性的一面,而庐隐和郭沫若在看到海洋积极的一面时,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海洋的负向性。
郭沫若“五四”新诗中的海洋体验有给人带来不适的一面,它已经暗示着海洋的力量具有非人的一面。在《海舟中望日出》中,海洋给人虚无、空洞、动乱、荒凉和惊悸的不适感:
铅的圆空,/蓝靛的大洋,/四望都无有,/只有动乱,荒凉,/黑汹汹的煤烟/恶魔一样!//云彩染了金黄,/还有一个爪痕露在天上/那只黑色的海鸥/可要飞向何往?//我的心儿,好象/醉了一般模样。/我倚着船栏,/吐着胆浆……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159 页,第108,第198 页,第212 页。
Grice(1967)提出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on Principle” ,即说话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规则,相互配合。合作原则包含的四个准则是: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其中质的准则要求不说自己认为是不真实的话、不说自己没有足够证据的话。跨文化商务交际中的模糊限制语的运用遵循了该准则。
在一种颇有庄子“圆空”“无有”的风格叙写中,郭沫若赋予了诗歌中的海洋以“黑暗意识”,海洋积极、温馨甚至安静的一面荡然无存,转而成为一种具有异质性、陌生化的、带有隔膜的海洋。诗人在这里使用了“远取譬”的喻象方式,用恶魔指代煤烟,天上也能留下海鸥的爪痕,无疑通过强制阐释的方式赋予诗歌以陌生化效果,同时通过这种强制阐释生成了诗歌的张力。这种异质、陌生的海洋仿佛具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带给人呕吐、眩晕的不适感,而这种海洋体验正是一种以亲历性为基础的真实的海洋,它蜕去了美化的外衣,呈现出其中的残酷与真实。海洋不再是沟通、连接的桥梁,也不再是抚慰人心的艺术装置,而成为一种现实的、具有距离感的阻隔,也成为诗人要克服的对象。海洋与人的分离、对立在逐渐加剧,双方的边界与结构在这种博弈中不断发生变化,海洋的自我意识不断从人的意识中脱轨,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觉之物。表面上抒情主人公急不可耐地宣布战胜了海洋,实则海洋已成无法真正战胜的物自体。在《巨炮之教训》中,“博多湾的海岸上,/十里松原的林边,/有两尊俄罗斯的巨炮,/幽囚在这里已十有余年,/正对着西比利亚的天郊,/比着肩儿遥遥望远”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159 页,第108,第198 页,第212 页。。在这里,海洋成为阻隔人与家乡的沟壑,成为阻断人与人情感交流的异物,它引发了人的思乡之情,因而它也成为人所要克服的对象。但实际上这种克服是不可能的。
在郭沫若的“五四”新诗中,海洋不仅是异质的,也是浑浊不堪的,它暗示着一个腐朽、污浊的现实世界。如《黄海中的哀歌》:
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我的故乡,/本在那峨眉山的山上。/山风吹我,/一种无名的诱力引我,/把我引下山来;/我便流落在大渡河里,/流落在扬子江里,/流过巫山,/流过武汉,/流通江南,/一路滔滔不尽的浊潮/把我冲荡到海里来了。/浪又浊,/漩又深,/味又咸,/臭又腥,/险恶的风波/没有一刻的宁静,/滔滔的浊浪/早已染透了我的深心。/我要几时候/才能恢复得我的清明哟?③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159 页,第108,第198 页,第212 页。
诗人以峨眉山上的清泉自比,描述了自己在海洋之力的吸引下如何“流落在大渡河里,/流落在扬子江里,/流过巫山,/流过武汉,/流通江南,/一路滔滔不尽的浊潮”,最终被冲荡入海,成为大海的一部分。但这大海却是污浊、腥臭和充满险恶的,它被郭沫若用来代指现实,而自己这滴清泉,最终也在污浊的海洋中迷失了自己,诗人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也能感受到诗人自己也已经沦落为海洋污浊中的一份子了。海洋不仅在理论上被视为异质之物,当其降落人间时,郭沫若赋予它的,不是理想式的纯净,反而是现实感极强的污浊,海洋的负性特征再一次得到加强。
同为降落人间的海洋,《暗夜》中的海洋则是悲戚的,它显露出一种日常性的悲伤和凄惨:
天上没有日光,/街坊上的人家都在街上乘凉。/我右手抱着一捆柴,/左手携着个三岁的儿子,/我向我空无人居的海屋走去。//——妈妈哪儿去了呢?/——儿呀,出去帮人去了。/——妈妈帮人去了吗?/——儿呀,出去帮人去了。//远远只听着海水的哭声,/黑魆魆的松林中也有风在啜泣。/儿子不住地咿咿哑哑地哀啼……/儿子抱在我手里,/眼泪抱在我眼里。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159 页,第108,第198 页,第212 页。
“海洋”在郭沫若的“五四”新诗中是一种具有毁灭性质的宏大力量,它已经脱离了人的掌控范围。在《新阳关三叠》中,“我独自一人,坐在这海岸边的石梁上,/我在欢送那正要西渡的初夏的太阳。/远远的海天之交涌起蔷薇花色的紫霞,中有黑雾如烟,仿佛是战争的图画”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104 页,第39 页,第151 页,第189 页,第180 页,第199 页。。诗人独自一人远眺海洋时,跃入诗人眼帘的美景瞬间就转化为一幅战争图景,其中的隐喻表达着十分显著的事实:海洋的美丽与灾难的转化只在瞬间。它已经提示人们,海洋的本质终究是一种强大而无法掌控的力量,因而往往发展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在郭沫若最为著名的诗篇《凤凰涅槃》中,诗人对海洋汹涌的毁灭性具有深刻的认识:“啊啊!/我们这缥缈的浮生/好象那大海里的孤舟。/左也是漶漫,/右也是漶漫,/前不见灯台,/后不见海岸,/帆已破,/樯已断,/楫已飘流,/柁已腐烂,/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唤,/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104 页,第39 页,第151 页,第189 页,第180 页,第199 页。在这里,海洋是具有毁灭一切力量的凶残之物,它摧毁了所有能够栖息、依靠的空间,让人处在一个不确定的时空中漂流,这是一种断裂性的破坏,它使身处其中的个体处于孤独和茫然之中,而且这种孤独和茫然是没有尽头的。在这里,郭沫若再次为我们阐明了孤独、迷茫的来源:海洋的破坏性力量。它也暗示着大变动时代中如蜉蝣一般的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尤其是青年,无法在变动中改变自己、改变社会,缺乏根本的信念和勇气,因而迷茫、困顿和孤独。
在《岸上(其二)》中,海洋的深不可测及其背后隐藏的令人恐惧的力量再一次得到显现:我独自一人/坐在这海岸上的渔舟里面,/我正对着那轮皓皓的月华,/深不可测的青空!/深不可测的天海呀!/海湾中喧豗着的涛声/猛烈地在我背后推荡!/Poseidon 呀,/你要把这只渔舟/替我推到那天海里去?”③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104 页,第39 页,第151 页,第189 页,第180 页,第199 页。。那些在传统诗歌中的纯粹审美对象如今已换了一副面孔,成为一种无边无际、深不可测、无法捉摸更无法把握的异质力量,更让人感到后怕的是,这一力量是非人的,是对抗性的,是处在对立面的,它像一个邪恶的小人,将人推入一个毫无边际的深渊,让人时刻处于漂浮状态之中,永远无法靠岸,因而它制造了一种绵延不断的恐惧、不安和孤独。其实诗人已对海洋的危险有所体认和警觉,在《偶成》中,诗人已经体认到海洋的危险性:“月在我头上舒波,/海在我脚下喧豗,/我站在海上的危崖,/儿在我怀中睡了。”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104 页,第39 页,第151 页,第189 页,第180 页,第199 页。诗人明白,海洋看似美丽、温馨的外表其实只是一种短暂的掩饰,其背后蕴藏着危崖式的凶险,一不小心就会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海洋的宏大力量最终因为无法掌控而给人带来灾难,它喻示着海洋这一力量最终转化为一种完全破坏性的力量。在《洪水时代》,海洋让人联想到史前时代的洪水,它是一种灭绝性的破坏力量,给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灭顶之灾:“我望着那月下的海波,/想到了上古时代的洪水,/想到了一个浪漫的奇观,/使我的中心如醉。/那时节茫茫的大地之上/汇成了一片汪洋;/只剩下几朵荒山/好象是海洲一样。/那时节,鱼在山腰游戏,/树在水中飘摇,/孑遗的人类/全都逃避在山椒。”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104 页,第39 页,第151 页,第189 页,第180 页,第199 页。海洋成为洪水猛兽,激起人沉睡已久的恐惧体验,这种恐惧不是个体性的,而是一种具有集体无意识性质的共同体验,因而其震撼效果更为显著,其带给人类的灾难也更为深广,甚至几乎造成人类生命的灭绝,足见其力量的毁灭性质。在《吴淞堤上》一诗中,诗人进一步发挥、阐释了海洋的毁灭性:“一道长堤/隔就了两个世界。/堤内是中世纪的风光,/堤外是未来派的血海。/可怕的血海,/混沌的血海,/白骨翻澜的血海,/鬼哭神号的血海,/惨黄的太阳照临着在。/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大陆,陆沉了吗。”⑥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104 页,第39 页,第151 页,第189 页,第180 页,第199 页。一幅恐怖的末日景象呈现出来,而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正是海洋本身。海洋成为一个屠戮生命的死亡之地,诗人在这里特别突出了海洋的死亡性质,它不仅仅是带来灾难,而且从根本上褫夺着人的生命,把人间变成地狱、变成世界末日。而这一惨象其实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海难而已,可见海洋还没有使出它的全力,也从一个侧面可知一旦其用尽全力,其后果无法想象。人在海洋面前的渺小与无助再一次得到凸显。《冬景》同样对末日景象的海洋进行了简述:“海水怀抱着死了的地球,/泪珠在那尸边跳跃。/白衣女郎的云们望空而逃,/几只饥鹰盘旋着飞来吊孝。”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第210 页。地球已经死亡,人自然也就不再存在,留存的只有海洋、泪珠,连天空飘浮的云朵也望风而逃,足见其恐怖程度。
不管是郭沫若对海洋“静”之孤寂的书写,抑或是对海洋“动”之“凶险”的书写,其实都暗含着一种反思。在郭沫若的大部分诗歌中,海洋都是一种正向的力量,具有反抗压迫、破旧立新、追求自由等多重积极意义,而郭沫若诗歌中对海洋的负向书写则显示出他对海洋及其代表的力量的一种反思,体认到力量转化的辩证法:一旦力量不能为己所用,则极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敌对的毁灭力量。而且这种毁灭性的力量是不在破旧立新这一维度上的,因此它构成了进步道路上的阻隔和障碍。而郭沫若之所以会创造这一负向性的海洋,与当时的整体环境不无关系。“五四”的兴起与发展是短暂的,紧接而来的是持续的落潮和沉默时期,理想的失落,价值观念的破裂成为当时青年人的普遍状态②中南区七所高等院校合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第20-28 页。,郭沫若明显体认到这一现实并将其通过海洋书写表现出来。反动势力的反扑是血腥而残酷的,曾经的战友转而成为敌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整个社会的环境急剧转换,就像他在《黄海中的哀歌》中所表现的那样,整个社会业已污浊不堪,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恐怕都难以独善其身,杀戮、死亡和阴谋成为一种常态。郭沫若也深陷于悲哀之中。
郭沫若“五四”新诗中负向性的海洋书写提示我们,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不仅创造了一个破旧立新的正向世界,也创造了一个平静、幽寂、死亡的负向世界,它所显示出的是郭沫若诗歌中的一种复杂性。负向性的海洋书写昭示着一个诗学问题,即郭沫若诗歌的日常化面貌。在郭沫若的“五四”新诗中,对旧社会压迫的反抗和对新世界理想的追寻都是政治性的,郭沫若在这样的海洋书写中表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海洋精神,而当进入日常的琐碎、循环往复中时,日常就成为政治的低潮存在,它对政治和革命具有一种消解作用,因而其正向的书写在此遭遇了挫折,理想下降,转而成为一种贴地的现实,因而其海洋书写就呈现为负向性。它所展现的是郭沫若在其“五四”新诗中处理复杂现实的不同策略和取向。在表达理想时,往往与政治结合,并使用一种激昂的语调,形成一种正向的诗学理念,而在处理日常时,则往往捕捉到一些灰色的细节,因而形成了一种负向的诗学理念。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两种不同取向的海洋书写(诗歌理念)能够在郭沫若诗歌中并存的原因。如果再细致一些,不难发现这种负向的海洋书写也与郭沫若承续的诗歌资源有关,这里的资源当然不会是李白和惠特曼,而恰好是陶渊明、王维和柏格森。其中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诗歌线索,而这种诗歌线索也与郭沫若两种不同的诗学取向一致。李白、惠特曼的诗歌理念都与政治密切相关,政治性较强,而陶渊明、王维和柏格森则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善于挖掘日常中的诗歌张力。因而郭沫若负向性的海洋书写自然是接受陶渊明、王维和柏格森的影响,而这也刚好影响了他的负向性诗学。对平静、虚空、孤独、死亡的关注分别取自三人不同的侧面,陶渊明的平静,王维的虚空,柏格森对孤独和死亡的倾注,这种诗学的理论渊源在郭沫若的诗歌中得到了传承,并被他综合发挥。
三、结语
如果说郭沫若“五四”新诗中对海洋的正向书写表达了他破旧立新、反抗一切压迫的精神主张,反映了其对西方式自由民主理想的追求,映照出一种“力”的美学的话,那么他对海洋的负向书写则表达了一种清寂、孤独、悲伤乃至死亡的意识,这一意识反映了郭沫若“五四”新诗中的另一向度,即深受不同诗学取向的影响而无法摆脱的事实、对世界幽暗之处的开掘和一种日常诗歌范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