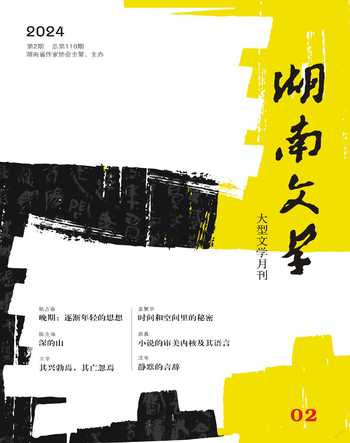不幸的生活与叙事的疗愈
黄德海
在《诗可以怨》里,钱锺书谈到了司马迁著名的“发愤说”:“《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以至刑罚折磨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
沿着这个意思推论下去,现在的很多小说,非常可能是一个“发愤”即疏通郁结的过程,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疗愈。这类小说首先需要展示的,是郁结本身。从这个方向看,无论《在山中》还是《世间的盐》,费晓熠关注的,是那些无法用简单方法处理的不幸生活,以及这些不幸带来的郁结。
《在山中》讲的是失去母亲的兄弟俩,哥哥大脑受到损伤,弟弟则一直感受到压力。《世间的盐》的主角妄想症逐渐严重,越来越多的时间生活在臆想里,跟真实世界建立不起良好的关系。无论他们的表现多么不同,都因为生活的遭际而内心有所郁结,幸福对他们而言遥不可及。
不幸的生活世间多有,要怎么写才算得上一个不错的小说呢?费晓熠用的是部分遮挡的方式,从不给出全知视角,叙事仿佛电影的主观镜头,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读者只能随着某个主人公的眼睛去发现。这样的视角限制,有效保护了小说的叙事动力,不致因剧透太多而让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
《在山中》的信息获取渠道是“他”。读者跟着“他”,发现这个家庭的不幸在于母亲抛夫离子去跟商贩私奔,随后异父哥哥得了脑膜炎,治疗后变得又聋又哑。因为“他”女友的善意参与,哥哥跟随“他”到城里看病,诊断的结果是“除了脑膜炎,他哥的脑部还受过伤,这才导致智力发育迟缓和思维混乱”。沿着这条线索,“他”逐渐意识到,“没有什么商贩,没什么抛夫弃子,从来都只有一个女人,想带着她的骨肉走出去”——母亲是父亲买来的,她想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困住自己的大山,却被人阻止,哥哥头部受伤,从此变得聋哑,而“他”则在很长时间里剔除了记忆中的这部分。
《世间的盐》叙述者是“我”,照小说开始的说法,“我”到峡岛去找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度过了艰难的时光,但在离开时杀死了她。随后,“我”坐上绿皮火车离开峡岛,中途下车来到箩州,经历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在某个迷离惝恍的时刻,“我”意识到此前的故事都出于自己的臆想,那些“我”以为的迫害、欺骗、杀害,不过是妄想症发作的产物。小说来到结尾,读者意识到,“我”并没有杀死自己的女友,只是在意识到妄想袭来时,自己溺毙于海水之中(小说技术上,这里有个问题或许需要注意,“我”已溺亡,是谁讲了上面这些呢?)。
把这些不幸的生活连带人物的郁结讲出来,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并非只是展覽。如果我们没看错,费晓熠叙事的重心在于纾解或疗愈。
《在山中》里,哥哥又聋又哑,“他”心事重重,因为两人都经历过母亲被拦截下来,然后消失了的过往。可记忆太过沉重,他们都无法直视。直到哥哥被点出脑部受过伤,“他”才开始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事。哥哥则在挖出一具白骨之后,认为终于救回了母亲,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在始终遮挡着部分事实的叙事中,小说完成了兄弟俩的创伤记忆修复。
《世间的盐》里的“我”,一直生活在妄想之中,这妄想不仅折磨着他自己,也一并折磨着自己的女友。“我”不肯承认自己患有妄想症,因此双重折磨一直存在。直到女友说出,“有病得治,你已经出现妄想症状了,得干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才稍微清晰地辨认出现实生活的样子,恢复了拥有幸福感的能力,至死还紧握着跟女友的合影。
谈论古希腊文学时,经常出现卡塔西斯(katharsis)这个词,陈中梅释义为:“katharsis既可指医学意义上的‘净洗’和‘宣泄’,亦可指宗教意义上的‘净涤’。”在汉语中,卡塔西斯通常被翻译为“疏泄”“净化”或“陶冶”,如果用在写作上,其实就可以是打开郁结的意思。费晓熠的小说,是否部分上有这样的疏泄效果呢?
没有人能完全把不幸扭转为幸福,不过,在叙事中疗愈不幸中的某些部分,已经足够有意味了,不是吗?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