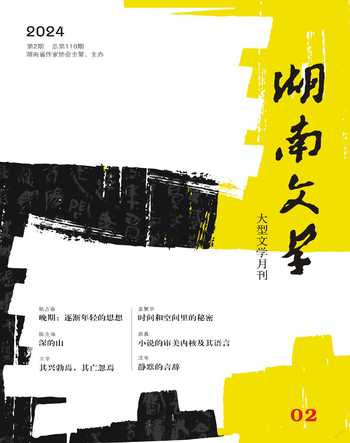小说的审美内核及其语言
阎真
文学作品是一个思想性的存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也是历史、哲学等层面的存在。但作为这一切的基础,它是审美的存在。只有在审美存在的意义上,我们才能说,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存在、社会历史存在等,才是合法的、有意义的,或者说有效的存在。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无意义的、无效的存在。因为,我们是在谈文学。
既然我们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社会学的教科书,我们就不能超越艺术判断而直接进入思想的分析。它是审美的存在,审美性就是它的本质,也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审美性体现在什么方面?体现在这个作品的艺术具体性。艺术具体性是它的价值起点,也是它的价值终点,至少是价值起点。不然,文学有什么独立的存在意义?有什么属于自身的学科定位?说到价值终点,我们可以说,从艺术具体性出发,它还有基于审美性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等等。而历史内涵和思想意义的表达,要从艺术的通道进入,才是文学意义上的合法表达。如果说绝对点,审美性也是价值终点,即使一部作品的这种审美并不通向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思想表达,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完成了的作品。比如我们读《红楼梦》,审美性就是它的价值终点。我们知道这个人物的性格、那个人物的形象等等,至于这个形象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如王熙凤有什么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很难说,但我们不能因此说王熙凤这个形象是没有意义的。她的感性、生动性,就是她的意义。所以说,艺术标准是前提性的、基础性的标准。在这个前提下,这个基础上,我们进入思想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等。这样一个前提,在我看来是不能超越的。虽然在某些批评实践中,比如说女权主义批评、社会学批评、政治批评、社会历史的批评等,不谈作品的审美意义,直接进入分析批评,也是可以的。不一定每次批评的时候都把审美、艺术放在前面,然后再展开其他方面的批评,因为我就是谈“那个”问题。比如说评《孔乙己》,我就直接谈思想意义;比如《三国演义》,我就不从形象的艺术性出发,我直接谈正统观念的问题,小说有没有尊刘反曹。但我作为一个艺术本位论者的基本观念是,我们是在艺术标准这样一个默认的前提下展开思想的、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批评。
同时,我也认为,艺术是起点,但并不是一切。小说还要有精神层面的表达,用具体超越具体,就是肯定精神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的表达。超越具体,它的格调、境界,它的思想表达等等,也是很重要的,这种表达跟艺术当然不是脱节的,要得到艺术的呈现。虽然思想性有它的独立价值,但它的独立价值不能脱离艺术性,脱离了就不是在谈文学了。我们分析作品的时候,可以在默认其艺术性的前提下分析它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这种对思想价值、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价值的分析,就是大命题写大文章。小说的命题在什么层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层面,这个命题比较容易获得社会普遍的认同。如果在个人小情感的方面,这个命题的境界可能会上不去。比较鲁迅和琼瑶可以更明白何谓“大命题写大文章”。鲁迅的小说创作在数量上也许只有琼瑶的几十分之一,但是它的意义和分量远远不止琼瑶的几十倍。为什么?琼瑶写了那么多,几十部小说,鲁迅的小说就是薄薄的两个小册子,《呐喊》《彷徨》,再加上《故事新编》。但是琼瑶的意义和价值根本不能与鲁迅相比。大命题写大文章,这也不完全是个艺术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有感受的。什么感受呢?我的小说《沧浪之水》,写的是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知识分子心态,收到了比较好的社会反响,现在已经再版八十多次了。后来我又写了《因为女人》,想以此讨论现代女性面临的情感挑战。我开始設想,这个命题,这个小说,不是有更广泛的社会性吗?有些人对政治文化不感兴趣,他们可能对我们这个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们遇到的挑战有兴趣。这个话题不是更加有普遍性吗?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界,对《沧浪之水》以及后来的《活着之上》的评价还是要高些。它们的销量还是要多一些。所以说,在中国这个语境中间,大命题写大文章,这一点还是非常有效的。应该说,这种有效性,也是世界性的。
说到艺术,特别是小说的艺术的时候,语言就是一个核心指标。这个指标有什么意义?这个指标对于小说作者来说,具有身份界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你只有恰当地运用了语言,作品在语言表达上有审美的感觉,你才够资格称为一个作家。如果你的语言平板、规范,没有弹性、张力、活力,没有那样一种“用毕生的才情和心血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感觉,那么你的语言就是很平庸的,你作为一个作家也是很平庸的。一个语言平庸的杰出作家,这样一种存在状态,虽然在我们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存在着,但在我看来,这是不能够成立的。对于一部小说来说,语言艺术是它的价值基础。汪曾祺说,一部小说非常优秀,就是语言差点,这种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就像人们说一个音乐作品非常优秀,就是旋律差点,一张绘画作品非常优秀,就是色彩差点,这种说法同样不能成立一样。如果我们同意汪曾祺的说法,用这样的眼光看中国新文学,文学史格局的变化将是震撼性的。所以我说,文学史不能因为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理由,将语言平庸的作家置于核心地位。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这句话表达了什么?第一个层次,它表达了,作为艺术,文学跟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是不同的。简而言之,绘画用色彩、线条来表达,音乐用旋律、节奏来表达。音乐可以没有一个字,可以没有词,比如交响音乐。但文学作品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它必须有文字。但这个层次没有解决语言艺术的问题,因为也有平庸的语言,用语言来表达的艺术作品中,有平庸的作品,也有优秀的作品。因此,这句话的第二个层次就说明,用语言构成的文字材料,有些是艺术,有些不是艺术。报告、通讯、论文、时尚杂志文章等等也是用语言构成的,但是它们不是艺术,至少不是文学艺术。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大多数用语言构成的文字材料都不是艺术。艺术要有形象和情感这两大要素。我们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时候,就是在说文学的语言是有形象性的,是有情感性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触及到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的真正的内核没有?也没有。因为有情感,有形象,也可能是非常幼稚的作品,如平庸的小说。小学生写的那些作文也有情感性,也有形象性,它是艺术吗?你说它是艺术也可以,是很低层次的艺术。当然有形象性有情感性,我们都可以说它是艺术,都是文学。
但是,好的文学和坏的文学的分野在什么地方?这就要进入第三个层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核心的表达。这句话,它真正要表达的,就是优秀的文学和平庸的文学的分野所在。也许我不应该用“优秀的文学”这样的字眼,“优秀的文学”还是有点不准确。因为有时候一部作品没有充沛的语言艺术,它在别的方面还不错,它也成了文学,甚至我们还不得不说它是“优秀的文学”。但是至少我可以这样表达:好的小说,它的语言艺术和平庸的小说的语言艺术层次是不一样的。很多有名的作品,它在语言艺术上是比较一般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充分体现出语言的艺术,它不过是有情感性,有形象性,而且情感或许还很强烈,但是,语言上不一定达到了艺术境界。它只是用规范的、正统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语言的表达当然有它的长处,就是人人都懂。规范的语言人人都懂,但是没有给人一种创造的感觉,即这个作家写的句子,是别人写不出来的。如果一般读者觉得,这样的句子我也可以写出来,那肯定是没有语言艺术的,没有体现出“用毕生的才情和心血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样一种语言的才华和境界。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一些现代文学名作,比如说茅盾先生的《子夜》《幻灭》《动摇》《追求》,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等,在语言艺术这个指标上,是比较一般的;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红岩》等等,在语言艺术上也是比较一般的;后来得了茅盾文学奖的不少作品,在语言艺术上也都是比较一般的,比如《钟鼓楼》《将军吟》《沉重的翅膀》等等。这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也不能说它们一点语言的艺术都没有,而是语言的艺术性整体比较一般。那么什么作品语言艺术是非常好的?这充分体现在鲁迅的小说《祝福》《孔乙己》、老舍的《骆驼祥子》、钱锺书的《围城》、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陈忠实的《白鹿原》、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长恨歌》等等小说中,还有莫言和贾平凹的小说。这些小说有那种语言艺术的感觉。总而言之,如果要区分一部作品有无语言艺术的话,我暂且做这样一种比较直观的、但也不失为准确的、朴素的判断:有语言艺术就是让读者觉得“我看得懂,但我写不出”;没有语言艺术就是让读者觉得“这个我也写得出”。
责任编辑:罗小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