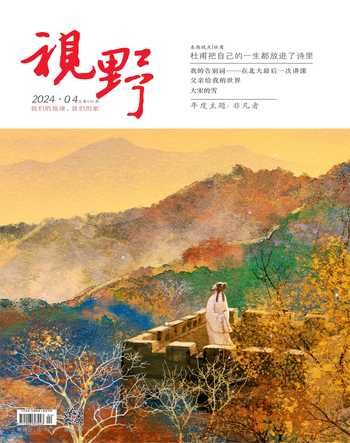我的告别词
钱理群

今天是我在北大,在大学正式讲台上,最后一次讲课,所以要利用最后的时间,说一说我最想对北大学生讲的话,我对北大学生的期待。
关于“北大失精神”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我们都是普通的老师与学生,无力抵挡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坚守”:当政治的逻辑、资本的逻辑笼罩一切时,我们还要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
因此,我对北大学子有两个期待。首先是——
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这就是说,你或许从政,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政治家、公务员,而不是谋求私利、见风转舵的政客和唯唯诺诺、无所事事的官僚。
你或许经商,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創造精神的企业家、经营者,而不是投机取巧、谋取暴利的奸商,无所作为的庸商。
你或许治学、任教,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你也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学者、教师、编辑和记者,而不是出卖灵魂的帮闲、帮忙文人,混迹文坛学界的无用之人。
当然,如何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遇,也有不同的气质和才能,因此,其表现形式、发挥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同学可能表现比较突出,发挥比较充分,成为一个杰出人才;更多的同学则尽职尽责,但也自有操守:有所为(创造),有所不为(怀疑、批判),更有独立、自由的思考与人格。这是我们的底线,是不能轻言放弃的。
我还有第二个期待——
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的大地。
在1999年12月,我写了篇短文:《新世纪寄语青年》,我这篇短文的重点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是希望北大学子,也希望我自己,目光永远向前——要听得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这里说“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是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的:21世纪,无论是世界、中国以至我们自己,都会遇到非常复杂的、难以预测的情况,这将是一个既有大发展,又会有许多新的困惑以至迷茫的时代。这就很容易产生“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今天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诸位讨论。
当年鲁迅在他《野草》里的《过客》中,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文章中的“小女孩”(或许就包括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的在座的诸位)说:前方是“花园”,但这很可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美丽的梦;“老人”(大概就是我这样的饱经风霜的一代人)说:前面是“坟”,这或许是反映了更根本的真实。问题是面对这样的前景的态度:“老人”宣布,他将“休息”,不再往前走;而鲁迅笔下的“过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却在短暂的犹豫以后,表示:我不能“回转去”,也不能“休息”,因为“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我只得走!”
“过客”的这种“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的精神,是很有启发性的。这里所说的“声音”其实是自己内在生命的“绝对命令”,就是说,不管前面是什么,即使是“坟”,也绝不后退,绝不停留,绝不气馁,绝不放弃,要“走”,“往前走”,不断地探索、寻找。我在这里郑重地把鲁迅的这一“过客精神”推荐给诸位,就是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什么情况下,即使是最困难,似乎绝望的时候,也不气馁,不放弃,“目光永远向前”,“不停地往前走”,保持积极向上、向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精神状态。
我的“目光向下”的期待,则包含了我的一个隐忧。北大的教育越来越成为伪精英教育。
所谓“伪精英教育”的要害,实际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通过北大这座桥梁,挤进既得利益集团。这本是蔡元培那一代先驱所反对,所要竭力避免的。所以蔡校长在就任第一天的演说中,就谆谆教导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一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大家不妨看看今日之北大,谁入学不是为了做官、致富,北大早已成为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了!问题是,北大以及中国大学的这些蜕变是有社会基础的。
在应试教育下,诸位吃得“十二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寒窗苦”,好不容易通过“千军万马独木桥”,闯进了北大这个最高学府,不要说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家长,连你们自己,也都希望“近水楼台先得月”,用北大这块牌子挤进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以及你们的家长,希望通过读北大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被培养成社会精英,即所谓“跳龙门”,或者说社会底层成员的向上流动,这都是正当的、合理的,这也是一种基本权利。
问题在挤进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这也是社会培养的)。更严重的是,到了北大以后,所接受的又是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蔡校长竭力反对的极端之国家主义教育和极端之实利主义的教育,而这两大极端教育,表现在北大这样的所谓重点之重点大学,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伪精英教育,不是培养真正的社会精英所必有的公共利益意识、社会关怀、底层关怀,而是灌输以“他人为敌人”的弱肉强食的所谓竞争意识,鄙视劳动、劳动人民。
在这样的教育下,所培养出来的所谓“尖子”学生,他们身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而且是建立在高智商基础上的,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信仰、信念的,精密、精细筹谋的利己主义;二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不仅存在认知上的陌生感,而且在情感和心理上都有一种疏离感,他们似乎都是世界主义者(尽管他们把爱国主义的口号喊得响入云霄),但其实不想也不能进入他国世界,只有孤立的个人,这样的失根无根的状态,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痛苦,但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不会感觉到的,因为这个社会会使他们感到游刃有余,他们正在被这个体制培养为接班人。
为谋利可以听命一切。培养并输送这样的接班人,是正在贯彻的国家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之极端的伪精英教育的目标所在。完成这样的国家使命,就是一流大学了,如果进一步还能够执行国际资本的意志,那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而我们所能做的,依然是绝望地反抗。提出希望北大学子“目光向下”,正是要自觉地抵御这样的伪精英教育。所谓“目光向下”,就是要关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谋利益: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
以上这番话:关于大学教育,关于北大传统,關于我对北大学子的期待,都是一些胡思乱想,也很不合时宜,有些话可能会犯禁,同学们也未必同意,但都是我的心里话,已经憋了很久了,说出来,也就是“立此存照”。讲完了,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这些年,我突然成了北大最有争议的人物。之所以会这样,无非是从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开始,我不断地发出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的批判的声音,原因也是我太爱北大,爱之愈深,也就骂得愈厉害。其实,我的批判或骂,就是我最后这几次课所讲的内容,不过是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和想法而已。
我也曾想,我在北大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曾经说过,燕园的林子很多,各样的鸟都有,我大概是一只乌鸦,北大的一只乌鸦。我说过,北大如果都是乌鸦也不行,都是喜鹊可能也不行,学术、教育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各样的鸟。这就叫“兼容并包”。我希望成为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有自己独立个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我从来不试图将自己的人生之路、治学之路,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给学生,我最喜欢对学生说的话,就是“我姑妄讲之,你们姑妄听之”。但无可讳言,这些年我对北大越来越失望。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似乎不太适合在北大生存了。我大概是该走的时候了。
这些年,我和许多北大以外的青年通信,是深感北大在这些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的。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神话,我写回信的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它;但我又不忍心打破: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经济的双重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失去了梦乡,连梦都不能做,那就太可悲、太危险了。当意识到北大的表现使这么多年轻人失望,我突然感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因为我是北大一个成员,北大的问题和我有关。坦白地说,过去我在北大内部批判北大,就很少联系到我自己,现在听到了北大外的年轻人批评的声音、失望的声音,就觉悟到这就是在批判我自己:我和北大同时站在被审台上,我们辜负了民族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的期望!
现在,我要离开北大的课堂、讲台了。这意味着,一段与北大的因缘的结束,一段与课堂的因缘的结束,一段自我生命的“死去”。
但我的生命的活力还在,一段新的生命也就在结束、死去的这一瞬间开始。
有同学问我,老师,退休后你要到哪里去?
我的回答是——
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
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的改革。
这“三回归”就是回归家园,回归生命的起点。
同时要始终守住鲁迅。
该说的都说了,就到此为止吧。谢谢大家!
(桑宁摘自微信公众号“琐碎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