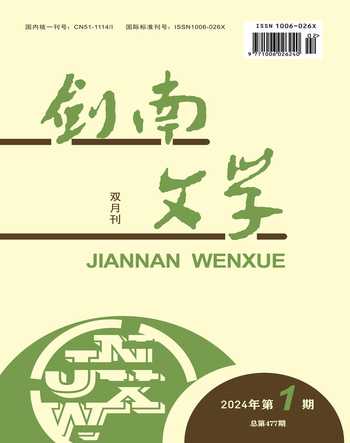潜沉于心灵深处的乡土记忆
近段时间以来,笔者常常喜欢翻阅一些过往的旧书。这似乎有些追随先贤的遗风,据说当年的鲁迅、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名流就有翻阅旧书的嗜好。这些所谓的旧书,有的厚重得如金子打造出的砖头,有的轻盈得如一片洁白的羽毛。这些旧书主要为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但更多的是文学方面的著述,包括众多本地作家出版的各种文集,王德宝的《浮出泥沼》便是其中之一。这是王德宝出版的第一部散文诗集,是他在各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大量散文诗作品,作者也因此成为那个时期诗坛上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关于这部薄薄的散文诗集,笔者依稀记得,以前曾写过几篇评论文章,便静下心来细细地展读。随着重读的渐次深入,再对照所写的评论文章,进行认真详尽的检视,竟然发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地方性的文学创作而论,它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诗集。因为它不仅仅把作者对于故乡、对于亲情、对于爱的全部记忆,毫无保留地呈奉给广大读者,还将作者对于故土、亲人、情爱的深沉眷顾,描绘得是如此的情感纯净、思想饱满、灵魂通透,从而富于了情思之华的内核和诗意之美的张力。
笔者历来认为,意欲走进一个诗人的诗意世界,就必须首先对这个诗人的生活经历与人生际遇有所了解和认知,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探寻,既有助于我们理清诗人为什么会走上诗歌创作之路,又得以明白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表达的内心情感和思想意图,也更能够知晓诗人具有怎样的个性气质和灵魂内里。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考察诗人创作之路的缘起,也是探究诗人诗意之行的终点。诗人出生于川北丘陵深处一个非常普通的乡村,其童年和少年的生存经历,与许多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农村人一样。由于当时的生产技术相当落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再兼土地十分贫瘠,所产出的各种粮食便十分有限,除了完成交公粮的任务,家里的粮食已是所剩无几,如果再逢久旱不雨的天灾,收成就更见其少,甚至是颗粒无收。因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儿童,不是成天喝稀粥和玉米糊,就是吃两三坨煮熟的红薯,备受贫穷和饥饿的反复折磨。从另一个角度看,深居于起伏的丘陵之中,满眼皆是错落有致的田畴、弯弯曲曲的田埂、涓涓流淌的小溪、点缀山间的院落、围绕房舍的竹林、袅袅升腾的炊烟;举头仰望,湛蓝如洗的天空、悠然自得的白云,不时有飞鸟划过的留痕,即便是从天而降的潇潇雨水,或是霏霏细雨,都会给人以丝丝缕缕浪漫意绪的感受;村民在田里默默劳作时的场景,人们在来来往往中传递出的淳朴与友善,亲戚之间的不时走动与互访,流散于乡村的各种民俗风情。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贴春联、挂灯笼,小孩子给长辈拜年,一家人欢欢喜喜地迎接新年的到来。如此秀美的山水风光和丰赡的人文意向,都给诗人的心灵以深深的浸润,并沉积为一个个难以忘怀的故乡影像。正是因为这种双重意义的故乡影像,以及发生的诸多事件和细枝末节的深刻影响下,才逐步养成了诗人朴实的思想与敏觉的心灵、沉稳的性格与浪漫的气质。带着这样的思想、心灵、性格、气质和双重意义的故乡影像,诗人才渐渐地步入到与其心灵、思想、性格、气质深度暗合的诗意世界,致力于对散文诗艺术的美学建造。
细细品味诗人的这部散文诗集,它给笔者最为深刻的审美感知与印象,便在于诗人对于亲情的真诚倾诉和至情描写。在诗人的生命历程中,虽然曾遭遇了童年、少年时代贫穷与饥饿的折磨,但在他的感知意向里,却自始至终都被一种温暖的亲情紧紧包围着:父亲深深的关怀、母亲默默的怜爱、兄弟殷殷的抚慰……这些亲情一直储存在诗人的心灵深处,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光的更替,便慢慢地沉积为一种深刻的情感记忆或灵魂记忆。这样的记忆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不断发酵、恣意生长和无限地蔓延,最终演变为诗人笔下一行行富有思想蕴意和美学精神的散文诗。“我点起一支香烟,回味在你身边的日子。那些日子被阳光镀得金亮……”(《想念父亲》)。在这首散文诗里,阳光无疑是一个富有某种隐喻色彩的词汇,这种阳光穿越了诗人的内心和灵魂,成为一束束凌跨时空、凝结华能的光芒;它在照亮诗人的同时,也辉映出父亲壮年时的身影。这种深入到骨髓之中的生命感受和无尽思恋,使诗人一下子回到了久别的故土,并沉入到温馨而浪漫的情感回忆中。诗人仿佛看到了父亲膜拜犁铧像膜拜“一种遥远的图腾”的专注神情、“在褐色的土地上”艰难劳作的场景和充满无限希冀的目光;好像亲耳聆听到了母亲在拉风箱时奏响的“四季歌”,在家里“拉燃一片温馨”时谱的“伟大音乐”;似乎嗅到了从父亲皲裂的皮肤里流溢出的汗腺味、沾满双手的泥土气息和从烟囱里冒出的熟悉的气味。在《父亲生活的那片土地》里,诗人充分调动起全部的感觉器官,整体而非片面、复杂而非单一地感受父亲生活的那片土地,字里行间浸透着浓郁的情愫、深沉的眷顾、执著的思念。在这种思恋与眷顾之中,诗人的内心可谓是苦乐交织、喜忧参半,因为这时的诗人,业已“走出那片生长蔬菜和粮食的土地,走进城市”,而父母却被“孤独地留在那里”,只能一次次地弯曲着身体耕耘土地,“在重复劳作里体会手的价值”和艰难生存的生命况味。在这种从回忆到思念、从思念到感受、由感受而审视、由审视而颖悟等繁复心理的转换当中,不仅流露出诗人对于亲人的深沉眷顾和无限缅怀,而且揭示了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劳动是人类的第一生存手段和生命存在的必需。这种意义的揭示,较之于那些单纯或者是故作高深莫测的抒情之作,在思想内容上显得更为厚重沉实,在意义表达上更加深邃博广,诗人的情感也显得更为真实而深切,富于耐人寻味的深刻蕴意。
亲人和故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属于人的情感、内心和灵魂范畴,一个指向地理空间的存在意义。然而,在人的情感记忆里,亲人和故乡总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它们有如一个生命体的两面,显示出同质与同构的意义,或者说充满了哲学思想内蕴。所以,没有亲人的故乡,或是没有故乡的亲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无法成立的。诗人自然明白这样的道理及其蕴含其中的深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的引领下,慢慢地走进故乡的深邃时空。
在诗人的感觉意向里,《信里的风》是从遥远的故乡吹拂而来,它有如一股股溫煦的和风,不断地撩拨诗人之于故乡的深情回忆。“厚厚的家信如肥沃的土地,生长着我的故乡。啊!故乡,你那厚实温暖的土地上,曾经躁动着多少不安的希望!可是不到秋天,它们就和清晨那一树树晶亮的小太阳一样,被雪亮的犁铧埋葬在黄土地上……,于是,在山那边,老有一片片淡蓝色的记忆,在一本本翻开的书上飘来飘去;老有一支鹅黄色的笔,把沉重的心事栽进一个个雪白色的方格里……”就一个人的思乡方式而言,它无疑是多种多样又极为复杂的,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才最具有精神价值和艺术美感呢?这首先要取决于作家对故乡的精神探寻的深度,其次才是审美视角切入的独特性。由对一封普通家书的阅读而生发的感怀,使诗人一下子沉浸到故乡那种熟稔的画面里:厚实温暖的土地、清晨鲜红的太阳、埋葬的雪亮犁铧,便一一浮现在诗人面前,在情志的整合下又凝聚为整个故乡的影像。这不能不说是富有了独特的意义,因为此时的家书,已然不再是某种单纯意义上的语码建造形式,而成为了把此时与彼时、诗人与他者、往事与当下有意链接的精神纽带,背后暗藏的则是由情感与思念、回忆与探寻连缀的复合体。对信的阅读和由是生发的感怀,便无异于是诗人与故乡的再次情感链接,故乡才被诗人幻化为一座活性风景。当然,在诗人感知的深度中,复活的不仅仅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更有着人这个故乡的中心。于是,“乡村青年和夏夜的麦秸堆”“打开栅栏的女人”“收获时节的欢歌笑语”便次第呈现在我们面前:“从嘉陵江上浮来的夜岚就像恋人无处不在的情思,轻轻地依偎在他身旁。散乱的麦秸扎着他托颊的手臂。他在微微的疼痛里感到一丝甜蜜的忧伤”;“女人打开栅栏,栅栏扎在六月的阳光里……女人看到一种明净和深邃。女人在明净的心情里想起那些逝去的岁月,女人在那些岁月里清清净净地抿嘴微笑”;“诱人的麦香也一潮一潮地涌过来,抚弄着他们绵绵絮絮的话题。他们的话题已经远离收割、小麦和土地。他们用谛听过土地和庄稼的耳朵,静静地谛听来自他们内心的声音”。所以在诗人的情感深处,故乡就是一个由自然形态、情感形态和艺术形式凝结成的复合体。
意图考察一个人的情感记忆是否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笔者以为当属一个人在童年时代的情感记忆。因为在童年时代,不仅是一个人最富于自然本质的生活和充满天真无邪的心性,也是构成他或她情感记忆的主要内容和最为纯洁的部分。尽管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无法以理性分析来获得对事物的深刻认知和智性判断,但历经了情感记忆的东西会一直沉积在大脑里,只要有相似的情景、事件乃至细节的触动,它们便能够纷纷复活,成为一个人的永恒记忆。中外文学史上那些大家名流的成功之作,莫不含有深刻的童年记忆成分。
诗人自然谙熟其中的奥妙所在和神奇魅力,才会把对于亲人、故乡及其往事的回忆,用一种独特的声音来加以有力地复现。“远方总是让人神往的……在你的心目中,遠方永远是美好的。那里没有滴落在破旧衣衫上的眼泪,没有人在黑夜里两眼放光地算计别人。那里有的是恬静的微笑,友好的言行,纯真的少男少女像一片片欢乐的云,飘向他们渴望去的地方。在他们身后有袅袅的炊烟从屋顶上升起来,像一位痴情的少女,踮脚远望,呼唤着谁……你听见了来自远方的呼唤。”(《最初的声音》)这与其说是诗人在童年时代对“远方”的深情凝望,不如说是诗人在成熟之后对“远方”的独到理解,或者说是诗人对理想生活的一种美好憧憬。正因为如此,那个一直镌刻在“最初的声音”里的梦便跃然纸上,让读者得以充分领略诗人朦胧迷离的梦境和他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童年时代的梦,并非全然是完整而美好的,由于内心的稚嫩、感受的不足、认知的局限、想象的欠缺,这样的梦大多显得如零散的碎片一般,所以在诗人的感觉里,“梦是一种夜里生长的植物。这种脆弱的植物,始终抵不住白天的冲击,天亮的时候就会像泡沫似的消失……并不是所有的梦都是圆满的。不圆满的梦往往会被我们的尖叫刺破。这时惊出的汗会比白天更多”。在这种情势下,“撕梦”便成为诗人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把梦撕开,人才能在明朗的现实里感到生命的安全、真实的依傍,才能在真切、深透的生活里“重新组合一些渴望和想念”,让“一缕阳光,几片绿叶,在山上流露出另一种生命的韵味”。自然而然,在童年的梦境里,也有《背后那双眼睛》在冷冷地注视着自己:“你的心像猎人视野里的小鹿,在茫茫草原上慌张地择着路。有时经过了十字路口,你也不敢回头让他看见额上的汗流成了小溪……。”诗人内心的惊悸,不仅通过恰当的比喻得到形象化的体现,而且昭示出他对世界的恐惧性体验和认知。诗人正是通过童年时代的情感记忆和对梦境的重构性描绘,将其对于亲人、故乡的记忆锁定于自我认同的艺术格式中,又借助这样的艺术格式使自己得以回归到由想象与艺术双向构造的故园里。诗人对于亲人的深沉情感、对于故乡的深层眷顾,从中可见一斑。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在他或她历经了繁复与沉重的现实生活后,或者说是在历经了诸多的生活挫折与人生磨砺后,依然能够挺立自己的身躯和灵魂,以客观冷静的思想正待人生,面对这个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世界,时时事事对社会与时代、民族与世界进行深刻的反思。作为一位知名的诗人,自然不能例外。从这个角度看,这部散文诗集都是诗人在人生成熟之后的创作,因而,无论是诗人对于亲情的情感倾诉,还是对于故乡的至情描绘,抑或是对于爱的真情表白,就不仅仅是滞留于某些表象上,而是以对现实社会和生存景况的智性穿越,以不断提升的认知能力和持续净化的人生境界作为前提,予以深度意义的精神考察。正是因为如此,诗人的散文诗创作便更多地融入了对历史、哲理的深层思考和追问。
作为大自然里的一种普通植物,艾草在寻常的社会生活中并不为人们重视,但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它却异乎寻常地“香了起来”,不仅被请进林林总总装饰华美的室内,而且还“登上了众人仰望的位置”,一时之间,成为我们民族生活中的一个辉煌焦点。《端午节》中的艾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有关,更与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关。诗人用艾草这种植物来隐喻象征人和历史,将这三者紧密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探寻、追问,不仅揭示了它们之间相互变化的戏剧色彩,而且说明了崇高与平凡的相对性和可变性,这就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历史所具有的两面性。在漫长的中国哲学史上,对于五行中的火的种种诠释和阐发,我们已经不陌生,诗人在《火》这篇散文诗里,通过对火的历史审视来概括人类的历史,揭示火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双重意义,从而显示出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审美价值。“点燃一堆火,这样,火就能从一个抽象的词语里脱离出来,我也就能披着一件衣服,在火的光芒里翻阅火的历史。我会看到最初的火光,怎样从猿人的额上传递到山顶洞里。那些暗夜一般的烟雾,像黑压压的蝗虫,越过秦皇汉武的烽火台,向历代蔓延。所到之处,残垣断壁。最初的黑暗,在蜷缩一角的百姓脸上曳动……这些曾经灼伤过多少代人的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却温暖着我。它们欢快的呼啸,就像我们童年的笑靥:圣洁、明净。”诗人由火的历史推及人的历史,认为那些凡是“肆意拨弄”火的人,最终都成为一堆“焦骨”,而对那些善于用火的人而言,既能从中得到深刻的警示意义,又会在它的燃烧中“感到温暖”,由此揭示了遵循或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人,必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碑无疑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常见之物,只因不同的人用各自的方式塑造不同的碑,无论是死去的历史学家、领袖人物、英雄豪杰,还是正活着的芸芸众生,都在塑造自己的碑。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讲,死者或是生者的心中都有一座各自灵魂认同的碑。“死者可以在碑里自由出入,同活人握手或交谈,可以报复,但不用凶器。活人看见他们的影子。活人不再害怕看到他们的影子。生者也可以出入碑,同一些死者叙旧、言和,或者继续一笔没有了结的生意。我们同死者一起走进过去或者未来,我们的影子同死者并肩前进。”从中不难看出,在诗人理性认知的界面里,碑实际上成为对一个人的人性思想和人格魅力的深刻揭示与有力彰显。
著名文学评论家丁帆在《面对乡土 如何选择——从作家对乡土文学的观念视角谈起》一文里指出:“毋容置疑,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意识的认同,以及个体无意识的文化身份认同,乡土文学对于深深扎根在个体心理暗陬中的农耕文明情结形成了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世界文学尚如此,中国文学也不能例外……中国乡土文学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被镶嵌在‘中国风景的巨大画框之中,既可以是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悲剧描写,也可以是浪漫主义田园牧歌的风景诗描写。”如此而论,诗人在这部散文诗集里所表现出来的,无疑更偏重于浪漫主义田园牧歌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掺杂了些许现实主义的美学元素,并明确地传递出三个方面的思想蕴意:一是对于亲情的真实诉说,二是对于故乡的真情描述,三是对于心中之爱的真诚告白。如果从整一性的角度出发进行审视,我们便不难发现,这三个思想蕴意又合而为一,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的核心便是乡土世界。这样一个乡土世界,既是诗人独自拥有的,又是富于人类学意义的。因而,无论是诗人对于亲情的真实诉说,还是对于故乡的真情描述,抑或是对于爱的真诚告白,皆无不是围绕这个核心来予以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在这部散文诗集里意欲表达的思想主旨,就是一个兼具了完形意义与审美价值的乡土世界。这是一个缀合了亲情与爱情内力,融入了质朴与醇厚品格,熔铸了现实与理想含蕴,有形又无形的乡土世界。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浓郁的抒情色彩、丰繁的审美想象、意象的精心打造等,皆无不是这部散文诗集显在的艺术特征,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都不过是一些艺术表象而已,真正的重点或核心在于:诗人并非像某些流行于文坛的诗人那样——不是沉浸于文字游戏的玩弄,就是追随矫情造作的诗歌风气,或者是刻意地追求西方现代艺术的怪异迷离——反倒以情感与心灵为基座、以真诚与樸实为本质、以丰富的审美想象为抓手、以虚拟与写实手法为突破,自始至终融合了诗意表达的民族精神。因而,诗人的散文诗创作,既富于独特的个性气质,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以浪漫主义为主、现实主义为辅的艺术产物。
具体而言,它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艺术特征:首先,诗人的散文诗富有浓重的情感色调和别样的抒情韵味。对于任何一个在散文诗创作领域里有着丰富成功经验的诗人都明白,散文诗的情感色调是从作品中漫溢出的情感氛围和思想格调,欲意强调作品的情调之美,就必须赋予作者以高迈的人生修养和人格魅力、优秀的道德情操和精神旨趣、卓越的艺术直觉和领悟能力,并通过对美的深刻体验、感知和发现,创造出具有很强的艺术力量和美感效应的作品。散文诗的抒情韵味是指作品的语言既要有情感真切、意态生动的特质,又富于含蓄蕴藉、意境深远、意味悠长的韵致,在写景状物时力求神似,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留有充分的想象空间,使读者通过艺术联想产生新的意境和情趣。诗人在进行其散文诗创作时,便特别注重对情调和韵味的营造,自觉地把自身体验到的东西用内在情感来浸润,以精神探寻来穿越,使它们完全成为一种情感的存在体,在这个基点上,再以纯净的思想和审美的个性进行有意识的拆解和重组。因而诗人笔下的情景、人物、事件及细节,便一一整合为富于别样韵味的巧妙艺术。其次,诗人的散文诗具有明晰的动态感和音乐感。为了使意象或形象显得更加鲜明生动,诗人常常采用速写的方法,将某一时刻产生的情感起伏、内心变化,赋予内在的精神和律动的灵魂,以强烈的生命感知和人格力量增强其灵性,凭借自由舒展的想象和巧妙的语词搭配,在时空之间、主客体之间运用关联动作,或平行跳跃,或穿插组接,使散文诗富有了奇特的美感效应。再次,诗人的散文诗充满着纷繁多质的意象美。诗人在散文诗创作中十分重视对意象的发现与创造,无论是对已逝往事的回忆,还是对现实情景的写照,他都注重对具象进行艺术化的改造,使它们充满迷离奇幻的意象感,又通过意象切割的手法传递自己丰富的内在情感。诗人不时地运用意象切割的手法,用以分解意象之间造成的某些断裂,使其对情感的表达葆有自由跳跃、快速流变、无常转换的效果。或是以意象碎片的黏合与分扬,变换出令人难以捉摸的空间,折射出作者无法言明的心理状态;或是将中心意象剪辑成无数毫无规则的意象碎片,任其随意飘忽、自如腾挪,创造出有如梦境一般的陌生离奇;或者是采用意象叠加的手法,把一个思想置放于另一个思想之上,造成意象间互为幻化的审美效果,用以反映各种不同生态冲突下人的复杂情愫和丰繁心理。这种繁复多质的意象创造,既使诗人的散文诗艺术到达了某种高度,也能更为有力地显现出作品所具有的审美内蕴。
在一个人的生命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着对于亲人、故土、呵护、关爱的温暖记忆,这些有如驻在我们灵魂居室里的珍品,与我们的人生始终相随,用怎样的艺术方式来进行表达,才能显现出令读者欣悦的美学境界?这是值得我们每位作家反复思量和努力求索的。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对这个作家是否具有真善美意识和人文情怀的表明,也是对其思想深刻程度的一种确证。王德宝在散文诗的创作中,便表现出同亲人、故土始终相随的深度之魂,因为他不仅用艺术方式成功重塑了心灵的故土、亲情的雕像,而且富有美学探寻的精神特质。
【作者简介】
冯源,本名冯学全,曾就读于绵阳师专、四川师范大学,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绵阳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影视艺术研究。发表文章7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