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明月共潮生:弗鲁梅利《四首中国诗歌》
黄静雯
《四首中国诗歌》(Fyra kinesiska poem)是瑞典作曲家古纳尔·德·弗鲁梅利(Gunnar de Frumerie)为钢琴和声乐而作的一部作品,共包含四首小曲,其中第一首与第二首创作于1929年,后两首创作于四年后,即1933年。

弗鲁梅利1 9 0 8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附近的纳卡(Nacka)。他自幼便展现出了钢琴家的天赋,最初跟随母亲学习钢琴,十二岁起跟随伦纳德·伦德伯格(Lennart Lundberg)学习钢琴,后获珍妮·林德(Jenny Lind)奖学金,随即在维也纳和巴黎继续深造,成为钢琴家埃米尔·冯·绍尔(Emil von Sauer)和阿尔弗雷德·科托(Alfred Cortot)的学生。1925年,弗鲁梅利开始了自己的创作。1928年,他在一次作曲家比赛中一举夺得三个一等奖。
从大型歌剧到钢琴小品,弗鲁梅利探索过各种形式、体裁的创作,其中,他的钢琴作品约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创作的歌曲也尤为受人推崇。尽管关于弗鲁梅利的现存资料可知,他的作品除了在瑞典和欧洲部分地区外辐射范围并不算广,在国内和国际上可能也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未曾占得一席之地,但在歌曲领域,他在瑞典仍小有名气,如今也被认为是瑞典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英国作曲家、钢琴家弗兰克·梅里克(Frank Merrick)曾表示,即使弗鲁梅利为钢琴和管弦乐所作的变奏曲和赋格1942年才在伦敦出版,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弗鲁梅利及其作品的钦佩之情。

弗鲁梅利的《四首中国诗歌》取材于四首中国的古诗词,并以四首诗词的德语译文为唱词。四首诗词的译文皆来自德国诗人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的《中国之笛》(Die chinesische Fl?te)。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大量古代诗歌与文化典籍开始输出至德语文化国家,德语文化世界大约也从这时开始涌现出一种“中国热”(Sinomania)。这场“中国热”自十九世纪末持续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德国近半个世纪之久。大约自1890年起出现的“中国诗歌热”(主要是“唐诗热”)是德国这场“中国文化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中国诗歌被译成德文,对德国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正是那时,德国在科学、社会和文化层面上正经历着全面迈向“现代”的转型,文艺界表现出了一种对新型现代艺术、现代诗歌的热烈呼唤。自此,德语文化中逐渐出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思考,各个领域慢慢开始建构作为“他者”文化代表的中国形象。二十世纪初,改写中国诗歌的潮流逐渐达到巅峰,中国诗歌在德国、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907年,汉斯·贝特格出版了《中国之笛》,其中收录了贝特格译介的若干首中国唐代诗歌。对于他第一次读到法语译版中国诗歌的震撼,贝特格曾写道:“第一次读到中国抒情诗的时候,我就完全被迷住了。我遇到了一种多么可爱、优雅的诗歌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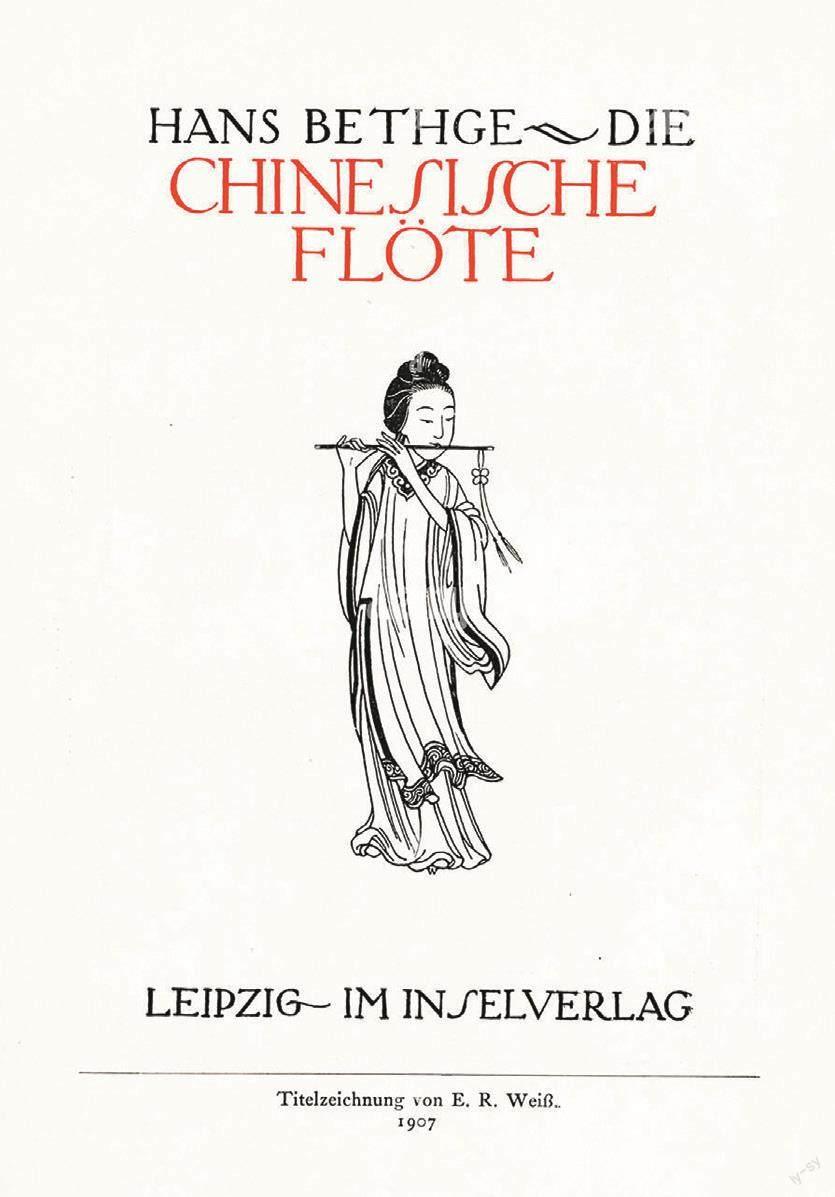

即使贝特格的译文属于转译而非直译,即使贝特格对中国诗词的改写建立在法国汉学家德理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所译的《唐诗》(Poésies de lèpoque des Thang)等当时已有译本的基础上,但《中国之笛》仍被认为标志着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古诗在欧洲传播的高潮。而且多位音乐家都曾采用其中的译文文本创作,如马勒《大地之歌》六个乐章都采用了《中国之笛》中的译诗,潘德列茨基《第六交响曲》也选用了其中的八首诗歌。不管是文学界还是音乐界,都听到了中国传去的笛声,勾起了缱绻情丝。
弗鲁梅利《四首中国歌曲》中的第一首《河上》(Auf dem Flusse)的歌词为贝特格所译的杜甫诗词,原诗无从考证。仅从译后文本窥见,贝特格的译法更注重对自然意象的突出,改写相对自由,或许在语言和风格上都做出了较大的改变。在译介的二次创作下,尽管有着“碧波向天光,我心向佳人”的歌词,但却难以从中体会到杜甫“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与“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也难以看出其沉郁顿挫的写作风格。不过,经由弗鲁梅利的第三次创作,此诗放于《四首中国诗歌》的开头,其与杜甫不甚相符的轻快也可起到抛砖引玉之用。整部作品中,人声旋律线条柔和,音乐进行中级进为主,辅以简单钢琴伴奏,多使用单音或音程,音乐语言简洁凝练,情绪循序渐进,不至于聽罢开头就已然心有愁绪,以致沉疴,而是在弗鲁梅利的清澈之声中,发散出“我心向佳人,佳人在何处”之思。
第二首作品《寂寞》(Die Einsame)取材自南北朝诗人王僧孺的《秋闺怨》。贝特格着重突出了诗中“遥泪非一垂”与“徒劳妾辛苦,终言君不知”的韵味,而弗鲁梅利借由此唱词达到了其音乐作品中情绪的逐次递进,音乐从舒缓含蓄逐渐转至哀伤婉转。全曲无节奏变化,钢琴伴奏音域较低,下方声部的持续音也几乎贯穿全曲,为本就起伏不明显的旋律再添上一抹忧愁底色,但又不至于靡靡,因为诗与乐皆保有“昭质不亏,夷然大雅”的特点。
第三首《流放者》(Der Verbannte)写于四年后,为四首中篇幅最长的一首,原诗为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二》。这首诗也是四首中原文与译文意象对应最为全面的一首,“落日”“北斗”等都能找到相差无几的描述。同时,在这一首中,能最为明显地看出弗鲁梅利对中文行腔韵字的模仿感,几乎每一个德语音节都配有对应的音符,一音一字,相互映照。调性上也存在一些对于中国传统五声音阶的运用,为音乐涂抹上东方色彩。正如歌词分段,弗鲁梅利在创作时也有明显的划分性。首先,在“Lento. Misterioso e lugubre”的指示下,音乐开始渲染神秘、萧瑟又夹杂些许阴郁的秋之氛围;此后通过节拍变换、调性变化等手段,观照词意和词情,对音乐进行段落划分;最后由实景转向虚景,由写景换至写情,淋漓尽致地完成虚实对比、循环往复的叙事构建,塑造出时空和心境的转变。

最后一首《河边傍晚》(Abend auf dem Fluss)取材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贝特格的译本是对《春江花月夜》的缩减再译,不管是对原诗的意象还是对内容都有所省略。贝特格似是只注重对原诗“意义”的提取,但弗鲁梅利在“以诗入乐”的过程中,又很巧妙地融进了“意韵”。最开始人声进入前,整个《四首中国诗歌》中首次出现切分音,再加上左手持续伴奏音型,从听觉上让人联想到江水滚涌,未见其“春江”,先闻其“潮水”。尽管译文歌词中并无此句,但全然暗合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之景。人声起,波涛再缓落,但附点音型仍隐含在伴奏中一直持续至曲终。唱到“静谧”(Ruh)时,长持续音和渐弱的力度变化又给作品附着上了“愿逐月华流照君”的韵味。全曲最后结束于高音上,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歌词虽仅为感叹月亮,但“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的叹息也随之而来。
弗鲁梅利在创作中吸收了各种不同的影响。他曾说,欣德米特对他影响深远,勃拉姆斯和德彪西也对他的创作发展意义重大。而《四首中国诗歌》则是他在“中国热”期间与中华文化、中国古代诗歌接触的结果。

弗鲁梅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以对形式严谨性的追求为特点,《四首中国诗歌》中的严谨性也可见一斑。从作品中可看出其对于各元素间严丝合缝的契合度的要求,音型与意象是相对应的,如切分音、附点音型与滔滔江水的意象契合,速度变化与诗中相应心情也有所符合等。在平仄韵味上,弗鲁梅利的音乐也可圈可点。一方面,所选贝特格的译文充分符合德语诗歌的美学特征,且符合德语诗歌韵脚要求,某种程度上也与中国诗歌的押韵有所相似。另一方面,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以乐从诗”的过程中,弗鲁梅利始终试图贯彻音符与德语音节的对应,模仿中国诗词抑扬顿挫之韵。
此外,弗鲁梅利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声乐作品,具有清澈、纯净和稀疏的特点,且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旋律优美、和声新颖,音调想象力丰富,又保持着相对自由的状态。《四首中国诗歌》如同弗鲁梅利笔下的一幅水墨画,寥寥几笔便能勾勒出氛围与意境,无不体现着弗鲁梅利对于音乐创作的字斟句酌以及刻画入微的意象描摹,同时又有中国水墨画的留白之意,伴奏或人声偶有空白,却余韵悠长。《四首中国诗歌》虽为弗鲁梅利的早期作品,成熟度或有欠缺,但其仍以敏锐的直觉诠释了文本,为当时瑞典乃至欧洲的音乐爱好者带去了一轮中国的圆月。以诗入乐,以月和乐,月乐与共,同话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