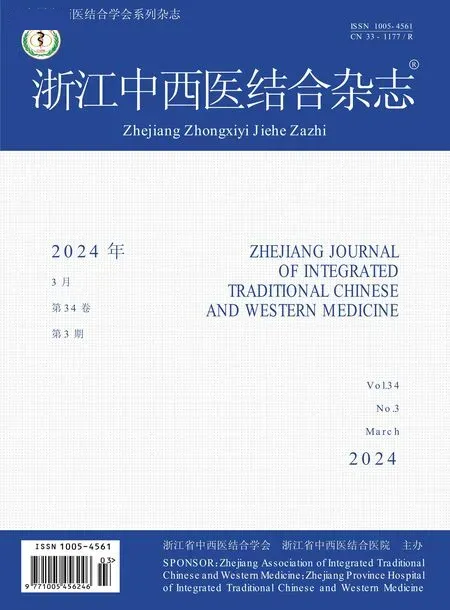中西医外治非哺乳期乳腺炎研究进展
吴金媛 刘玲琳
非哺乳期乳腺炎(non-puerperal mastitis,NPM)是一种发生在女性非哺乳期的乳房良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近年发病率呈增长趋势,具体病因尚不明确,可分为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granulomatous lobular mastitis,GLM) 及浆细胞性乳腺炎(plasma cell mastitis,PCM)[1]。NPM 病情复杂,疗程长,目前尚无规范化的诊疗方案。常用的内治方法包括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抗生素治疗和中医中药等[2-4],但口服大量激素和抗生素副作用相对明显,且病程长、易复发、临床变证多。外治法具有治疗作用直达乳房病所、且不需要经过肝脏的首过效应和肝肾代谢的优势,对机体整体影响较小。现将NPM 中西医外治进展作一综述。
1 西医外治法
西医外治法是在现代外科学指导下所进行的、与通过药物治疾病的内科相对的一种治疗模式,既包括了经典的手术,也包含各种运用现代技术直接作用于体表器官的治疗方法,目前临床中常见治疗NPM 的方法大体有以下几种。
1.1 外科手术法 外科手术是目前治疗NPM 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常见方式有单纯肿物切除术、扩大切除术、微创手术、精准手术、扩大切除+整形术、单纯乳房切除+假体再造等。单纯切除及微创手术多只切除病变部位的肿物及周围少许正常组织,但随访发现其复发率可高达50%。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广泛局部切除应是手术治疗NPM 的基础[5]。有学者提出扩大切除的方式,病灶切缘≥1 cm 以上,或进行病灶“四步探查”,即病灶中心区域、乳头后方软组织及主导管、周围腺体内孤立病灶、周围脂肪组织等扩大清扫,以减少顽固性NPM 复发风险[6-7]。随着手术精准化的兴起,任辉等[8]将亚甲蓝定位结合彩超引导的术式运用于NPM,在彩超引导下,用0.25%亚甲蓝注射液在距离病灶边界外1 cm 定位于腺体表面,进行病灶的精准切除,避免盲目扩大切除造成对正常腺体的副损伤,维护乳房外形美观。程旭峰等[9]则采用“雕刻式切除术”,术前通过MRI、彩超定位病变范围并做体表窦道标记,沿乳晕取弧形切口,放射状逐步切开病变窦道及分离腺体,选择性切除病灶组织及扩张病变导管。但该手术方式尚处研究阶段,对于病变范围较大,表面皮损较多的患者并不适用,另外手术过程复杂,术前定位不够精准,术中出血、耗时等问题并无明确报道。针对巨大肿块、多发破溃瘘管的重症患者,乳房整形及重建技术也逐渐应用,因涉及皮瓣选择、游离、整形美学及重建技术等各领域专业知识,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1.2 引流法 引流法常用于NPM 脓肿期,传统的操作是穿刺抽脓或小创口切开引流排脓,但该法属于盲穿,对浅部脓肿效果更好,深部病灶难以定位准确。随着超声医学的发展,在B 超引导下可对深部脓肿进行精准定位并给予穿刺抽吸,可防止深部酿脓或向外破溃形成难治性窦道。但单一的抽吸法由于针口细小,术后难以放置引流纱条,可能存在反复积脓的现象。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将超声引导下穿刺灌洗/置管冲洗、持续负压引流术(VSD)引入NPM的治疗中——在超声引导下对乳房脓肿穿刺后,以生理盐水、抗生素等药物反复灌洗直至脓液变清,能进一步有效清除残余脓血,降低局部伤口张力,同时术后持续清洗能够控制细菌感染,减轻炎症反应,有利于脓腔闭合和炎性肿块吸收。相关研究表明,穿刺灌洗、负压引流等技术在缓解疼痛、减少换药频次、促进创面愈合和维护患者乳房外形等方面均有较大优势[10]。
1.3 乳管镜治疗 纤维乳腺导管镜最早是为直视观察乳腺导管内病变、解决乳头溢液的诊疗难题而诞生,实现了乳管内微小病变的精准定位和诊断,而后逐渐运用到NPM 的治疗中。PCM 是NPM 的一大分类,多表现为乳头部瘘管、乳晕区肿块或脓肿、乳头凹陷、溢液等,通常认为是由输乳管窦扩张伴分泌物积聚引起导管内膜溃疡、渗漏,引起炎症反应,从而形成乳晕周围脓肿,病变主要累及乳头后方大导管。乳腺导管灌注疗法是通过乳管镜疏通清除导管内分泌物,并将药物灌注于病灶处,反复冲洗使药物扩散吸收,促进脓腔愈合,常用的药物包括抗生素、激素、中药水煎药液等。王灿、彭金娟、冯得财等[11-13]分别报道用乳管镜冲洗联合中药、地塞米松、甲硝唑等灌注治疗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在抑制催乳素分泌,降低患者IgG、IgA 水平,改善患者免疫功能,缓解乳房疼痛、缩小肿块、保护乳房外形等方面均有更好的效果。
1.4 局部激素治疗 GLM 是NPM 的另一大类,目前认为其与自身免疫相关,故类固醇激素是主要治疗方法。相较于口服糖皮质激素带来的副作用如库兴综合征、骨质疏松、糖尿病等,局部注射或外涂可使激素直接吸收,减少全身反应。方红燕等[14]研究证明,在炎症肿块周围注射曲安奈德可使炎症范围局限,促进无菌性脓肿吸收,快速消散病灶区水肿,促进瘘道收缩愈合,从而使病灶缩小。Cetin 等[15]也报道用曲安奈德局部病灶内注射联合0.1%曲安奈德乳膏外涂病损乳房对比口服甲基强的松龙32 mg/d,其临床有效率高于口服治疗组,且全身副反应发生率、复发率更低。另外一项前瞻性随机研究对比了局部外用类固醇激素软膏组、口服类固醇激素组、外用及口服激素联合治疗组,三组之间的治疗有效率无明显差异,外用组治疗时间较长,但患者依从性高于另外两组,且全身副作用较少[16]。因此,局部类固醇外治逐渐成为GLM 的重要治疗方法之一。
2 中医外治法
中医外治法历史悠久,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提到:“外治可与内治并行,而能补内治之不及”,在一定程度上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针对NPM 的治疗,临床多以疾病分期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包括箍围法、溻渍法、切开引流法、药捻或纱条引流法、拖线挂线法、切开扩创法、垫棉绑缚法、热熨法等。
2.1 肿块期 在肿块形成早期,患者多表现为乳房局部团块红肿疼痛,皮温升高,伴或不伴发热恶寒或下肢结节红斑。此期多数医家强调当“以消为贵”,以箍围、溻渍为法。箍围法即借助箍围药的截毒、束毒、拔毒作用而起到清热消肿、散瘀定痛等作用的一种敷贴方法,可根据病情选药研为细末,并酌取醋、酒或油类等调敷于患处四周。“溻渍”是指将浸泡于药液的纱布或棉絮敷于患处。临床常用金黄膏、三黄膏等油膏或冲和散、金黄散等调成糊状或是中药水煎剂等贴敷于乳房肿块以达治疗目的。
2.2 脓肿期 NPM 病久蕴热,血败肉腐成脓,脓成当以排尽为要。古籍有载,脓成当“以刀开之”“针之”,使邪有出路,热毒得清,防止袋脓,这与现代切开排脓的做法不谋而合。一般皮下浅部脓肿多以简单穿刺或小切口为主,达到排脓目的即可。对于深部脓肿,除用超声定位穿刺外,部分学者主张在排脓之后要尽量用球头银丝探查脓腔深度、数量和范围,用刮勺刮尽脓腐瘀血;对于脓腔清理后的护理包扎,可用棉垫或纱布折叠成块,衬垫于皮肤表面,再予以绷带加压绑缚;或用蚊式钳在创口处清除坏死皮缘,使创面红活,再用燕尾纱块绑缚,蝶形胶布牵拉收口,加压包扎固定,确保创面生长愈合,不留死腔。
2.3 瘘管期 复杂肉芽肿性乳腺炎多见多发脓腔、破溃、瘘管形成,《外科证治全书》记载:“再治其漏,法用附子饼、豆豉饼……如未知内之深浅,可先以猪鬃探之,然后用绵纸卷药为拈,量其大小深浅塞入,日易日塞,至愈乃止”,强调以灸法或药捻为主。这类复杂创面采用单一的手法难以完全收束,容易形成假性愈合而反复溃脓,因此多在局部排脓后在脓腔中置入提脓药捻,捻去脓腐方可生肌收口;也可借用球头银丝深入探查瘘管基底部明确病灶延伸范围,以粗丝线或纱条贯穿于窦瘘中,将祛腐生肌药物掺于丝线上,形成挂线/拖线法,通过每日来回拖拉,将药物置入管腔内,使其充分接触未切开的内腔疮面,发挥引流脓腐及腐蚀收敛窦道的作用,同时保留未受累皮肤及乳房内组织,将乳房外形损毁程度尽量降低[17]。
针对重症NPM 患者多发脓腔、破溃、瘘管的肿块,中医也强调不拘一法,综合运用外敷、穿刺、热熨等各种手法,辨证施治,防止变证、坏证。
2.4 僵块期 多数学者认为NPM 后期肿痛缓解,脓液排尽,肉芽瘘口收敛闭合,部分患者遗留肿块“欲消不消,欲脓不脓”,形成僵块,当属“阴证、半阴半阳证”。传统治疗手法多采用艾灸或药物热熨法,随着技术发展,红外线、中药定向透药仪、热敏灸等也逐渐用于临床。所谓“阳化气,阴成形”,通过艾灸或者以具有温阳通络散结作用的冲和膏、桂麝膏外敷,疏通局部气血,化痰散结可帮助肿块吸收。王筱璇、陈梅兰等[18-19]也报道用四子散、外敷1 号方借助红外线等热力刺激使中药成分活化,渗透肌表达到疏通经络、温中散寒、调气活血、散结消肿等功效,帮助乳房僵块消散吸收,缩短口服药物疗程。
2.5 其他外治法
2.5.1 普通针刺治疗 针刺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适应证广、疗效明显、操作方便等优点,《灵枢·九针十二原》记载“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气血……”。除整体辨证取穴外,多在病灶处施以围刺或点刺。周甜甜等[20]报道一例毫针围刺治疗NPM 病例,以整体取穴加左乳病灶处以6 针的多针围刺法,局部加盒灸,经过20 次/40 d 的治疗后,患者左乳肿块未再复发,未触及左腋下肿大淋巴结。研究表明,围刺法能增加针刺刺激量,减轻患者病灶疼痛感,同时清泻局部邪热,防邪外扩。浮针是由针刺改良而成,通过在病灶皮下层进行散扫较大范围刺激皮下结缔组织和浅筋膜,通过改变疏松结缔组织的空间构型释放出生物电,改变细胞的离子通道,调动人体的内在抗病机制,从而迅速缓解病痛[21]。黎芳等[22]报道用浮针联合甘露消毒丹口服治疗NPM,对比单纯口服中药组,浮针配合口服中药组能明显降低患者炎症反应,改善患者免疫功能,降低复发率。
2.5.2 艾灸及火针治疗 一般而言实证、热证禁灸、禁火,研究发现艾灸治疗外科疾病能调控炎症反应的中枢和外周作用机制,通过调节炎症因子和信号通路,缩短创伤愈合的炎性阶段,加速进入增殖修复期[23-24]。而火针以热焦灼皮肤,大开孔穴,帮助痈脓顺畅排出,以泄热毒,病理研究表明火针可消除或改善局部组织水肿、充血、渗出、粘连等病理变化,加快局部循环,促进代谢,具有消坚散肿、促进慢性炎症吸收作用,同时可激发机体对病变或坏死组织的吸收,使受损组织重新恢复[25]。刘胜教授[26]总结前人经验,归纳火针治疗当以分期选用不同针具和刺法,如脓肿期以“品”字多出穿刺、溃疡期以细针浅刺、疤痕期用细针围刺等,扩大了火针在NPM 的应用。林毅教授[27]则改良传统火针,以电加热直径为0.3~0.5 cm 的粗火针行“洞式烙口引流术”治疗NPM 巨大脓肿,针刺后在外口及内壁产生焦痂附着,形成内壁光滑的管状通道,满足充分引流脓液的需求,出血少,痕迹小,疗程短,疼痛轻,更能被患者接受。目前该法受专业设备限制,为推广带来一定难度,但不可否认,火针治疗因其独特的疗效逐渐显示出潜在的优势。
2.5.3 刺络拔罐 刺络拔罐是指在经络穴位或病灶处先予三棱针点刺放血后再施以火罐的治疗方法,可达到疏利经脉、行气活血、祛瘀生新的作用。郑明慧、丘平等[28-29]均报道将拔罐运用于NPM 的相关案例,能改变小毛细血管通透性,改善局部微循环,达到消散肿块,提高治愈率,降低复发率的效果。
3 讨论与展望
NPM 病因与乳汁淤积、高泌乳素血症、自身免疫、感染等相关,治疗以糖皮质激素、抗生素、免疫抑制剂等为主,但这些药物副作用明显,因此外治法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单纯穿刺抽脓可以缓解脓肿病情,但大部分不能完全根除病灶,复发率较高。外科手术是根治NPM 的首选方法,目前争议主要在术后复发率及乳房美观上,因此应根据患者疾病的阶段、病灶范围及乳房大小谨慎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长期糖皮质激素外用可能会引起乳房皮肤萎缩、水肿、毛囊炎等副作用[30],且目前激素的选择、剂量、注射深度及位置等均未形成共识,仍需进一步探讨实践。中医外治相对简捷灵活,根据疾病分期选择不同的治疗手段,疗效明显,病程缩短,对乳房外形损毁较小,具有积极临床意义。但目前相关研究均存在样本量较少、对照设计不够严谨、随访不到位、有效性缺乏循证依据支持等问题,难以有效推广。后续需进一步完善研究设计,以更好评价中医外治法治疗NPM 的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