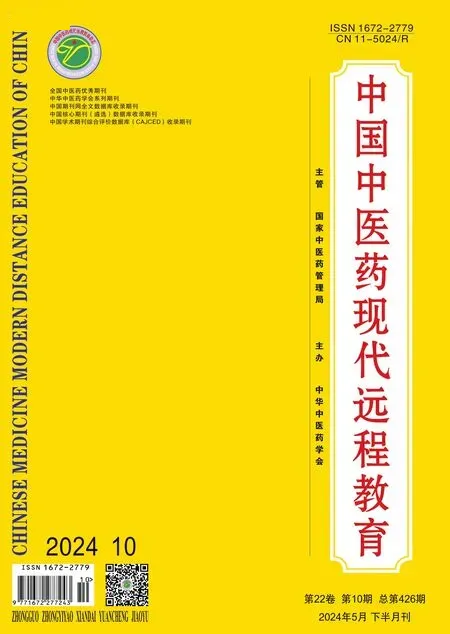赵树华教授在慢性肾衰诊治中治未病思想的应用 *
王贤雅 赵树华 李 丹
(1.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肾病科,吉林 长春 130117;2.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中医科,吉林 长春 130000)
慢性肾衰是众多慢性肾脏疾病的共同结局,往往表现为肾功能不可逆的进行性减退[1]。慢性肾衰属于中医学“溺毒”“关格”“水肿”“癃闭”“肾毒”等范畴。溺毒首见于清代何廉臣所著的《重订广温热论》,书中谓:“溺毒……头痛而晕,视力朦胧,耳鸣耳聋,恶心呕吐,呼气带有溺臭,间或猝发癫痫状……舌苔起腐,间有黑点”。《类证治裁·闭癃遗溺论治》曰:“闭者,小便不通。癃者,小便不利”,凡小便排出甚少或完全无尿排出者,统称癃闭[2]。慢性肾衰的病位在肾,涉及脾、肝、心、肺,病理产物为湿、痰、瘀,基本病机为脾肾阳虚、湿毒内停。慢性肾衰的病性属本虚标实,本为脾肾阳虚,导致水液代谢失权,水液代谢障碍而生湿;脾失健运聚湿成痰,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痰湿蕴结,湿浊纠结,最终湿毒内停。慢性肾衰的早期逆转、中期遏止、晚期防变是其诊治难点。而2000 年前,《素问·四气调神论》中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已经提出“治未病”思想,为后世的疾病诊治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赵树华教授系吉林省名中医、吉林大学二级教授、一级主任医师、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导师,尤其擅长慢性肾衰的治疗,重点将治未病思想贯穿于慢性肾衰的全程治疗中。本文将赵树华教授防治慢性肾衰患者病情进展的治未病思想总结如下。
1 重视感受外邪防传变
1.1 重视外感在慢性肾衰全程的危害临床中,慢性肾衰患者经常容易感受外邪,出现发热、恶寒、流涕、头痛、身重,继而引发咳嗽、咳痰,并随着病情进展出现目胞、跗胫水肿,最终可以导致肾衰加重。因此外感是慢性肾衰患者病情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3]。
赵树华教授认为,慢性肾衰患者素体脾肾阳虚,阳虚则卫外不固,容易感受风、寒、湿等外邪,伤于肌肤腠理,而见发热、恶寒、身重、头痛。外邪从鼻入肺,初见流涕,继而肺气郁闭出现咳嗽;素体脾虚运化无力,“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4],表现为咳吐痰涎。随着病情进展,肺气受损,不能通调水道,水液犯溢肌肤,出现目胞、跗胫水肿。最终正气虚损更加严重,脾肾阳虚更甚,出现恶心、呕吐、乏力、尿少,甚则出现喘促、不能平卧等症状。
1.2 防治慢性肾衰患者外感三法结合治未病思想,赵树华教授提出了慢性肾衰预防外感三法:平素扶助正气、感邪内外兼顾、邪盛预防传变。
1.2.1 平素扶助正气赵树华教授认为,慢性肾衰患者容易感受外邪的根源为脾肾阳虚,加之久病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失常。因此其治疗全程需要固护正气、补肾健脾。赵树华教授常用黄芪、党参、山药、白术、茯苓健脾益气,杜仲、菟丝子、补骨脂、沙苑子补益肾阳,同时间断应用玉屏风散健脾益气、补肺固卫。
1.2.2 感邪内外兼顾赵树华教授认为,慢性肾衰患者一旦感染外邪,即存在邪正交争,属本虚标实。首先应当做到标本同治、内外兼顾,其次要分清邪重为主还是正虚为主,最后要辨明寒热及病位。对于风热感冒,常以银翘散、桑菊饮化裁;风寒感冒常用小柴胡汤、桂枝汤加减。同时注意到慢性肾衰患者容易兼夹湿邪,酌情予藿香、砂仁、厚朴、白扁豆、滑石等化湿行气、利水渗湿。对于正虚与外邪并重的患者,注意内外兼顾,如素体气虚或年老体衰的慢性肾衰患者感冒,则应用参苏饮扶正,以助表药散邪,使解表祛邪之力直达病所。
1.2.3 邪盛预防传变邪正交争之际,若正气转复,祛邪外出,则能扼慢性肾衰进展之势于未然;若正气虚损,邪气深入,则将导致疾病传变。赵树华教授认为,风寒湿邪从口鼻、皮肤侵入于肺,使慢性肾衰患者肺失宣发肃降;平素脾虚,失于运化,痰饮内生,聚而生热;平素肾虚,失于摄纳及气化。因此若外感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导致患者湿毒内阻,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脾失运化,出现纳呆、腹胀、便溏或大便黏滞难下;湿毒与痰饮互结,加之久病入络而成瘀,肾不能化气行水,而出现尿少、水肿;浊毒蓄积而出现口中溺味;肾不纳气,肺气不足,出现动则喘促,甚则张口抬肩;水气凌心最终导致心脉失养,出现心悸、胸痹;浊毒久酿而生风动血,出现烦躁、抽搐;浊毒与瘀血阻滞,上犯清窍,出现嗜睡、昏迷、躁狂等。
因而在外感早期正邪交争之时,在应用扶正药物助邪外出的基础上,注意固护五脏之气,防治其他脏器的传变和衰惫。
1.2.3.1 宣肺理气 补肾泻肺 防湿毒壅肺此时外邪损伤肺气,浊毒壅滞肺脉,通过宣肺理气、补肾泻肺可以防治邪毒壅肺、肺气壅滞[5]。赵树华教授常用麻杏石甘汤辛凉宣肺、清肺平喘,为预防尿少、尿闭引起的胸腔积液、腹水,应用益肺之源、补肾纳气的都气丸,配合健运脾胃、利水渗湿之品,如茯苓、猪苓、泽泻、滑石等。若患者已经出现胸腔积液、腹水,可以应用葶苈大枣泻肺汤、十枣汤、疏凿饮子及中药灌肠等方法治疗。
1.2.3.2 温补肾阳 利水消肿 防水气凌心慢性肾衰患者感受外邪,肺失通调,水液代谢失常而积聚,加之病久,脾肾阳虚不能化水,水饮内停,上凌于心,故见心悸,动则喘促、咳唾频作;饮溢肢体,故见肢体水肿;水饮阻碍中焦,胃失和降,则脘痞、纳呆食少、恶心呕吐;阳气虚衰,不能温化水湿,膀胱气化失司,故小便短少。此皆为水饮内停之象。
赵树华教授认为慢性肾衰需防治水气凌心,平素注意固护脾肾阳气、健脾行水,常以茯苓、白术、苍术、车前子、薏苡仁为基础药物。一旦出现心悸、喘促、咳唾不止的水气凌心症状,赵树华教授即认为此证以脾肾阳虚为本、水气内停为标,主张以扶助正气为主,予真武汤加减以温补肾阳、利水消肿,酌加活血化瘀之川芎、当归、泽兰、益母草等;若气促不能平卧,大汗淋漓,脉数无力,即予参附注射液以温阳固脱。
1.2.3.3 平肝潜阳 行气利水 防肝阳上亢慢性肾衰晚期阴阳俱虚,外感后导致肾脏衰惫。“肝有相火,有泻而无补;肾有真水,有补而无泻”,肾阴不能涵养肝木,容易导致肝阳上亢。所以慢性肾衰晚期会出现顽固的头痛、眩晕,临床上可见血压居高不下。
赵树华教授在慢性肾衰的早期注意到固护肾阴,在健脾利水消肿的过程中,酌加生地黄、枸杞子、墨旱莲、女贞子以及龟甲、鳖甲等血肉有情之品,以滋补肝肾。若出现肝阳上亢所致的烦躁易怒、睡眠多梦、头痛眩晕等症状,赵树华教授以平肝潜阳、滋养肝肾为治则,予天麻钩藤饮、镇肝熄风汤或丹栀逍遥散加减,常配以生地黄、何首乌、白芍等滋补肝肾之阴;并注意此时肾衰患者存在湿毒蓄积,需要通腑泻浊,不可妄用峻下中药一味泻下,需要润燥通便,方选麻子仁丸、当归龙荟丸。
2 重视饮食不节防内伤
2.1 重视饮食不节在慢性肾衰病程中的危害
2.1.1 饮食不节导致多种宿疾而诱发慢性肾衰临床中,患者的慢性肾衰很多来源于痛风、消渴、肥胖等多种宿疾或嗜食膏粱厚味,或因“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或因“脾胃俱旺,能食而肥,脾胃俱虚……或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盖脾实而邪气盛也”。而这些宿疾久病及肾,肾络受损,封藏不固,以致精微下泄,开阖失司,出现尿中精微物质下注,形成“尿浊”,即蛋白尿。病久,肾气不摄,肾阴耗伤,终成慢性肾衰,出现肢体水肿,夜尿增多,尿浊加重;病久排尿减少,水气凌心,而成呼吸喘促,动卧加重[6]。所以赵树华教授认为,许多宿疾因饮食不节或饮食偏嗜而发生,又由此导致肾络受损,肾气不固、肾阴不足,最终形成慢性肾衰。
2.1.2 饮食不节导致慢性肾衰进展大量文献记载了饮食不节、偏嗜五味、不知寒凉等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的不良后果。宋代严用和在《济生方》中记载:“善摄生者,谨于和调,使一饮一食,入于胃中,随消随化,则无滞留之患。若禀受怯弱,饥饱失时,或过餐五味、鱼腥、乳酪,强食生冷果菜,停蓄胃脘,遂成宿滞。轻则吞酸呕恶,胸满噎噫,或泄或痢,久则积聚,结为癥瘕,面黄羸瘦”。《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素问·五藏生成》又曰:“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䐢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
结合古代医学典籍,赵树华教授认为饮食不节制、过食肥甘厚味可导致湿热内生,痰浊内停,同时导致脾胃损伤;偏嗜五味,导致脏腑虚损,气血不运。而慢性肾衰患者为饮食所伤后,脾胃运化不利,导致水液代谢异常和水谷精微不能达于肢体百脉,久之水肿、尿浊加重,病久肾络损伤加重,慢性肾衰不断进展。
2.2 防治慢性肾衰患者饮食不节之法
2.2.1 病初行气导滞消积赵树华教授认为,慢性肾衰患者病初伴有饮食不节,应防治饮食自倍导致的饮食积滞,避免食积后引起的脾胃损伤、气机瘀滞,避免过食肥甘厚味后湿热内生,加重元阴元阳的耗伤。此时多选择《丹溪心法》中的保和丸治疗,应用山楂、神曲、半夏、茯苓、陈皮、连翘、莱菔子等。方中重用山楂,其能消散一切饮食积滞,尤善消肉食油腻之积,为君药。神曲消食健脾,善化酒食陈腐之积;莱菔子下气消食,长于消谷面之积,并为臣药。君臣相配,可消一切饮食积滞。因食阻气机,胃失和降,故用半夏、陈皮行气化滞、和胃止呕;食积易于生湿化热,又以茯苓渗湿健脾、和中止泻;连翘清热而散结,共为佐药。诸药相合,共奏消食和胃、清热祛湿之功,使食积得消、胃气得和,热清湿去,诸症自愈。
2.2.2 病久健脾祛痰湿瘀赵树华教授认为,慢性肾衰患者病久,伴有饮食不节、偏嗜五味等问题,往往存在严重的脾胃虚弱;同时长期的饮食不节已经导致痰浊、湿热内生,加之肾脏虚损,病久痰湿互结,瘀血阻滞。因此治疗上一方面要健运脾胃,另一方面要注意对病理产物的清除,祛痰湿瘀。受张元素“养正积自除”思想的影响[7],赵树华教授积极应用枳术丸,并根据病情随证加减,应用橘皮枳术丸、曲麦枳术丸、香姜枳术丸、半夏枳术丸等。
枳术丸代表消补二法,可以补不碍胃、消不伤脾,主要用于调理脾胃,可使胃痛、呕恶、腹痛、腹胀、肠鸣、泄泻等症状缓解,机体功能得复。方中白术健脾燥湿,枳实泻痞消积,使浊气下降;荷叶芬芳养胃,使清气上升。枳术丸加橘皮则为橘皮枳术丸,原主治老人、小儿元气虚弱导致的饮食不化、脏腑失调、心下痞满,针对慢性肾衰患者脏腑气血虚弱的特点,用该方使患者过食、重食而不至于伤食成病。曲麦枳术丸为枳术丸加神曲、炒谷芽、炒麦芽,可以健脾胃、消宿食。香姜枳术丸为枳术丸加木香、干姜,主治冷食伤脾引起的脘腹冷痛、食谷不化,随之泻下完谷不化之便,主要针对慢性肾衰患者嗜食寒凉引起的泄泻。半夏枳术丸为枳术丸加半夏,主治冷食内伤脾胃初期,症见脘腹痞满、疼痛、恶心反胃。
对于发冷、发热、口渴、苔黄者,考虑食积化火,可加黄连、黄芩、大黄兼清内热。对于小便频数、淋漓涩痛者,可加泽泻、车前草兼清下焦湿热。针对痰浊较重者,可加全瓜蒌、半夏、天竺黄、浙贝母、杏仁等。针对湿热较重者,可加苍术、黄连、黄芩、黄柏、秦皮等。针对瘀血阻滞明显者,可加益母草、牛膝、鸡血藤、当归、桃仁、红花等。
3 重视劳倦失度防虚损
3.1 重视劳倦失度在慢性肾衰病程中的危害古代文献关于劳倦失度的论述较多。《素问·举痛论》曾说:“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清代周学海的《读医随笔·证治类》曰:“疲劳汗出,则气伤津耗,气不足以运血,津不足以载血矣”。而汉代华佗的《中藏经·劳伤论》更是认为:“劳者,劳于神气也;伤者,伤于形容也”,于是很显然劳倦尚且属于劳于神气阶段,而非伤于形容的阶段[8]。
《素问·灵兰秘典论》言:“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这就是说肾是主导力量运动的器官,用力过劳会伤肾。肾为元气之根,其气亏虚则出现机体功能活动低下。肾藏精,是化生气血的根源,影响着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等生命过程。随着肾精的逐渐耗竭,人体气血、经脉、五脏六腑衰损,出现“五脏皆衰,筋骨解堕”,疲劳不可避免[9]。而肾精亏虚,可致清窍失养,故常见头晕头痛;肾藏志,肾虚则志不定,故见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肾虚则清窍失养,故发头昏、头眩、头痛,正如《万病回春·虚劳》有云:“(世人)不知百病生于肾”[10]。
赵树华教授根据古代文献对劳倦过度的记载,结合慢性肾衰患者劳倦过度后出现的肾功能恶化、气血逆乱、五脏衰惫等症状,提出避免劳倦损伤肾脏的观点,嘱慢性肾衰患者避免劳累过度,尤其不能熬夜、运动过度、思虑过度、房事失节。
3.2 防治慢性肾衰患者劳倦失度之法赵树华教授将慢性肾衰伴有劳倦的患者进行分型,气虚型治以健脾益气,方用参苓白术散加味;气血两虚型治以益气养血,方用八珍汤加减;气阴两虚型治以益气养阴,方用四君子汤合左归饮加减;气虚夹郁型治以益气开郁,方用甘麦大枣汤加减;气虚夹瘀型治以益气化瘀,方用补阳还五汤加减;肝郁脾虚型治以健脾疏肝,方用柴胡疏肝散合香砂六君子汤;肝肾阴虚型治以滋阴补肾、养阴柔肝,方用六味地黄丸合一贯煎加减;脾肾阳虚型治以补肾温脾,方用金匮肾气丸加味。
4 结语
感受外邪、饮食所伤、劳倦内伤是慢性肾衰反复进展、恶化的重要原因。赵树华教授在慢性肾衰患者外感的防治过程中,遵循治未病的思想,早期固护正气以预防外感;若遇外感则积极祛邪外出,固护脾肾阳气;若外感之邪深入,则固护五脏以防传变;若生传变,则标本同治、清补互充,最终起到延缓慢性肾衰进展、改善患者预后的作用。在慢性肾衰患者饮食失节的防治过程中,赵树华教授主张初期行气化积导滞,晚期健脾清湿痰瘀。在慢性肾衰患者劳倦失度的防治过程中,赵树华教授主张气血、脏腑双补,避免劳倦内伤导致慢性肾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