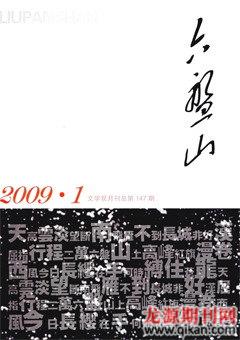王怀凌其人与《棉花》
红 旗
真正认识王怀凌并熟悉他是读了他的诗作《棉花》之后。
多年读书,最为感悟的是:一个作者要写诗,必须自己是诗,心中有诗,怎样的品性决定怎样的诗作,也就是“诗如其人”。对于王怀凌,以前似曾认识,也恍若相互寒暄过,但多半客套于泛常的应对,没有深刻印象。一次翻阅《绿风》诗刊,看到一组《西部以西》诗歌,看到发表在其中的《棉花》,不由细细品读,才算真正注意了诗的作者——王怀凌。
过去在老家农村接触过棉花这种作物。摘棉花、晒棉花、拣棉籽,甚至帮着大叔大哥捆扎好棉花锭,交给公社收购站。棉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元素。而我对棉花独有一番情愫:它有白皙的颜色,却不显娇柔的艳姿;它有飞扬的愿望,而从不轻浮;它有温暖的怀抱,但毫不贪婪吝啬;它紧紧贴着我们的身体,从不故意让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在成熟的季节里,棉花在枝头悄悄分娩,人们小心翼翼为其接生,在丰收的棉田里到处洋溢着采棉人的歌声和棉花骨朵儿奉献的烂漫。这正如诗中“在棉花盛开之前,所有的花朵都应该熄灭\九月,广袤的新疆大地在棉花温暖的怀抱中沉醉”。王怀凌用睿智的目光和善于思辩的抒写,使我对他的诗作以及本人肃然起敬。这样的笔调需要怎么样的心情和见识才能培育?这样的感知和自然而然的表达又得益于怎样的基础呢?我相信,这一切都出于一个人的秉性和对自然界的热爱,对劳作的理解和对文字的娴熟。于是,我以文取人,想象他是一个优雅的儒者,一定拥有广博的学识、淡定的风范、深刻的启悟和潜心的写作。
当一次有人向我介绍王怀凌时,我十分惊讶,他是王怀凌?这样年轻,年轻得近乎脱俗,一身迷彩服,似乎和气中暗藏了许多傲骨。他自然地伸出手与我相握,并告诉旁边人:“我们是老熟人了,他是老牛。”此时庐山苍竣,在我眼中反而不近情理。
从此以后我便和王怀凌真正成了老熟人。我们(包括单永珍、杨建虎)经常聚会谈诗歌。他们是老诗人,各自有不凡的成就,我年龄虽比他们大但起步最晚,于是他们三人对我都有一定影响,关心我、激励我(常常叫我青年诗人)。我有时把自己的作品和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自我挑剔(尤其是王怀凌的作品,光《棉花》我就比较了无数次),得出的结论是:我年轻,他们成熟,王怀凌是个老家伙!
现在我可以直接说王怀凌这个老家伙了。他固原师范毕业,在乡镇当过教师,到文教系统当过于事,在政府机关办公室干过,又去一个乡镇当领导(一个九品开外的芝麻糊糊官)。会开车(有时下乡工作自己驾车)、会喝酒(划拳老手、边掷骰子边猜对方眼神)、会调侃(这家伙笑容里有自信)、会写书法(我好不容易讨了一幅他自认为很糟的字,这家伙更好的字或许是想要点润笔)、会吼秦腔(有一位姓陈的秦腔专家特别喜欢他的唱腔……)、很自负(自称每年抽时间写一些国家重点刊物能发的东西就行了,果真如此)、很忙活(公干忙得不可开交,还抽空和爱好文学的兄弟们打拼)、高兴时唱一出周杰伦后现代的《菊花台》……反正这家伙很绝!在诗作中他潜移默化地叙述着一种对劳动生活、对普通农民工的热爱,“一望无际的棉田和天南海北的拾花人\在这个最忙碌的季节里秘密邂逅\从西海固出发的拾花人像蜜蜂一样\涌出乌鲁木齐火车站蜂箱\转眼就被一片白色的花海淹没\当他们在十月的花事中苏醒过来\那个和我一样累弯了腰的男人……”这种情感只有日积月累的沉淀,才能付诸笔墨生动地表现出来,这里我仿佛读到了《诗经·采薇》中“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日归日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的感觉。他笔下的西海固不是荒凉无助的,是充满乡土气息,具有昂扬拼搏活力、具有一种风起云涌的契机和一种温和的坚持。记得在一次谈笑中他说:“泰山只是雄伟,并不很高”,果然他在诗作《我站在泰山之颠》里写到“我高出泰山一米七八”。这是一种荡气回肠的现代生活禅,这种意象在他平常生活、在他的作品里处处独立存在。又如《棉花》中“……那个和我一样累弯了腰的男人,由衷地感叹着\新疆的大地之大,棉花。之白,少女之美”。
每次读他的诗,我总会感叹:这样宽阔胸怀的诗人,这样有才华的诗人,如果他能专心致力于笔耕多好啊。
当然,我知道的王怀凌并不是唯美的,也许只是一些单枝片叶,他的主干还需以后交往中多多观摩和体会。我想“窥一斑便知全豹”、“觑一叶而知秋深”一定有它的道理。最后,我以他的诗顺便做结尾:
我告诉你西海固:蒲公英的泪珠被风暴挟持
苜蓿梦见紫花的海洋工蜂畅想甜蜜的爱情
我送你一朵云你一定会热泪盈眶,但我只送你一声叹息
西海固只是中国西部的一块补丁在版图上的位置
叫贫困地区或干旱地带我在西海固的大地上
穿行为一滴水的复活同灾难赛跑……
[责任编辑:单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