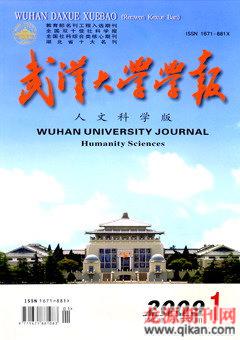“此在”
唐桂丽
[摘要]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思想集中于他的范畴“此在”中。“此在”不是灵魂、精神和人格式的主体,也不是“意志”、“强力”等生命体。“此在”首先意味着生存,人通过生存,表明他存在;其次意味着“现象”或思想,通过思想显示或思念着而存在。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存和思想是同一的过程,没有生存,“此在”无法存在;没有思想,生存无法得到显现,存在处于黑暗之中,无法得到澄明,而存在的澄明是海德格尔的真理。
[关键词]海德格尔;此在;生存;思想
[中图分类号]B516.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1-0028-06
对人的思考始终是人的那份对自己无法割舍的爱,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思想集中于他的那个范畴“此在”中。在众多对海德格尔“此在”的解读中,总产生一种不尽然、不过瘾的感觉,于是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路标》等书找来读,其中收获的那份痛苦、兴奋与幸福,只有自己能够知道。在对海德格尔“此在”范畴的整理中,笔者认为生存与思想的合一是其根本点,便写下这份体会,以求教于大家。
一、生存论式的“此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命
要理解“此在”的生存论样式,首先必须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虽然不是存在者,但存在从来不是作为存在者的对立面而存在,存在不在存在者之外,也不在存在者之上作为存在者总体而存在。存在就是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去存在”。这里,你看不见分立或对立的二者,只有存在者,存在就是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去成就其所是的过程或状态。作为过程和状态来说,存在永远不是一个确定的在者,它只是一种可能性,只是一种“将在”,它永远处于生成中。作为生成,存在并不预先给予存在者什么,它不规定、不赋予、不创造存在者。它只是让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去存在,存在者成为一个特定的存在者,那么一定是这个存在者本来就如其所是的。然而,存在者虽然没有预先被存在规定、赋予、创造,但却是在“去存在”的过程中成就自身,即获得规定,这样存在是存在者获得规定,成就自身的基础或根据。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存在者的存在,作为过程或状态的存在,也就始终如此地去经历和发生着,不会留下什么特殊的痕迹。因此,存在者在如其所是的那样去成就自身时,常常使存在处于被遗忘的境地。正是“此在”这个特殊存在者的存在,使存在的敞开或被遮蔽成为重要的,也使存在获得关注,并被照亮。
“此在”这个特殊的“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的去存在”(第52页),而这种“去存在”就是它的生存。海德格尔反对把人理解为主体、灵魂、意识、精神和人格等这类东西,如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在他看来人“是在现成存在和摆在那里这种意义上加以领会的”(第60页)。因此,海德格尔尽量避免使用“生命”与“人”这样的术语,而使用“此在”这个范畴,为的就是说明“此在”的生存论性质。
海德格尔不认为先有独立的人或独立的世界,然后才有人与世界的相遇。海德格尔认为人最基本的状态就是他的“在此性”,即他进入周围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逗留,“烦忙”。“在此”是人逃不开的最初状态。人没有高高在上的独立性,也没有自己独立的世界,他有的只是“在此”的情境。因此,海德格尔的人,不是一个理性的认识者,也不是一个像叔本华、尼采式的非理性的生命体,他的人是一个生存者。海德格尔对人的生存性的强调,是通过他对“在世界中存在”的分析来达成的。人必须进人或逗留在世界之内。这样,人才能接触在世界之内的现成存在者,而存在者也只能这样向人展开自己,成为人可领会或通达的东西。这说明,不是先有人或世界,然后才有它们在一起的关系,而是由于这种“烦忙”的方式,此在和存在者才如此照面,人与其它存在者经由“烦忙”形成关系。此在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烦忙”着生存于此的人。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此在”的生存论性质,我们需具体地了解一下海德格尔的几个重要提法:“在世界之内”、“烦忙”和“诗意的栖居”。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在世界之内”。对“在……之中”海德格尔强调的是居住、逗留,强调地是“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逗留之”。即我生存在世界之中。这种生存有两点需要强调的:一方面强调了“此在”在此的那种日常性,“‘此即是世界,具体的、朴实的、现实的、日常的世界。做人即是沉浸于、扎根于和嵌入这个地球、这个世界的普遍物质和事实性物质之中。”(第111页)海德格尔用“在世界中存在”来表达我们从根本上内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因此,“此在”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者,他是进入日常生活世界,生存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他不能脱离日常生活世界而存在。另一方面强调了那个“居住、逗留”,海德格尔在后期尤其对这个“栖居”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海德格尔对“栖居”的强调,主要关注的是“在世界内存在”的“此在”与“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关系,前期,海德格尔强调对非此在式存在者的操作、利用和领悟;后期,海德格尔则强调的是一种爱护和保护。
由此,产生了前后期“此在”在生存样式上的差异。前期,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界之内的存在,具体体现为“烦忙”:“在世界中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第83页)其中,打交道指的是操作、使用“非此在式”的存在者。这样“非此在式”的存在者常常作为“用具”与“此在”相关,海德格尔将其区分为“当下上手状态”和“现成在手者”。其中,“当下上手状态”指被自如地使用的“工具”,人称手使用着“工具”,以至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工具的存在,而此时,则是工具最本己的存在状态。而“现成在手者”则指不能称心使用的工具。由于人不能自如地使用它,才会去留意和关心它的存在,对其做理论上的“观看”,这时的工具虽被人观察、留意,但却不是其最本己的存在状态。到这里,我们只是说明了由“烦忙”而形成的“此在”与“非此在式”存在者的状态。那么,世界的状态是怎样呢?显然,世界不是由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组成的,因而不能从存在者状态的性质来把握;世界也不单纯是此在的状况,因而也不能由此在这个特殊存在者的状态去识认。由此,世界其实融身于那些上手状态的指引之中,融身于我们对工具的自如的操作与使用中,融身于“烦忙”本身中。我们之所以能够“烦忙”,表明我们对世界的熟悉,正是这种对世界的熟悉,使我们依据其中,却不自知。那么,世界在什么时候被此在所把握呢?海德格尔认为,在上手东西处于触目、窘迫和腻味的状态时,世界才得以呈现,并被此在所把握。由于“烦忙”体现为对世内存在者的操作与使用,“烦忙”的顺利与否,则取决于工具的称手与不称手,而在称手与不称手的“烦忙”中,此在的烦、畏、焦虑、操心得以呈现。因此,前期的海德格尔在两个意义上关注“烦忙”:一为操作和使用,人依据对物的本质之熟悉而操作与使用着物;二为观察、识别与研究,当世内存在物不称手时,人开始对现成在手之物的研究。当物与世界处于被操作与使用时,它们存在但被遮蔽;当物与世界处于被观察与研究状态时,它们暂停存在却得以被领悟和呈现。
后期,由于对居住、逗留中爱护和保护的强调,此在与世内存在者的关系发生了转移,海德格尔提出了他著名的“看护者”、“牧羊人”的提法。前期的海德格尔仅仅只注意到逗留和持续的存在于世,后期的海德格尔应该说已经注意到人是如何地逗留与持存于世的。海德格尔从居住的古词“bauen”中指出,除了“居住”的原意外,还同时意味着“爱护与保养”,从而概括出“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一种保护”。在后期的海德格尔那里,世内的存在者不再仅仅是作为操作和使用的“用具”的身份而存在,而是作为“聚集”而存在,“聚集被叫作物”,作为这一物,聚集着天、地、神、人这四重整体。栖息指的是在大地上、在天空下、在诸神面前与人一道逗留,而保护则意味着:“守护这四重整体的本质。”前期和后期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一样。前期的世界是人烦忙于此的场所,它更多指的是周围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人是扎根或沉沦于日常生活世界中。后期的世界,海德格尔具体提出了天、地、神、人这四方,其中的每一方都要以它自己的方式映射着其余三方,并同时映射着自己,从而进入四方形成的那种纯一性中。四方由于环绕作用,相互依偎在一起,柔和地、顺从地嵌合为世界,每一物都居留在四重整体中,体现着这四重整体的聚集,发生着物之为物的物化。因此,物并非通过人的所作所为而在场的,它是由四重整体世界化了的世界而形成的,所以,栖居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建造,而是保护,保护那由四重整体的环化嵌合而成的世界或物。这样,海德格尔后期的世界在境界上比前期具有更强的超越性。前期人更多地栖息于日常生活世界,由之,人也更多地沉沦于世,体现为烦忙、烦神与操心;后期人栖息于天、地、神、人整合的世界中,因而,他强调这种栖息的“诗意”性。而这种“诗意”指一种让栖居的筑造,而这种筑造又指一种“采取尺度”意义上的筑造,而这尺度海德格尔指的是来自于神的人的本质。海德格尔说:“人以神性来度量自身。这种度量一旦发生,人就能根据诗意之本质来作诗。而这种诗意一旦发生,人就能人性地栖居在大地上。”
二、思想着的“此在”——现象意义上的生命
此在作为一个存在者是“为它的存在本身而存在”,这个存在本身海德格尔称之为“生存”,因而,此在始源地是一个生存者。然而,此在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者,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对存在的领悟,“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这样,此在的生存过程,既是它的存在过程,也是它对存在的领悟过程,因而此在还是一个领悟者或思想者。但是,海德格尔反对将领悟或思想作为人的一种特有能力来理解,他不赞成“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说法。因此,领悟或思想是此在在生存过程中生存状况的一种显现或展示,所以说领悟或思想在海德格尔那里更具有“现象”的意义。
作为“显示者”、“公开者”的现象,海德格尔说“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意指这样的显现者:存在者的存在和这种存在的意义、变式和衍化物”(第45页)。可见,海德格尔的现象就是“显现者”、“公开者”,它显示和公开的是存在,具体而言,它指的是存在的开启、敞开、显现,指的存在者已经在存在,存在的意义和根据已经在获取,存在的其它衍生形式已经在确定。现象除了涉及存在的开启、显现、公开外,还涉及一个如何开启、公开和显现的问题。海德格尔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指“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公开者”,这种方法是一种还原、回归或还乡,他强调的是“回到事物本身”,实际上,表明了存在拒绝从主体的角度被把握和认识,并同时拒绝作为客体而存在,存在是从其存在者去存在的过程中,展示或显现自身,体现为存在的开启、显现。现象不是一种对物的心理表象,也不是对普遍性本质的外露的现象,它是一种存在者去存在的显现过程。“回到事物本身”强调的是回到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二指“把某种东西展示出来让人来看”,存在的这种被看的状态,暗示了“看者”,观众的存在,没有看者或观众,存在的显现、敞开、表演则没有意义。因此,存在离不开此在这个特殊的存在者;没有此在,存在就不能被看,它的敞开和遮蔽就没有意义。因而,存在是那种需要被领会为如此这般的存在。另外,领会或思想存在,不是指那种从既有的范畴和逻辑规则出来去领会或思想存在,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以现象的照面方式给予的和可用这种方式解说的”方法,这里强调的现象是此在与某种东西的照面,因而,海德格尔的“现象的”方法实质上是生存论方法。现象作为存在的显现、敞开,是此在与某种东西的照面,这种照面强调的是此在进入或逗留在世界中,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即在“烦忙”中,此在与其它存在者照面,并领会或通达其它存在者;而其它存在者则向此在敞开它如此这般存在的过程,即向此在显现,让此在看其存在。没有此在的这种“生存”,就不会有现象。
由此可见思想的“现象”性。思想在海德格尔那里不是一种形而上学,不是主体的一种能力,它是存在的现象,是对存在的追问,是力求开启、显现存在,是对存在的澄明。海德格尔的思想开始在传统哲学终结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通过形而上学和从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的诸科学都不可能通达那“待思”的东西,因此,海德格尔叫停西方传统的思想,那种他称为觉知的思想,那种“表象着在其对象性中的对象”的思想,那种“让在场者如其站立和放置那样站立和放置在我们面前”的思想。于是,海德格尔大声地宣称:“在我们这个可思虑的时代里,最可思虑的东西显示于我们尚未思想。”原以为这个有待思想者向人隐匿其自身,形象地说从人那里扭身而去。然而,那个自行隐匿的东西虽然抽离我们,却以一定的方式抽吸着我们,我们被引向那个自行隐匿者。当我们被引向那个自行隐匿者时,我们通过显示到自行隐匿者之中而存在,我们在显示那个自行隐匿的东西,这时,“人是显示者”,人在显示,也就是人在思想,或者说人通行在追问有待思想者的路上。所以,思想不是表象,不是觉知。不是对站立在我们面前对象的映射,思想是一种显示,一种追问,一种领悟,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向我们自行隐匿的存在的显现,即“现象”。这样,对海德格尔来说,与思想相关的就是两样:一是“待思的东西”,就是那个存在,它在海德格尔那里,一会儿是自行隐匿的东西,一会儿是“澄明”,“思想必然要对这里称为澄明的那个事情以特别的关注”;二是显示或现象。这样,思想就犹如踏上了一条路,“思想就在这条道路上追踪某个东西并且领悟这个东西”。那么,作为显示或现象的思想如何思想呢?
作为现象的“情绪”、“领会”、“倾听”、“言说”、“阐释”。人作为显示者,作为现象者,作为思想者,他的革命性就在于,“张三”不再被作为一个符号化的物式的具体人来把握,也不再被作为一个所有人的总和的类的人或一切人都具有的共同本质的人来识认,更不会被作为表象式的心灵实体来确认。人在海德格尔那里简单地说就是把存在者的存在显现出来,或现象出来。具体来说,人在生存的过程中,现身为“情绪”、“领会”、“解释”、“陈述”、“言谈”,总体上来说,现身为“烦”。这里让我们领悟到海德格尔不把人称为人,而称为此在的妙处,因为人在此就现身为“情绪”、“领会”、“解释”、“陈述”、“言谈”,换言之,
“情绪”、“领会”、“解释”、“陈述”、“言谈”不是人的某种能力或部分,它就是此刻在此生存着并现身着的人,也就是说,“情绪”、“领会”、“解释”、“陈述”、“言谈”也就是人本身。同样,在这里也让我们领悟到,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才是人的主人”,不是人有语言,人构成或操作语言,而是言谈、语言本身此刻现身为人,也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就是存在之家,就是为存在所居有、并且由存在来贯通和安排的存在之家”。也就是说,语言不为人所拥有,语言为存在所拥有,语言聚集着存在,显现着存在,当然,在此刻显现着存在的语言本身,也就是生存着显现着存在的人本身,即此在本身。思想也是如此,思想不是一种技艺,“思想乃是存在的思想”,对此,海德格尔强调从两方面来理解,“思想乃是存在的,因为思想为存在所居有,归属于存在。同时,思想又是存在的思想,因为思想在归属于存在之际倾听存在。”,简单地说,思想属于存在,思想显现存在,因此,思想不是人的一种能力,思想就是人本身,作为显示存在的人本身。这样“情绪”、“领会”、“解释”、“陈述”、“言谈”、“语言”、“思想”都是人本身,都是显示存在的显示者,都是存在的现身者。
三、“此在”的革命性——生存与思想的合一
在这里,我们已经发现了海德格尔“此在”的革命性,也就是对于人的本质理解的革命性。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明确地提出,传统人道主义者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体现为使人在人性中寻找人的尊严,而海德格尔认为“人在其本质中为存在所要求”,也就是说,他已经不从人性这个形而上学基础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是从存在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在他那里,“本质性的东西并非人,而是存在”。即是说,对人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并不是人,而是存在。换言之,人专注和关心的也不是人,而是存在。那么,人是如何切近存在的呢?海德格尔反对那种站在存在之外,对存在做科学和理性式的把握,而主张通过生存,他称之为“绽出之生存”的东西来把握存在,而这种“绽出之生存”由于它是“在存在之澄明中的站立”,从而表现为,人内立于存在的真理之中守护着存在的真理。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人是通过“绽出之生存”来思想存在,生存和思想对于海德格尔的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对于他的此在来说,乃是生存与思想的合一。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情绪”、“领会”、“言谈”作为此在的现身,显示出它们就是人本身。注意这里的人本身,不是指“情绪”、“领会”、“言谈”作为人的能力或部分或结构而存在,而是指它们作为人的生存的展开状态。前面我们也提到,人的生存在海德格尔那体现为,人“在世界之中”的“烦忙”与“烦神”以及“诗意的栖居”。那么,在这种“烦忙”与“栖居”中,人如何存在呢?海德格尔认为,人在这时就展开为“情绪”、“领会”和“言谈”。因此,“情绪”、“领会”、“言谈”是人的生存的展开状态。
具体来说,有情绪,表明人作为那样一个存在者以情绪的方式展开自己的生存,通俗地说,人或是心平气和地烦忙着,或是心烦意乱地烦忙着,这种情绪表明,人随情绪的闪烁,在世界中与世内的存在者打交道,这样,世界,共在的他人以及在此的自己,在这样的情绪中被展开。因此,情绪不是人的心理活动,而是人在生存过程中在此以情绪的方式现身。在众多的情绪样式中,海德格尔最关注的两种情绪是“畏”和“怕”。
“领会”作为此在的一种能在的存在方式,首先区别于逻辑学中那种与现实性相对的可能性与潜在性,这种“能在”指的是那种“为何之故”去在的状态,而这种“为何之故”表明,人对事物这样或那样去存在总已有所领会。“领会”的生存论形式也有两种“筹划”和“视”。关于“筹划”不是指拟定计划,按计划安排自己的存在,而是指“为何之故”本身,因此,它是作为一切可能性的可能性而存在。关于“视”也不是指用肉眼等感官去观察的那种看,而是指随着人的生存过程,世内的存在者展开自己让人看,这种视是与此的展开一道存在着的视,这种视作为领会活动是离不开生存的,它是人在生存过程中,与世内存在者的照面,世内存在者处于无掩蔽的澄明状态,人才能看。“视”的这种生存性不可或缺。
在“领会”的基础上,需要关注的还有“解释”和“陈述”。领会造就自身的活动称为解释,因而解释是将已有所领会的东西整理出来,这样解释是真正属于此在的,在解释的活动中,构筑着此在的意义。在这里,我们终于发现海德格尔给人留下了一点真正属于人的东西,那就是基于解释构成的意义世界。只有此在才能够是有意义或没有意义的。陈述是解释的衍生形式,而在解释中构筑的意义,通过陈述被展示出来,述谓出境,传达出来,从而被分享。
“言谈”是对可领会状态的勾连,不过那是发生在共在基础上的对可领会状态的勾连。在言谈中,海德格尔强调的是那种分享,对那种可领会东西和现身情绪的分享。因而,言谈是在共在中发生的,它的生存论的表现形式有听和沉默。在听中,此在作为共在对他人是敞开的,因为不听或听得不对,就意味着不懂或没有领会,也意味着存在的遮蔽。沉默是那种真正有所领会和理解的沉默,这种沉默能够公开出“闲谈”的无根性和虚无性,或者说非领悟性和非理解状态,公开出对存在的遮蔽,并消除“闲谈”。因而,言谈“揭示着世界和揭示着此在本身”。这样,言谈既是共在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存在现身的方式,是存在显示和公开自己的现象的方式。
从上述对“情绪”、“领会”、“言谈”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既是人的生存方式,也是展示、显示公开存在状态的过程,它的生存过程和作为显示的思想过程是合一的。它在生存着,同时也就在显示或思想着。
当然,海德格尔也分析了一种他称为“沉沦”的日常生活状态。沉沦揭示着个人与他人共同存在的状况,海德格尔形象地称之为混迹于世界之中。海德格尔首先排除了人们对沉沦从道德的角度,即坏的或恶的角度来理解的倾向,他强调沉沦仅仅是人们的一种日常存在的方式,这种日常与他人杂然共存的状态就是沉沦。而这种日常的沉沦具体体现为“闲谈”、“好奇”和“两可”的状态。
其中,“闲谈”只展示出人们聚在一起进行着言说这件事,但人们对言说所涉及的东西本身并没有太多的领会,也不太专注和关心言谈所涉及的东西,从而展示出“闲谈”的无根基状态。“好奇”产生于人们对世界作“工件”式操作与烦忙的停顿中,或休息中的那种寻视状态,海德格尔认为这时的人们仅仅从外观上去看“世界”,这种方式的看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而仅仅是为了看本身,他把这种看称为“放纵”,即任由自己流连在对与自己照面东西的不断翻新的追求中,这种状况体现了人到处在而又并无一处真在的状况。“两可”展示出的是人们在日常沉沦中的这样一种境况:无论是“世界”、共在的他人还是此在本身,他们看上去似乎被真实地领会了、把捉了、说出来了,其实却不是如此,或者他们看上去不是如此,而其实却被真实地把捉了的这种状况。这种“两可”状态,表面上体现为一种无所谓的情形,其实却展示了人与他人的一种紧张的相互窥测、相互偷听的状况。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沉沦?海德格尔以为:一方面由于人们在闲谈中被引诱到公共解释中;另一方面,这种公共解释给人以自信,从而将人带人一种“安定”的情绪中;结果,这种安定将人引入一种异化的存在:即本真的人在对人隐蔽着;这种异化指人被挤压入非本真性之中,进一步跌入那种非本真的无根基的、虚无状态,无法自拔,海德格尔给出的名字叫“自拘”。海德格尔就这样通过“引施”、“安定”、“异化”、“自拘”层层深入地揭示出人的存在的那种非本真性。
人们沉沦着,非本真地生活于世,表明人生存着,却逃避着对存在的思想,人们生存着,但人们却拒绝去领会、去视、去听,存在在人们沉沦时,对人处于遮蔽状态,人们在逃避思想存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对自己的放逐,也呈现出人生存的无根性和虚无性。这样,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们可以无思想地去生存,但人们离存在很远,也表明了他的不存在。
因此,真正的生存是思想与生存的合一。人们通过他的生存,去领会、看、倾听存在的声音,思念着存在,在这种思想中,看护着存在,并且与存在在一起。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思想的根本点,人没有取得像上帝那样的创造者的位置,人也不是那个可以把世界对象化的主体,对世界进行统治和主宰的人,人只是通过自己的生存,去领会、看、倾听存在,人通过他的生存进入这个世界,然后,在天空下,在大地上,与神相视,或舞蹈、或歌唱、或宁静地看与视。人不创造,也不建立什么,他只是去生存,并且.去思想。
责任编辑涂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