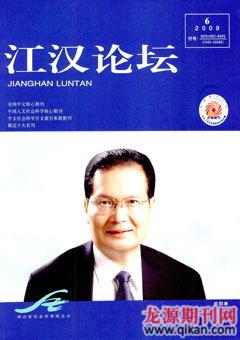中国经济学家面对诺贝尔奖的理论尴尬
刘开云
摘要:诺贝尔奖开设已有一百多年了。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直被国人引为骄傲,也令世人瞩目。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本土学者为何难出诺贝尔奖得主?究竟是什么抑制了我们的科学创新潜能?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一种“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的长期并存,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这些问题颇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
关键词:诺贝尔奖;数学模型;数学化;科学理性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6-0057-05
一、“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之惑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直被国人引为骄傲,也令世人所瞩目。然而,遗憾的是,屈指算来,诺贝尔奖设立已有一百多年了。但眼下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会上,不曾听见有中国籍学者的名字。对此,有人叹息。有人不平,也有人默然。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在100年前,高尔基甚至认为“科学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系统”。而恩格斯则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中国,科学界常有人提出:中国何时能产生牛顿、爱因斯坦?演艺界则常有人提出:中国何时能产生梦露、麦当娜?而中国的绘画界,则常有人提出:中国何时能产生凡高、毕加索?中国本土学者为何难出诺贝尔奖得主?这或许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它绝不是一个伪命题。不管怎么说,在历史指针已指向21世纪的今天,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梦想,无疑是最能牵动中国莘莘学子“科学神经系统”的情结或梦想。当今中国是一片经济热土,它更呼唤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诞生!
我们知道,诺贝尔奖分设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及医学、经济学、文学、和平6个奖项。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更是盛产诗人和作家。然而,中国的作家至今仍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这实在是令人尴尬,令人遗憾,令人匪夷所思。客观地讲,在文学方面,据称似乎存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语言障碍,甚至存在所谓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致使在交流、对话方面莫衷一是,而中国作家的作品或许不易入围,更难获取诺贝尔奖。当然,勿庸讳言,我们作品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恐怕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基本的判断。
在经济学方面,我们过去偏重于研究传统政治经济学,偏重于计划经济理论,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对市场经济理的研究,缺乏对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而后者乃是当今世界经济学研究之主流。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几乎对数学模型力不从心。因而,在经济学这一学科,也因文化尤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人们长期对西方经济学、对数学模型拒之门外,从而导致中国学者在相当时期内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可喜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正在与国际接轨,但无疑这里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作为一种国际公认的奖项,存在文化的差异、语言障碍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诸方面的影响因素都有可能,并起一定的作用,但起关键性、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恐怕还在于成果本身的实力。在既定的游戏规则前提下,真正的勇者、智者,首先必须是诚者:胜也好,败也好,愿赌服输,无话可说,谁叫你技不如人?竞赛不会结束,明年再见吧!自我反思,承认差距,奋力追赶,这或许才是科学理性的态度。遗憾的是,我们有一些学者,动辄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语言障碍,以及所谓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为搪塞,甚至“情绪化”地认为评奖存在不公,而对获取诺贝尔奖失去信心。存在类似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它对我们自己执着追求,探索真理似乎是无益的,甚至会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再说,老是强调那句“北欧的某些诺奖评委别有用心”。不仅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也似乎难以令人信服。顺便指出,尽管美国、加拿大、西欧、北欧国家夺得了90%以上的诺贝尔奖项,但前苏联或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危地马拉、圣卢西亚、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等,均有学者摘取诺贝尔奖。这些国家的学者所获奖项,大多为文学奖,但也有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及医学、经济学奖项。上述国家,且不说大多存在语言差异、文化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差异,但似乎并没有妨碍这些国家学者的获奖。这给我们的启示也正在于此:就像人们需要遵守游戏规则一样,我们既然可以认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评奖规则,那么,也就没有理由不去接受诺贝尔奖这一国际科学界、经济学界、文学界的“奥赛”评奖规则。
在中国的学术界,这里主要指经济学界,“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几乎同时存在,因而出现以下悖论:一方面渴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获得诺贝尔奖;另一方面研究成果似乎又与获取诺贝尔奖的一些基本标准或要求相背离。比如,市场化、民营化、“经济人”假设、数学模型等,乃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也是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理论权威,在改革开放实践冲破旧的理论禁区已30年的今天,却仍然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或不屑一顾,甚至“坚决反对”。在中国本土学者中并存的这种“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及其悖论,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悖论(或二律背反),但它却是一个与学术问题紧密相关的悖论,我们姑且称之谓“准学术悖论”。这种看似“非学术的”悖论,却十分令人困扰。剖析这一悖论,从表象来看,它似乎只是涉及到学者们的学术兴趣以及对获取诺贝尔奖的兴趣高低或是否有牢骚甚至浮躁情绪等;对于有志于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又对现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不感兴趣甚至“坚决反对”者,它似乎有点类似叶公好龙或自相矛盾的典故。进一步分析其深层的根源,恐怕与学者长期形成的某种思维定势(习惯性思维方式)有关。
二、数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
上述由“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引出的悖论,犹如一个人对同一问题,一会儿举起右手说“坚决支持”,一会儿举起左手说“坚决反对”。当然,他并不是直接反对获取诺贝尔奖,就经济学而言,他反对的只是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及“数学化”的方法(如市场化、民营化、“经济人”假设、数学模型等),而这些学术范式和分析工具恰恰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重要因素。这种悖论,它所凭借的理论,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然而,将它置于“科学无国界”、“学术无禁区”、“全球化”的背景来科学理性地审视,其局限性或矛盾甚至荒谬之处则是不言而喻的。
笔者赞同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先生的这种说法:“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国界的问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天文学与无产阶级的天文学、中国的天
文学与世界的天文学之分。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是分析工具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流行观点,即囿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因而渲染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论述,笔者不太赞同。比如,李成瑞先生认为,近20多年里,“许多媒体大量刊载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这就使得对西方经济学右的倾向愈来愈严重,……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他甚至引用材料指出:“现在是私有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面临严重挑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泛滥。如今“反对经济学‘数学化…的有关论述已不属鲜见。例如,尹世杰先生前不久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经济学应该“数学化”吗》。该文指出,“经济学决不能‘数学化”,“反对‘数学化的偏向”。文中甚至借用另一位学者的语言,称“一些人鼓吹经济学的‘数学化”,“是伪学问”,“属伪学者”。而何炼成先生则撰文认为,“数学分析和模型的构建太多”,是“数学教条主义”,“洋八股”,甚至对使用“产权”、“寻租”、“后工业化”等名词概念都不赞成。还有一位名叫余斌的学者,最近大胆地提出:“我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他解释道:“以前的全盘否定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我的不是,我是基于学术逻辑来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我是学数学出身的,西方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模型,这些数学模型都是有问题的,西方经济学不是在运用数学,而是在糟蹋数学,西方经济学在学术逻辑上站不住脚”。
应该看到,现代经济学已愈来愈“数学化”、公理化,它与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化。的确,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它又是一门交叉科学或边缘科学。如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它们似乎没有意识形态之分。至于统计学、概率论、数理统计、博弈论等,更是纯技术、方法论的。因而,似乎不应笼统地将经济学界定有意识形态,也不应将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如定量分析、数学模型、“数学化”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因为它属于数学工具,而数学显然是没有意识形态之分的。作为分析工具或武器,它是无“意识”的。比如,一把宝剑或一枚炸弹,它决不会有“意识”,关键是看它用在谁的手上。若用在魔王之手、本·拉丹等恐怖分子之手,它会使人头落地;但用在正义者之手,则不然。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将现代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及定量分析、“数学化”视为异己力量,或洪水猛兽。同自然科学领域一样,作为重要的分析研究工具,数学暨“数学化”如今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方法论支点。我们知道,诺贝尔奖设立之初(1901年),只有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与和平5个奖项,直到1969年,才设立经济学奖。这一年,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朗纳·弗里希和荷兰经济学院教授扬,丁伯根因为“使经济学有了数学的准确性,并给了它一定结构,从而使定量分析和对各种假设的数学证明成了可能”,从而分享了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继而第二年(1970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则颁发给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的获奖领域是“局部与一般均衡理论”,获奖成就是“运用科学研究方式发展了静态与动态经济理论,并提高了经济科学的分析水平”。萨缪尔森是作为当代对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而获奖的,而他半个世纪之前撰写的巨著《经济学》,集当代经济学之大成,至今仍然风靡全球。他一直坚持认为,数学对于理解整个经济学起着最本质的作用。可以说,从1969年至2008年,在60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他们几乎既是经济学家,同时又是统计学家或数学家。当今世界,经济学理论研究已日趋精密化、数学化、公理化、模型化,在统计学、数学方法“渗透”经济学的同时,实验方法也在向经济学领域“挺进”。自然科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受控实验被引进经济学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应运而生,从而改写了经济学长于经验统计数据描述而缺乏科学实验的历史。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被誉为“实验经济学之父”,也正是这一创建实验经济学的贡献,史密斯当之无愧地摘取了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需要指出的是,实验经济学的创立,其方法论的基础除了实验方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或“数学化”的程度极强,且其中主要是博弈论;而200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奖给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教授及美国的托马斯·谢林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博弈论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这是继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约翰·纳什教授、约翰·豪尔绍尼教授和德国的莱因哈德,泽尔腾教授之后,经济学家再次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再看200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亦由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摘取,他的贡献是“加深了人们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费尔普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一位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其数学功底深厚。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他与弗里德曼分别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费尔普斯曲线”。我们知道,“菲利普斯曲线”是出生于新西兰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统计学教授菲利普斯1958年在一篇题为《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与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的文章中提出的,这一理论表明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也证明了“菲利普斯曲线”适用于美国。卢卡斯、布坎南等经济学家都围绕“菲利普斯曲线”展开了争论。饶有趣味的是,菲利普斯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而围绕着“菲利普斯曲线”问题,至少有6位美国的经济学家获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即萨缪尔森(1970)、弗里德曼(1976)、布坎南(1986)、索洛(1987)、卢卡斯(1995)和费尔普斯(2006)。而200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由三位美国人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获得,以表彰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机制设计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综合运用@。200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摘取,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此前,曾有38位美国人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第一次颁奖。截止2008年,已有62人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其中有39位美国人获奖,占了将近2/3。这些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多是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他们的获奖成果中几乎都运用了大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自古以来,人类经济活动都要讲求效率或效益,要讲成本核算,要计算投入与产出。从用手指头数数到现代计算机(电脑)的运用,人类经
济活动中运用数学的方法和手段不断提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如此赞叹: “45年前一名熟练操作员用台式计算器需3个月,用当时最先进的大规模计算机需40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一项多重回归分析,现在用电脑不到30秒钟即可完成了。”现代经济学和统计学必须“用数字说话”。“用数学说话”,定量分析从来就是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基础;而数据、数字、数理统计、数学模型、数学、“数学化”理所当然又是定量分析的基础,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我们的经济学、统计学及其定量分析,甚至还要越来越依靠计算机这个神奇的“电脑”去运算,令人们在“数学化”的基础上又加上“电脑化”。
三、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奖的距离有多远
在学术界,发现悖论,分析和研究悖论,有助于促进学术的繁荣和科学的发展。许多貌似科学的理论(实属悖论),在未被发现和指出其弊端之前,曾盛行一时,但后来终究被人们“识其真面目”。本文所指的因“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形成的悖论,本身所承载或依托的理论背景,似乎难以经受严格的逻辑推导,充其量只是一种“尴尬的理论”。当然,若要识其“庐山真面目”,还需要人们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和探寻,并需要借以唤起人们蕴藏着的科学理性精神。用笛卡尔的话来讲:“我思故我在”。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有的章节甚至满纸都是)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据、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
例如,利润率公式:于科学研究,它不是文学创作,更不是“儿戏”。仅凭“想当然”或“拍脑袋讲话”、“闭着眼睛讲话”能行吗?“亩产万斤粮”,甚至“亩产10多万斤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言而喻,无论历史地看还是逻辑地看,经济学研究充分运用数理统计、数学方法,并趋向“数学化”,乃是这门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学日益“数学化”的趋势,与中国经济学家数学功底欠佳的确形成了矛盾。对经济学“数学化”爱恨交加,或许也反映了不少学者的心态。更进一步地讲,它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界几乎普遍存在的“诺贝尔奖情结”与“诺贝尔奖情绪”的困扰和尴尬。翻阅我国的学术刊物,不难发现,许多论述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典型的悖论模型或案例。当然,在这些悖论的背后,也蕴藏着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治学方法、不同思维方式的博弈或争论。而对于学术问题,只有百家争鸣,才能越争越明。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东西羁绊着我们科学奋飞的翅膀?众所周知,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开设伊始,“数学化”便是其评奖的硬条件、硬尺度、显规则。而必须正视,数学功底不深,“数学化”的强度不够或缺陷,乃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软肋。加之人们对市场化、民营化、“经济人”假设等似乎仍然心有余悸,相关分析研究往往着力不够,这些恐怕是构成中国经济学家难获诺贝尔奖的重要因素。此外,如果我们纵有一些满腔的“诺贝尔奖情结”,却又有一些始终挥之不去的“诺贝尔奖情绪”:既不愿与国际主流经济学家交流、对话:也不愿接受国际主流经济学家通用的学术范式和分析工具;甘愿关在自家埋头苦干,孤芳自赏,甚至于还批判人家的东西;或渲染存在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以及所谓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而影响评奖的客观性、公正性,这样,“天上会掉下馅饼”吗?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不会“花落咱家”,相反,我们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距离甚至会愈来愈远。
中国本土学者的诺贝尔奖之梦,何时才能梦想成真呢?有人分析。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一般建国多少年就会产生;也有人指出,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才有望出现。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它需要假以时日,也需要中国经济学家的执着追求、辛勤耕耘,更需要创造能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茁壮成长的环境和土壤。同时,也要“挥手告别”那些浮躁的、非理性的“诺贝尔奖情绪”,营造更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科研环境及生活条件。相信我们的经济学家会更加勤勉,夯实数学功底,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诺贝尔先生若泉下有知,相信他是不会让中国学者的汗水白流的。最后,我们愿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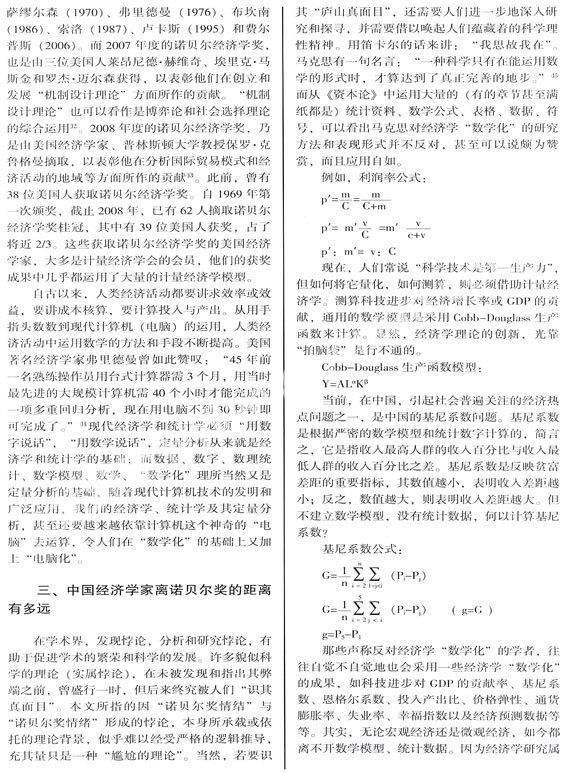
责任编辑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