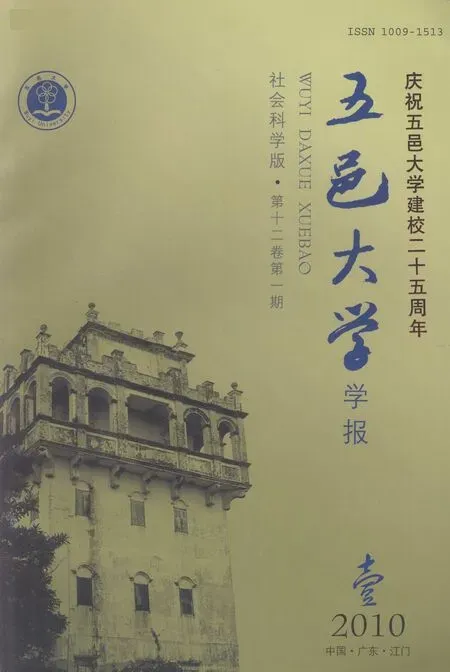舞头与引舞补说
黎国韬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舞头与引舞补说
黎国韬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对唐宋宫廷队舞中的舞头、引舞、戏头、引戏等进行辨析可以发现,引舞与舞头、引戏与戏头均是不同的概念,而引舞、舞头在功能上的部分重叠是造成二者被混淆的主要原因;引舞之出现并不始于唐代,至迟隋代已有之。以上观点对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考》中的一些学术见解将有所修正。
舞头;引舞;戏头;引戏;《宋元戏曲考》
在唐宋宫廷队舞当中,“舞头”与“引舞”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两个脚色。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第七章《古剧之结构》有云:
脚色之名,在唐时只有参军、苍鹘,至宋时而其名稍繁。《梦粱录》(卷二十)云:“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辍耕录》(卷二十五)所述略同。唯《武林旧事》(卷一)所载“乾淳教坊乐部”中,杂剧三甲,一甲或八人或五人。其所列脚色五,则有戏头而无末泥,有装旦而无装孤,而引戏、副净、副末三色则同,唯副净则谓之次净耳。《梦粱录》云:“杂剧中末泥为长。”则末泥或即戏头。然戏头、引戏,实出于古舞中之舞头、引舞。(原案:唐王建《宫词》“舞头先拍第三声”,又“每过舞头分两向”,则舞头唐时已有之。《宋史·乐志》有引舞,亦谓之‘引舞头’。《乐府杂录》傀儡条有引歌舞者郭郎,则引舞亦始于唐也。)则末泥亦当出于古舞中之舞末。[1]
可见舞头与引舞不但是唐宋宫廷队舞中的重要脚色,而且对后世戏剧脚色“戏头”和“引戏”之形成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特别值得关注。王氏的发现可以说是古代戏剧史研究中的重要贡献,然而在表述中却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宋史·乐志》有引舞,亦谓之引舞头”一句,就有将引舞与舞头混为一谈的嫌疑。又如“引舞亦始于唐也”,也与引舞在唐以前已经存在的事实不符。此外,“末泥亦当出于古舞中之舞末”一说也不妥当。①为此,笔者拟就舞头、引舞等问题作出一些补充探讨,旁及戏头、引戏等问题。
一
先从舞头和引舞的一些史料说起。所谓舞头,顾名思义应是宫廷舞队中处于起首位置具有带引功能的舞人。据唐人《教坊记》载:
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择尤者为首尾。首既引队,众所属目,故须能者。乐将阙,稍稍失队,余二十许人舞。[2]
以上所述是唐代宫廷队舞的一些情况,所谓“首既引队”之“首”,显见是指舞头,这须要由“能”舞者担当。十国时花蕊夫人《宫词》又有云:
舞头皆著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每日内庭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墀。[3]
所谓“队”,自然是指“队舞”表演,其首则是“著画罗衣”的“舞头”,与《宋元戏曲考》所引王建《宫词》中的舞头是同一脚色。结合以上有关舞头的文献可知其功能主要有三:一是在宫廷队舞中起引导队伍的作用,所谓“引队”、“先拍”是也;二是在宫廷队舞中司职具体舞蹈动作的表演,所谓“分两向”、“能者”是也。三是既会舞蹈,亦兼司歌唱,所谓“唱得新翻御制词”是也。在引导队舞这一功能上,舞头与引舞有些相近,故易混淆,在此先提请注意。
引舞经常出现于宋代宫廷队舞的表演之中,又被称为“竹竿子”,今以宋人史浩《鄮峰真隐大曲》中的《采莲》大曲为例:
五人一字对厅立,竹竿子勾,念:“伏以浓阴缓辔,化国之日舒以长;清奏当筵,治世之音安以乐。霞舒绛彩,玉照铅华。玲珑环佩之声,绰约神仙之伍。朝回金阙,宴集瑶池。将陈倚棹之歌,式侑回风之舞。宜邀胜伴,用合仙音。女伴相将,采莲入队。”
勾、念了,后行吹《双头莲令》,舞上,分作五方。竹竿子又勾,念:“伏以波涵碧玉,摇万顷之寒光;风动青蘋,听数声之幽韵。芝华杂遝,羽幰飘飖。疑紫府之群英,集绮筵之雅宴。更凭乐部,齐迓来音。”
勾、念了,后行吹《采莲令》,舞转作一直了,众唱《采莲令》:(略)。
唱了,后行吹《采莲令》,舞分作五方,竹竿子勾,念:(略)。
花心出,念:“但儿等玉京侍席,久陟仙阶,云路驰骖,乍游尘世。喜圣明之际会,臻夷夏之清宁。聊寻泽国之芳,雅寄丹台之曲。不惭鄙俚,少颂昇平。未敢自专,伏侯处分。”
竹竿子问,念:“既有清歌妙舞,何不献呈?”
花心答,问:“旧乐何在?”
竹竿子再问,念:“一部俨然。”
花心答,念:“再韵前来。”
念了,后行吹《采莲曲破》。五人众舞到入破。先两人舞出,舞到裀上住,当立处讫。又二人舞,又住,当立处。然后花心舞《徹》。竹竿子念:“伏以仙裾摇曳,拥云罗雾穀之奇;红袖翩翻,极鸾翮凤翰之妙。再呈献瑞,一洗凡容,已奏新词,更留雅咏。”
念了,花心念诗:(略)。
念了,后行吹《渔家傲》,花心舞上,折花了,唱《渔家傲》:(略)。
唱了,后行吹《渔家傲》,五人舞,换坐,当花心立人念诗:(略)。
念了,后行吹《渔家傲》,花心舞上,折花了,唱《渔家傲》:(略)。
唱了,后行吹《渔家傲》,五人舞,换坐,当花心立人念诗:(略)。
(中略)
唱了,后行吹《河传》,众舞,舞了,竹竿子念遣队:“浣花一曲媚江城,雅合凫鹥醉太平。楚泽清秋余白浪,芳枝今已属飞琼。歌舞既阑,相将好去。”
念了,后行吹《双头莲令》,五人舞转,作一行,对厅,杖鼓出场。[4]512-515
此曲所述正是宋代宫廷的队舞,而“竹竿子”这一脚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引舞”,正式的职官名称则是“参军色”。归纳竹竿子的功能约有以下数种:其一,队舞开始时用一根形似“竹竿”的道具“勾”队②,就是把舞队带引出场。其二,念致语,即引文中的“念”,这种致语,一般都带有祝颂性质。其三,与舞队中的花心对白、问答。其四,队舞结束时“遣队”,也称放队,即遣散舞队出场。其五,数次“念了”之后,“后行”才奏乐,可见竹竿子又有指挥乐队的功能。
从《采莲》大曲队舞的表演过程看,引舞竹竿子只司勾、念,并不参与具体舞蹈动作的表演,也不歌唱,这与上述舞头之进入队舞表演有明显不同。换言之,引舞与舞头在队舞中是两个不同的脚色。《宋史·乐志五》所载能更清晰看出这一点:
每祭各用乐正二人,执色乐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计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皆召募补之。乐工、舞师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给。其乐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习;引舞、色长、文武舞头、舞师及诸乐工等,自八月一日教习。于是乐工渐集。[5]
上引比较清楚地显示,“引舞”、“色长”、“文武舞头”、“武师”等为古舞中的不同司职,因此引舞决不同于舞头。③而前引王国维语笼统地说“戏头、引戏实出于古舞中之舞头、引舞”,又说“《宋史·乐志》有引舞,亦谓之‘引舞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把引舞和舞头(引舞头)混为一谈了。
二
是什么原因令王氏没有对舞头和引舞作出清楚的区分呢?这大概是由于二者均处于舞队前列,且在宫廷队舞中都具有引导功能。然而既已有引舞,何以又须舞头引队呢?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原来,在宋代宫廷舞蹈中有时并不出现引舞竹竿子,而直接以舞蹈演员兼司引舞,如《鄮峰真隐大曲》所载之《花舞》,其开始和结束有两段表演的提示云:
两人对厅立,自勾念。[4]518
唱了侍女持酒果置裀上舞,相对自饮讫,起舞三台一遍,自念遣队。[4]520
可见《花舞》与前引《采莲》大曲队舞不太一样,《采莲》有引舞竹竿子勾队、遣队,但《花舞》没有出现竹竿子,而是由两个舞蹈演员自导、自演,自念、自遣。另一证据就更特殊了,《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载:
第五盏御酒,独弹琵琶。(中略)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舞。小儿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余人,列四行,每行队头一名,四人簇拥。(中略)乐部举乐,小儿舞步进前,直叩殿陛。参军色作语,问小儿班首近前,进口号,杂剧人皆打和毕,乐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毕,小儿班首入进致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是时教坊杂剧色鳖膨刘乔、侯伯朝、孟景初、王颜喜而下,皆使副也。内殿杂戏,为有使人预宴,不敢深作谐谑,惟用群队装其似像,市语谓之拽串。杂戏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6]92
这段记载显示,小儿队是队舞,队舞前有“小儿班首”,应就是舞头。但小儿队的舞头在“且舞且唱”的同时,又能够“入进致语”,甚至“勾杂剧入场”。这就是说,即使参军色(笔者案:参军色即引舞竹竿子的正式官称。)在场的部分情况下,舞头也可以“引”戏。由此可知,舞头不但在舞蹈表演时位置处于队伍的最前面并参与表演,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兼有平时不参与表演的引舞(参军色)的一些指挥职能,尤其是“勾队”的职能。这应当就是舞头与引舞容易产生混淆的一个主要原因。
舞头与引舞虽然在表演中有时会出现功能重叠,但毕竟是不同的脚色,所以必须区分清楚。而在古代戏剧史研究中,这种区分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涉及到古剧脚色戏头和引戏的起源问题。如前所述,王国维把戏头和引戏的起源追溯到舞头和引舞,这得到了近代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其表述确实又有些笼统和含混,一旦将舞头和引舞区别清楚,则王氏“戏头、引戏实出于古舞中之舞头、引舞”一说便可以更加准确地表述为:“古剧脚色中的戏头出于古代队舞中之舞头,而引戏则出于引舞”。
事实上,当舞头和引舞分别衍生出古剧脚色戏头和引戏之后,戏头与引戏在功能上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和舞头有别于引舞相似。据《梦梁录》卷二十《妓乐》云:
且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先吹曲破断送,谓之把色。[7]
按王国维的说法,末泥色即戏头,所以宋杂剧脚色戏头的功能是“主张”,而引戏色的功能则为“分付”。《梦粱录》没有把主张和分付解释清楚,对此胡忌考证:
本身属“末”色,参加宋杂剧前段(艳段)演出则名曰“戏头”。参加赞导而与剧事表演无关者名曰“引戏”,故对戏剧言,其实即剧外人,故称“外”。[8]
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即引戏色只司赞导而不入戏,这与宫廷队舞中引舞的竹竿子(参军色)只司指挥而不参与舞蹈具体动作的表演一样。而与引戏不同的是,戏头则须要进入戏剧中以司艳段的演出,这与舞头为队舞之首并“能”舞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舞头与引舞功能之区别实可对应于戏头与引戏功能之区别,它们之间的渊源与分野十分清晰。但如果混淆舞头与引舞区别,则戏头与引戏也会找不到其所以发生区别之原因,于是就会有王国维含混而论之的情况出现。
此外,前引《宋元戏曲考》的那段文字还有一个问题,即王氏提出唐代始有引舞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据笔者所知,引舞之制至迟在隋代已经确立,且因应文舞、武舞的不同,引舞舞具亦有所不相同。据《隋书·音乐志中》载:
岂乐人,武弁,朱褠衣,履韈。文舞,进贤冠,绛纱连裳,帛内单,皂领袖襈,乌皮鞮,左执籥,右执翟。二人执纛,引前,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武舞,朱褠衣,乌皮履。三十二人,执戈,龙楯。三十二人执戚,龟。二人执旍,居前。二人执鼗,二人执铎,二人执铙,二人执錞。四人执弓矢,四人执殳,四人执戟,四人执矛。自旍已下夹引,并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9]
以上引文所言甚明,隋代宫廷文、武二舞已有执纛或执旍而“引前”者,他们“在舞人数外”,显见就是并不参与队舞具体舞蹈表演的“引舞”。唐代之有引舞乃承隋制,《大唐六典》卷十四载:
文舞之制,左执籥、右执翟,二人执纛以引之。(中略)武舞之制,左执干、右执戚,二人执旌居前。[10]
引文中文、武二舞的执纛、执旌以居前者,与隋舞中“引前”者一脉相承,也就是引舞。从中不难看出,王国维“引舞亦始于唐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引舞至迟从隋代就已经存在了。
三
总而言之,唐宋宫廷队舞与后世戏剧的形成有极为密切之关系,队舞中的舞头和引舞与古剧脚色中的戏头和引戏之间渊源尤深,辨析清楚舞头和引舞的区别,有助于理解戏头和引舞的渊源与区别,也有助于反思和修正一些传统的学术观点。
另外,朱权《太和正音谱》曾提出:“引戏,院本中‘狚’也。”[11]这种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因为引戏不入戏,旦(狚)则是一剧中主角,二者不当有渊源关系。事实上,旦的前身应是入戏的戏头,更早的渊源则是入舞的舞头。在前引《采莲》大曲中的舞女自称为“但儿”,当引舞竹竿子不出现的时候,部分舞女兼有自念、自遣的功能,所以她们实际上是舞头而兼司引舞之职。《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载:
第七盏御酒,慢曲子。(中略)参军色作语,勾女童队入场。女童皆先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四百余人,或戴花冠,或仙人髻鸦霞之服,或卷曲化脚袱头,四契红黄生色销金锦绣之衣,结束不常,莫不一时新妆,曲尽其妙。杖子头四人,皆裹曲脚向后指天幞头,簪花,红黄宽袖衫,义襕,执银裹头杖子。皆都城角者,当时乃陈奴哥、俎姐哥、李伴奴、双奴,余不足数。亦每名四人簇拥,多作仙童丫髻,仙裳执花,舞步进前成列。或舞《采莲》,则殿前皆列莲花。槛曲亦进队名,参军色作语问队,杖子头者进口号,且舞且唱。乐部断送采莲讫,曲终复群舞。唱中腔毕,女童进致语,勾杂戏入场,亦一场两段。讫,参军色作语,放女童队。[6]92
比照前引《鄮峰真隐大曲》可知,上引所载的“杖子头”也就是《采莲》大曲中的“但儿”,她们“且舞且唱”,均为队舞中的舞头而并非引舞的竹竿子。女童队的舞头当竹竿子在场的情况下,也和前述的小儿队舞头一样,可以“勾杂戏入场”,实际上就是戏头在特殊情况下偶尔兼司了引戏竹竿子(参军色)的职责。复由于但儿和杂剧旦脚、院本狚等同声,她们之间显然有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或者说旦、狚本源于舞头但儿。④所以,朱权的说法应更正为:“舞头但儿为戏头之前身,而戏头又为院本中狚之前身也。”朱权的错误也是由于没有把引舞与舞头区分清楚而造成的。这又表明,对引舞和舞头的辨析,不但和戏头、引戏直接有关,而且牵涉到旦脚起源的问题,所以是颇具探讨价值的。
注释:
①关于“末泥亦当出于古舞中之舞末”一说之误,笔者另撰有《舞末与副末》一文详为辨析,兹不赘述。
②这根形似竹竿的道具也被称为“竹竿子”,其形制及渊源详见拙文《竹竿子补证》所考。
③笔者案,上引“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一句的正确标点为:“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因为引指引舞,头指舞头,“引”字和“头”字之间应该顿开。
④关于旦脚与但儿之关系,可参见徐筱汀《释旦》一文。
[1]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王国维遗书(九).上海:上海书店,1983:588.
[2]崔令钦.教坊记[M].罗济平,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
[3]全唐诗[G].北京:中华书局,1960:8977.
[4]朱孝臧.彊村丛书[G].上海:上海书店,1989.
[5]脱脱,等.宋史[G]北京:中华书局,1985:3032.
[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李士彪,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7]吴自牧.梦梁录[M].傅林祥,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286.
[8]胡忌.宋金杂剧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9:131-132.
[9]魏徵,等.隋书[G].北京:中华书局,1973:343-344.
[10]李隆基..大唐六典[M]李林甫,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291.
[11]朱权.太和正音谱[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54.
An Additional Explanation of Wu Tou(Dance Head) and Yin Wu(Introduction to Dance)
L I Guo-tao
(Research Center fo r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e,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 distinction of the term sw u tou,yin w u,xi tou,and yin xi used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court dance reveals that these terms were all different concep ts.The confusion over yin w u and w u tou resulted from the partial overlapping of their functions.Yin w u appeared no later than the Tang Dynasty;in fact it already existed in the Sui Dynasty.The above observation is a co rrection of some view s in Wang Guowei’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 rama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 u tou;yin w u;xi tou;yin xi;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 rama in the Song and Yuan D ynsaties
I206.2
A
1009-1513(2010)01-0043-04
[责任编辑文 俊]
2009-08-3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观念、视野、方法与中国戏剧史研究”(批准号:08AZW 002);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珠三角地区传统民间舞蹈研究”(批准号:07JDTDXM 75004)。
黎国韬(1973-),男,广东广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史、古代史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