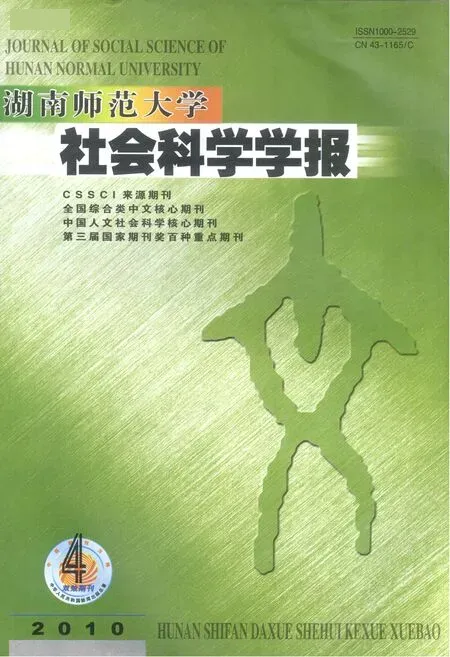明代话本小说创作冲破程朱理学樊篱论存疑
——兼与高教版《中国文学史》商榷
易小斌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明代话本小说创作冲破程朱理学樊篱论存疑
——兼与高教版《中国文学史》商榷
易小斌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高教版《中国文学史》将明末话本小说的兴盛归因于明中叶陆王心学的兴起,以至于认为明代话本小说创作冲破了程朱理学樊篱。以“三言”为例,我们不应该将其拔高到“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甚至“歌颂婚恋自主,张扬男女平等”,“具有尊重女性的意识”等高度。事实上,“三言”的创作更多地受到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并没有跳出理学思想的樊篱。
理学思想;话本小说;“三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观念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上深入人心,如明代的小说即被冠以“一代之文学”称号,获得后世的大力推崇。这背后凸显出文学研究对文学与文化思潮之间关系的注重。以明代话本小说为例,学界对话本小说特别是“三言”、“二拍”的重视与评价,就是将其置于明代中后期活跃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的。一种文学现象产生的背后固然有其特有的思想文化背景,但假如纯以思想文化论文学,则可能导致误读。如十多年来影响甚大的高教版《中国文学史》对明代晚期小说的评价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高教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关于“三言”等明代话本小说的评价紧紧抓住“王学兴起”这一思想文化背景,将其看成是“重要契机”。称其“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因而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纷纷张扬起不顾天理而求世俗爱好的个人的情欲”,“他们面向现实,注重用通俗的语言,真实而细致地开掘和表现人的心灵,特别是由此而出现的一些有关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作品,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致使明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1](P9-11),等等。似乎明代话本小说正是受到“王学兴起”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影响,起到了在思想上对“欲”的肯定和对“情”的推崇,是对正统儒学(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叛逆。事实真是如此吗?明代话本小说真的冲破了程朱理学思想的樊篱吗?本文试图以“三言”为例来阐述明代话本小说的真实面貌,期望获得方家的批评。
一、从“制欲”到“情”“欲”
程朱理学在明代被确定为官学,奠定了明代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思想基础,也确立了社会市民一般的道德观念。与原始儒学以“礼”框定男女之别不同的是,理学的核心观念是以“理”来压制男女之欲,“人虽有欲,当有信而知义,故言其大无信,不知命,为可恶也。苟惟欲之从,则人道废而入于禽兽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则顺命。”[2](P1053)在“以道制欲”的主张下,对《诗经》中的“情”也进行了重新解读,“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贞信之节,而不知天理之正也。”[3](P38)所谓“天理”,即纲常伦理;而纲常伦理发端于男女之欲(男女之交)。程朱理学家认为,现实中男女之欲常常与儒家的理想规范分裂,因而,救赎之道,惟有以“去人欲”来“存天理”。
明代中叶出现的陆王心学,一般被看成是程朱理学的对立面,但是在核心思想上,二者没有根本的分歧。如王阳明在政治上也并不反对纲常名教,“此心纯是天理”,“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4](P9)只是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的“良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王学左派”的王艮对制欲的态度仍然十分明确,“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见,便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良知一点,分分明明。”[5](P717)无欲在他这里是人性的至善境界。何心隐在反对“无欲”的同时,坚持“寡欲”,主张合理制欲。王学左派中,惟有李贽是个“另类”,但在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他的影响力有限,其对晚明话本小说中性爱的张扬有多大影响,也不宜过高估计。事实上,当时程朱理学始终居于主流地位,阳明学派一度还被定为“伪学”,由于阳明先生的事功学术,成就于江西,因而也主要流布于江西,其影响主要也在江西。脱离阳明学派的历史条件,过高估计其对文学的影响,就会导致无法解释为什么“随着明末政治形势的严峻,人文思潮的变化,大致从侧重于重情到倾向于重理,虽然更关心现实,但说教气味更加浓重”。[1](P185)自然更加无法解释:“它们在肯定情和欲时,往往过分地强调人的自然本能,有过多直露的秽笔而遭到人们的訾病;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大谈忠孝节义、因果报应,散发着陈腐的气息”,这种矛盾,“‘二拍’比之‘三言’更为突出。”[1](P190)
晚明文学理论上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情”的推崇,以汤显祖“人生自是有情痴”[6](P1093)的“至情论”为代表,表达了对程朱理学的叛逆声音,试图以“情”来抗衡“理”。反映在其戏曲创作中,写出了诸如《牡丹亭》等一曲曲至情至信、生生死死的爱情赞歌。然而,这种创作主要是作为一种个性存在,是否具有普遍性,代表当时的主流?尚值得商榷。比如天启年间,作为“三言”的编撰者冯梦龙,提出“主情说”,同样是对情的推崇,其意义却完全不同。他说:“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彼以情许人,吾因以情许之。彼以真情殉人,吾不得复以杂情疑之。”[7](P21)可见,冯梦龙的“主情”并非反对理,而是力图纠世儒之偏,认为情是维系理的必要条件,是理的附生物,是理的润滑剂。理的规范要具有可行性不能脱离“情”。同样,他又提出“情”“色”乃一体一用:“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8](P320)正像他提出情是为了补充理一样,他提出色既是为了补充情,还是为了区别淫(纵欲)。他与袁宏道“拂情以为理”[9](P1290)也不一样。“袁宏道在《与龚惟长先生书》中公开宣扬追求人间的真乐乃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乃至‘宾客满席,男女交舄’,‘妓妾数人,游闲数人’,寻欢作乐到‘朝不谋夕’、‘恬不知耻’的地步。”[1](P10)而冯梦龙对情是有着清晰的边界的。“情,犹水也。慎而防之,过滥不上,则虽江海之决,必有沟浍之辱。”[7](P366)可见,冯梦龙对“情”的肯定,立意还是维护程朱理学主流价值规范。这里还必须提到冯梦龙在《序山歌》中所说:“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论者多据此判定冯梦龙是借男女真情,揭发礼教的虚伪。应该说,这是片面的。冯梦龙之所以提出“主情说”,就是看到礼教的规范在现实施行中产生了可行性的困惑,因而,产生道理上是这样,而实际上不无虚伪的表现。他并非彻底否定名教,指斥名教虚伪。况且《挂枝儿》编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山歌》稍后,此时冯梦龙三十多岁,正是忙于科举考试的时期。他是把这些山歌当作自己的“私情谱”来看待的。“私情”之外,特别是作为“六经国史之辅”的“公情”(以“三言”来“导愚”)时就另当别论。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言之。当然至于其对情的阐发,不可避免地投射到编撰“三言”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多少起到了对名教流行的虚伪的讽刺作用。
二、“三言”中的妇德与明代主流理学思潮
明代正统理学思想对女性的要求是讲求妇德的,有论者指出,对女性贞烈观念的强烈要求,明代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以“三言”为代表的话本小说,并没有超越这一正统理学的框囿,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赋予了新的要求。
首戒淫妒。戒淫妒是原始儒学时期便有的对女性的要求,《诗经》、“三礼”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和规范,此后一直长盛不减。冯梦龙秉承这一观念,提出:“女德之凶,无大过于淫妒。”[10](P753)有学人统计,“三言二拍一型”共收有二百四十则故事,其中以“戒淫”为主题的故事,占篇数约四分之一。[11](P1)
贞节观念。对女性贞节的要求高低,最能看出正统理学思想的影响程度。高教版《中国文学史》极力张扬“三言”“歌颂婚恋自主,张扬男女平等”,认为这样的作品在“三言”、“二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也最脍炙人口。“描写爱情故事时,还具有尊重女性的意识,流露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宋明以来的封建婚姻关系中,贞节观念是套在女性脖子上的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突破贞节观念是晚明人文思潮影响下尊重人性、妇女解放的一种表现。”[1](P188)真实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的。作为“三言”的编撰者冯梦龙恰恰是主张守节的。“夫忍五载而死孝,妇忍三岁而死节,慷慨之谊俱以从容成之,卓哉!”[7](P7)他对守节的赞美即可明证,而“情”不过是守节的驱动力。或者说,赋予了守节以合理性、可行性。特别引人瞩目的是,“三言”对妓女这一种以出卖色相而生存的特殊群体,也提出了“贞节”的要求。这一方面符合明代对女性贞烈的强烈要求这一社会思潮,另一方面体现了将女性贞节观念普遍化、绝对化,连与贞节观念背道而驰的妓女也不能背离这一要求,希望把她们也拉回到主流的理学规范轨道。对违背正统理学规范的女性,“三言”对其处罚相当严酷。有通奸行为的女性基本上都受到了严惩,或死于丈夫刀下,或被正法。《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中的杨氏,仅仅因为一句戏言就被丈夫一顿暴打并逐出家门,走投无路,自缢身亡。而同样出轨男性,“三言”则表露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那就是为男性开脱。如《乔彦杰一妾破家》听乔彦杰与妓女沈瑞莲同居两年,乔因此家破人亡,然而,小说却为其抱不平:“虽然好色贪淫,却不曾害人,今受此惨祸,九泉之下,怎放得王青过!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也。”这些出轨男性,既未受到官府的制裁,也未遭受到他人的杀身之祸。他们的结局不好,只不过是作者为了告诫男性不要贪淫,要从身体健康需要的角度出发节欲。因此,小说对出轨男性充满了劝诫的叙述,而对出轨女性的惩罚实际上则是给女性标示的一种道德警戒。更有意思的是,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多为商人,而这些商人大多属于小本生意,终日在外奔忙,目的不过为了赚取蝇头微利,并没有多少优越感和社会地位。而高教版《中国文学史》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充分地说明了生气勃勃的商人正在取代读书仕子而成为时代的宠儿。他们在拥有大宗财富的同时,也能得到非凡的‘艳遇’。他们趾高气扬,开始俯视社会上的各色人等,瞧不起穷酸的‘衣冠宦族’和文人学士,纷纷表示不愿意与他们联姻结好。在金钱面前,门第与仕途已黯然失色。”[1](P186)
服务功能。第一是审美功能向服务功能的转变。要求女性艺术精通,才情兼备。无论是《钱舍人题诗燕子楼》中的关盼盼,“歌喉清亮,舞态婆娑。调弦成合格新声,品竹作出尘雅韵。赋诗琢句,追风雅见于篇中;搦管丹青,夺造化生于笔下”,还是《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的刘素香,都能以诗词与男性相唱和,还有那“又且通于音律,凡箫管、琵琶之类无所不工”的小娥(《裴晋公义还原配》),“十五六岁时,诗赋俱通,一写一作,信手而成,更兼女工精巧,亦能调筝弄管,事事伶俐”的金玉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以及《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莺莺、《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瑶琴、《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王娇鸾等等,都赋予了审美功能向服务功能的转变,高度关注女性内在气质。在冯梦龙的理学观中,男女两性的不平等是由生理上的差异所决定的,对女性的歧视与正统理学观念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事。主四方之事的,顶冠事带,谓之丈夫,出将入相,无所不为,须要博古通今,达权知变。主一室之事的,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日之计,止无过饔飧井臼,终身之计,止无过生男育女。”[12](P123)甚至,对女性的要求比过去更高,要“女子能识之”、“女子能急之”、“女子能周全之”。[7](P90)对女性不让须眉的歌颂,实际是对女性赋予更高的要求,能更好地服务男性,“女性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才、胆、识都是以男性谋求利益为终极目的,并不代表女性自身性别意识的觉醒,遑论其性别地位的提高。极言之,这不过是男权中心话语对作为男性工具的女性功能的又一次与时俱进的调整和规范。”[13](P31)其次是要能助夫求名。如金玉奴,“凡古今书籍,不惜价钱,买来与丈夫看;又不吝供给之费,请人会文会讲;又出资财,教丈夫结交延誉。”于是,其夫二十三岁发解,连科及第;《李公子救蛇获称心》中的称心甚至连续三次“飞身入院”,为丈夫盗取科举试题,并为其代答。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赵春儿、玉堂春、白玉娘等都是为了丈夫求取功名,不仅出谋划策,而且还想方设法筹措资费。可见,仕途在“三言”中并没有黯然失色。
由上可知,明代话本小说的创作并没有跳出程朱理学的樊篱。“王学左派”特别是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标揭,阐述“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思想在以“三言”为代表的明代话本小说中没有得到反映,更谈不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1](P9)。
三、“三言”中的“另类真情”与“理”的和解
为了进一步了解明代理学思潮与话本小说的关系,我们再选取高教版《中国文学史》重点肯定的“三言”中的几篇小说为例来加以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三言”的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冯梦龙将其置于“三言”之首,表明了他对蒋兴哥做法的赞同,反映了他所倡导的真情的回归。高教版《中国文学史》予其以高度评价:“王三巧被陈大郎引诱失贞,丈夫蒋兴哥知道后虽然‘如针刺肚’,万分痛苦地休了她,但还是对她深情不减,十分尊重,只是责怪自己‘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三巧被休后,听了母亲‘别选良姻’的劝导,也就改嫁。陈大郎的妻子在丈夫死后,也痛快地‘寻了个对头’。最后蒋兴哥也不嫌三巧二度失身,又破镜重圆。”“在这些市民身上,讲究的是人生的真情实感和尊重自己爱的权利,传统的三从四德、贞操守节之类已失去了支配的作用。”[1](P188-189)这显然不合乎事实,因为,蒋兴哥的做法只是一个“另类”,不足以推翻前述“三言”对贞节观念的强化。这种“另类”的做法暗合了冯梦龙的“私情”,同时也并不见得就超越了程朱理学的规范。因为对于当时的男性来说,女性出轨意味着对男性家庭地位的侵犯。所以,更多的时候,招致的是男性的报复暴行。如蒋兴哥明明知道错在自己,却仍要休妻。至于蒋兴哥后来纳王氏为妾,更大的原因恐怕是在自己吃了人命官司的时候对王氏救命之恩的报答。我们并不否认蒋兴哥与王三巧的真情,然而最终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所宣扬的更主要的是对宋明理学中知恩图报的“义”之“天理”的肯定,而非对“传统的三从四德、贞操守节之类”思想的超越。
其次,再看《宿香亭张浩遇莺莺》,这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式的情爱故事。少女莺莺与张浩私定盟约的故事与《西厢记》相类似,但结局却大不一样。当莺莺闻知张浩为父母所逼而另娶她人之后,并没有听凭命运的摆布,而是大胆地诉之于父母,告之于官府,指控张浩“忽背前约”,要求法庭“礼顺人情”。高教版《中国文学史》认为小说“实际上肯定了‘情’对‘礼’的挑战”。然而,我们不难看到,这种“挑战”其实最终还是“情”和“礼”的和解。因为莺莺的举动只是单方面的,可以归结为个性使然(为情驱使),而张浩是因不敢违抗父命(礼)而背约,大团圆的结局还是取决于“礼”(官府)。同样的故事,在《王娇鸾百年长恨》中,却是以悲剧结束,表明了情的力量仍然不足以与礼相抗衡。
再看《卖油郎独占花魁》,主人公秦重和莘瑶琴同样是一种“另类真情”,先是秦重对“花魁娘子”的色相“身手都酥麻”的迷恋,而莘瑶琴则直到了解秦重是个志诚君子时才动了感情;秦重则担心这个“平昔住惯了高堂大厦,享用了锦衣玉食”的她当不了卖油郎的妻子。我们不怀疑“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相爱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的关系”。[1](P188)因为真情萌发而不是受金钱权势驱使的例子还有《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的玉兰和阮三,然而,阮三的结局却是因纵欲而命丧闲云庵,玉兰竟然成了朝廷旌表的节妇楷模。这表明,有时候小说作者对情和欲的抒写是较为随心肆意的。但更多的时候是深受正统理学规范的制约。如“三言”中有大量来自对宋元话本的改编,从这些改写中最能看出明代理学思潮的影响。如宋本《张生彩鸾灯传》,到话本《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的改写就是其中一例。情可以超越生死,主人公为了自我爱情的表达,可以舍弃生命,其勇气感人至深,是至情的写照,但是到了“三言”中,却被改写。原来宋本中男女主人公为情而死的坚定是“以死向君”,转变为“生死相随”,伴随着女主人公对情的含糊是男主人公更为猥琐,由原来的“岂肯独生”,变为“岂忍分离”,最后两人只是“相抱而泣”,一个感人至深的殉情故事最终却沦为一场近乎作秀的表演。[13](P86)原因就在于“三言”的编撰者用正统理学话语对男女主人公的行为进行了大幅的修正,修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吻合正统理学观念。
总而言之,认为“三言”表现了男女平等以及婚恋自主、尊重女性的看法只不过是某些文学史家一厢情愿。“三言”中不仅有对女性身体的刻意关注(《蔡瑞虹忍辱报仇》),特别是按男性审美要求而书写的三寸金莲(当男性无法战胜灾难时便归咎于它),不仅有对钱色交易的细致描写(《新桥市韩五卖春情》),还有对红颜祸水的倾情演绎。当写到男性没有勇气担当爱情的时候,没有半点指责之意,反而将人格的萎缩看成是良知觉醒之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当写到离乱变故中的女性遭受深重的苦难时,归结为“女祸论”,而男性的命运反而更加发达。这就是“三言”的真实面貌。受制于小说编撰者的思想文化意识,小说中偶尔出现的“另类真情”喘息其间,只能如灵光一闪似的,很快消逝,体现正统理学规范的叙事总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傲立。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宋)程 颐,程 颢.河南程氏经说(卷一)[A].二程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宋]朱 熹.诗集传(卷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4][明]王阳明.传习录(上)[A].王阳明全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明]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辞[A].汤显祖诗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明]冯梦龙.情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3.
[8][明]冯梦龙.警世通言[M].长沙:岳麓书社,2002.
[9][明]袁宏道.德山麈潭[A].袁宏道集笺校(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明]冯梦龙.冯梦龙全集(第 3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1]冯翠珍.三言二拍一型之戒淫故事研究[D].台北:台北中国文化大学,2000.
[12][明]冯梦龙.醒世恒言[M].长沙:岳麓书社,2002.
[13]刘果.“三言”性别话语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Impeaching Theory of Narrative Novels Creation in Ming Dynasty Breaking down Mental Barriers of Cheng-Zhu’s Neo-Confucianism——Discussion with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Higher Education Press)
YI Xiao-b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Hunan 412008,Chin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Higher Education Press) attributed the booming of narrative novel creation in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rising of Lu-Wang parapsychology in middle Ming dynasty so that it was considered to break down the mental barriers of Cheng-Zhu’s Neo-Confucianism.Take“San Yan”for example,we should not praise it to the height of “affirming reasonable requirement of human needs,claiming equality between people,seeking for the natural evolution of personality and even extolling free marriage and equality between sex difference”.Actually,the creation of“San Yan”was more influenced by Cheng-Zhu’s Neo-Confucianism and did not jump out the barriers of Neo-Confucianism.
Neo-Confucianism;narrative novel;“San Yan”
I206.1
A
1000-2529(2010)04-0116-04
(责任编校:谭容培)
2010-01-05
易小斌(1971-),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以夏炘、朱一新为中心
——以《程朱阙里志》为例